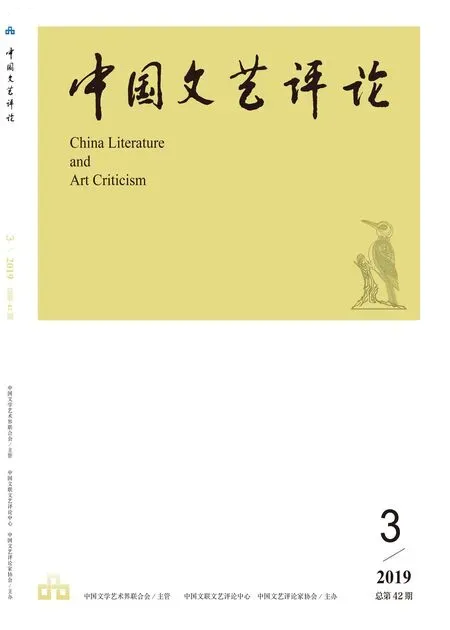莫言: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荆轲
采访人:张同道
2018年11月29日,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王斑等主演的《我们的荆轲》在首都剧场圆满收官。该剧自2011年登上话剧舞台之后就收获较高口碑。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摄制组就话剧《我们的荆轲》与戏曲、诗歌等文艺创作采访莫言先生。以下为访谈整理稿。
一、与话剧结缘
张同道(以下简称“张”):
莫言老师,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新作《我们的荆轲》也是您首部剧作集。该书收录了《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三部剧作及您关于《我们的荆轲》的访谈,还收录了大量精彩的话剧剧照。您最早怎么与话剧结缘?莫言(以下简称“莫”):
我从小就有戏剧情结。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电影看不到,只有到了春节前后,生产队放假,有点空闲,村子里的业余戏剧班子才唱几天茂腔。文化大革命之前唱传统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节妇烈女、孝子贤孙,“文革”开始传统戏不让唱了,就将样板戏改编成茂腔,这让我从小就对舞台艺术感兴趣。我辍学以后,在大哥中学语文课本上(当时中学语文课本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种,汉语主要是古文语法方面的,文学就是节选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的片段),就从这样的教材里边看到了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这样一些话剧剧本片段,那个时候我就对话剧很感兴趣,也知道有这么一种艺术,在舞台上全靠说话,没有唱腔。我当兵以后接触的书也跟话剧有关系。在山东黄县,就是现在的龙口,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黄县图书馆的管理员,他借来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也借来了郭沫若、老舍、曹禺的剧本,我对话剧就更感兴趣了。
我没有发表过的处女作实际上是一部话剧。那个时候也正是话剧最热的时候,当时有一部轰动了全国的话剧,叫《于无声处》,是讲“四五运动”的时候跟“四人帮”做斗争的故事。我写了类似题材的话剧,寄给了解放军文艺社,他们回信说我们不能发表这样大型的剧作,请您寄给剧团,或者给其他发表剧作的刊物看一看。当时我很高兴,终于收到了出版社一封笔写的回信,而不是铅印的退稿信。
后来,写话剧的这个兴趣我就压下了,开始写小说。1997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报社,但还是跟军队文艺界的很多朋友有密切联系。那个时候空军还有话剧团,找到我跟部队作家王树增,让我们俩给写《霸王别姬》的历史题材话剧,我们一块儿商量了很久,然后分头去写。多年后,我想把这部剧收入我的剧本集,跟王树增商量,他很大度,说这部戏就是你的作品,不要署我的名。
《霸王别姬》的剧本写好以后,空军话剧团在人艺的小剧场连续演了一个月,后来这个话剧也作为文化部外派演出的剧目,去过埃及、慕尼黑,参加过非洲和欧洲的话剧节,也曾经去过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我还跟团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演出很受欢迎,也由此激发了我写话剧的热情,下决心要写一个历史剧三部曲。紧接着就有了《我们的荆轲》。
荆轲也是一个写烂了的题材,电影、电视剧、戏曲、话剧,都有很多同题材的创作。怎么样写出新意来,我确实是想了很久。空军话剧团找到我,希望我来写,我感到难度很大,没有答应。在往家走的路上,突然感觉到有了灵感。《我们的荆轲》这个题材不能按照老路数来写,应该赋予它一种新的个性化解释,围绕着荆柯刺秦的动机和目的展开,跟过去的写法要有不一样的思维。荆轲为什么要刺秦?他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我想看过我这个话剧的,都会感觉到我的解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莫言先生在剧场接受访谈后摄影 (摄影:刘鹏飞)
荆轲这个几乎被定性的历史人物,在我的剧本里面有了新的面貌,他的人性得到了一种全方位的拓展。这个戏我写得很快,七天就写完了初稿。当我打电话让导演来拿剧本的时候,他说拿提纲是吧?我说剧本。他大吃了一惊。当然后来还是做了一些修改。没有来得及排演,空军话剧团就撤销了。后来沈阳话剧团把这个戏拿去演过几场。
2009年春天,我到北师大参加一个活动,跟北京人艺的任鸣导演同台演讲,顺便说到这个戏。任鸣说你发给我看看。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推荐给了他们剧院。人艺那时的院长张和平组织专家论证,看这个剧本有没有搬上舞台的价值。剧本获得了大多数人的通过,认为可以演。他们也对剧本提出一些意见,认为还应该让荆轲这个人物有一个更高的、关于理想和人格的追求。我对剧本又进行了一番修改,添加了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章节。荆轲在易水边上迟迟不出发,太子丹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在等一个高人,跟高人有约,今天在这里见面。到底是真有这个高人呢,还是荆轲的一种托词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借着这样一个情节,荆轲向观众倾诉了他心目中的高人的形象,这也是他自己关于人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加上这个片段,使戏有了本质性的提高。
这个戏在北京演了三轮,三十多场,后来还去过彼得堡演出。因为这个戏,我获得了中国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这也是话剧界的最高荣誉。
剧本《锅炉工的妻子》实际上是《霸王别姬》的一部分,原作叫做《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当时设计了新旧两组人物,跨越了古代和当代两组人物,围绕着事业和爱情展开故事,进行对照,过去是霸王、吕雉、虞姬,现在就是钢琴教师、音乐指挥和锅炉工。排演时大家感觉有些乱,篇幅也太长,没法演,索性就把当代这一块抠下来了。出剧本集时,我把抠下来这部分做了修改,添加了内容,使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剧。进大剧场容量不够,但是作为一个小剧场的演出还可以。
钢琴教师、锅炉工、音乐指挥,这三个人在改定后的剧本里面都比过去要丰富多了。尤其是锅炉工这个进了城的农民形象,在最后一稿里也变得非常明确。在原稿里面他就是一个受害人、无辜者,是一个愚昧、老实、忠厚的人,在新的剧本里面,赋予他另外的面貌,丰富了另外一些性格。钢琴教师、音乐指挥这两个人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他作为当地的农民实际是占据优势的。进了城以后,地位发生了逆转。知青和当地农民结婚,酿成悲剧,这也是最近几十年的文学作品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老故事。所以我想我这个剧本应该给这个老故事增加一点新的展示。
二、《我们的荆轲》
张:
我们集中说说《我们的荆轲》。刺秦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它的内涵已经盖棺定论,以荆轲为代表的侠义精神在几千年里广为流传。但是在您的作品里来了一个大翻转,应该说是一个彻底的翻转,这个翻转的动机是什么?莫:
我对历史戏有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当成现代戏来写,所有的历史剧实际上也都是现代剧作家借旧瓶来装新酒。如果你按照古人对历史的解释来写,那再现历史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其像荆轲这个被写滥的人物我还能怎么写呢?无非就是把电影话剧化,把戏曲话剧化,把人家该唱出来的,我用语言、用大白话把它说出来。如果没有人物性格的重塑,没有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新的解释,这样的戏是没法写的,写了也没有意思。基于这个理念,我千方百计地想,怎么样能让荆轲变成我的荆轲,或者说我们的荆轲呢?这个题目也是一种提示,《我们的荆轲》,就是说剧作家、演员和观众,我们共同塑造的一个新荆轲,是和过去的荆轲不一样的。想来想去,既然是把历史故事当当代故事来讲,把历史戏当现代戏来写,荆轲实际上就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从事的刺客的行当,跟我们在文坛或在其他行当里面的工作是相通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在他们这个侠客行当里面,也是存在着的。什么事情让我们感觉到痛苦、愤怒、纠结,荆轲在他那个时代也应该跟我们有类似的感受。这样写起来就非常方便,所以这个戏就有点穿越。演出刚开始就是一群人,在北京的人艺剧场,各自点名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人物。这么一段穿越性质的台词,就把这个戏搞得不是那么堂堂正正的历史戏的感觉了。我们没有特别要求观众进入历史,而是提示观众把这个历史故事当现代故事来看,把荆轲的故事当成自己的故事来看,用自己的心来理解荆轲。
张:
这里特别写到荆轲就是一心想出名,而且怎么能够把这个名出得更大、更绝、不可企及,这样一种处理也是结合了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吧?莫:
我是一个作家,在文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我相信其他行当里的人,也会有类似的体会。无论多么高尚的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也生活在现实当中,他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也同样会遇到很多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般的烦恼。所以,尽管荆轲是一个高大上的历史人物,但实际上在他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俗世里面各种烦恼同样会纠缠他。所以我要把历史人物当成现代人物来写,要给荆轲找到一个刺秦的动力。难道仅仅是为了报答太子丹赐给衣食这么一点恩情吗?这当然也是理由,但他应该有一种更高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追求。刚开始也许他有这种想法,就是为了灭掉秦始皇这样一个强者,因为他给周围的国家带来了不安。为了不让弱国的老百姓与政权受到秦国的威胁,他要除掉秦始皇。在剧中,他跟燕姬的辩论过程中,发现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燕姬扮演了秦始皇,把他所有的刺秦理由一一都给否定了。最后荆轲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理由来刺杀秦始皇的,他找不到一个理由。最后只能是为了出名,他要刺秦。燕姬帮他设计,出名当然要出最大的名,用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名声,既然你把自己的性命都要抵押进去,那么就应该博取一个千秋万代的美名,一个豪侠之名,而不应该仅仅把他刺死就算了。那么这就来了,到底该不该把秦始皇刺死,到底把他抓住了不杀死能够出的名更大,还是利利索索地一剑封喉让他死掉出名更大?在燕姬的引导之下,经过反复讨论,还是认为抓住他能杀而不杀,这才能够让你把这个名出得更大,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是你故意把他放掉的。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功利化的论证的过程,一个排演的过程。
我想真正的历史学家看了《我们的荆轲》会生气的,我们把荆轲刺秦这一个高大上的故事给降格了,对荆轲的人格也是降格处理。但是我想他也推翻不了,因为按照剧本的逻辑它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我也认为故事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成立。尽管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解释会让很多的观众和历史学家认为是胡闹,是戏说,但是从剧本的逻辑来看能够成立。我想这样一种说法、这样一种写法是应该允许的。
张:
文学不是科学。莫:
对。因为秦始皇就是一个争议人物,他的功过是非评说了几千年也难盖棺论定。有的艺术作品把他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暴君,有的文学作品把他塑造成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实际上我想这两者都是成立的,说他是暴君,他也确实是个暴君,焚书坑儒;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伟大的帝王,也是成立的。不管怎么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版图第一次统一起来了,殊途同归,度量衡也统一了,文字也统一了,为中国版图开疆拓土。虽经几千年的变迁,但是秦朝时候确定的版图现在基本还是保持了。张:
您这里面还特别设计了燕姬这个人物,她好像是荆轲的人生导师,充满了智慧,很理性,而且她还有现代女性对命运的思考。这个人物是怎么构思出来的?莫:
我想舞台剧也好,电影也好,必须有女人。如果全是一些大老爷儿们在舞台上是不好看的,也不好演。《史记》里面也讲太子丹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断送美女送珠宝给荆轲,那送过去一个燕姬也是在情理当中的。荆轲住在豪宅里面、身边有个女人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不能仅仅就是送了一个帮着做饭的女性,她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女性,有思想的女性。燕姬是不是太子丹派来的卧底?是不是秦始皇的卧底?这都很难说了。她的身份和出身设置得比较复杂,她是给秦王梳过头的宫女,后来秦王把她送给了太子丹,那也可以说她就是秦王的卧底。秦王送给太子丹的时候,就是让她去监视太子丹,后来太子丹又把她送给了荆轲,也许太子丹又让她来监视荆轲。这样复杂背景出身的一个女性,她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最终她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她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荆轲的人生导师,还是秦始皇的一个卧底?最终是她说服了荆轲,能杀而不杀秦王,等于是她保护了秦始皇的性命,也可以说是她导演了历史,成就了荆轲的万古英名。最后她又被荆轲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一剑杀死。杀燕姬这个情节,我作为编剧也受到了很多的追问。第一就是演员问,他为什么要杀她?也有一些观众问,他凭什么要杀死她?我说我也没完全想好。我只是感觉写到这个地方,应该让荆轲把她杀死,所以他就把她杀死了。我觉得在艺术作品里面有时候留下一些连作者都不能很好解释的细节,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作品的弹性就会大大地增加,这让读者的脑筋会轰隆隆地运转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批评这是故弄玄虚。张:
这里面有一段荆轲对燕姬的情感表白,要在出发前夕过一次正常人的生活。其实这是典型的用现代观念来解构古代侠士的形象,古代文化对女人是很轻视的。莫:
荆轲毕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超越了名利的人。他刚开始也是一个名利之徒,也像那些同行们嘲笑他的,拿绿豆粉丝、小磨香油到处去送礼,希望别人能够提携自己成名。但是后来在跟燕姬的接触中,他觉悟了,超越了名利境界,进入一种更高的追求。第一个就是关于真正爱情的,对纯真感情的追求,不仅仅为了自己低级欲望的满足,而是有更高的精神方面的契合。所以我想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男人对女性应该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重视、尊重,但是也有例外,古代也有不要江山要美人的帝王。所以我想荆轲在那个时代做出这样一种举动,有这样一种心理,有这样一种追求,也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古人大概没这么黏糊,没这么多柔情。我前面也反复说过,这个戏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故事,是一个历史的旧瓶装当代的新酒这么一个创作模式。张:
我也看了关于这个剧您写的序言,说作为一个50岁的作家,经历了那么多,要敢于对自己下狠手,要敢于揭露自己的内心。您说每个人灵魂深处都藏着一个荆轲,这该怎么理解?荆轲的心理,您是用自己的心理活动去演绎吗?莫:
写作就是不断地用自己的心理体验来赋予人物以灵魂。如果要写荆轲,那我首先就应该站在荆轲的角度甚至把自己变成荆轲,来体验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遭遇。我每写一笔都想我要是荆轲,我会怎么想。我想荆轲就是我,也是可以成立的。这跟《我们的荆轲》这个题目是吻合的,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荆轲。有一个哲学家评论《丰乳肥臀》时说,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也有人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阿Q。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身份的。他写到小说里的好人,要用自己的灵魂深处最高尚的一面来赋予这个好人的所有行为合理性,所有的语言也符合他的性格。他写到小说或者剧本里面的坏人的时候,也要调动他人性深处那些最阴暗的想法,努力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坏人。这就是一个作家创作过程中跟作品里人物的同化,这是写作者的基本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很难写好。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写到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将要死的时候,他自己都呕吐起来了,他自己感觉到满嘴都是砒霜的味道,他已经把自己跟作品里的人物同化在一起了。有的作品之所以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可信,就在于作家在写的时候与人物同化的程度还不够,所以显得故事假,人物假。
三、“诺奖魔咒”与文体实验
张:
您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整个过程中非常的淡定,是不是跟您写《我们的荆轲》的经历有关系,在此之前您已经对出名这样一件事做过一次很冷静、很深入的思考?莫:
第一就是跟家教、家风有关系。我父亲教育我们要低调自省,一直提醒我们低调做人,夹起尾巴做人,不要咋呼,不要猖狂,不要骄傲,不要目中无人。这样一种教育当然也有负面影响,你可以说他世故,甚至说别的更难听的话,但是我还是认可这些东西。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在巨大的荣誉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不至于丧失理智。我心里很清楚,文学无第一。如果我是数学家,证明了一个数学原理,或者我是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定律,这时候当然可以骄傲,可以狂,因为是你发现了,是你发明了,你确实了不起。文学不一样。很多人会承认自己不懂物理,不懂数学,不懂化学,但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不懂文学,不懂小说。大家都懂,大家心中都有好小说、好作家的标准。尽管我获奖了,但并不说明我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猖狂一点,也只能说我是中国当代比较优秀的作家之一,这已经很高调了。得了文学奖确实不应该咋呼,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自省,更加客观地来评价自我,也更加客观地来评价同行们的作品。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具备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我在写《我们的荆轲》这部话剧的时候,对名利的分析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操练。我自认为已经把名利对人的牵制和伤害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当我陷到名利场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态度。现在回头来看,清醒的程度还不够。
张: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名利的追求也是这几十年的突出追求,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但能不能从里面走出来,这是个大问题。莫:
功利不是完全负面的东西,它有它正面积极激励的作用。全世界的军队都有奖励机制,立功嘉奖,各种各样的勋章,各种各样的荣誉。第一是对你作出贡献的奖赏,更重要的是对你未来的一种激励,对其他人的激励,就形成了一种向上追求奋斗的整体的昂扬的精神状态,这是非常正面的。当然如果你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把这个当做终极目的来追求,尤其对文学来讲,这肯定是误入歧途了。哪有一个人会说我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得茅盾文学奖而写作?我觉得这样是得不到的。也许当你忘掉了这些奖的时候,你的作品才能够真正地写好,这些奖才会来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较难了,我也做得不好。我也经常会被名利的东西所牵扯,因为它的磁场是很强烈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含着铁,你不可能完全对这种磁场没有感应。能够及时地冷静下来,这就可以了。张:
您因小说而得到公认,但是您还同时写话剧,又发表了戏曲、诗歌,这样你把文学的主要类型几乎全尝试了,您心目中对自己是否有这样一个内在的驱动,就是我要涉猎文学的主要门类?莫:
我对戏曲有一种报恩之心。因为各种艺术门类是触类旁通的,我过去的小说创作得益于民间戏曲甚多,像咱们这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出现了《檀香刑》,这部小说跟我的故乡的茂腔戏紧密相连,里面有大量的戏曲元素,而我从小就是接受了民间戏曲的熏陶、滋养。当年也希望将来能够写一部戏曲,来回报这种艺术形式对我的滋养之恩。2017年发表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也是我十几年前就想写的。200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讲当中,我讲了母亲当年给我讲述过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说将来会把它写成一部戏曲文学剧本。一直拖了好多年,终于在2015年的时候写完了,之后把它修改发表了。
一个剧本写出来,能不能搬上舞台,要受很多方面制约。一般的舞台演出本,大概有一万四五千字就足够了,我这部有三万五千字。如果要搬上舞台,还要做很多修改。这样一种文学形式的尝试,我想对我的小说创作是有积极作用的。反过来说,我写这么多年小说,对我写剧本也是有帮助的。我写小说,要写故事,写语言,要塑造人物,这个在戏曲里面也是通用的,戏曲也要塑造人物,要在舞台上出现典型的人物形象,让观众看了以后不能忘记。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舞台上的典型,就是这个人他唱的说的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人在整个故事里面碰到各种各样困境时的处理方法也跟别人不一样,这是写小说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要求。
我写诗歌实际是为了向诗人致敬。我只有写过这种诗,我才能够更好地读别人的这种诗;我只有写过戏曲文学剧本,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戏曲文学剧本。过去,有很多诗我看不懂。我写了几组诗之后,感觉到那些当年看不懂的诗,现在看得很明白。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也知道有时候某些诗歌里面的一些话,诗人也是不明白的,但是他也写出来了。这就像我刚才讲荆轲这部话剧里面,荆轲刺燕姬这个行为,荆轲自己也不是完全理解,但是他干了,我写了。总之,这个多种文体的实验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2018年第5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我把《红高粱》和《高粱酒》这两个中篇小说的情节写成了一个戏曲文学剧本。还有就是《十月》刊物上发表了根据我的小说《檀香刑》改编的同名歌剧剧本。2018年12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下一步我应该写小说了。
张:
可能大家对您的最大期待还是小说。莫:
是啊,我写诗歌,写剧本,很多人在观看,个别人在辱骂和诅咒。就好像是我在投石问路一样,好像是河里先来了一条鲫鱼,又来了一条草鱼,大家都期待一条巨大的金色鲤鱼在后面出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是把各种各样的作品都看得很重要,都是很认真地写的。当然大家对我的长篇小说充满了期待,这个我再怎么说也没用。大家既然都希望我写长篇,我肯定还是要写的。不是大家希望我写我就必须写,是因为我心中还有几部长篇的构想,所以我要写。长篇这种艺术形式确实是小说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也最考验一个作家的耐性、体力、才力。从我获奖之后第二天开始,我就想怎么样突破所谓的“诺奖魔咒”。有人说,这个人得了诺奖就不能再创作了,就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种现象确实有它的客观原因。这个客观原因我也充分体验了,就是在时间精力上各种各样的牵扯,在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这都是存在的。好在我获奖的时候还比较年轻,57岁,应该还是创作的盛年。用五年的时间摆脱出来,进入新的一轮创作。看起来这个过程有点长,但正在逐步地实现。现在对于我来讲,最大的理想就是写出一部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来。当然它也可以是个短篇,也可以是个剧本,这个都没有限定。
现在实际上真是需要定力。不管你们怎么样地说,怎么样地猜测,甚至怎么样地贬低,你看,完了,江郎才尽了,这个作家到此为止了,这个我觉得也要沉得住气。我就是五年没有写作,六年不出长篇,八年不出,十年不出又怎么样呢?其实没人真正把我当回事,更没有人把我写不写长篇当回事。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可以写了。
现在对自己的最大考验就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慢慢来,不着急。现在这个时候任何的仓促和着急都只能坏事。所以我就先写一写短篇,写一写剧本,写一写诗歌,使自己的写作技巧不至于生疏,使自己的头脑时刻在文学里面得到一种训练,保持一种创作的激情和对文学素材的敏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