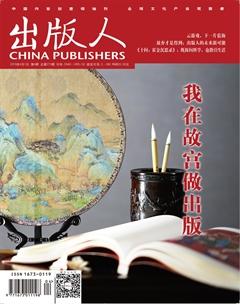更识人间有真味
张熵
当今的中国,每座城市外表都很接近。唯有饮食习惯,方可成为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签。城市已经变得极为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楼宇之间烹饪的食物和空气中食物的香气。而这些香气则赋予了不同地域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情味。
比如来自高邮的汪曾祺先生,刚好这老头也特别喜欢一句宋儒——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而往往食物才是与四时最为匹配的,丰富的食材,更替的转移,被种植进了太多的感情和故事,我们被裹挟在时代的长河里,不免也有着自己的情感和故事。一本以饮食为主轴的汪曾祺文集《肉食者不鄙》,传达了汪老的人生感悟:不热爱美食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只有懂吃、会吃的人,才能感受到活着的美好。
在《素食的故事》篇幅的最后一个小故事《黄油烙饼》结尾,“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这般近似白描的独有写法,让我们的心头也跟着紧了起来,寥寥几语就将味觉和童年混合起来,让记忆和时代交织于此。其实我很想被还原此文刊载于1980年第2期《新观察》之后的场景,遥想那会“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桎梏刚刚被打破,“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也刚刚被“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取代。当代文学随即进入“新时期”,估计“新文学”的春风让当时的汪曾祺率先就想到的是自己的童年,或者说是自己的故乡,这与谈吃大全的其他篇幅有着质的不同,那边说到鱼即是“清蒸、汆汤、红烧、糖醋”等,提到川味胡豆则是“酥、脆、咸、甜、麻、辣”等,无一例外都是具象到色声香味触法,依六根,接六尘,从自觉到觉他,可谓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或许这从他稍后发表的《受戒》更能看出端倪。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用钱钟书的这句话来说汪曾祺的文字好像还有几分贴切,刚好在此书的推杯换盏间隙,也能看到诸如他的老师沈从文等人,那是一个何其熠熠生辉的时代,一边是极度匮乏的物质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另一边则是薪火传承的弦歌不辍。同样在该书的《四方食事》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昆明独有的米线、火腿等食材在里面如同梅花间竹般次第展开,更有甚把昆明的雨和昆明的年都一一囊括进来,无一不写而又写无不尽。还真是让人觉得这汪老头如同《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和洪七公的综合体,一来爱玩二来爱吃,对食物细致的描绘,对生活热爱的流露,所以才让他的文章兼具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味,比如在《做饭》中为我们描述了“到了一个新地方……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对苦难安之若素,待生活云淡风轻。或许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而实际上,在现代生活节奏越來越快的当下,人们在奔波忙碌中通过简单的美食寻找味觉的快乐。一些人乐于享受工业化流水线食品,但也有人不辞辛苦仍然在饮食上坚持传统。对于美味的渴望,源自人类的本能,然而关于美食,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选择,嗜荤茹素,快食慢餐,都有各自的理由。
今天,空前丰盛的食物和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并存,我们常常迷惑吃什么该怎么吃如何吃等问题,陷入佛家所言的“无明”,归根结底就在于内心不够简单。如果到先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他们或许会这样告诫,我们短暂的一生——广厦千间,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穷其一生,始得大道至简。
临此涕零,方觉三餐非淡。
——烙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