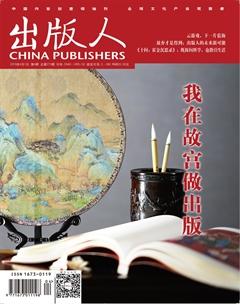诗意地搭建文字的巴别塔
谷立立
用“灰色”来形容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大约是贴切的。这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有多么阴暗,而是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荣耀。他就像美国文学史上的梵高,终其一生无法摆脱“记住还是忘掉”的魔咒。他本该像纳撒尼尔·霍桑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永久地镌刻在文学纪念碑里。可偏偏,他把名字写在了水上,任其四处漂流,不留下一丝痕迹。直到去世半个世纪后,小说《白鲸》才为他赢得了迟来的名声。而他更多的作品,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远离了主流的目光,成了“看不见的经典”。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阳台故事集》算不得传统的写作。19世纪的麦尔维尔尽其所能,写出的却是现代味十足的文字。这里很少有完整的故事,跌宕的情节更无从谈起,反倒是像水流一样的语句,总让人联想起大海的沉郁。《阳台》是优美的散文诗;《本尼托·赛莱诺》是真实案件的笔录;《英肯特达群島,又名魔法群岛》是缜密的岛屿百科全书。或许,麦尔维尔更愿意做19世纪的精神分析师,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传统作家。他的写作就像潜水,徐徐地进到人类意识的最深处,把梦境牢牢地握在手中。6个短篇,6种情绪,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漠然处之,时而伤感愤懑,共同构建出麦尔维尔的文学世界。
《阳台故事集》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部沉思录,都隐含着个人与环境的抗争。麦尔维尔相信,这世间仍有美的存在。然而,他也知道,丑就在美的旁边,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共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就像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一文中所说,“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阳台》一篇,朝北的阳台被视为通往“仙境”的起点。仿佛只要坐在这里,就能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大海。看吧,低伏的麦浪在群山的掩映下起起落落,就像翻腾的波涛,“宁静的八月正午覆盖着深沉的草场,如同沉寂覆盖着赤道”。甚至,阳台的主人相信自己会在不久后开始一次远行,穿越“仙女跳舞的魔圈”,到达梦想的仙境。
可是,当他真正走了出去,才发现“仙境”不过是一座破破烂烂的老宅。孤独的少女坐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一边缝补弟弟的衣服,一边与影子交谈,把远方的阳台当成了幸福的所在。当然,这不是幻灭,而是清醒。麦尔维尔曾在海上漂流,深知大海的善变。它很美丽,也很残酷。无数次,他眼见着同伴无声无息地消失。或者倒在退潮里,或者命丧浅滩上,或者被洪水卷走。只应了一句话“不管你多不高兴,大自然一点儿也不在乎”。这里不难看出麦尔维尔的世界观,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定胜人”。愚蠢的人类不会真正懂得自然的心思。就算用枪炮劈开了大山,把刀具架上了树干,将小路变成了大道,他们仍然是自然的手下败将。
那么,何不放下武器,观察自然、探索自然,顺应它的存在而存在。毕竟,像亚哈船长(《白鲸》的主人公)一样狂妄地反抗自然,必会迎来最终的毁灭。仿佛是为了与上述观点形成呼应,麦尔维尔写下了《英肯特达群岛,又名魔法群岛》。这是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因1835年达尔文的莅临而举世闻名。不过,就算名声在外,“魔法群岛”仍然是荒凉的代名词。火山喷发的岩浆铸成了它的轮廓,反复无常的气流造就了它的生态,它比极地还要荒凉,“容不得野兽中的弃儿”。再比如《钟楼》。就像是陆地上的《白鲸》,把个人与自然的较量写了个清楚透彻。小说中,钟楼设计师班纳多纳醉心于建造一个颇为前卫的自动敲钟人。只是,这种悖逆自然的产物,不但不能“展现人类的荣光”,不能让班纳多纳成为永恒,反而不紧不慢地为他敲响了丧钟。
果不其然,在落成前夕,钟楼设计师就死在了他亲手制造的机械手里。一年后,钟楼轰然倒塌,什么都没留下。或许,这正契合了麦尔维尔的话,“鲁莽的奴仆顺从于更为鲁莽的主子,正是他的顺从要了自己的命”。问题是,如果自然不是抗争的目标,那么他的抗争又将指向哪里?是虚无的社会,也是疏离的人际。就像《巴特比》。与班纳多纳汲汲制造的机械奴隶不同,抄写员巴特比从来不是事事受制于人的小跟班。面对上司安排的事宜(核对抄写的材料、去邮局取信件、离开事务所、搬出办公室),他统统以一句“我不愿意”加以回绝。这种“不愿意”,是拒绝的言辞,也是沉默的抗争。如麦尔维尔所说,“他是一个孤独的看客,把独处看成繁华——就像一个单纯的、转世的盖乌斯·马略(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在迦太基的废墟上沉思”。
或许,麦尔维尔赋予巴特比的角色,远远不是庸庸碌碌的小职员,而是温和、善思、自省的诗人,就像他自己。在美国作家巴里·吉福德的短剧《伟大的真正考验》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麦尔维尔仍然在思考写作的意义:“如果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比起人心可能拥有的整个天堂的显露,在自我和思想讳莫如深的秘密里有更多的力与美。”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力与美让他如此迷恋,不敢轻易忘记?让我们再次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在满目疮痍的岛屿上,诗人麦尔维尔意外地找到了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坚信,这种古老的生物就是“格斗的公羊”,从不轻易认输。哪怕明知不可能,也要在不可能的地方生生冲出一条路来。
“我曾经看到它们在行进途中顽强地抵住岩石,又是推、又是挤、又是扭动,一心要将其取而代之,绝不改变路线。它们受到的毒咒就是,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它们必须要有苦工那样的勇往直前的勇气。”不过,像苦工那样“勇往直前”的难道仅仅是加拉帕戈斯象龟?当然,还包括麦尔维尔自己。终其一生,他很清楚作家唯一忠实的是自己的笔尖,于是不管不顾、奋力写作。哪怕这样的写作,从来不曾将他推上成功的巅峰,品尝到被世界仰望的滋味。都知道,伟大的作家从来是跨越时空的预言者,麦尔维尔也不例外。日复一日,他用诗意的笔触,搭建起一座座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巴别塔。这里,美梦与噩梦相互牵手,自然与人性交相呼应,俨然一幅真实的世界图卷。或许,这才是麦尔维尔存在的意义。
——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