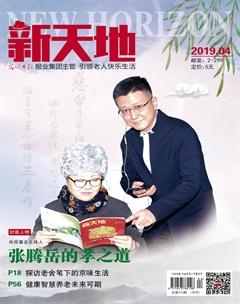“鬃人白”:技艺世代传
辛娅
“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鬃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盘,个个鬃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这便是冰心先生在散文《我到了北京》里提到的老北京鬃人。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记者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鬃人白”的家,采访了传承人白大成先生和他的儿子白霖。
把鬃人传下去
80岁的白大成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北京鬃人的传人。1959年,白大成因病休学,在养病期间,学会了鬃人制作的要领。他找到“鬃人王”的第二代传人王汉卿,打算拜他为师。可是,王汉卿当时已经改行做起了无线电修理,只剩下在临街的窗台上还能摆着几个做好的鬃人。
眼看这门手艺濒临失传,白大成不甘心,“老先生听说我想学,倒是挺高兴,把鬃人的工艺流程和制作特色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就这样,鬃人在白大成手中又活了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初,白大成还给市政府写了封信,申请营业执照,几经辗转,终于在王府井的美术服务部有了属于自己的柜台。改革开放后,白大成的鬃人制作更上一层楼。在地坛庙会上,他工艺精巧的鬃人立即成了抢手货,“鬃人白”的名号也就此传开。
别看鬃人个头不大,真正做下来却需要40多道工序。在王氏鬃人的基础上,白大成苦心钻研,不断在制作工艺上升级改良,“传统鬃人顶多也就三四寸高,在泥托上面安一根秫秸秆作为支架,用细铁丝折成胳膊,虽说也能像皮影戏里一样来回摆动,但显得单薄,脸谱也比较写意,下半身只是一个锥体,少了戏曲人物应有的招式。”
白大成在人物的“筋骨”之外裹上棉絮,为其填充“血肉”,看起来更加饱满,个头也长到18厘米左右。以往的彩纸服装被替换为光泽鲜亮的丝绸,纹样细致华丽,为了凸显挺括的效果,他还在绸布背面裱上一层宣纸。每个人物有了自己独特的表情和脸谱,就连背后的靠旗,乃至头上的翎子,也都与真正的京剧行头如出一辙。衣摆之下,白大成创造性地让鬃人的一条腿高高抬起,“就像京剧人物刚出场时候的亮相动作一样,倍儿神气!”
在白大成看来,做好鬃人,单靠手上功夫还远远不够,“素材和灵感往往来源于丰富的戏曲知识和古典文学,对评书演义也要有了解。像三国戏就有成百出,提到京剧《华容道》,你得能讲出具体的故事情节,知道关羽和曹操的扮相如何,不然根本无从做起。”作为资深戏迷,白大成在家中收藏了上千件戏曲专题的物件,从绣品到瓷器,足足十五个门类。对于京剧的四功五法,他早已烂熟于心,经典曲目更是张口就来,《八大锤》《三英战吕布》《大闹天宫》《挑滑车》等都成就了他的鬃人代表作。
不懂戏做不好鬃人
对于这项独门手艺,白大成从未想过藏着掖着。早在2004年,他就借网络广募传承人,一时间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电视台的人说,他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白大成回忆说:“陆续上门的要求学艺的人很多,有下岗工人、待业青年,也有商人和全职太太。”
在交谈中,白大成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鬃人制作视为一种生财之道,希望以此发家致富,对于戏曲、文学和绘画却一窍不通。“你问他《定军山》是什么戏,他完全不知道,人物也分不清楚,又不感兴趣,不想去学,这就很难办。”
白大成坦言,要想掌握精髓,并非三招两式即可,前期必须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如果只是生硬模仿,最终会糟蹋了这门手艺,“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花钱买鬃人的其实都是懂戏的,做得是不是生动、有没有韵味,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听过这番话,慕名而来的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无奈之下,白大成只好将手艺传给唯一的儿子白霖。“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做了20年的鬃人,从小就是看着这些长大的。”白霖表示,自己在大学时选了外语专业,原本只是希望帮助父亲把鬃人手艺介绍出去,但从未想过动手去做,“后来看父亲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又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失望,就硬着头皮挑起了这个担子。”
所幸,白霖在儿时学过京剧,又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再加上数十年的耳濡目染,上手并不困难,“只可惜,现在对京剧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鬃人作为衍生品也就成了小众消费品,一个月也未必会做上一套。说到底,手艺归手艺,职业是职业,不可能靠这个谋生。”
悉心栽培后来人
如今,白大成已退居幕后,儿子白霖挑起了鬃人传承的担子,更多的时间里,白霖从事的还是“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在课堂上教授的传统手工艺也不再局限于鬃人一种,“我们的文化传承曾经出现过断档,目前真正缺失的是土壤,我要做的就是翻地工作,慢慢恢复基础,让更多人重新感受到这些老北京玩意儿的乐趣。”
白大成也经常带着孙子白岳鹏到梅兰芳大剧院或天桥听戏,给孙子讲一讲鬃人背后的故事,“至少不希望这门手艺从我这里消失,更不想让‘盘中戏成为绝唱。”白岳鹏每周学国画,“不管将来是不是能继续传承,起码让他有点基础吧!”通过耳濡目染,白岳鹏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现在已经开始参与制作鬃人了。
2019年对白大成来说有着特殊意义,自己将迎来80大寿。孙子白岳鹏也将度过第一个本命年。回想起与鬃人结缘的60年,白大成感慨良多。“这些年不仅见证了传统手工艺的兴衰起伏,也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对于未来,祖孙三代满怀期待:“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受到更多人的喜欢,人们的生活品质也能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