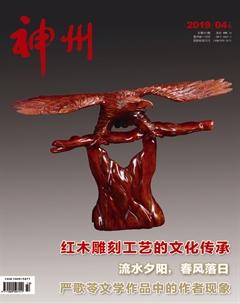此中有真意
方小真
年味会在喧闹声中消失吗?莫言感慨:“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氛围,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南渡北归中,流转于各种过年的仪式,流年带来的温情让我相信年的恒久。年,是中华几千年的沉淀,是辛劳了365天的人们向壮阔的生活表达的崇高敬意,它流入我们的血液,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从新生到暮年,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洋溢着真善美的流年。
冰心回忆童年的春节,年前忙碌的母亲,张罗家人的新衣鞋帽和过年用的美食,卤肉、红糖年糕、灶王糖等构成舌尖上的春节。父亲则为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由传统民族乐器组成的乐队演奏,加上璀璨的火树银花,热闹非凡。大年初一换新装祭祖,给长辈拜年,正月里由各个村落冬闲的农民组成的队伍来“耍花会”,元宵夜点起寄寓人丁兴旺的灯笼,街上“灯如昼”,游人众多,空气中充满记忆熟悉的味道。寄寓这美好心愿的传统,贴对联辞旧迎新,祭祖表达对先人的敬畏,走亲访友团聚和乐,添灯寓“添丁”等等,带有温度的习俗让辛勤了一年的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温情,这些传统习俗带给人们久违的仪式感,让人安稳,《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过年意味着团圆,那份“家人常在,灯火可亲”的期盼,牵挂了一年的久别重逢,洗去归途中的疲惫,带来充实与愉快。
而今在我故乡的小城,人们依旧钟情祖先留下的传统的过年方式,南北文化的差异使我深感故乡过年方式的独特,家乡的年是从廿四开始,廿四祭灶神,祖母会烙上芋饼去祭拜,传说这天灶神上天,要为灶神爷准备干粮,廿五打扫房间,把家里整理的干干净净,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廿七制作鼠壳粿,开始筹备过年的各种食物,除夕是贴春联挂灯笼,祖母会把准备好的祭品去祭拜门神,她对着家里的每一扇门,虔诚地叩拜,感恩门神一年的守护。按例,年夜饭用的大部分食材得先去祭拜祖先,过年得和先人一起热闹。淳朴的农民感恩天地、先人的庇护,在年底用祭拜的方式来答谢,这种感恩意识从古至今,留于一代又一代土地的子女的心中。大年初五是游神庆典,人们是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仿照古代官员出巡的仪式,在村里走一圈,以示神灵所到之处,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通过这种仪式,人们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居住环境,自己的生命,前程及愿景都接受了神圣的保护,这是对新的一年的期盼。正月里大大小小的活动让年得到延续,等到正月结束,一切才重归平淡。
不管是热闹,还是简单朴素,万家灯火中洋溢的国与家的幸福感,都构成年味,而这种幸福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因为这种期盼是我们一年奋斗的动力,也是我们的归宿。
苏童《白雪猪头》中的母亲,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凌晨便到街上排队买猪肉,作品中的母亲为了买到猪肉,满足孩子们对肉的需求,从争执到妥协。年前是母亲最忙碌的日子,她忙家务和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为孩子们缝制衣服。在艰苦朴素的时期,家庭主妇承担起满足家人过一个温饱年的愿望的任务,她们操劳生计,上街抢购紧缺的食物,挑灯夜战为家人缝制衣服。深夜里缝纫机应和着窗外的北风在歌唱的声音,依然是很多人听过最动听的声音。千百年来,家庭主妇们用女性特有的温柔,不管物质匮乏或者富足,都为家人操办一个个温馨的年,她们用灵巧的双手-烹饪出寄寓美好的一道道佳肴,带给我们一个舌尖上的春节,这些美味也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久久不能忘却,她们也是传统的守望者,虔诚地守护着老祖宗留下的习俗。小时候的年是祖母在操办,长大后这个重任交到母亲的手里。与祖母相比,母亲做的事少了许多,她不再追求每件事都亲力亲为,开始用各种代替品去代替过年必备的东西,图的是方便。母亲仍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因为她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张罗着。
团圆的愿望,衍生出中国独有的春运,来之不易的那张归途的车票,串联起离开家的人儿对家乡新的记忆。岁岁年年人不同,流年让人成长也让人日渐沧桑和年迈,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归心似箭。一年又一年,父亲的春联写得越来越有底蕴,母亲的甜糯米酒酿的愈来愈香醇,青丝白发间看到流动的年,看到辛勤浇灌的幸福树正在开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渡过流年,见证着中国大地的发展历程。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於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可见放鞭炮的习俗从古至今都有。陈忠实在《过年,家乡人圆梦的炮声》中用朴实厚重的文字记录了过年时最让他陶醉的炮声,叙写家乡人在新旧年之交时放鞭炮的习俗,排山倒海般的爆炸声由灞河对岸传过来,洋溢着厚重的诗意,隐约可以看到空中时现时隐的爆炸的火光。作者回忆小时候他与父亲放鞭炮的场景,放鞭炮是一种仪式,父亲夜观天象,争取成为最早放鞭炮的一个,这是对传统的敬重,时过境迁轮到“我”和孩子们放鞭炮,在开阔的天地间,“我”和孩子們放得更欢势,到了1991年只剩作者一人留在老家,作者一人放响鞭炮,转身接受渐近的炮声的洗礼,独自面对星光下的白鹿原。
祖辈们守着脚下的土地,用先辈们留下的传统方式过年,严谨地守护那些条条框框的仪式,父辈们还按记忆中祖辈们的仪式过节,但不够严谨,他们在守护自己童年时的记忆,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离开土地,开始让繁琐的仪式简约,开始遗忘传统。过年是需要人撑着的,当那些执行祖宗留下的过年习俗的人都不在了之后,年就塌了。
家乡的炮声,见证了时代的变化,在陈忠实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的鞭炮声是响彻天地的,因为这一年,千万农民圆了千百年温饱的梦,仓廪足了,以前人们期待过年有吃有喝的时代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天天都有过年样子的生活,这是时代巨变,国家前进对千万农民的回馈。鞭炮声是家乡农民集体自发的一种表述方式,是最可靠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述。在我的记忆中,除夕夜连绵不绝的鞭炮烟火声,正是家乡人对一年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新一年的祝福和祈祷,这些鞭炮声是国泰民安的征兆,也是人民幸福的见证。
怀念过年的真情,正如作家笔下的春节,充满着人情味,质朴的人们在生计中表达对生活的诚意,在思念中追忆逝去的美好。年味不随时岁改,年年在时序中重复久违的幸福,当圆梦炮声响彻地北天南时,每个人都能在守护美好的传统中收获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