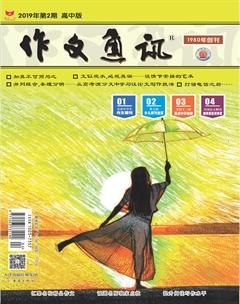梨花落
王莘瑜
梨花落,三尺红台。
兰花指,碎步九龙口,一啼万古愁。
“种福得福如此报,愧我当初赠木桃。”
一曲《锁麟囊》唱罢,他去了后台卸妆。一层层油彩之下是一张俊美的脸庞,此刻眉间却似蹙非蹙,一双丹凤眼如一潭深邃的湖水,映出坚毅又略忧郁的目光。
“今儿园子里的人坐得不太满哪。”
“可不是,这两天人是少点儿。”
“唉,大概年轻人都忙吧?”
他坐在角落里,双目微阖,默默听着师弟们的谈话。散了场的后台嘈杂喧嚣,他却一个人安静地待在角落里,为着日渐萧条的戏园子发愁。
他叫张筱筠,是当地最有名的京剧旦角,扮相漂亮,加上一副清脆空灵的好嗓子,好像天生就是干这行的。七岁学艺,至今已唱了三十年的戏,接手这个戏园子也五六年了,他却丝毫不敢懈怠。演员们的水平越来越高,观众却越来越少,为了将京剧发扬光大,为了这一帮人的生计,他绞尽脑汁。
半晌,后臺的人散尽了,园子里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张筱筠拿起一柄玉竹折扇,那是师父留给他的,他一直带在身边。他缓缓站起身,桌上泛黄的戏折上镌着字迹清秀的唱词,那是他亲手改编又誊写的:
“灯花落,红蜡凝固在卷角。”
他走出戏园,颀长的背影清瘦了许多。
四月的风依旧携着一丝凉意。风起,柳絮飞扬,乌云散去。他走在街上,看着行人匆匆的脚步,街边林立的高楼从远处一一聚拢而来,又奔向身后。他很快到了家,院里的梨花开了满树,游丝一样缭绕的清香溢满院子。又是一阵微风拂过,雪白的梨花从树枝分离,如曼妙飞舞的梦蝶,在点点金色的光晕里打着旋儿,盈盈散落。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他轻吟浅唱一句,声音清澈如水。
“真好听!”
七岁的儿子小南不知何时从屋里跑出来。
“爸爸,你今天怎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他轻笑,摇头,牵起儿子的手。
“爸爸,那我跟你说一件你肯定开心的事。我要跟你学唱戏!”
他一愣。他在儿子面前从来都温和慈爱,此刻身上却发出一阵寒意,眼睛里射出凛冽寒冷的光,像是一柄利刃能把人刺伤。
小南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一向性情温和的爸爸如此可怕。自己说错什么了吗?
“学戏?你以为学戏是件轻松好玩儿的事吗?你以为会唱几出戏就能衣食无忧?我告诉你,你要唱戏,便是不要自己的出路了。”
小南呆住了。他虽然不能完全听懂爸爸的话,但他明白爸爸不同意他学戏。意外的结果让这个尚不知事的孩子不知所措,感到深深的惊讶、恐惧和疑惑。他是在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中长大的,堂鼓声、丝弦声是他童年的梦,爸爸在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俯一仰都令他痴迷。爸爸总爱唱的那几出戏,他一听就明白,也能跷起兰花指,用稚嫩的童音有模有样地唱一句“海岛冰轮初转腾”。他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看得出爸爸对京剧的热爱,也隐约知道爸爸为传承发扬京剧付出的努力。可当自己兴致满满地向爸爸吐露学戏的愿望,等着看到他欣喜的神情,听到他欣慰的称赞时,等来的,却是一阵呵斥。这犹如晴天霹雳。
小南终于缓过神来,哭着跑回了屋。
张筱筠一言不发地呆在原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刚才为什么会对一个孩子说出那样的话。痴念了一生的戏,为何如今被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曾经令他骄傲沉迷的事,如今为何魅力不再?从前看到唱戏的好苗子,他也常常劝别人家父母让孩子学戏,尽管总是得到冷漠的拒绝,可怎么到了自己孩子这里,却立即斩断孩子学戏的心思呢?自己心心念念的传承呢?
“丁零零——”
电话铃声打破了沉寂的气氛,是师弟来的电话:“师兄,老娘今儿总算是出院了。可多亏了您的帮助,借您的钱我一定尽快还。”
“没关系,不急……”他望着满院梨花苦笑。给师弟母亲看病的钱是自己借来的,家里的积蓄都投进戏园子里了,尽管这是他热爱的事业,奈何世事跌宕,现实凉薄。
“回首繁华如梦渺,残生一线付惊涛。”
梨花落满肩头,他没有拂去。
几日后,戏园子。
“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断肠……”他声音依旧婉转动听。
戏散,他对镜卸着脸上的妆,却在镜中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是儿子。
他转过头,看不出悲喜,只是脸上有些憔悴。
虽然脸上带着一丝畏惧,可小南还是开口了:“爸爸,我真的想学戏。”
“会很累。”
“我不怕累。”
“不一定能学成。”
“那也总要试试。”
“可能没有出路。”
“有人学才会有继承,才会有出路。”
张筱筠看着这个七岁的孩童,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当初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唱,恍然间已经三十多年了。自己不也是七岁学的戏吗?戏里戏外度一生,多情扮作无情演。
传承发扬这事很难,可总要有人去做才可能实现。他终于知道,他有多爱这个戏台,他对京剧的发扬光大有多期待。
檀板收,声乐止,台本合,人影绰。
夜风乍起,梨花纷纷落了满地。
“这才是今生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