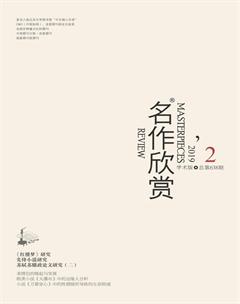绿色世界的不和谐音符
赵超群
摘要:“非喜剧因素”对于一部喜剧作品而言有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皆大欢喜》中的“暗色因素”解构了传统批评中的亚登森林的形象。亚登森林是《皆大欢喜》主要故事发生地,原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想国度。然而,通过分析发现,死亡的气息、对乡下人的贬低和对美好爱情的解构等“暗色因素”使得亚登森林变成了绿色与黑暗并存的“双面”森林。这些“暗色因素”深化了莎氏喜剧的艺术内涵,揭示了人生哀乐参半的哲理,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喜剧 《皆大欢喜》亚登森林 暗色因素
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是一部田园式喜剧,大约创作于1599年。这部喜剧共有五幕,其中有四幕均发生在亚登森林(又译阿登森林)。因此,全面把握亚登森林的含义对深刻理解此剧含义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许多批评家如诺斯洛普·弗莱,都将《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视为典型的“绿色世界”。在这一世界中,现实中原有的疑难和不公全部消解,敌人握手言和,有情人也终成眷属。除此之外,cNKT共收录的有关莎剧中“绿色”或者“绿色世界”的论文也一致将剧中的“绿色森林”视为和谐世界、理想王国的代名词,并将它视为莎士比亚人文情怀的体现。然而,笔者认为,剧中的“绿色世界”其实有着诸多不和谐音符,这些音符与整部剧的戏剧氛围有些格格不入。想要全面把握莎士比亚喜剧的内涵,不可忽视这部喜剧中的非喜剧因素,特别是剧中的“暗色因素”。
“暗色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刘继华在《欢乐中的深刻:莎士比亚喜剧(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研究》中提出。“暗色因素”是指那些既不对人物的命运带来死亡的威胁,也不是由于什么严重事件而给剧中人物带来危险或困难的因素,它们与莎士比亚喜剧的氛围以及喜剧的欢喜结局明显格格不入。不可否认,亚登森林在人文主义抒发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那里,主人公们自由自在,大胆追逐爱情,它是这些逃难人们的庇护所。但是,笔者同时也观察到,这个被誉为和谐理想世界的亚登森林也有着很多“暗色因素”,如死亡的气息、对乡下人的贬低和对美好爱情的解构,亚登森林明亮的背后是一个“暗色世界”。亚登森林是一个和谐与不和谐共生共存的世界,我们必须进行全面解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背后的深意。
一、绿色世界中的黑暗音符——死亡的气息
由于受到死亡的胁迫,剧中主人公被迫逃至亚登森林。在这一绿色世界中,每个人都自由自在,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吟诗作乐,主人公的死亡胁迫似乎已无影无踪。然而,在静谧安详的亚登森林中,死亡的气息总是如影随形,为这个欢喜世界笼上死亡的气息。第二幕第一场,场景转到亚登森林,老公爵赞叹来到森林后悠闲自在的生活,表达着自己对这片绿色世界的喜爱,但是接下来却突然转换到了一头鹿被猎杀的场景。喜剧还未上演,死亡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随着故事的展开,尽管各种欢声笑语、机智对话不断吸引着观众的眼球,但莎士比亚时常在不经意间抖出一些关于死亡的包袱,如体力不支而濒临死亡的老仆人亚丹和离开族群而死亡的鹿等。除此之外,在第三幕第五场中,薛维厄斯称菲琵为“习惯于杀人的硬心肠的刽子手”,菲琵则说“假如我的眼睛能够伤人,那么让它们把你杀死了吧”。剧中情侣机智的对话中穿插的话语充满了刽子手、杀戮等与死亡有关的词语,这从侧面印证了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
死亡本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莎士比亚却把死亡淡化并将其散落在欢乐喜剧的各个角落,减轻了死亡所带来的压抑和绝望。尽管如此,无论何种死亡形式,都会消解喜剧的欢腾,让人们在欢乐褪去之后陷入沉思,从而深化喜剧的内涵。借助欢乐之中时而出现的死亡,莎士比亚似乎意是在告诉观众和读者,死亡从来都是世间的一部分,即使是在逍遥自在的亚登森林,人们也无法摆脱死亡的追赶。死亡阴影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人们恐惧,更多的是让人们珍惜当下的生命。
二、绿色世界中的嘲讽——对乡下人的贬低
在亚登森林中汇聚着两类人群,一群是来自宫廷的达官贵人,另一群是森林周边的乡下人和牧羊人。然而,莎士比亚笔下的乡下人无不遭受着贵族阶层的鄙夷。剧中达官贵人对于乡下人的鄙夷主要表现在乡下人所居的地理位置及语言方面。首先,亚登森林位于乡下,属边缘地区。相对于宫廷而言,亚登森林就是一个“沙漠”,如奥兰多情诗中所写:“为什么这是一片荒碛?因为没有人居住吗?”来自宫廷的达官贵人虽然在这里载歌载舞、自由自在,但在他们的描述中,亚登森林寒冷萧条。试金石更是直言不讳:“哦,现在我到了亚登了。我真是个大傻瓜!在家里舒服得多嘞。”除此之外,从乡下人和贵族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科林问他:“您欢喜不欢喜这种牧人的生活,试金石先生?”“先生”一词在原文中是“Master”,也包含着主人的意思,这一个词语显示了二者之间的阶级差异。也许由于这些贵族阶级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种用词上的“阶级性”,所以贵族阶级在举手投足之间对乡下人都充满了鄙夷。甚至连某些批评家都认为,在角色设定和乡下人所使用的语言方面,“当地村姑虚荣、愚昧,神职人员无知,这些边缘地区的方言缺乏优雅和美感”。这种认知或许是源于不同角色之间的语言——乡下人所用的语言都是粗俗的,而贵族则经常使用诗体。
虽然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肯定人的地位及主体性力量,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和地位,但当时英国底层阶级的人民似乎并不在被肯定和被强调的范围之内。或者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无法跳脱社會阶级的局限,或者是莎氏有意而为之,将这种固化的阶级现象戴上欢乐的面具,呈现给大众,从而引发思考。无论为何为之,对乡下人的嘲弄是消解亚登森林和谐的又一“暗色因素”。
三、绿色世界中对爱情的解构
爱情是莎士比亚喜剧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莎士比亚尽情地讴歌真挚、纯洁的爱情,赞扬男女主人公追逐爱情的勇敢。世人对《皆大欢喜》中的爱情也是津津乐道,因为剧中四对情人终成眷属,在狂欢的氛围中举行了婚礼,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阅读方面的完结感。需要明确的是,莎士比亚“并没有盲目乐观地相信知识的力量、爱情和友谊的作用。在礼赞知识,憧憬无私的友谊、纯洁的爱情的同时,也透露出了他的怀疑、困惑”。于是,他在这些明快的主题背后,掺杂进一些暗色因素。在《皆大欢喜》中,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一些爱情方面的“暗色因素”却解构着剧中爱情的美好。
《皆大欢喜》中的恋人们对爱情的自由追逐仅仅存在于虚幻的亚登森林中,并不能出现在封建古老的宫廷之中。莎士比亚借剧中人物杰奎斯之口对爱情的幻想进行了无情嘲讽:“在你的爱情路程上,你只带了两个月的粮草。”剧中的试金石和奥菊蕾坠人爱河后便急于结婚,但是目的似乎并不单纯。奥菊蕾说:“好,天爷爷保佑我们快活吧。”试金石说:“我们一定得结婚,否则我们只好通奸。”看来,试金石结婚的目的同奥菊蕾一样,是为了“快活”。试金石和奥菊蕾这对恋人的爱情充斥着娱乐嬉戏的态度,存在着不忠的潜在性,莎士比亚对这对恋人的塑造消解了爱情的神圣和纯洁。对比剧中奥兰多和薛维厄斯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态度,试金石和奥菊蕾的娱乐态度揭示的是带有肉欲的爱情。此外,试金石曾独白:“假如结婚结得草率一些,以后我可以借口离开我的妻子。”这表明试金石和奥菊蕾可能都不会对爱情忠诚。他的恋人奥菊蕾本就存在对爱情的不忠,只不过不是对试金石的不忠。在第五幕第一场,一个名叫威廉的村夫本打算向奥菊蕾求婚,但奥菊蕾却声称他“跟我全没有关涉”,直到奥菊蕾听见试金石的威胁,她才劝威廉“你快去吧,好威廉”。奥菊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本来就很可能与威廉是恋人关系,只不过试金石出现以后,她又半推半就地投向了这位宫廷傻子的怀抱,她对爱情的不忠是显而易见的。
莎士比亚或许借罗瑟琳之口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态度:“这个可怜的世界差不多有六千的岁数……人们一代一代地死去,他们的尸体都给蛆虫吃了,可是决不会为爱情而死的。”莎士比亚并不否认真爱的存在,并不束缚人们追逐爱情的自由,但是,他却通过剧中对爱情的解构来警告人们爱情的虚幻。正如肖四新所说,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实际上已经在向我们暗示:真正的爱情其实只是人类“无事生非”的“仲夏夜之梦”,其结果只是“爱的徒劳”。
四、暗色因素的意义
暗色因素的出现是戏剧发展愈加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悲剧和戏剧的界限是十分严格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起源于“酒神赞美歌”的序曲,而喜剧起源于“下等表演”的序曲。因此,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悲剧是崇高的艺术,而喜剧则被标榜为滑稽搞笑的下等娱乐。正是这种固有的成见导致了彼时的悲喜剧因素很难融为一体,以至于悲剧有着强烈的痛苦感,而喜剧则过于欢快和轻浮。中世纪时期,悲喜剧因素逐渐交融,而到了莎士比亚时期,悲喜剧因素才开始相互映衬,使得作品的内涵更为深刻复杂。《皆大欢喜》虽然不是莎士比亚典型的悲喜剧作品,但他在创作完《皆大欢喜》两年之后便进入了悲剧创作时期。莎士比亚由喜剧时期到悲剧时期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具体而言,《皆大欢喜》中的暗色因素可以说是他转变过程的前兆。“莎士比亚喜剧将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滑稽等在不损害其喜剧基调的原则下有机融合在一起,使得剧情发展轻松中有庄严,从而达到以悲衬喜、以悲促喜的艺术效果,形成别具一格的喜剧体系。”这些暗色因素的使用深化了喜剧内涵,在轻快氛围中引发观众的深刻思考,极大地深化了喜剧的意义。
另外,暗色因素的使用也是传达时代声音的有效途径之一。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莎士比亚时代的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人文主义得到了颂扬,人们开始关注“人”,赞美人类的伟大和美好。作为时代的先驱,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他看到了人类的美德和自由,通过歌颂爱情来表现人类的勇敢和人文主义精神,而他早期喜剧作品中的绿色世界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成为他人文主义理想的表现途径之一。尽管当时的社会逐渐变得开明,但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颇多,如贫富悬殊迅速扩展,底层农民、贵族地主、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等。人性和人类生活本就十分复杂,美丑并存,莎士比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探索人性的复杂和深邃,抨击人类局限与时代弊端。于是,其早期喜剧作品中的“暗色因素”便愈加明显,剧中人类的顽疾得到揭示,“人”从不同的角度也不断得到渲染。正如张泗洋所言:“一方面,他(莎士比亚)相信自己的理想是美好的,因而不断地去阐发它,以促其实现;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的观察越来越准确,生活阅历越来越丰富,认识也就越来越近于社会的本质,这就使得他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有些不切合实际。”
五、结语
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通过“暗色因素”的使用,使得亚登森林成为一个绿色与黑暗并存的“双面”森林。死亡的气息消解了喜剧的欢腾气氛,对乡下人的贬低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矛盾,而对美好爱情的解构则展现了爱情虚无缥缈的一面。莎士比亚对这些“暗色因素”的使用并不是简单地将悲喜剧因素混杂在一起,而是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用一定的悲剧性色彩深化喜剧的思想内涵,并消解其过度娱乐的特性。莎士比亚通过嘲笑与戏弄,揭露人生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使得观众在歡声笑语之后反思人类自身的弱点,以求超越自身,从而提升道德思想水平。由此,我们才能更加辩证地看待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对之进行解读,以理解其最为深刻的内涵。虽然和莎氏的其他喜剧作品相比,这部喜剧在整体结构和人物饱和度上稍稍逊色,但是因为它完成于莎士比亚创作转型期,所以《皆大欢喜》不仅仅是一部欢乐的田园喜剧,其喜剧创作意义和社会内涵还有待发掘。本文所讨论的《皆大欢喜》中的暗色因素并未涵盖该剧的所有暗色因素,更未囊括莎士比亚所有喜剧中的暗色因素,但即使文中提到的这几点足够让我们认识到,暗色因素在莎士比亚喜剧中应用是相当普遍的。这些暗色因素在欢喜的气氛中加入了一抹暗色,深化了喜剧作品的思想内涵,促使观众和读者思考社会与人生等方面的意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