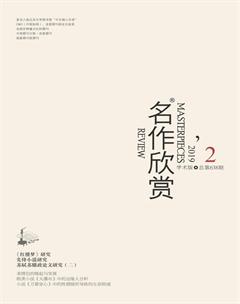自由灵魂的欢乐场
魏玉洁


摘要:游戏说认为诗歌在其创作、发展、性质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糅合了游戏因素,并与其相通,不容分割。卡明斯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视觉艺术性著称,他不拘一格的词汇和标点运用、打破常规的语法规则、栩栩如生的视觉排版让诗歌更具趣味性。本文从卡明斯诗歌的形式、语言及社会意义三个层面探析卡明斯的游戏诗学,分析诗人如何将游戏因素注入诗歌创作,给予“一战”后美国文学创作以新的活力,探索诗人欲借助游戏化的诗歌创作所追求的自由的精神生存空间。
关键词:游戏诗学 诗歌 卡明斯 自由精神 创新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是20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仅次于罗伯特·弗罗斯特。他的诗以其对词语的大胆解构、对标点符号的创新性运用、对诗行的独特排版而闪耀20世纪的美国文坛。但也正因其独树一帜、个人色彩鲜明的创作,他早期诗作的出版困难重重。二十五岁时,年轻诗人怀才不遇,他亲自选编的诗集《郁金香与烟囱》(Tulips and Chimneys)经三年屡次付梓被拒。直到1925年,因对“美国文学的杰出贡献”获得日晷奖,才坚定他对文学创作的信心,为其日后引领美国诗坛实验之风预埋伏笔。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诗的突出、变异、语相隐喻以及诗画一体的特征等方面,而对诗人的游戏诗学及诗歌中的游戏化表征却鲜有研究。本文从游戏诗学角度来看这位风格自成一派的前卫诗人如何把诗歌变成了自由灵魂的欢乐场。
在关于诗的起源的众多说法中,有一种是诗起源于游戏。荷兰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认为所有的诗都来源于游戏,他说:“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游戏功用。它在心智的游戏场、在心智为了诗所创造的自身世界中展开。……它们披戴着‘普通生活的装束,并受到不同于逻辑因果律的关系的约束。”康德认为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free play)”。弗洛伊德则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要重新获得那失去了的童年时代的笑声……艺术,本质上必然是一种游戏活动”。在此语境下,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自然具有游戏属性,并服务于人类的快乐原则。诗源于游戏,又反哺于游戏者的心智,必然与游戏杂糅相融,不可分割。
一、形式创新中的游戏精神
诗歌与游戏的结合首先体现在诗歌与游戏的同质性。赫伊津哈说:“游戏是这样一种行为,在时空的界限之内,以某种可见的秩序,按照自由接受的规则进行,并且在必需品或物质实用的范围之外……而这些品质也适合于诗性创造。”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为自由接受的规则,二为物质实用的范围之外。他实际上强调了游戏的诗歌创作不受特定形式的制约;诗歌服务于人类的精神层面,而不是拘囿于物质实用的范围。这一观点同弗洛伊德不谋而合。弗洛伊德认为“由于文明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压抑,人失掉了许多为规范制度所不许可的快乐……人便运用艺术来重新获得失去了的那些快乐。艺术的目的一开始便是为了使人摆脱禁忌与压抑”。现实生活中的繁文缛节限制人的自由,压抑人的天性,所以,为了舒缓心灵,寻找快乐和自由,诗歌等艺术应运而生。那么诗歌用以愉悦人类的目的性便很明显了,而这一目的则需要借助诗歌的外在形式来得以实现。
赫伊津哈指出,“语言有节律或对称的安排,通过押韵或谐音造成的符号的妙用,对于感觉的精妙修饰,对于短语的人为以及艺术的加工——所有这些都是游戏精神的丰富表达”。也就是说,游戏精神实际绵密糅合于诗人创作诗歌的每一阶段:对语言的精雕细琢、韵律的安排、诗歌的最终呈现方式的考虑等。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卡明斯的诗歌带有极为鲜明的游戏特征。
首先,卡明斯诗歌排列版式整体呈现出的效果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不像传统诗人作诗一般,韵律和谐,诗节规整,卡明斯的诗歌,乍一看没有韵脚,诗行排列杂乱无章,但仔细深究却发现每首诗都更像一幅画。正如他本人所言:“我的诗,少数除外,实质上都是画。”如他的一首诗《one》(图见下页)。这首诗的内容极其简单,只用一个单句描写了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落在墓碑上的场景。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字母的拆分和重组以及诗行的错节,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极为漂亮且规整的对称图案。以“ght”为中轴,上下两段诗行完美对称:首尾完全相同的“one”,分隔上下的括号,甚至连对称的每行的字母数量都几近相同(除了“isuponagra”这一行有10个字母,而与之相对的一行“snowflake”有9个字母外)。而如果我们从横向观察,可以发现,中间“alighting”与一对拆散的括号形成了一个弧形,就好似一座坟墓,而它的上下两行“asnowflake”“is upon a gra”就如墳墓旁的列位牌,继续往两边延伸的单个字母成行的“one”“vest”仿佛在形拟飘摇的雪花。而诗中所写的那片在墓碑上的雪花或许正是“is upon a gra”这一行多出的那一个字母。
虽然这首诗内容简单,但是其中深意仍值得探究。诗歌首先以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开场,给读者以阅读期待:或许这首诗是关于圣诞节,关于孩子嬉戏玩闹,关于任何与雪有关的欢乐场景。但行文至结尾,画风突转,变成了一块墓碑。这样一来,前文预设场景“飘落的雪花”的浪漫感觉急转直下,演变成“人如浮萍水自流”的悲怆。而墓碑意象本就带有肃穆寂寥的感情色彩,这里与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形成强烈对比:一端是黑暗,一端是明亮;一端是浑浊,而另一端是纯洁。含有巨大反差的两个意象被安置在同一个场景中,猛烈的冲击力直击人心。或许是一位逝去的故亲,一位早已被人遗忘的英雄,抑或是某个素昧平生的人,静静地躺在地下,只有一片雪花做伴。这种凄凉是深入骨髓的,是散发于字里行间的。不知诗人落笔时是以何种心境,但当这幅场景闪过脑海时,那种无言的寂寞和苦痛怕是任何言语表达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首诗中,卡明斯借助雪花和墓碑两个意象,通过对文字的重新排列组合,勾画出一幅墓地的场景,表现出了雪花飘零的动态之感。诗歌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加强了诗歌感情氛围的渲染,加强了作者和读者对诗歌主题的理解和丰富感受。
另一首诗《r-p-o-p-h-e-s-s-a-g-r》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诗表现了一只蚂蚱在草地中欢腾跳跃的场景,卡明斯借助字母的拼接,将整首诗变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蚂蚱,有学者绘制出下图:显而易见,卡明斯的诗在关涉蚂蚱主题时,不仅其内容为蚂蚱,诗歌内容的整体呈现也变成蚂蚱。如此一来,视觉效果深化了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使诗歌表现内容更加生动,可观可感。当然,卡明斯的诗歌主要是通过对单词的解构、拼贴、剪裁,对标点符号的运用,对诗行进行重组得以实现最终的“画诗”(poem picture)效果,实现对意象的勾勒,而不是像中国古代寄情于景的诗歌,通过对语言的描述去表现。正如王群所言:“卡明斯诗歌形式上的视觉主要是从直观的语言文字的组合而不是从语言描摹的形象中得来的。”但这种方式并没有让他的诗落入文字游戏的俗套,而是借助这种视觉效果更进一步深化主题意义,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就如少儿文学作品中故事的插画一样,它的存在让我们更直观,更容易接近主题,接近作者。
二、游戏化的诗性语言
游戏与诗歌的亲和更进一步体现在诗歌语义中的游戏因素。众所周知,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并不能作为诗歌语言直接运用。原因在于,普通语言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只是信息的承载体,没有任何表现力而言,而诗歌语言则相反,它“植根于语义学、心理学和美学组成的网络中,其本身能够产生一种张力,以唤起读者的某种特殊情感反应”。同样地,赫伊津哈指出,“艺术语言不同于日常用语之处在于它使用了特殊的术语、意象、修辞等,这并不是人所尽知的……诗性语言凭借意象所做的正是与意象游戏。它用文体安置它们,将神秘注入其中,以便每个意象都蕴含对奥秘的回答”。换言之,诗歌语言正是通过对普通语言的陌生化才使其更具诗胜,更具神秘感。读者只有在经过大脑神经机制的解码后才能揭开诗语的神秘面纱,洞察其背后的深意,这与普通语言的直白带给读者的暴力冲击截然不同,相应的审美体验也不可同日而语。
卡明斯的游戏化诗歌创作则更进一步体现在其对于意象的运用及对诗歌语言的把握方面。因为卡明斯诗歌的视觉艺术性,部分学者攻讦卡明斯的诗只是文字游戏,没有任何深意蕴含其中。实际上,不同于具体诗,或称具象诗(concrete poem,“二战”后兴起,用“文学手段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语言本身,把语言作为一种物质来对待;语言的特点、结构及功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文字游戏,卡明斯的诗歌除了其对形式视觉的别出心裁外,还有语言的意象性在其中。他诗歌中不乏通过意象的叠加,辅之以色彩与光的描写来表现主题的诗,如《thesky》(图见下页)。这首诗写了如糖果一般秀色可餐的天空,轻盈的粉红色让人眼前一亮,柠檬色和绿色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娇羞,巧克力色则为这俏皮的画面增添一分凉爽,天空下面是一辆火车喷着紫色的烟驶向远方。整首诗好像是在描写一幅想象力丰富的小朋友所作的画,蜡笔下是儿童眼中的世界,没有黑暗,五彩缤纷。那里的天空似糖果一般诱人,即使烟也如紫罗兰一般梦幻。卡明斯充分运用色彩来强化意象,选用较低饱和度的粉色、柠檬色、绿色、巧克力色和紫罗兰色,色彩搭配和谐不沉闷。诗中色彩名词的复数化(pinks、lemons、greens、violets、chocolates)暗示图画中不同色彩的叠加繁复,好似万花筒中的五彩斑斓。其中“lemons”“chocolates”“violets”既是实在的物,又是颜色,是复合视觉意象,给读者双重冲击。而修饰色彩的形容词,如“spry”“shy”“cool”则将色彩拟人化,赋以人的感知,让整个画面变得灵动、真实。值得一提的是,卡明斯还打破了人们对色彩的常规认知。一般认为粉色代表温柔,绿色代表活泼,巧克力色代表甜蜜,诗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活泼配之于粉色,羞涩配之于绿色,而清爽则配之于巧克力色。这种认知的偏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增强了语言对读者的冲击力。
此外,诗中寥寥几笔便完成了空间的置换,由天空到地面,增强了诗的立体性,诗的画面感也随之增强。最后的动词“spouting”(喷射)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前面的诗文均是在描写静物,纵然几个形容词为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之感,却终究是读者想象出来的,而末尾的“spouting”则是让这幅画活了起来,进行时态让动作有了连续性,在读者脑海中形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作。诗的末尾将spouting、violets拆分成四行,好似在模拟火车嘟嘟吐出的烟雾,更是形象备至。在这首诗里,卡明斯利用三维空间想象,勾画了一幅远景涵盖天地,近景却又精细入微的饱含童趣的图画,实现了光、色、景的统一,是一幅動静结合、声感交融的佳作。
另外,卡明斯诗歌中对词汇的陌生化处理更为其诗歌增添了一种趣味性。词汇在他的诗中不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而是再一次被解构成由单个字母构成的含有丰富意蕴的语义体。如在《flattened》中,为了使“不停地咳嗽”这个动作更加生动直观,卡明斯没有直接给出“cough”这个单词,而是将其变异为“ccocoucougcoughcoughing”:首先引出“c”字母,接着引出“CO”,然后是“COU”,每次多一个字母,以此类推,直到完整地拼出“COUgh”。因为字母“c”的发音可以类比咳嗽声,所以它每出现一次,读者就可以感受到一次咳嗽声。同样是表现咳嗽这个动作,卡明斯的变异做法使得这个动作在读者想象中出现了6次,因此更具画面感,更加生动。此外,字母之间连接紧密、不留空格,给人一种紧张的压迫感,而动词的进行时态则暗示咳嗽这个动作一直未停,让人难以喘息。在上文提到的另一首诗《r-p-o-p-h-e-s-s-a-g-r》中,“grassshop”就被他变异为“gRrEaPsPhOs”,字母顺序被打乱,大小写字母交替排列,如一只蚂蚱在草丛中跳高跳低地觅食玩耍。因为独特的构词,一个普通的单词便使得整首诗变得更有画面感,更有张力。卡明斯对意象的运用、对语言的陌生化和解构使得他的诗歌本身成为游戏化诗歌的最好注脚。
三、游戏书写中的济世价值
诗歌的游戏化书写并不代表其创作是不严肃的。基于对卡明斯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中的游戏化分析,部分学者质疑卡明斯的诗是否真正能称为诗,是否可以把它等同为游戏。如果诗只是简单的游戏,那么文学的严肃性何在?为回答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厘清诗与游戏之间的区别。郑炀和曾在论证诗与游戏的区别时指出,是否满足“更深层次的心理需要”是判别二者的主要区别。他认为游戏不需要交流,是游戏者一个人的狂欢,而艺术则需要交流,读者需要通过再度体验去同创作者的灵魂沟通。这种交流和沟通其实正是赫伊津哈所说的“一种‘陶醉读者并使其心驰神往的张力”。换言之,一首诗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和情感宣泄的产物,其中必定杂糅着诗人的主观情绪。而这种杂糅一方面是自己单向的情感输出,另一方面则是试图与读者产生双向共情。创作者希望自己内心的孤独、愤懑、惆怅抑或是轻陕在凝定为艺术形式时,能与读者产生共鸣,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诗歌给读者带来的“净化”(catharsis)影响。所以,诗相较于游戏的高级之处在于,诗对读者的心灵震撼。虽然诗与游戏同样都是作为参与者情感宣泄的载体,但诗更进一步地成为创作者与读者交流的媒介,这是单纯的游戏所不具备的功能。
另一方面,诗歌与游戏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社会影响力。相较于游戏只对游戏者个人产生愉悦式满足,诗歌的影响还涉及社会层面。因此,诗歌不仅仅是宣泄工具,更是创作者高贵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的体现,即如西德尼所说“诗歌要以教诲与悦人为意旨”(t0 instluct and delight);也如荣格所言,“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集体人,一位带领并且塑成全人类之潜意识的心理生活者”。因为被寄予更高的社会意义,一部作品便不再是创作者的无病呻吟,更要具有社会价值。这是“更深层次的一种心理满足”,而不是满足于一种“纯粹游戏式的愉悦”。
毫无疑问,卡明斯的诗歌同时满足了读者游戏式的愉悦和更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其诗歌带给读者游戏式的愉悦主要得益于其视觉艺术性。如前文分析,他打破常规作诗法则,用拆字、叠词、断句等手法,纸张作画板,词语作颜料,绘制出一幅幅画诗。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直接暴力地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该如何解读一首看似杂乱无章的诗?生出这一疑问后,读者的好奇天性被激活,引发后续的主动投入。相较以往阅读的被动接受,此时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读者开始主动参与其中,配合诗人完成这场诗歌游戏。这种主动性自然催化读者进一步接近诗的内核,感受詩人通过诗作暗示却未作明确说明的深意。由此,诗在被读者仔细解读后,藏匿在诗行里的情感复活,诗歌重新焕发生命力,读者与诗人达到共情,一场游戏得以圆满。另一方面,卡明斯的诗歌带给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则得益于其在诗中的思考和社会责任感。卡明斯的诗歌不尽然都是对排版的大胆革新,对语言的创新运用,其中更含有一个文化人所具有的良知。看到社会系统的黑暗、文化的故步自封和病态现象的猖獗不息时,作为一个艺术家,卡明斯以自己的诗歌为武器来捍卫自己心中的正义。如《may》:
mayibe gay,like everylark,wholiftshislife/froma11 the dark,who wings his why,beyond because,andsings anif/ofday toyes
在这首诗中,诗人希望自己能像云雀一样快乐,远离生活的黑暗,用质疑的眼光看诸多既定解释,把每一个不确定的日子用歌声变成肯定。显然,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云雀生活的艳羡,表达对黑暗社会的厌弃和对理性有序社会的向往。不同于卡明斯的其他诗呈现出的独特视觉效果,这首诗循规蹈矩,并没有太多排版上的新奇创意,但是几个简单语法词汇的运用却很别致。Because的语法功能为引导原因状语从句,本身的含义是“因为”,用来解释原因。这里卡明斯借用because的语法功能意义指代社会教条,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教条约束着人们,阻止他们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而why的语法功能为引导疑问句,即“为什么”,对自己不理解或不满意的行为发出疑问,这里则指代对社会教条提出质疑。简单的两个引导词却暗示了现代人如同一片荒原寸草不生的精神状态,随波逐流,麻木不仁,没有批判精神。同理,后文的if的语法功能是引导虚拟条件句,意为“假设”“如果”,而yes的语法功能是表示肯定、确定。结合当时“一战”结束和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if暗示社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yes则代指安定的生活,“ifofdays toyes”实际暗含了作者希望不确定的日子可以变得确定的心愿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不满和求变的迫切,也批评了整个社会病态的精神现象。诗中不仅有作者自己的觉醒,也包含了作者希望唤醒麻木的众人、做出改变的期待。这是一种文化人的责任担当,颇有一种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兼济天下”的胸怀。因此,这首看似简单的小诗却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
帕布罗·毕加索曾对艺术家做出这样的评述:“如果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就会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承认,因为如果他得到承认、理解和赞同,那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已经变成没有价值的人云亦云了。一切新的东西,一切值得做的事,都不可能被承认,因为人们看不见未来……”从这一层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卡明斯第一本诗集的出版屡次被拒,也能理解卡明斯这独具一格的诗歌为何能在诗坛长青,因为他的诗歌所表现出的实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自己所热爱的诗歌抱有的热忱。卡明斯的诗歌中有他作为一个游戏者对追求自由快乐的大胆尝试:他对诗歌极具创意的排版,对绘画技巧与诗歌的完美结合,让他的诗歌真正变成了自己可以掌控的游戏。但他的诗歌不仅是游戏,更有超脱于游戏的社会意义:睿智冷静的思考和文化人的社会担当。他的诗歌从来都不是一人的独自狂欢,而是诚挚地邀请读者与之共舞;他试图通过自己大胆的创作方式让读者领悟到他对诗的独特理解,对美国诗坛呆板落后诗风的不满。于他而言,诗歌变成了一个欢乐场,遗世独立于社会之中,宣泄他的不满,安抚他的悲痛,分享他的快乐,安放他自由的灵魂。卡明斯的诗歌是他在故步自封的文化进程中的自我审视和作为一个主流文化的局外人对众人“当局者迷”状态的理性批判。卡明斯在游戏中追求改变,在游戏中引领了美国诗坛的新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