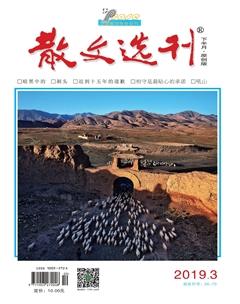激动
我是一个80岁的老作家、老兵、老人,干什么事情都想干好,经历的事情多了,认识得也比较深刻,我去年就写了一篇《十八岁哥哥告诉小英莲》,前年写了《十八岁的墓碑》,获“三毛散文奖”。
写《十八岁哥哥告诉小英莲》的时候,我专门到甘南去了一趟,因为刚当兵的时候,我参加了两次平叛,一次是甘南平叛,一次是西藏平叛。先到甘南,我是汽车兵, 1957年年底到甘南的时候,我还没开车,是副驾驶员。到了大概2012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我特别想到甘南去一趟。到甘南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想把那个平叛的路线再走一遍,那里有两个喇嘛寺特别有名,想看一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写的这个人,《十八岁哥哥告诉小英莲》的小英莲,我写的是甘南临夏州临夏县的一个姑娘,她嫁给了我们部队的一个高原汽车兵,嫁给高原汽车兵以后,他们领了结婚证,没有结婚。这个男的叫韩廷富,他就得病了,得病后在西安住着,他说了一句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话:“我没有见过女人。”实际上,他已经和他的未婚妻王英莲(《柳堡的故事》里面也有一个叫英莲,她也叫王英莲)领了结婚证,但没有举行婚礼,临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意思是想见见英莲嘛。但是人家家里人或者周围的人都不愿意见,你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农村的姑娘去见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战士?后来没去成,他就去世了,去世以后,我看到他那个日记本上写了王英莲给他写的《九九艳阳天》的那首歌。《九九艳阳天》是王英莲赠给她心爱的战士的,当时部队给他记了一等功,连队的指导员看到这个以后,就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就是从这开头。写了封很长的信,直接找到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就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宣传,然后总后领导就派我去采访这个事。我看了王英莲,看了王英莲的妈妈,看了这个战士的妈妈,就是王英莲的婆婆。我怀着按捺不住的心情,写这个,当时就是2015年我专门到甘南去,我就是想再采访一下那个王英莲,但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见她。
我想到什么呢?她现在起码三四十岁了,我怎么采访她,怎么能把这样一件事在她面前提起来,到了临夏以后,我就在想,不能去,要去的话,捅人家的伤疤。一个农村姑娘,你给她提几十年前她的未婚夫死了以后,把那些事提起来,我在这之前一直想采访,没有采访。我就写了这个事,希望大家看。
我前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叫陈元生的女儿,她有大概十多年没给我来信,突然给我打个电话:“你是王宗仁老师吗?”我说:“我是啊。”“你是谁?有什么事吗?”她说,我是陈闻君,后来我才想起,“噢,是陈闻君。”她是高原上一个汽车兵陈元生的女儿,陈元生死了半年以后,这个女儿出生了,出生以后她母亲就改嫁到湖南了,把她扔給爷爷奶奶了,她的爷爷奶奶就把她养大,养大以后,到了15岁爷爷奶奶去世了,去世前,爷爷奶奶告诉她:“拿着这个信,你找部队去,你去找部队去。你没有家了,爸也没了,妈也没有了……”老人死了以后,陈闻君就拿着这封信,坐火车、坐汽车、步行到了高原,找到部队,就知道哭,把信给了一个文艺兵。
这个文艺兵下决心让她当兵,虽然她只有15岁,就让她找到青藏兵站部宣传队的一个队员特招,后来就放到那个什么女兵连去了,她也没这个特长嘛。就这么一个故事,我写过一篇散文,写得不好,叫《第十棵白杨树》,这个好多课本的课都选了,就是写给陈闻君的。她后来到北京来学习的时候,我给她做工作,我找总部干部说这个小孩一定要留在北京,人家就不干,人家就要回高原去,说:“我没有家,我爸在高原上,我就要回到高原去。”
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说我要好好把这个陈闻君写一写,但是我又怀疑:一是我现在年纪太大了,我要写就得找她妈,我找她妈我给她妈怎么说去,这个陈闻君就不愿意找她妈,当时我给她做了好多工作,让她复员以后去找她妈,她说,她妈对她很冷淡,已经有好几个小孩了。要是不找她妈妈,这个散文写出来以后又缺了一大块,就不好写。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写的这些事情没有假的,我不可能假,好多人就讲你写这个东西是不是都是假的,包括那个18岁的妹妹,还有那个《十八岁的墓碑》,那都是真的,那个三毛奖一个一等奖把我评上了吗?那都是真的,那是前年写的。
我这次如果下决心要写,我就写这个陈闻君,就这个15岁的小孩到部队,她来电话以后,我那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这姑娘十多年了没给我打电话,突然她来这个电话。记得我在第四军医大学的时候,我是流着眼泪在给他们毕业班讲陈闻君和陈元生,陈元生现在就埋在格尔木的烈士陵园,第一个墓地就是一等功的陈元生。
陈元生怎么回事呢?他得了高原反应开着车在高原上走,他已经生命最后时刻,他把车开了大概四十多公里路,停在一个兵站,接下来他就死在方向盘上。半年后,他的女儿陈闻君出生了。
我今天很激动,一个80岁的老人遇到这些事情,如果不激动,我觉得你就当不了作家。我可能讲的是闲话,与我这个好像没关系,希望闲话不闲。散文创作没有什么奥秘的地方。我看过的散文很多,因为每年都要编两本中国散文年选,我看很多人有很多好题材,但是写不好,着急得没办法。就好比鸡蛋,把它做成什么样才好呢?你可以炖鸡蛋、炒鸡蛋、荷包蛋……但是都没到家,为什么?把鸡蛋变成小鸡,这才是真正到了最极致。小鸡,它是有生命的,它从一个生命转化成了另一个生命,小鸡还可以下蛋,若是公鸡它还可以叫鸣,它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我们写散文,一定要把散文往极致的地方推,尽量地提升散文的意境。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作家,我和他很熟。他写了一篇散文,我问他:“能不能把这个题材再写一下?”他说:“我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写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开始谈朋友。后来两人先后上了前线,他们只能写很短的信,打电话要跑很远的地方,有时候电话都不能打,可是女兵在一次抢救伤员的时候中弹死了,男兵上战场的时候就把象征着他们之间爱情的花带在身边。我说:“这个题材好得很,你如果不写就糟蹋了,是一篇很好的散文!”结果他就写了一个老兵的回忆,事情是怎样怎样的,作者根本进不去。他用第三人称写不行吗?为什么非得当一个记录员呢?这个题材本可以写好的。你不要以为打仗不能写爱情,没有这一说。
我写过《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还写过《嫂镜》,早在二三十年前写的。讲的是一个哨所里面,他们从没看过一个女的,有时候过一个狐狸也是公的,我就这么写的。但是有一天,突然排长的爱人从杭州来了,这18个兵一下子就活了,嫂子来的这一个月,教他们唱歌、学习文化、给他们做衣服,整个边防哨所一下子活起来了。一个月以后,嫂子要走了,战士们不让她走。可是嫂子要回去上班呀!临走前哨兵们让嫂子答应他们一个条件,明年还要来。可嫂子光笑,不说话。排长说,你嫂子怀小孩了,明年来不了。战士们说,那你把照片给我们留下。嫂子后来想了想说:“我不能留这个照片,我要给你们照一张最漂亮的、我最满意的照片寄给你们,我回到杭州后给你们寄。”战士们依依不舍,把嫂子送下山。回去以后,嫂子再三想:“我寄一张照片不行。我要给18个兵,每个人寄一张照片!”她还写了一封信。
这信都是真的,我只是稍稍加工:“我看到那些战士们,差不多每个战士的床上,翻开褥子,都压着明星的照片,有些还藏得很严,我看了以后,心里很酸。”她在信上跟排长说,“你把我这个照片发给每一个哨兵,让他们大大方方地把我的照片贴在他们的床头,把那些明星照片都给清理掉。”就是这么件事,后来排长接到这封信后,把照片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可这照片怎么处理,老把这照片放在身上也不行,后来大家一想,买了18个镜子,把嫂子的照片放在里头,挂在每个哨兵的床头。一个嫂子变成了18个嫂子,我们每天看到的是18个嫂子,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丝毫没有夸大,但是我把它变成了文学,细节实际上就是这样,我现在讲的时候心里还很酸。后来知道的人多了,凡是从这儿经过的人都要来看看这个嫂镜,18个嫂子,最后我只虚构了一个情节:一个将军知道这件事情后,从老远的地方专门来给这个嫂子恭恭敬敬地敬了个礼,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文章就这么结束了。这个文章,大概4500字,不到5000字,后来那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刊登在《文汇报》上,大半个版面,配上题图,特漂亮!林飞老师后来让李晓峰问我:“《嫂镜》是真的还是虚构的?”我告诉他是真的,一点都没夸大。有些生活,你把它变成文学,还是要高于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当然很生动,但是群众需要的不是那个原汁原味的生活,而是毛主席讲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存在于生活当中,又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当中。
克里木唱过一首歌《达坂城的姑娘》,是新疆达坂城的一首民歌。在三四十年代,就有这么一首歌,完全是原汁原味: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达坂城是个好地方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达坂城是个好地方
达坂城是个好地方,牛羊肥又壮
达坂城的姑娘美,小伙儿也漂亮
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
这是最早的《达坂城的姑娘》原始的词儿,后来慢慢就变成这样:
达坂城的甜瓜大呀,西瓜大又甜
达坂城的甜瓜大呀,西瓜大又甜
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
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三千六百皮鞭
就是再挨一万六千皮鞭我也情愿
最早,王洛宾到了兰州以后,遇到了达坂城来的一个小伙子,维吾尔族,当时在兰州举行晚会时唱了这首歌,王洛宾听了确实很好,词是这样的,可能是第一个也可能是第二个。后来王洛宾又专门到了新疆,他把词儿改了:
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
西瓜是大又甜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两个眼睛好漂亮
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唱着你的歌儿 带着你的嫁妆
赶着马车来
可是现在,他又改了。大概一二十年前,我采访克里木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这首歌采访了他,而且给他写了一个散文),我问:“你为什么要加一句话呢?”他说:“不是我加的!”加的什么话呢?
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
西瓜是大又甜
達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两个眼睛好漂亮
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嫁给我
唱着你的歌儿 带着你的妹妹
赶着马车来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人家不要嫁给别人,要嫁给你,还带着她的妹妹来,怎么回事?”
后来,他依然唱的是“带着你的妹妹来”,他就愿意唱原始的歌词,我们后来把那句“带着你的妹妹”给去掉了。但我很欣赏这一句话,因为我采访了克里木,“带着你妹妹来”,不是说把你姐妹俩都娶了,就娶你,这不是显得你更好吗?更漂亮吗?生活当中,好多东西我们不要怕,它好像涉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没有的事儿,什么东西它都有它的来头。克里木很厉害,他还要坚持唱这个。源于生活是让你深入生活,原汁原味地采访生活,接近多一点,再多一点;高于生活,就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
我这个人爱好太多太多了,我最喜欢的是集邮。作家,你的涉及面要多一些,要真实一点。知识要渊博,知道得越多,你的想象力才越丰富,创作的时候早晚能用上。同样一件事,有些人可能只认识一两个层次,可如果知识丰富、经历丰富的话就能认识到一尺、一丈,所以说炒鸡蛋也好,炖鸡蛋也好,荷包蛋也好,你没有把鸡蛋变成小鸡。美国有一首民歌:“田野里开满了鲜花,鲜花都到哪儿去了?让姑娘们采走了。姑娘们都到哪儿去了?让小伙子们娶走了。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去打仗当士兵了。士兵们都到哪儿去了?战死进入坟墓了。”最后一句话:“坟墓上开满了鲜花!”我们写作也一样,主题要缝上,草原上的鲜花、姑娘头上的鲜花都好,但都不是最好,最好的是坟墓上的鲜花。这种悲壮的力量,给人的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把主题烘托得很高。
我们陕西有个民歌:
第一次到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爸爸打了我两呀么两烟袋
第二次到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呀么两锅盖
第三次到你家,你呀你不在,
你家的大黄狗把我咬出来
第四次到你家,我从你的窗子钻进来,
你的裤腰带死活解不开
第五次到你家,你爸你妈都不在,
咱俩在门缝后咿呀嚯嚯嗨
这就是语言,大白话!文学就是这样,没有形容词,很深刻,但是它又浅。凡是深刻的东西都是浅的,深入浅出。像齐白石画画,一笔一转,两点,从繁到简,鱼就活了。我们搞文学创作,就是要把自己搞好,让自己丰富起来,多读一些书,多经历一些事儿,让知识面更宽,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