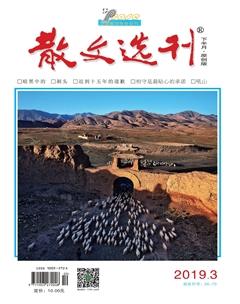一如春日繁花,永不凋落
夏梓言
距县城约五十公里的一所小学。
没有校门,没有校牌,短短的长满青苔的围墙,三四间破旧的教室,几块斑驳的黑板,十几张陈旧的课桌,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当。学校很老,已经没有人知道它的年岁了,我们只能看见屋檐下的石头被滴水滴成了一个个深洞。围墙边上的老树已许多年没发新芽。教室外的墙角长了野草花,开得瘦小。
它虽破虽老,却又神圣无比,庄严不可侵犯。因为,它是整个山村里唯一一个有国旗的地方。那像红霞、火炬的国旗是它暗淡的岁月里唯一的亮点,也是我少年时,在寂寥的群山中见到的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那是很多年前的秋天的一个日子,是十月一日。孩子们起得很早,天还未破晓,他们就到了学校。当太阳在山的那边,缓缓升起。风中夾杂着野花的幽香,十一个个头高矮不一,穿着补丁衣裳的孩子们,就整齐地站成一排,看着他给自己系上新发的红领巾,然后望着他慢慢地将十多米高的旗杆放倒,郑重地将一面已旧了的国旗绑上,慢慢地将旗杆立起来。这时,他起头,十一个在晨风中、在阳光下伫立的孩子们就会大声唱起国歌。
歌声在秋天的山里久久回荡。他和孩子仰起了脸,看旗杆顶头的国旗随风飘扬。他露出了笑容,孩子们也是。那笑容里全是自豪。
他,那个戴眼镜,穿着布鞋,瘦高的老头是这里的校长,也是这里唯一的老师。
那十一个孩子就是这里的学生,而我便是那十一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们喜欢喊他:校长老师。
在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光线极暗的教室里,他给我们讲国旗的红,他说国旗和红领巾的红色都是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的,当时年少的我们还傻乎乎地闻了闻脖子上的红领巾,看看有没有血腥味。放学回了家,我还把红领巾放洗脸盆里泡了泡,果然一盆水,一会儿就全红了。第二天,我告诉老师说:“老师,您说的是真的。”老师摸着我的小脑袋,笑了。
后来长大了,才晓得是因为新红领巾褪色。但是老师并没有告诉我真相的教育方式,却让我印象深刻,这样生动的比喻也让我对革命先烈有了深深的敬意。
他给我们讲抗战故事,告诉我们先烈们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开创这么一个和平的世界。虽然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流过的血,流过的汗。
当时年少的我们,虽然不大听得懂,但我们却记住了那个秋天,还有他说的那个1949年秋天的故事。他说那个秋天的下午三点,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气吞山河地说:“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他不紧不慢的讲述中,我看到他眼角有泪,而他却不自知。
那个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一花不与百花同的秋天一晃就是69年。
己未年的秋天,是国庆。
我从黄州乘车回到蕲春,回到那个小小的山村。母亲说:“学堂要拆了作村队部。”我听得愣了一下。母亲口中的学堂就是我所写的那所小学。
午后,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看学堂。短短的墙破烂不堪,就连昔日绿油油的青苔都不见了,墙头有野草在风中飘荡。
站在学堂门口,我似站在时光之内,又似站在时光之外。
有人喊:“细伢,你干吗的?”
回过头,没戴眼镜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个老头,是他。
我叫他:“校长老师好!”
他背已驼,鬓已霜。我以为他已认不得我了,但是他却记得。我们坐在老树墩上说起十几年前,国庆节升国旗的日子。我发现他的额角有很长一块儿疤痕。
他说很早以前,也就是我父亲一辈读书的时候,学堂本没有旗杆,是他跑到山上砍来一根竹子,将国旗套在竹竿上,然后把学堂前面的一棵香椿树进行了简单的修理,砍掉了部分树枝,最后把套着国旗的竹竿用绳子绑在树梢上。从此,学堂才有了升旗和降旗仪式。
“旗帜不倒,灵魂就不会倒。我只要在这里一天,红旗就会一如春日繁花,永不凋落。”他说。
教文学的我,被他这句话给震慑到了,多么有力量的一句话呀!
一起聊了很久,太阳也落了山去。
暮色四合,开始起风。风真大啊,我们的说话声传了很远。
回到家,夜里我与母亲说起下午在学堂碰到他的事。母亲说他是一位好老师,让我多向他看齐。
母亲说他退休了,现在就住在学堂后面。还说他几年前也是为国庆节升国旗,早晨骑摩托车往学堂赶,秋天山路打了厚厚一层霜,异常的滑。他在上一个陡坡时,摩托车前轮滑了,六十多岁的他被重重地摔了出去,额头被割开了好深的一道口子,都能看到骨头,他的膝盖也破了,肘部伤了,满身是泥的他立即爬起来,重新启动摩托车,再次前行……跤一个一个地摔,每摔一次都伴随着钻心的疼痛。在摔了十跤后,一身泥水地赶到了学堂时,二十多个孩子看到他满身是血,全吓到了。
母亲话音一落。我猛然间想起他额头上那长长的一道疤。
那一瞬间,我哭了。
倘若,学堂旗杆上那面国旗是一朵红花,那么他绝对是那个护花的人。我无比的希望村队部快快动工建好,因为那样国旗就会永远地飘荡在那里,一如春日繁花,永不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