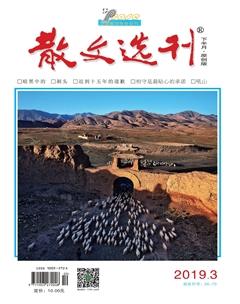每一片瓦都遮风挡雨
林延军
台风过后,小院里零星洒落着破碎的红瓦,一片狼藉。父亲只穿着裤衩,光着肩膀,先是爬上铁大门,再攀上铁大门上面的门檐水泥板平台,父亲站在门檐,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瓦片、瓦刀、绳子和已经搅拌均匀的水泥浆桶。只见父亲用绳子一头绑在水桶两端的耳朵,绳子另一端则远远地抛向屋顶,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像猴子一样利索,爬上了屋顶,直到将水泥浆桶等工具全部吊上屋顶,朝着屋顶修补的位置,一步一步挪过去。那时候已是深秋,天气转凉。
母亲回到屋里,我也跟着回屋。母亲站在屋里漏水或破瓦的位置,用竹竿对准屋顶轻轻敲一敲,再报坐标,欲通过这样的方式里外呼应,告诉屋顶上面的父亲,捅到的位置需要修补瓦片。父亲只能“闻声寻瓦”进行定位,但是,父亲几乎是凭感觉和之前在屋内数过大概的坐标来找位置,最终在目标位置多铺几块瓦片。
南方的瓦屋铺瓦,有“仰铺式”和“俯仰式”两种,我老屋屋顶瓦片是采用后者铺设,两列瓦中间的缝隙,再用简瓦作俯瓦多铺一列压缝。四季轮回,周而复始,屋顶终究还是会漏雨。补瓦时,父亲在两列简瓦之间再铺一层新瓦片,凹面朝上,一片叠压着一片,瓦片两端再用水泥泥缝儿,这样“补瓦”才算完成,这时,补瓦用到的是“仰铺式”。
此刻,屋顶就像菜畦,瓦片就像生长在菜畦里的青菜,等待父亲挥刀动瓦“除虫”。“除虫”后的屋顶,新瓦盖旧瓦,远远望去,像一条天然大裤衩,补丁这里一块,那里一片,又像武侠电视剧丐帮长老衣服的“袋子”。
南方的天气捉摸不定,刮台风、打雷、暴风雨隔三岔五,记忆中,父亲“补瓦片”也自然多了起来。有一次,父亲带上屋顶的瓦片不够,便在屋顶上呼喊母亲再递传几块瓦片上去,也不知道母亲是慢了还是不及时,父亲在屋顶上大发雷霆。我只是隐约地记得,那时候是凛冽的冬天,朝屋顶上看,只看到父亲的背,披着一件作为“工衣”的白衬衫。我站在小院里,雖然穿着厚厚的衣服,但是感觉阵阵发抖,风吹得更猛了。
只要来台风,屋顶就会漏雨、滴水,父亲又要爬上屋顶补瓦,每一次补瓦,父亲都会朝母亲发脾气。每次台风,老屋都会元气大伤,我无法忘记父亲补瓦片的姿势,也忘不了父亲在屋顶朝母亲发脾气的画面。这座屋顶补了又补的三间瓦房,便是我小时候居住过的老屋,似乎瓦片陪着我一起长大。
三间瓦屋在我的村庄,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有。像这种乡间的瓦,最平凡不过了,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找来具有凹槽的简瓦造“小船”,用一根棍子卡在简瓦里,再用绳子绑住棍子做牵引,简瓦前后没有做任何封闭就直接放在小池塘里,以为会浮起来,谁知道一放进池塘就立马沉了下去,后来只能拖着它在水里划来划去。现在想想,玩着不会浮水的“小船”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
后来,父母做起小生意,我们家从农村搬到圩镇上居住,搬离了老屋。在城镇,抬头便是洋楼,基本很少看到瓦屋。从此,老屋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像被遗弃的孺妇,孤零零地待在村庄里。那年除夕,我们又回到老屋,只见小院里杂草丛生,长势逼人,最高的杂草已高过父亲的身高。当父亲和弟弟纷纷挥起锄头锄杂草时,我看到劳作时父亲的背,只是这次父亲的背已没有当年魁梧了。而瓦屋屋檐下悬挂着破瓦,瓦片在大门前也洒落一地,或长满青苔,或堆积厚厚的一层污垢,我忽然警醒,这是岁月的涤荡,是印痕,是沧桑,是衰老。
许多年后,我看过城市古典园林的绿瓦,看过乡村古屋的灰瓦,看过首都巍巍故宫的琉璃瓦,它们或风情万种,或残缺不堪,或庄严气派,从泥土的根脉里来,到绚丽的色彩里去。我读过唐朝诗人李商隐“一春梦雨常飘瓦”关于瓦如梦似幻的描绘,看过当代作家王剑冰《乡间的瓦》,领悟其对瓦的情愫。但是,我依然念念不忘家乡的瓦,是雷州半岛特有的红土煅烧而成的瓦。
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走在乡镇的路上,路旁有几个满头大汗的农夫在盖房,两个人在搬运着瓦片。我心想,现在乡镇建房不都是建洋楼了吗,怎么还有用到瓦的地方?走进一问,原来是建猪舍,此刻,我又想起当年母亲向父亲传递瓦片的情景。
其实,在瓦的世界里,它似乎有自己生存的方式,每一片瓦都会遮风挡雨,就像父亲母亲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