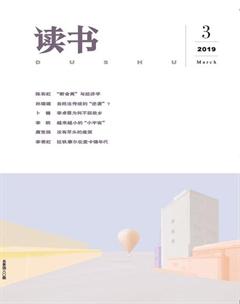陷落的与永恒的
张屏瑾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结尾,著名的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也许就为了要成全她,成千上万的人的命運都改变了。张爱玲写这小说的时候还太年轻,《传奇》《流言》里少不了年轻放狠的态度,说不尽的苍凉大多挂在嘴上,战乱年代是历史打了个盹,因此“海派”得以屏息定神,凝视当下,倒反看出许多“人性之永恒”来,即使是不彻底的。
这大概就是小说家的梦想,在一些极为特殊的东西中找到通向真理的路途,特殊可以幻化成各种奇异的形式,进而生出无穷的艺术创造的可能,而真理,谁不想一窥其面目呢?
不过中国人的爱智总是离不开对历史的把握,在汉语世界里,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十九世纪末海派乍一兴起,跟这种泛历史主义的习惯形成了一些冲突,舶来品、无根基,为一时的热闹、痛快、不讲章法,甚至不择手段,这是当年“京海论争”时人们对于海派的非议。实际上,历史本身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看待历史的方式当然也会随之生变。海派杂糅无数悖反条律:既与刚刚诞生的市民理性有关,也跟情/欲纷纷扬扬的碎片有关;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也抖不尽鸳鸯蝴蝶小家闺阁;孕育出激进的抗争意识,也被各种各样的拜物教占领。从远处看,上海是中国历史的沧海一粟,是飞地,也是“非地”(non-place)——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方,朝近处看,从这里开始讲述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是必然的,如果在传奇之外,还有可能用某种追求真理的眼光来探询这座城市背后的本质的话,那么海派传人也并非不值得一当。
在这个意义上看,王安忆跟海派小说的渊源关系就比较复杂,为了突破洋场中各种表象之间的悖论,她总是采用正反合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洋洋洒洒,总是力求辩证。她多次尝试用长篇小说来讨论,在这座城市里,究竟什么东西在对我们的生活起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是主流,发生了怎样的角力,结局为何,余韵怎样,各种力量声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得通过实际对象来把握,第一种对象当然是人,历史中的人,城市里的人,不光是故事主人公,而且是高度特征化的形象,落实了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当代英雄”,这宛如回到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但是,自二十世纪起,有关人的叙事限度越来越大,荒诞丛生,一地鸡毛,风流云散。相反,物质的历史变得越来越重要,仿佛物比人更能承担命理天道,比易朽的肉体更能承载长时间去芜存菁的考验,显现出某种永恒的答案,新文化史的流行就是一个明证。当然,此物首先得是机械复制时代仍有灵韵的物。在王安忆这里,二0一一年的《天香》写出一部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风俗文化谈,而二0一八年最新的长篇小说《考工记》的主角也是一栋年久失修的古宅,从晚明而来的灵韵最终流浪衰败于二十世纪。
所以可以再次重审王安忆小说的独特性,她要找“名”“实”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而在具体表达上,她又接续了海派书写尽善尽美的风格。她的写作对象无不在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获得了肉身的存在与具体性,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完全静止下来,往往是被丢人了冲突激烈、变化剧烈的更长的时间中,无论是一个人,一座园子,还是一栋古宅。这也显露出她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作家与知识分子之一的本色,纵使这群人后来对时代的变化所得出的结论各有不同,他们仍然可能是中国社会最后一批既充满了文化主体感和优越感,又始终不懈地想象一种总体性存在的知识分子。拿王安忆的作品来看,她用长篇小说一次又一次地呈现自己思考这一总体性存在的过程,我注意到,她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有微妙的调整,这似乎显示出了作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困惑,而正是这种犹豫不决和困惑,成为艺术创作的理由和动力,也造就其丰富性。讲一个好故事,比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达到这种效果。
这一次的调整又是建立在她之前讨论过的问题之上,这么说并不代表着要读这部小说就得读王安忆的所有作品。不过如果你真的读过她的大部分作品,定能感受到某种不屈不挠的叙事伦理。一栋古宅的失修、毁坏乃至倾覆,历时大半个世纪,宅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已走散,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单个个体就可以隐喻整个时代,比如《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她一个人的命运可以放得很大,又可以扩得极多:“这城市里有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相反,《考工记》里的陈书玉是被祖宅困着,既不能放大,也无法流动,好像注定了要由他来和这所宅子共进退。不过也有例外,在革命的高潮期他竟然外出串联过,具体怎样却不得而知,成了小说中的一段留白。总体来说,这个人变成了古宅的一枚渺小缩影,古宅庞大的形体,令无形的命运也有了形体感,像一切庞然大物一样,越破败越显出它的大,而宅子里的人却越来越紧缩,人数压缩、衣食压缩、感情压缩,最后只剩下一个万年单身汉,越发是个“小我”,只求退守,只求保全。唯一膨胀过的一次是在困难时期暗自大嚼香港寄来的补给品,口腹狂欢比照出生机委顿。宅子和人,这一巨一细形成了鲜明对比,“小我”最强烈的愿望是能够修复祖宅,达成永久平衡,但这宅子,欲保护而不成,欲修缮而不得,最终濒临坍塌,全面陷落,宅子里的人也终于不知所终。
故事始于四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脆弱的临界点,历史悬而未决,万事万物引而不发,也是一个藏尽玄机的时刻。这里的四个青年,被誉为“西厢四小开”——十分海派的称谓,可以激发无穷的想象与书写。小说一开始,花开四朵,各表一枝,看起来也是有说不尽的传奇故事要展开,但实际上所谓“小开”故事只略微盘带了一下,很快就绮罗散尽,各自遗世独立。一次神秘的出行拆散了四个人。陈书玉一行是一九四二年“稻子收割之后”离开的上海,是时中途岛战役已经胜利,太平洋战场曙光初现,大局的波动脉络开始与普通人的行止接洽,而等到两年之后,一九四四年秋天陈书玉回到原宅,正是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上海伪政权开始动荡的时刻。这四个人可以说从一开始,命运就被编织进了历史转折的潜流与漩涡之中,他们年轻时在上海滩的交游,原本体现了上海城市中最浮浪的那一层面,但仔细一看,这又不是武侠小说中独门功夫的写法,而恰恰是去表现各自的累赘和包袱,即使是其中有木工传世手艺活儿,可称薄技在身的一位,后来做的是倒卖获罪人家家藏古董的生意,于是祸线埋伏其中。因此开篇的一点点西洋景,终究是堕入百无聊赖的尴尬与虚空,真正的传奇开始于时代斗转星移时代之际,命运感也才开始呈现。
《考工记》里几次出现“宿命”这个词,读来有点扎眼,从陈书玉的眼睛看到朋友们的遭际,他就会在脑筋里蹦出这个词。问题在于,这个词属于谁,谁能用,谁来用?城市中的“小开”们,小资产阶级和手工艺者,小市民,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如陈书玉所想,总是在“这边”和“那边”之问徘徊,留在“这边”还是过渡到“那边”,又怎么才能渡过去?成了永远的心结。事实是,他们四人中有三个留在了“这边”,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但偏有剩下的一个改名换姓去了“那边”,而且成为权重人物,时代的悲喜剧就此展开。悲剧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喜剧,而悲剧和喜剧始终不能彼此相抵,只要看看“这边”去求助“那边”的几幕,两边都有原始强力,一边来自生活,一边来自哲学,但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这城市的主人是谁,到底这生活的主人是谁?
哲学与生活的对话正是王安忆始终不放弃的主题,更早时候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即以城市家庭为背景开展这种对话,充满了问题意识的实验性。到《启蒙时代》里,“谁启谁的蒙”的冲突感更加凸现出来。在我看来,王安忆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最为敏感的一个,而在上海写作,更加强了这一问题意识。上海曾有过中国最早的市民生活,是九十年代的“怀旧热”发生的一大源头。但在王安忆这里,日常生活问题又有它自身的重要性,并不能等同于怀旧,更不用说“怀旧热”与消费主义合流之后带来的种种弊病,这也是她后来为什么说自己并不那么喜欢《长恨歌》的原因。虽然“这边”“那边”的问题看起来在《考工记》里有了更明确的描述,但这一次的变化在于,两边不再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共享了“宿命”感,使得这部小说重新进入到一种对于人类思考和行为的限度,以及这种限度带来的混沌感的探究之中。
明显一点的在于“那边”的干部们的命运变化,小学校长在风暴来临之前选择退隐,书记副校长被遣返原籍,陈书玉颇为欣赏的那位新校女书记在运动中也受到冲击,高喊“向我开炮”……而一九四九年后对昔日玩伴始终避而不见的奚子,终于在风暴中现身,如丧家之犬,急急找藏身之处,就连最为神秘莫测的“弟弟”,新时期再度露面时,也缺了颗牙。其中最为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房产管理处的汪同志身上。汪同志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家里亦有些祖业,他是小说中来自“那边”的对古宅唯一真正感兴趣的,陈书玉代表“这边”和他就哲学与生活的问题颇有一些对话,但他终至自戕,而且莫名其妙地吊到了陈书玉家古宅的梁上,仍是从陈书玉的眼里看到:后楼那张残网里,以为挂着个蜘蛛,结果是个人!以至于他后来一直在心里追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翻成: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这里?!古宅牵引出的天道不仁,网住了原本可以对它进行裁伐的人。
不过,如果单看这些情节,那就只是从古华的《芙蓉镇》以来被讲滥了的一种故事而已,没有太大新意。《启蒙时代》以外还写过《流逝》《富萍》等小说的王安忆自然不会去重谈什么革命的因果报应问题。毋宁说,这里所呈现的问题是,人对于任何一种本质的认定都是一个艰难而艰险的过程,无论是必然留在“这边”或者是已经到了“那边”,都还是在新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探索。陈书玉几次遇到难题,或者在人生的转折关头,真心诚意地去向干部们请教、求助,多数时候他都得到了回应,因此才有了小说作为题记的一句话:他这一生中,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坏。“变坏”可以指人心的变坏,也可以指境遇的变糟。陈书玉勉强侥幸躲过了多次境遇变糟的危机,都与得到高人指点有关。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两次,一次是他问“弟弟”,改天换地之后他家的宅子该怎么办?“弟弟”回答:“顺其自然。”第二次是“文革”眼看就要开始,他又向新校女书记询问自己该怎么办,她回答:“不卑不亢。”两句四字箴言,加在一起的这八个字极有意味,不由得让人想到冯至在四十年代战乱中写下的诗歌,“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人在不断变化的命运中,试图把握自己,顺势而为,既不放弃,也不勉强,这当然是最理想的,而与此同时,这八个字也是对那无可把握的变化感的妥协和认同。虽然是以退为进,但毕竟是一种退守的态度,是对命运的不可知的承认。这样明哲保身的话出自“那边”的重要人物之口,而且是其中两个最优秀的——“弟弟”无论是地位、胸怀,还是能力,显然更胜从“这边”过去的奚子一筹。而那位女书记,可以说是陈书玉一生最为敬佩的两个女人之一,他敬佩朋友朱朱的资产阶级太太是因为朱太太有情有义,敬佩女书记则是因为她给他带来了对整个新时代的气象与风度的感受。重要的是这话并不带一点儿反讽,毫不轻浮,而是极为诚挚和认真的,仿佛天使启唇,唱出悲怆的预言,所以说他们是“纯良”的人。“这边”和“那边”之间出现了一种本不可能存在的知遇之感,把人们分开的东西,又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对永恒难题的吟唱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诗证史”的动机,可以说再次回到了诗学。在“考工”这一主题上,王安忆说她自己对于这座古宅的原型有过长期观察,古宅自身的形态确实十分重要,一次又一次唤起男主人公岁月经年的感喟,在灵韵与诗歌的意义上,这座古宅的物质形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梁思成等人都说过,中国的古建筑不求原物长存,因满足于木材之用,只讲重建,不重修葺,也没有典籍传授营造术的传统。房屋营造上表现出中国人寄寓天地的生命观,是人心重于典章,典章更重于物质的民族。小说里陈家老宅的来源不详,具体朝代失于记载,只能模糊估计,它究竟来自圣赐官制、世家流传,还是商贾经营、附庸风雅,也只能凭口头上的一点流传想象,以及宅子的各种结构样式、工艺方法,种种只鳞片爪来论证。但这些物的痕迹又往往是自相矛盾的,门楣窗棂上雕刻着繁复的八仙,一直到小说快结尾的地方,还出现了一只神秘的、带有塞壬花纹的窨井盖,塞壬对八仙,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只能猜想古宅是来自那“醒于新异,标准摇动”(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的时代,这古宅虽然今日一砖、明日一瓦地一天天在真实地衰落下去,同时又变得越来越抽象,乃至十分存疑,在人的心目中,它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陈书玉站在昼夜分际的古宅的阴影中,看那两重天地,“那一边有故旧,这一边有新知,他在中间,哪边也摆不脱,合不下,满心怅惘”。但终于他能够感觉到一种力量,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而且“不是原始的野蛮,而是出于一种理性”,这一种力量一定是摧枯拉朽,改变一切的;但它究竟意欲何为,却没有结论,他只能将之视为“考验”。可以说,他的一生始终在等待这种考验,犹如等待“靴子落地”;也可以说,为了迎接这种考验,他顶住了来自世俗人生的种种其他考验,比如拒绝了各种情感诱惑,甚至與患难见情的朱太太也绝缘了。王安忆小说中近来频频出现这类仿佛要与世界所有诱惑绝缘的人物,往往是男性,但是,他们又一再地表现出要去经受别的宏大考验的倾向,比如《匿名》中的荒野流浪。对陈书玉来说,他越来越发现他其实并不孤独,这宅子伴着他,他的朋友们,乃至“那边”的新人们,也在时刻等待着这种考验的到来,“顺其自然,不卑不亢”。因此不仅仅是心灵鸡汤,而是“时刻准备着”的一种凛然之心,最后他竟然也多少沾染了一点这种凛然之心,也有点像个英雄似的了。然而,这种考验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不停地去经受考验,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永恒的宿命故事吗?
不可否认的是,最后“煮书亭”无法修复,其现实原因又回到了生活本身,犹如今天在电视上演的后现代闹剧,产权无法明晰,利益无法摆平,无法满足所有人,因此就随它去吧。可见足以解构全部悲剧性和本质问题的,才是真正的难题。伟大的“无情”最终为合理性的“无奈”所替代,这是真正的陷落。长使英雄泪满襟。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