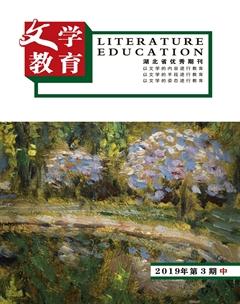往事如麻
妹儿,你听见没有?其实是大姐没有听见,也不知是大姐的老年手机有问题,还是姐的耳朵不斟酌了,大姐就是一个人使劲地吼,也不听我在说什么。大姐说,也没有什么,就是想看我还在忙不,想给我打个电话。四娃子没说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大姐一直在说,四娃子听着她唠叨半天,不但不觉得烦,相反觉得很亲切。
四娃子放下电话,紧接着就看见儿子发来的视频,可能是手机一直占线。视频里,雪花飞舞。儿子说,他放假不能回来了,想搭两点的车,去一个朋友那里玩,打电话说一声。
无语的瞬间。2018年悄悄地遛走,岁月年年如期,浮来浮去的思绪,青涩烙痛的过去,将在这个夜晚,将时光和冰心剪辑。
四娃子打开电脑,想用这种方式握住过去,紧紧地握住。
节日的问候,差点爆破了手机,四娃子默默地看,静静地为亲人和朋友祈祷,却一个信息都没有回,她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的朋友已经刻在了心里,问或者不问,他都在那里,想或者不想,他都会默契。无语便是给所有的朋友,一种安慰,一种宁静。
时光飞快地远去。今年的第一场雪。窗外回荡着歌曲。
四娃子依窗而立。这是一场美丽的雪,落雪夹杂着风的声音,就像一根无情的绳,把心打成了死结,纠结难解,一个人疑视窗外,脑海里,回旋着秒针的悸动。雪花飞舞,传递着清冷的气流,心却沧然无依。
午夜的雪,飘满了天空。四娃子拿出手机,又一次打开视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很遥远的一个冬天,有一个白发老人,依在一扇古老的门上,遥望着那个夜归人。
整个晚上,心被雪包围着。这一晚,四娃子想起了几十年以前的事儿,不过大姐只要在电话里,自己一个人咕咕喽喽说上一通,也不管对方听是不听,大姐就是大姐,她就是一桶满满的清水,她的人生只有整个长河沟那么大,外面的世界,被晕车挡在长河沟那个山崖口儿。
四娃子想不起大姐有多少岁了,想起大姐住的地方,有很多核桃和板栗,还有很多柿子树。想起小时候,大姐回娘家,总是背上背着侄儿,手里提着一篮子红红的柿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如果有苞谷面做上柿子馍馍,就是上等生活,打那以后,便天天盼着大姐回来。大姐的孩子和我们年龄相差不远,我和弟弟也不晓得自己是长辈儿,更不会明白,晚辈是个什么含义,有时候还会因为几个洋芋在一起打架。原汁原味的亲情,现在都被一个又一个的雪季带远了。
隐约感觉雪地里,那棵柿子树,就像大姐一样,坚守着她的阵地,等着逢年过节,亲人们忙着从千里之外赶回来。虽然家里热闹了,可是辛苦了大姐。木缸是大姐保管板栗的好对方,有了客人,就拿出甜甜的板栗,还有核桃和柿饼,大人们吃着,孩儿们闹着,大姐便去烧一块老腊肉炒酱豆,攒了好多山鸡蛋炒一盘腌制的野韭菜,大铁锅里大火烧得噼里啪啦的响,大姐一接开锅盖,哇,洋芋果儿掺米饭,有了这几样,我们这些人,个个儿吃成了大肚汉。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红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因为这年月,都有吃的,再没有人还惦记树上的那些柿子了,也就成了山村里的一道风景。
大姐的日子从来都不孤单,从结婚到现在,一个大队伍由她一个人统领着。因为大姐夫是一名乡村医生。起先是几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她就壮大她的猪子,鸡子,猫子,狗子,照她说的,人畜一般,都要善待。
记忆里,大姐就是屋顶上升起的缕缕炊烟,田地里绿幼幼地麦苗,秋天里黄灿灿苞谷坨。冬天的雪地里,歪歪斜斜的脚印,都是大姐踩出来的火苗儿。过年回家,走的时候,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牵挂,特别是回家走的时候,最好不要回头,怕触及到大姐眼角儿的清泪,还有风中飘弋的白发。
大姐有个好听的小名叫君玉,我爹那个时候,还算是个有墨水儿的人,那个年代,君玉还上了个二年级,虽然是背着小的上学,放学了手里还挎着个篮子,白天上学,回家必须得打一篮子猪草。
君玉慢慢地长大了,像大山上的一朵野百合,在风风雨雨中长大的她,扛起了我们姊妹六个的生活,像梯子坎一样区区蛋蛋的我们,只晓得她是大姐,一天到晚见不着人影儿,也不明白她起早贪黑是为什么,后来听说她还被选上了女民兵连长,还当上什么铁姑娘队的一个小官儿。那个时候,我刚记事儿,隐约记得君玉唱的一首歌,还说是他自己编的,歌词是:
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
大水山上的女铁匠
铁锤手中拿
钻杆叮当响
学大寨,赶大寨
石头疙瘩变成墙
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
风里来,雨里往
战斗在咱的工地上
敢把荒野变粮仓
铁姑娘队,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别人歇伙,铁姑娘们换下衣服,就给群众演戏。后来我大了,君玉也成大姑娘了,而且还有点小名气。君玉有人说婆家了,好像是个当兵的,不过没有成功。现在我都还保存着一个军用挎包,上面还有“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君玉写信很艰难,就请秀青写,秀青是我三姐,比我大两岁,她也写不到,君玉说,秀青就写,那就写“连花袜底儿都没做一双”。呵呵,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笑趴下。
君玉有一口红堂堂的木箱子,天天就是一把锁。我那个时候特别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可她偏偏就是不让我看。有一天,君玉出去上工了,那个年代大集体,我的机会可来了,我一定要看看那红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宝贝,于是我就恨透了那把大鎖,我没有办法,就找了一截铁丝,砸了一个勾勾,掏出来一块黑灯芯绒布。我并不知道那是君玉的心肝宝贝,那个时候大姑娘往婆家,打发三尺好鞋面,就是特重的礼物。那一天,我忙得不亦乐乎,把那块灯芯绒分成四大八块,因为家里有一只大花猫,还有两条大黄狗,我把他们的四只脚都武装得严严实实,这样我忙活了一整天,大花猫很温顺,让我给它穿上了,结果是又咆又叫,大黄狗就很难整了,不是我用好几碗饭来哄它,它是不会服从我的,就是那几碗饭,那个年月连人都吃不上,狗这一天捡了天大个便宜。
四娃子忙活一天,还以为做了一件大事,躺在墙角里,安心地睡着了。先是君玉发现灯芯绒不见了,后来是妈看见狗脚上的狗鞋,紧接着是发现那块豆腐,也被四娃子给狗吃了,这还得了?!不用说,就是那个祸根子四娃子干的猴戏。睡梦中,四娃子脸上还挂着甜甜的笑,还在为她白天能降服那几个猫兵狗将,超级得意。忽然,一棍子马鞭梢,落在屁股上,我的妈呀,马上起了一条红梗,四娃子一骨髅爬起来,从干檐上的那两根柱子上踿上去了,那一晚就在那上面睡了一夜,他们没有找着我,其实上面都是苞谷叶子,睡在里面怪熱乎,我估计妈那一晚上大慨没有睡着,虽然娃子多,四娃子调皮捣蛋也是娃子,她心里也许在心疼,四娃子那个时候不明白,她做的坏事还真的是值得挨打。
四娃子那几天是不敢回家的,只有天天等大人上工了,悄悄地爬下来,吃饱了剩菜剩饭,还是要找点事做的,四娃子闲得无聊,后坡上有一片松树林,松树长得密密麻麻的。那个时候是秋天,松树苞子挺多的,四娃子就上去整了很多松树苞子,松树苞子整完了,看见树丫巴上有几个鸦鹊窝,里面的小鸦鹊儿身上全部像针一样,四娃子就抓起来看,大鸦鹊叽叽喳喳从四方扑下来,吓得赶快把小鸦鹊儿放回去,后来只要四娃子从树下面走一趟,只要从松树扒那里过,鸦鹊们就像相互报信,一会就会一起叽叽喳喳叫唤,四娃子成了鸦鹊们的仇人。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两个大黄狗也会站在身旁,连一声赶一声地叫唤,那阵势简直就是给四娃子助威。
大黄狗成天跟着四娃子,东坡跑到西坡疯,四娃子在山上爬树,黄狗就在地上刨老鼠。有一天,大黄狗在一个石头堆里,叫唤着不走,四娃子跑回家没有理会,第二天一只大母鸡没见了,四娃子跟着狗,一直到了那个石头堆,看见周围都是鸡毛,气得四娃子和狗联合,抄了黄鼠狼的家,大黄鼠狼跑了,逮到两个小黄鼠狼,长那么大,那是四娃子做的一件特别有益的事。也难怪四娃子为一只大母鸡大动肝火,因为每年过生日,妈就会给四娃子煮两个荷包蛋,都是那只大母鸡生的。
四娃子这个样子,那也不怪别的,就因为她是四娃子。四娃子姊妹六个,上面都是姐姐,没有人注意到四娃子是个女孩子,四娃子简直跟长在地上的草没有区别,现在的阿猫阿狗也许还比四娃子金贵。后来四娃子脚下有了一个弟弟。四娃子的日子就更不用说了,四娃子经常会被遗忘在哪个角落,三更半夜突然冻醒,吓得大哭大叫,然后是累了一天的君玉,睡得迷儿八糊,起来一把将四娃子拎了摁到床上,然后是嚎着嚎着这一夜就过去了。
自从我爹走了以后,君玉这个名字,就再没有人叫了,可是逢年过节,这些名字都会跑出来,而且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奇怪的是,我爹我妈都会跟着记忆一起回到我的心中。
(作者介绍:杨仕珍,女,慈善家,热爱文学,现居湖北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