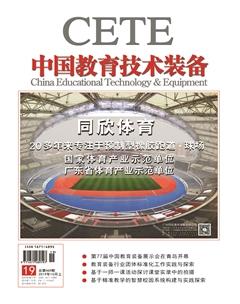教育技术装备发展传统与基石(续一)
新乔 赵晓宁 任熙俊
3 理论、实验和仪器的关系
科学发展与仪器设施的关系,是近代科学与教育产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从17世纪起就一直持续进行着。这种讨论事实上是与科学研究、科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交叉进行的,具体表现为实验与实验科学,仪器设施与应用、技术、方法的关系问题。
对理论与实验关系的不同观点 围绕实验问题的认识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实验依附于理论,即观察和实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实或检验理论,与此相对的观点主张实验有其自身独立的生命,“实验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检验理论。实验本身也许就是目的,或者更可能的是,它服务于其他目的而不是服务于理论科学”[8]27-28。
而理论主导的观点力图为测量(所谓测量,就是用某些方法为区别不同的事物确定相应的数字,以便在这些事物的某些共性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比较。测量过程必然牵涉到某种单位,以这种单位进行计数来给出测量的结果。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努力,直到18世纪初期还只认识到三种抽象的性质,这就是时间、长度和质量。对于别的性质,例如热,那时尚未发展出测量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性质比较次要。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对于新科学来说,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由于缺乏测量热的手段,招致许多谬误。在18世纪初,丹尼尔·华伦海特发明了温度计并标定了它的刻度,这是科学史上的一次突破。这种过程一旦开始,便相继提出许多新的测量单位)方法提供理论上的辩护。如在生理学实验室中,人们相信能够正确记录神经冲动的情况,是因为相信这些电子仪器设备的设计所依赖的物理学原理。然而,这只能将问题淡出视野,就像迪昂所明确承认的那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者都必须要问,那些为测量方法辩护的理论原则本身又是如何被证明是正确的?是通过另外的测量吗?又是什么表明了这些测量是有效的?[8]28
这些忧虑促使人们去寻求另一个能获得观察的有效性的策略,即与理论无关的策略。很多实证主义哲学家退回到“感觉—数据”,但是甚至连感觉—数据也要被视为不足以为信的。很多方法论学者试图将有效性建立在独立证实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方法,要得出同一个结果是不太可能的巧合,除非这个结果是对实在的准确反映。尽管这种论证方式在直觉下令人信服,而且在实验的实践中也被广泛地反映出来,但是它始终无法超越实用主义。[8]28
在物理学史中曾出现过试图消除理论依赖的两种方法——数据、测量,其一是由维克托·勒尼奥(1810—1878)提出的,另一个是由珀西·布里奇曼(1882—1961)
提出的。尽管维克托·勒尼奥的确没有做出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即其事业的高峰时期,人们还是很容易将其视作全欧洲最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的。他的声望和权威建立于他在很多物理学领域(尤其是热现象研究领域)实现的极端精确性上。在他的诸多成果中发现很少有明显的哲学化的痕迹,但是他的方法中一些重要方面却在其具体实践中有迹可循。[8]28-29
对于勒尼奥来说,对真理的探索变成“用精确的数据取代理论家们的公理”。如在他之前的其他人已经在假设人们认识到了一些物质的热膨胀模式(通常被假设为均衡的)的基础上制出了温度计。这些都要求助于各种理论的辩护,诸如基本的量热法或各种热量理论的观点,而勒尼奥否弃了这样的实践,认为要证实关于物质的热现象的理论是不可能的,除非人们已有一个足以为信的温度计。[8]29
然而,勒尼奥是如何设计一个温度计而不用设定任何关于物质热现象的先在知识的呢?他使用了“可比性”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某一类型的仪器应具有相同的读数值。勒尼奥把可比性视为正确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一认识使勒尼奥最终对能否保证测量方法的正确性持悲观的态度,这与那些独立证实的提倡者恰恰相反。尽管表明勒尼奥对任何基于理论的东西之稳定性都持不太信任的态度,但他仍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工作,去向人们展示那些被认为是支配气体变化方式的简单而普遍的规律仅仅是近似的。可比性虽不能保证正确性,但是它确实对实验结果提供了稳定性。[8]29
珀西·布里奇曼作为哲学家、物理学家,与勒尼奥一样表现出想要从测量的基础上消除理论的倾向,而且在关键问题上比勒尼奥更为激进。人们所称的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完全取消了有效性的难题,用测量操作来定义概念:“一般而言,我们使用的任何概念都不过是指一组操作;概念同义于相应的一组操作。”如此一来,至少在原则上,任何宣称测量方法是正确的断言就都变成只在同义反复式的意义上为真。[8]29
仪器设施促进的实验发展 17世纪,人们制造了大量用于研究的基础工具,其中仪器的发明是科学力量壮大的一个标志。新科学最后终于获胜,主要是因为它有了可以利用的仪器,其中望远镜和显微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世纪初,望远镜的发明使得天文学对天空的研究进行了一次革命。10年内,后来对生物学作出同样巨大贡献的显微镜也接着出现了。第一只精确钟表使人们能够以昔日不曾梦想过的精度测量时间;温度计的发明使得温度也可测量。[9]9
如迪布瓦·雷蒙的主要著作《关于动物电的研究》,针对的是认为存在一种控制生命的自发活力的思想。作为这一新有机物理学的例证,迪布瓦·雷蒙提供了他对动物电的研究结果。在神经的电行为领域,可以看到极不寻常的、易对物理科学实验方法做出反应的现象。早期还原论者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是熟练而勤奋的实验者,他们的仪器设施,尤其是路德维希的记波器、迪布瓦·雷蒙的电流计以及用来对组织进行电刺激的各种装置,标志着他们所在实验室的重要地位。[10]166
强有力的技术为生殖和生长的重要过程的无限制实验控制和评估打开了大门。罗伯特·科赫(1843—1910)卓越的实验活动及其告诫,加上创立科学的细菌学和疾病的病菌学说的主要人物路易·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到1880年时差不多已经证实,“医学和预防性的健康檢查将需要一个只有在实验室才能获得的新基础依据”,“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验室成为心理学家的培养基地。新兴的生理心理学家试图通过使用精确的仪器以及合理运用刺激,来创立一门严格的心理科学,以取代反省并描述精神状态的传统方法”。[10]181
理论、实验和仪器设施的相互影响
1)莱顿瓶的启示:实验生理学的例子。18世纪40年代,实验生理学兴起,与实验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稀薄的流体理论的出现相一致。正如化学从基于原子之间的吸引和排斥转向研究酸、碱和金属的化学特性一样,生理学从把身体的器官描述为杠杆、滑轮、泵、筛网转向研究诸如生长、营养、再生等使生命不同于机器的特征。[11]
当然,新的实验物理学和化学对生理学及医学有着直接的影响。电学允诺拥有关于生理学的答案,电鳗和敏感的植物是研究的候选生物,因为它们都表现出用电保护自己的特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电学家从他们的实验得出结论,通过电的种子发芽更快一些,通过电的植物出芽要早一些,通过电的动物比没有通过电的动物要轻一些。电鳐、圭亚那电鳗鱼和非洲的电鲶鱼都被研究过,以便发现它们电的来源。解释这些动物在导电介质中怎样产生电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亨利·卡文迪许证明,给定足够大的电容,电击可以在水下释放,他甚至用毛皮附在一个大号莱顿瓶上制造了一个模型鱼雷鱼来证明自己的观点。[12]124
电产生了肌肉运动,这表明,身体中的电很可能以流体的形式带着感觉刺激和运动指令在神经中运动。但是,早期机械论的失败警示人们要小心谨慎,因此,在18世纪中叶,主要的生理学家冯·哈勒论证说,把电物质等同于动物神经未免是过早的事情。哈勒的谨慎是明智的,因为18世纪的实验技术完全不可能揭示神经冲动的电化学本质。然而,内科医生很快明显成功地利用了电的治疗方法。因此,当路易吉·伽伐尼(1737—1798,意大利生物学家和医生,宣称动物组织能产生电,虽然后来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实验促进了电学的研究)认为蛙腿中包含着有机的莱顿瓶,当它放电导致蛙腿不时踢动时,并未使人们感到惊异。生理学中电现象的复杂性,使18世纪的实验者可望而不可即,但他们试图把物理实验结果应用到生命世界中去的想法却是重要的。[12]124-125
1747年,诺莱(英国物理学家)把丝的阴影投射到一个屏幕上,这个屏幕有量角器刻度,使他精确测量电荷而不干扰实验。1788年,伏特提出,莱顿瓶上的电荷很可能与“张力”(电强度)和莱顿瓶的“容量”二者成比例。伏特此前已经把电的定量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一些概念区别开来,遗憾的是,由于验电器的非线性,他没能确证这种关系。[12]73
玻璃的电学性质给所有早期的实验家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他们的理论假定,电流体不仅存在于带电物体上,而且存在于它周围的气氛中。富兰克林用烟,诺莱用细粉,去检测这种气氛的存在并展现其范围。电吸引和电排斥被假定是由这种气氛的直接作用引起的。玻璃不导电(除非加热时),但传播电的影响。豪克斯比和格雷能够轻易地透过几层玻璃吸引轻物体,电以弗通过玻璃还是没有通过玻璃呢?金属甚至湿布能导电,却屏蔽吸引效果。豪克斯比沮丧地发现,能穿透玻璃瓶壁的电吸引却能被薄平纹细布阻塞。电学理论家们就像他们长期未能区分电流体及其与电的吸引和排斥影响一样,也长期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的异常。气氛,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都不会是电,也不会是电的吸引影响。[12]71
伏特于1775年向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描述了他的起电盘。它由一个嵌进金属盘中的绝缘的用树脂和蜡做成的饼状物组成;带着一个被绝缘的把手的金属板放在饼的顶上。实验者首先通过摩擦饼或者从莱顿瓶给饼充电,使其带电;然后把金属板放到饼上并且接触板的顶部,以放掉由于荷电饼的存在而感应的电荷;然后握着被绝缘的柄,移开金属板。人们发现金属板荷了电。把金属板放到饼上,可将这种电荷转移到莱顿瓶。这个过程想重复多少次就能重复多少次,而不会减少饼上的电荷。伏特从这个实验引出结论说,“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从饼转移到板上,否则饼上的电立刻就会被耗尽;电停留在饼上,只有一种力到达板上;没有电氛或者以弗是耗不尽
的。因此,电氛不能解释起电盘。[12]72
18世纪末,与豪克斯比的气压光同样复杂的发现,把对电的研究转到一个新方向上。1791年,波伦亚大学解剖学教授路易吉·伽伐尼在其实验室里解剖一只蛙。他注意到,当其解剖刀刃碰到蛙腿中的股神经时,蛙腿就踢起来,还是与房间里一台正在发电火花的静电机一致地踢;而且只有他碰了解剖刀刃时这种踢动才会发生,他握住解剖刀的骨把柄时这种踢动就不发生。[12]74
如同气压光一样,这种踢动的原因超出任何既存理论的范围。伽伐尼认为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动物电,并且把蛙腿挂在野外一个铁架上的黄铜钩上,目的是把“气氛”电吸到蛙腿上,以此开始检验其理论。他压铁架上的钩子时,蛙腿就跳动,但这不是因为电氛。正如伽伐尼立刻发现的,黄铜钩与铁架之间的接触产生了电,而一个单独的金属不能使踢动产生。[12]74
伽伐尼必定极其敏锐地认识到这些反常,但是他没有任何适当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作为一名内科医生,他追求的是对蛙腿反常的生理学解释。而伏特对蛙腿反常知道得不多,对电却知道得多。他立刻发现,蛙仅仅起着电的检测器的作用,比当时的任何验电器都敏感得多。伏特立刻得出结论说,这电是由两种不同金属构成的回路产生的,而且这两种金属中至少有一种是潮湿的导体。弱电来自单个金属结,但他希望通过连续地连接几个结来成倍地增强效果。直到他最终想出把银片和锌片(产生最多电的金属对)堆起来的主意,似乎才有组合起作用。他用湿卡纸把每一对金属片分开,由此产生系列:银、锌、卡纸;银、锌、卡纸;等等,以锌为末端。正如莱顿瓶的情况一样,连接这个电堆的顶部和底部就产生电,不过不是莱顿瓶放出的单个电火花,伏特堆产生的是永恒电流。这个电堆在1800年宣布时引起轰动。在一年之内,安东尼·卡莱尔(1768—1840)和威廉·尼科尔森(1753—1815)在皇家学会就用过这种电流把水分解为氧和氢。流电引导了整个电化学领域,结果电磁学也就随之而来了。[12]74-75
本杰明·富兰克林没有察觉到负电荷排斥的事实,他的理论不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因为它要求失去电流体的普通物质排斥其他普通物质,而万有引力理论则认为物质是吸引的。弗朗兹·乌尔里克·西奥多修斯·艾派纳斯(1724—1802)在1756年僅仅假定正负电吸引和排斥性质的对称性,就消除了这个反常。不过,他这样做只是抛弃了一切电氛和以弗,电氛和以弗是他之前的电理论中的一部分。到1756年,实验证据已经使人们怀疑电氛,电的研究不得不变得更具操作性,理论的描述较多而解释则较少了。[12]69-70
1759年,艾派勒斯在《对一种电磁理论的考察》(1759)中对电容器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分析,但受到怀疑对待,很少有人阅读。对电进行测量的努力遭到挫折,与其说是缺乏仪器所致,不如说是在测量方面的混乱所致。这说明区分电荷、力、张力和电容的概念,需要一个包容这些概念的理论。[12]73
2)三棱镜:光与颜色。对颜色的研究也是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笛卡尔把各种颜色现象并入光学领域,在这之前,光和颜色曾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笛卡尔的哲学否定了诸如颜色这样的性质是物体真实性质的可能性。他坚持认为光是一种压力,通过由许多小球所组成的媒质来传递,“而颜色显然是一种感觉,起因于这类小球所具有的另一种运动趋势,即小球沿其轴转动”。基于从一次棱镜实验中所给出的相关证据,笛卡尔推断折射可以改变旋转的速率,转速加快导致红色的感觉,转速放慢导致蓝色的感觉。假设折射能改变旋转的速率,那么反射也可这样,正如网球弹跳时,球的转动也改变了。球面的类型决定着变化的类型,因而球面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尽管笛卡尔的论述中颇有武断和让人难以信服的成分,但他通过将真实颜色与表观色置于同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不仅取消了真实颜色与表观色间的区别,还把颜色现象归入光学领域。从此以后,颜色现象就成为光学的内容。[13]57-58
但是,人们并没有继续按照笛卡尔的术语研究颜色现象。这种学说始于一个假设——科学传统上的又一个常识性的假设,就如地球静止不动这一假设那样,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个假设:光在其原始自然状况下是白色的。[13]58
而对这一假设的挑战是由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牛顿来完成的。在考虑三棱镜下所见到的物体带有彩边这一现象时,牛顿提出一个新的研究颜色的道路。也许引起不同颜色的感觉的光线本来就彼此不同,而且以不同的角度被折射,因此,三棱镜可通过分开光线而非改变光而使不同的颜色显现。为检测这一观点,牛顿通过三棱镜观察了一根一半为红色、另一半为蓝色的线,线的两端看起来被分开了。这一由实验所证实的新观点,注定要将颜色的解释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确地建立起来,从此,这一观点一直是颜色研究的基础。牛顿的《光学》(Opticks)直到1704年才发表,其时距他最初获得这个想法已有40多年。[13]58
牛顿的颜色论首次发表时,他的同时代人普遍难以理解。因为大约2000多年以来,自从系统的自然哲学问世,白光就被认为是单一、原始的光,而牛顿却从另一角度认为白光是各色光的非均匀混合,每一种光都会引起独特的色感。不是白光,即不是混合光,而是其组成成分形成单色光。这种观念反转为人们所理解,他的观点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而笛卡尔仅凭推测。颜色不可能是物体的真实属性,而只是光引起的感觉,在接受了这一主张之后,牛顿把颜色理论彻底地纳入了光学。他推倒了真实颜色与表观色之分,把所有的色感都归于完全相同的原理。一些后来的科学家如胡克改进了他的观点,认为光是单个的、穿过媒质的脉冲。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人们现在所知的光波概念开始发展起来。[13]62
3)辐射、光谱、电磁波。在19世纪最后的20多年里,物理学曾坚实的基础遭受了空前的震撼。从那时起,物理学常常处在混乱之中,实验物理学家们使用越来越精密的仪器,理论物理学家们提出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理论,他们相互影响。[9]248
在1800年,赫舍尔本人就十分确信存在不可见的热射线,但是基于他那个“关键性的”实验,他放弃了这些不可见射线和可见光具有同种性质的可能性。此后,梅洛尼做出和赫舍尔相同的判断。而后来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包括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的连续光谱的概念,也正是依赖于新的、全面的理论和那些引人注目的实验,以及许许多多更加可靠的仪器这样三个方面的结合。正是光的波动说和不可见射线的干涉效应的确立,以及透热的棱镜和精准的温度计的结合,使大多数物理学家最终相信并接受了连续光谱的理论。[8]254
在19世纪,放射物理学的研究也从当初的出于纯粹好奇转变成一种重要的商业性活动。在这些转变过程中,人们也可以发现理论、实验和仪器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麦克斯韦也认为电量的静电单位与电磁单位的比率应该等于光速,但实验证据却不能够使得人们对他的理论消除疑虑。一些信仰麦克斯韦理论的人试图通过快速的振荡产生电磁波,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测这些电磁波。[8]254
1887年,亨利希·赫兹(1857—1894)用自己设计的仪器产生了预先设定频率的电磁波,这是后来所有无线电广播的基础。不过真正能够传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送的复杂信号,还有赖于后来古列尔默·马可尼(1874—1937)
发明的更为新颖的技术。另一方面,射频信号的接收和分析技术对纯理论科学也非常有用。[9]248
在发明电视之前,约瑟夫·约翰·汤姆逊(1856—1940)
于1897年用特殊设计的阴极射线管进行实验而发现了电子,后来又用他的学生查尔斯·汤姆逊·里斯·威尔逊(1869—1959)发明的原型的云室测定了电子的荷质比(即电荷/质量的比值)。从此,人们不再认为原子具有整体性。[9]249
湯姆逊于1897年发现了电子,证明原子并不是不可分割的;在其前一年,安东尼·亨利·伯克勒尔(1852—1908)也偶然地发现了天然放射性,揭示出粒子的另一种来源,这一实验结果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原子并不是不可分割的。伯克勒尔的发现并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仪器,他最初只是将一小块铀矿石样品、一把铜钥匙和一张照相底片一起放在一个抽屉里而偶然得到的结果。后来皮埃尔·居里(1859—1906)和玛丽·居里(1867—1934)继续研究放射性现象,终于发现了钋和镭,虽然他们未能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9]248
科学实践者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清楚,要想获得高质量的实验观察是极其困难的。在定量化科学的语境中,观察意味着测量。只要用到了仪器,关于其设计及运行过程中的正确性的问题就产生了——这对于那些试图发明与改进仪器设施及技术的人来说是一件有些棘手却再明白不过的事情。[8]27
4)理论对实践具有的重要导引作用。一些信奉牛顿的实验家知道发现定量的经验定律的重要性,但感到这个任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如米森布鲁克是熟悉牛顿在引力定律上的成就的,他在18世纪20年代花了很大力气去确定两块磁体之间的作用力。但是,最终他被迫承认失败,他写道:“我只能够作这样的结论,在力和距离之间没有比例关系。”作为事后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测错了对象,他测的是两个整块(球形)磁铁之间的作用力,而不是像夏尔·奥古斯丁·库仑(1736—1806)在18世纪80年代那样测量两个实际上孤立起来的磁极之间的作用,米森布鲁克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论的指引。[14]321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