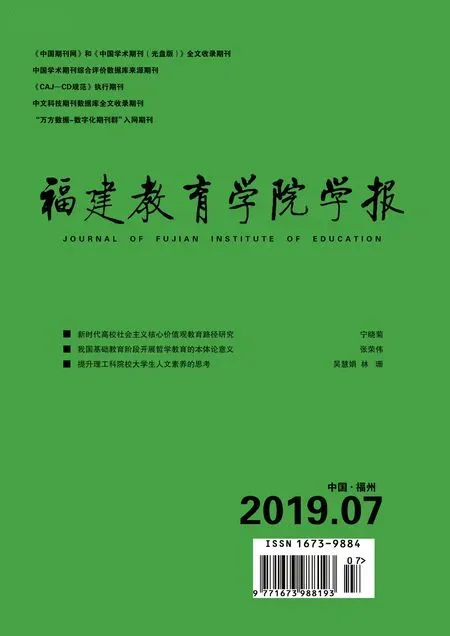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本体论意义
张荣伟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探讨基础教育阶段的哲学教育问题,首先必须对基础教育本身形成一个总体认识,对基础教育之于个人发展的核心价值进行合理界定。一般而言,我国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四个阶段。根据《教育大辞典》,“基础教育”亦称“国民基础教育”,它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国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1]根据《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Basic Learning Needs),“基础教育”即满足人的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该宣言第一条指出:“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法因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这种以“满足基本学习需要”为价值取向而对“基础教育”的宽泛定义,为探讨该阶段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在该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供整体视野和基本依据。
一、揭底:一则冷笑话的良苦用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培养人?这是所有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回答的两个最为现实的问题,因而常常被视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或原点问题。不难发现,对于这两个问题,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自觉地用语言和行动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就一线普通教师而言,可能早在读师范的时候,也可能在正式入职以后,也都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过思考或讨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两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由于历史、文化和个人境遇不同,对两者的看法往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
长期以来,网上流传着一则可以命名为《自己的看法》的笑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出了一道考题:请你对其他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在看完题目之后,非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粮食”,欧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短缺”,拉美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请”,美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而中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显然,这是一则“冷笑话”,或者说是一个“黑色幽默”,它差不多把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黑”了一遍,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看起来是在“黑”相关地区的小朋友,实际是在“黑”这些小朋友所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这则冷笑话的“潜台词”或“潜在逻辑”是:非洲地区极度贫穷,百姓饥寒交迫,那里的孩子第一需要的就是“粮食”;欧洲地区极其富裕,人民衣食无忧,那里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短缺”意识;拉美地区社会动荡、文化衰退,那里的孩子对“请”之类的文明用语比较陌生;美国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军力称霸天下,那里的孩子眼中自然没有什么“其他国家”;中国的教育以“应试”为主,唯书、唯师、唯上,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那里的学生熟悉书本的看法、老师的看法、上级的看法,但往往没有“自己的看法”。
并不否认,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逻辑,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逻辑,教育研究有教育研究的逻辑,或许以上对于“潜在逻辑”的解读不一定恰当、连贯,但必须承认的是,不论当前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状况如何,也不论《自己的看法》借用了何种修辞手法、打破了何种时空界限,当我们看到它夸大其实、荒诞不经、冷嘲热讽的一面时,也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沉重、无奈与苦闷,乃至难以名状的忧伤、忧郁与焦虑。事实上,每一位中国教师,每一位中国的教育理论或教育管理工作者,看到这则略显幽默但更具批评意味的冷笑话时,都不可能装聋作哑、一笑了之,相反,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反思:为什么中国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中国基础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学习经历,让这些孩子陷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当然,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改革与发展,有多种提问方式和应答逻辑。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旋律,我国基础教育一直处于反思和变革状态,无论在决策层面,还是在实践领域,包括在理论研究领域,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了“应该培养什么人”“应该怎么培养人”“应该办什么样的学校”“应该做什么样的教育”等起点性、基础性问题。而且不难发现,因为视角、立场不同,关于以上问题的论点和主张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分歧。从宏观层面来看,在解答这些起点性、基础性问题的过程中,从“三育”“四育”到“五育”,从“双基”“三维目标”到“核心素养”,无论理论框架还是方案设计,包括主题词和关键词,都一直处于不断建构和更新之中。[3]《自己的看法》这则冷笑话的良苦用心在于,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功能与价值取向尤其是培养目标和人才质量敲响了警钟,它以一种“国际比较”而又“滑稽搞笑”的形式告诫人们:我国基础教育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严重忽视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而且已经到了匪夷所思而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证实:一道数学题的测试结果
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最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但培养主体性、自主性以及提高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的重要前提是让学生拥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目前有待进一步确认的问题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究竟有没有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
在《智慧型教师的诞生》一书的序言中,田慧生讲过一件他主持活动教学课题期间发生的事情:[4]
为把课题前期的研讨引向深入,学校课题组设计了一道“数学题”,然后让一名数学特级教师对低、中、高三个年级段随机抽取的各20名学生进行测试。题目是这样的:一条船上载了25只羊,19头牛,还有1位船长,要求根据已知条件求出船长的年龄是多少?测试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居然都算出了具体“结果”,只有少数学生对试题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且质疑者低年级学生居多,中年级次之,高年级最少。
显然,该课题组精心设计这道“数学题”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数学知识和运算技能,而是为了考察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在笔者看来,与《自己的看法》那则冷笑话相比,这个可以命名为《船长的年龄》的真实案例,更值得中国家长和基础教育工作者深思。试问:为什么前例中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而该例中的小学生却出乎意料地算出了具体“结果”?为什么只有少数学生对这道“数学题”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且质疑者低年级学生居多、中年级次之、高年级最少?或许,最为简洁的逻辑前提就是:我们的孩子缺乏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在以批判性思维为特质的主体性、自主性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毋庸置疑,这道试题的“考察要点”在于其自身的合理性,而且考生是否对试题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追问,最能体现其思维品质,也是其数学素养的最好见证。其实,在任何领域,不论是日常生活、社会实践还是科学研究,一个人的关键能力就在于是否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是否能对“关键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从理论上讲,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让受教育者学会提问、善于质疑,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而令人痛心的,在《船长的年龄》这个实例中,对于一个本来就“问错了”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低年级同学凭借常识就能看出来的“错误问题”,很多高年级同学却视而不见、埋头计算,而且算出了所谓的具体“结果”。反观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惨状是:“随着学生年级的递升,受教育时间的增加,知识量的扩大,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反而在逐渐萎缩,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在淡漠,而对教师、书本的依赖、盲从、迷信程度则越来越严重。”[4]试问:长此以往,何谈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何谈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探因:一节语文课的潜在规则
如果说本文前两部分中的案例只是描述了基础教育阶段的一种现象和结果的话,石中英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后记中讲述的故事,则有可能揭示了导致此类现象、此类结果的根本原因。故事情节大致如下:[5]
在小学低年级的一节语文课上,教师正在带领学生学习“小画家”一课。该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冬天下雪了,大雪将整个原野都覆盖起来。清晨,小鹿、小鸡等小动物们都出来了,纷纷用自己的足或爪子在雪地上画出了美丽的图画。教师在完成了教学任务以后,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青蛙和蛇没有出来?不一会儿,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说:“老师,因为青蛙和蛇没有穿毛衣,怕冷,所以呆在家里没出来。”老师听了以后很不高兴,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在让这个学生坐下后,老师又问全班同学:“谁知道?谁能告诉大家正确的答案?”这时候,教室里静极了,再也没有人站起来回答。看到这种情形,老师说:“我告诉你们,青蛙和蛇是冷血动物,冬天需要冬眠,所以不可能出来。这个道理等你们上初中以后就明白了。”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为什么缺乏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为什么缺乏主体性、自主性?为什么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或许,这个可以命名为《教室里静极了》的故事已经道出了原委——身陷于一种“不知道就不要乱说”的课堂文化,受制于一种“只许听老师说”的潜在规则。并不否认,像这个故事中那样明确要求学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的教师并不多见,但不难发现,在有些教师的心中乃至日常教学中,依然藏有类似的观念和规则。试问:当一个教师直接告诉学生“正确答案”的时候,或要求学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的时候,是基于怎样的知识观和学习观?有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内心感受?作为这节语文课当事人的教师,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清醒的还是盲目的?在“分数至上”“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一应试教育背景下,一个教师如果没有专业发展意识,没有对教育教学智慧的自觉追求,何以摆脱“专制型教育”“灌输式教育”的束缚?何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结果来说,没有哪个教师不期望学生掌握正确的答案、标准的答案,更没有哪个教师期望学生掌握错误的答案、含糊的答案。但问题可能恰恰源自于此。无论在什么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如果在一个教师的头脑中,“结果”总是重于“过程”而意识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总是期望学生说出正确答案、标准答案,总是要求学生知道了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后再发言,必然会限制学生的提问、质疑和表达,必然会压制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必然会出现“教室里静极了”这样“一言堂”的尴尬局面。
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离不开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离不开真诚、和谐、开放的课堂,而这一切需要建立在科学的知识观、儿童观和学习观之上。可以说,一个奉行书本中心、权威至上,不能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开展教学的教师,不可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设出安全的课堂和自由的学习情境。《教室里静极了》这种专制型、灌输式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对“标准答案”的迷信和崇拜,进而在“只许听老师讲”这一潜规则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不知道就不要乱说”的听从文化。基于这种潜规则和听从文化的课堂的深层危机在于,轻慢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忽视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
教育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的事业,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项很危险的事业。我们必须警惕的是,现实中的课堂可能是愉悦、欢快、安全的,但也可能是沉默、紧张、恐慌的。进一步来说,在任何学校的任何班级中,都会有一些学生由于语言能力、想象能力、感受能力、理解能力或个人学习方法、努力程度方面的原因而落后于其他同学。这些学生常常成为课堂中的弱势群体,以致于,被边缘、被冷漠、被呵斥、被嘲讽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是,无论一节课传授的知识多么多、多么快、多么深,如果有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或个性方面的一些原因,而处于一种难堪、羞愧、压抑(迫)的学习状态的话,如果有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面红耳赤、语无伦次、低头不语,或者回答问题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话,这样的课堂绝对算不上什么高效课堂或理想课堂。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摆脱知识本位、社会本位、教师本位等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展现课堂的生命性、生活性和趣味性,让学生真正拥有一种轻松、活泼、自由的学习体验,真正享受学习的快乐和幸福,成为近20年来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6]
四、寻路:一种哲学味的学科教学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最重要场所,学科教学是学校开展哲学教育的主渠道。这是笔者之所以倡导“多学科渗透哲学教育”的基本前提预设。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动哲学教育,不能不考察幼儿园、中小学教师接受过的哲学教育状况以及个人的实际哲学修养。试想,作为一名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如果在入职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哲学教育,入职后又没有主动学习或受过相关培训,怎么可能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和明确的哲学教育意识,又怎么可能积极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
自2014年以来,笔者在推进“多学科渗透哲学教育”这一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方面,幼儿园、中小学教师想要顺利开展哲学教育,必须拥有比较扎实的哲学功底、比较开阔的学科视野和比较系统的儿童认知与发展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教师也会在开展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自觉地学习哲学和运用哲学,不断钻研所任教学科的学科本质,不断完善个人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理论,进而重构个人的哲学观、儿童观和教育观,逐步建立起个人的教学哲学和教育信念。
目前,积极推动幼儿园、中小学哲学教育的理论工作者大致有四类:一是哲学理论工作者,他们具有哲学专业背景,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学教学;二是教育学理论工作者,他们具有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背景,主要研究方向是基础教育改革;三是儿童理论工作者,他们具有早教专业背景,主要研究方向是童年哲学;四是文学理论工作者,主要研究方向是儿童文学。就这四类理论工作者而言,如果直接走进中小学校园(包括幼儿园),与中小学生(包括幼儿)“面对面”,亲自开展哲学教育的话,应该都不会遇到多大难题,应该都可以比较顺畅地完成既定的教育教学任务。但是,这四类理论工作者很少走进幼儿园和中小学,更少走进原生态的课堂,几乎没有与幼儿或中小学生一起聊哲学、做哲学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机会。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旁观者、守望者、评价者、促进者,更多的时候是在进行理论建构、舆论宣传或间接经验总结,有机会与他们“亲密接触”的并不是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而是一些较早意识到了哲学教育重要性的一线教师和极少数的学生父母。
就这些较早意识到了哲学教育重要性的一线教师而言,他们在师范毕业的时候即已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或者说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比较薄弱的理论板块可能在文学和哲学两个方面。而进一步的考察发现,目前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哲学教育的一线教师,大多数是具有汉语言专业背景的教师,可以说他们也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这是由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幼儿园、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决定的。必须承认,让这些教师上语文课或讲一讲文学,并不是什么难题,但他们能不能给中小学生或幼儿园的孩子讲哲学,能不能结合语文(言)教学自如地开展哲学教育,则会因人而异。事实证明,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或者说,从事不同学科教学的一线教师,在开展哲学教育的过程中会遇到各自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但总体来看,这些教师共同面临的问题则是自身的哲学修养和对所任教学科的本质的把握,而最起码的要求是,能够意识到所任教学科与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与内在关联,能够自觉地从教学内容或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彰显所任教学科的哲学品味——“哲学味”。
行文至此,笔者又想起了自己读初三时化学课上一段“开小差”的经历,而且犹豫再三之后,决定形成文字发表,以便与更多的朋友讨论、交流,或许能够为探讨学科教学的“哲学味”提供一种学生的立场和视角。这段经历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至今清晰记得的是,我那节课的那一刻“人在曹营心在汉”——开小差了。那节课老师在讲“碳”元素那一章的内容,而我却不知什么原因,眼睛在看着窗外“发呆”。没想到的是,老师突然大声喊到我的姓名,一字一句地问道:“你—知—道—碳—元—素—是—什—么—颜—色—的—吗?”我立马回过神,迅速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碳—碳—元—素—是—什—么—颜—色—的?我—我—不—知—道。”这时老师非常生气地说:“不知道?!那你就是个笨蛋!!”至于那节课我站立了多久,后来是怎么坐下来的,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当天放学刚到家,就被父亲训斥:“你今天的化学课是不是开小差、走神了?!上课不认真听讲,怎么能读好书……”
前些年,当讨论学科哲学以及通过学科教学渗透哲学教育等问题的时候,我会提起那节化学课上的尴尬与困惑,有时还会与大家展开认真的研讨,但至今难以确定的是:化学老师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提问?究竟是为了责难学生还是因为他当时就认为碳元素有颜色?至于我为那个问题困惑了多久,多久之后才确认那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也想不起来了,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后来的化学课上,再也不敢东张西望了。我就读的那所初中就在家门口,一直敬畏的这位化学老师也姓张,论家族辈分,我喊他叔叔。这位叔叔辛辛苦苦、认认真真教了一辈子书。我初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家乡,一直在外地求学、工作,尽管后来也和这位叔叔见过几次面,但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也没找到比较恰当的机会问他那节课那么提问的真实用意。
从本质上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会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懂得以哲学的眼光去认识世界和打量世界,从而过上一种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在笔者看来,所谓“具有哲学味的学科教学”,应该是“学科教学渗透哲学教育”的自然结果。试想:在那节化学课上,作为学生的“我”,如果有勇气、有机会反问、质疑,而能够与老师或同学围绕“碳元素的颜色”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甚至辩驳的话,会是怎样的课堂情景?会达到怎样的教学效果?事实上,无论是什么学科的课堂教学,只有把话语权真正还给学生,允许“乱想”“乱说”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具有哲学的味道,学生才可能真正拥有“真实的问题”“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收获”,才不至于有那么多学生为“船长的年龄”苦思冥想、瞎编乱造。
五、造势:一间多功能的智慧教室
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在于,呵护这一阶段学生的哲学天性,训练这一阶段学生的哲学思维,为这一阶段学生的哲学人生奠基。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内在关联、相辅相成。但从前文四部分的探讨来看,目前最需要也最薄弱的环节是基于不同学习领域和学科教学的哲学思维训练。
既然好思、好学、好问是幼儿和中小学生的天性,我们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就应该创设宽松、自由的学习空间和成长环境,让这一阶段的学生乐思、乐学、乐问,这样才可能培养出善思、善学、善问的优秀公民。从部分学校开展哲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来看,倡导以“哲思”为特质的学科教学,以“学科渗透”的形式开展行动研究,不但能够引发课堂教学的深刻变革,而且有可能打造富有智慧的哲思型教师和哲思型学校。
从理论上讲,学校教育的根本问题包括“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三个方面,而一旦落实到不同的学科教学,则细化转换为“教什么”“怎么教”和“为谁教”三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从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来看,一线教师要想弄清楚“教什么”“怎么教”和“为谁教”,最可行、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回到国家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并对与之配套的各类教材尤其是教科书进行深度解读和加工。只有这样,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才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真正做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学生才有可能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真正做到“用教材学而不是学教材”。
为了更具体地探讨“学科教学渗透哲学教育”的哲思意义与启蒙价值,我们不妨回到本文第三部分中点评过的“小画家”那一课,对那节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和论证。经检索发现,《教室里静极了》所讲的“小画家”那篇课文,本来的标题是“雪地里的小画家”,现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版)一年级小学语文上册第12课的内容,原文如下:
下雪啦,下雪啦!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小鸡画竹叶,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枫叶,小马画月牙。
不用颜料不用笔,几步就成一幅画。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他在洞里睡着啦。
作为一首儿童诗,这篇课文不但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而且非常生动地讲述了四种动物爪(蹄)的形状和青蛙冬眠的自然属性,富有童真和童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首诗中既有拟人化的文学表达,又有科学知识的设问与导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自觉地在文学修辞和科学启蒙之间进行灵活、适度的切换,才有可能兼顾儿童诗性思维和求真思维的协调发展,而一不小心,把握不好分寸,就有可能压抑学生的想象力和好奇心。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的核心品质是“实事求是”“滴水不漏”,所追求的是“铁板钉钉”“准确无误”,而文学构思的显著特征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所推崇的逻辑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就《教室里静极了》这个教学故事而言,教师的根本“失误”在于忽视了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水平,自以为是而又非常突兀地抛出了“冷血动物”“冬眠”之类的生物学名词(概念)。
正常情况下,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只要是具有教师资格而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都拥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方面的一般性知识,也都有自己特定的专业(学科)背景。总体而言,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以学科知识为主的本体性知识、以教育学和心理学为主的条件性知识以及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所需要的实践性知识三部分组成。但是,我们在推进儿童哲学教育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知识本身的深度与广度,包括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的熟练程度,尚不尽人意,尤其是在知识的分科教学和综合运用方面,不少教师会有力不从心的表现。从科学教育的角度来讲,《雪地里的小画家》这首儿童诗确实比较自然地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科学问题,可以很好地调动小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何打通诗性思维和求真思维之间的逻辑通道,如何结合诗歌讲好“冬眠”“冷血动物”之类的科学概念,如何恰到好处地“点拨”或“留白”,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于一个优秀教师而言,通过一门学科教学可以传授多门学科知识,利用一间学科教室可以实现多重教育功能。显然,《雪地里的小画家》这首儿童诗,不同的语文教师会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而且不同的科学教师来教这首诗,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也会有诸多不同。而这些不同教学方法恰恰展示了不同教师的专业功底和教育教学智慧。“智慧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手段和目的,教育对智慧具有内在性和必然性要求。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教师,不能没有智慧,智慧是教师职业的灵魂和魅力。”[7]因此,近年来,教育学界越来越强调大主题教学和跨学科教学,越来越重视智慧教师培养和智慧教室建设,而且也正是在建设和使用智慧教室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它的多重育人价值与功能。
六、守望:一批爱哲学的一线教师
没有智慧的教师,何来智慧的课堂?没有智慧的课堂,何来智慧的少年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需要一门又一门精品课程,需要一间又一间智慧教室,更需要一批又一批爱学哲学、爱讲哲学、爱用哲学的智慧型教师。这类教师的显著特点是勇于“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因而可称为“批判反思型教师”(reflective teachers)。在“批判反思型教师”的眼中,每个教师的教学都不一定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每个学生也不一定像教师想象的那样喜欢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我们常说“教育即启蒙”“教育即唤醒”,但启蒙和唤醒的前提是教师自身成为热爱教育智慧、追求教育智慧、拥有教育智慧的人。“通览教育史,每个生生不息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智慧,都有许多关于教育智慧和智慧教育的故事代代传承。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同样积累了丰富璀璨的教育智慧。这些以故事、对话、格言、语录、史料等形式存在的教育智慧,对于今天的教师而言,显然是无价之宝,理当充分开发和利用。”[7]
哲学常常被定义为一门“爱智慧”的学问,哲学也常常被视为教育的一般理论。一线教师对于哲学的热爱,其实就是对于教育智慧的热爱。严格来讲,一个爱哲学的一线教师的第一要务,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去学习或讲解某个哲学观点或某种哲学流派,而是要在不断反思个人专业实践(向经验讨教)的基础上,坚持专业阅读(向大师讨教)、专业交往(向同行讨教)和专业写作(向自己讨教),将自己“修炼”成为一名有哲学功底、有哲学素养、有哲学眼光的智慧型教师。正如朱小蔓教授所言:“教育智慧是优秀教师内在的秉性、学识、情感、精神等个人独具性格化的东西在特定的情境下向外的喷涌和投射。”“智慧型教师那临场的天赋、即席的创作、完美的应答以及润物而细无声的绝妙,是孩子们成长的福音。”[8]
就在本文即将杀青之际,《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9]
近日,福州8岁的二年级男孩小冯发现,课文《羿射九日》中前一段刚提到“江河里的水被蒸干了”,下一段又提到“他蹚过九十九条大河,来到东海边”。因此他质疑道:“既然晒干了,那后羿是怎么蹚的?是不是课文出错了?”
对于这个男孩的发现与质疑,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微博发文称:
这个孩子敢于质疑,能够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联系上下文,“蹚”字的确用得不恰当。教材编写组正在认真研究,会对教材进行适当修改,下个版本的教材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出现这种逻辑错误,确实非常尴尬,不仅人教社、教材编审者难辞其咎,一线(语文)教师也需要认真反思。课本中的问题由一个8岁的孩子首先指出,让我们见证了小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但相比较而言,一线教师却稍显迟钝而“慢了一拍”。其实,这则新闻不仅凸显了语文教材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他学科教材的尴尬。好在,“羿射九日”属于古代神话,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会信以为真。更尴尬、更危险的是,当前的教材中依然有不少虚构的故事被当成事实,依然存在牵强附会的心灵鸡汤以及似是而非的德育案例。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方案中,没有哲学教育方面的明确规定和要求,因而在中小幼学校中,主动给学生讲哲学、自觉与学生聊哲学或跟学生一起做哲学的教师非常少。而事实上,不论是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还是中小学各科的课堂教学,都可以和哲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也都需要逻辑层面、价值层面和审美层面的关照与引领。当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哲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像哲学家一样”质疑、探究、辩驳和论证,而不是要开设一般意义上的讲授哲学知识的哲学课。从“学科教学渗透哲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教师必须深入思考所教学科的本质特征,必须深入研究所教学科与哲学的历史渊源,以便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学科知识的情境性、相对性与不完整性——并非所有问题都有明确无误的标准答案,相反,很多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坚持联系、发展和辩证的观点。
近年来,在网络上乃至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人开玩笑说:你的语文(数学、外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吗?有意无意地将各个学科的教学问题“推脱给了”体育老师。不难发现,本文则将解决各个学科教学问题的重担“托付给了”那些爱哲学的一线教师。“我们会记住我们喜爱和憎恨的教师,我们会模仿那些让我们敬佩的教师,我们呼唤那些在早年生活中就学到的价值观——对别人、对更广泛的社会应该负有什么责任。”[10]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赞叹说:你的体育是哲学老师教的吗?你们学校的语文(数学、外语……)课好有哲学的味道!而那一天真正到来时,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堂教学改革,肯定又找到了一种颇有新意而又富有成效的重要举措,甚至在我们国家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乃至在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课程方案中,都已对哲学教育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