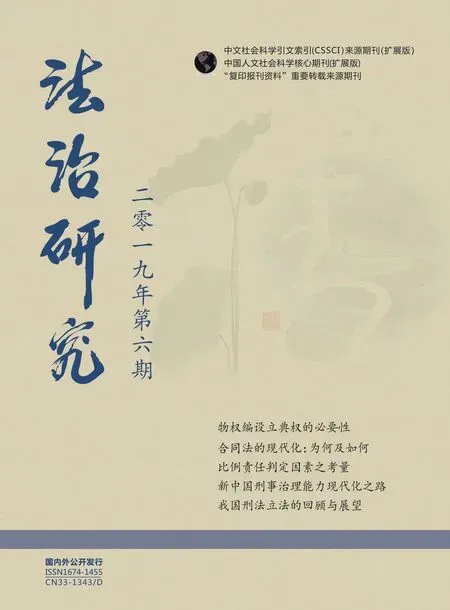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其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之协调
赵泽君
一、引言
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承认公民对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信息有权接触而政府对这种接触请求权有答复义务的制度。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在我国,80%的社会信息由政府管理,政府是信息的主要生产者、使用者、发布者以及管理者。《旧条例》实施十余年来,不断遇到新问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对公开的范围、公开的义务主体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常常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应当公开的信息和公开的方式引起争议。有鉴于此,国务院于2017年6月6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9年4月13日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与《旧条例》比较,《新条例》的内容更加细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仍然存在和暴露出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其中涉及信息公开与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就不仅需要对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问题、产生原因及其完善的路径进行反思,而且需要协调其与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之间的关系。
二、对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现状、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梳理
(一)对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现状的梳理
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最早始于观念比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之后由点到面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汕头市政务信息公开规定》于2003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深圳市行政机关政务公开暂行规定》于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于2004年1月20日发布;《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于2004年5月1日实施;《杭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于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他各地也紧随其后在本行政区域内陆续出台了此类规章制度。
各具地方特色的省、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其实践探索,对国务院2007年1月17日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到了促进作用。《旧条例》分5章,共38条,包括总则、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以及附则。其中,有三项主要制度,即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制度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和保障制度得到了确立。尽管《旧条例》界定了政府信息、确立了申请公开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及其职责,也规定了公开的范围和公开的程序以及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但在实施中暴露出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申请公开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不明确、公开的范围不够具体以及“答非所问”变相回避公开内容等问题。这反映出《旧条例》本身存在较大问题。①王万华:《开放政府与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内容定位》,载《北方法学》2016 年第 6 期。
为此,国务院在2017年6月6日公布了《修订草案》,经过近两年的酝酿,终于在2019年4月13日通过了《新条例》。《新条例》亮点颇多,主要有:
第一,降低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门槛。《旧条例》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主体时,又规定了“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的“三需要”门槛,客观上提升了申请信息公开的条件。为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新条例》第13条取消了依申请公开的“三需要”门槛,降低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条件。
第二,扩大了主动公开的范围。《新条例》在列举的应主动公开的信息中除了保留《旧条例》中原列举的11项内容外,又增加了4项,即共15项。②参见《旧条例》第10条,《新信息公开条例》第20条。不仅如此,《新条例》还建立了逐步扩大主动公开信息范围的新机制,这包括:信息公开动态调整机制,即对原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情势变化而的,应当公开;③参见《新条例》第18条。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机制,即多个申请人可以建议行政机关将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纳入主动公开的范围等。④参见《新条例》第44条。
第三,增加了信息公开的方式并强化了互联网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地位。从近几年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看,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方式较为单一和互联网形同虚设。与我国相比较,政府信息公开在国外已实践多年,尤其是信息公开比较成熟的美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息公开网络技术平台体系。⑤1994年 6月,美国政府创立了 GPO ACCESS,为美国公众提供在线政府信息资料库、寄存图书馆的免费馆藏、联邦机构的档案及法律文献等政府信息,成为美国最大的、用户访问频次最高的政府信息网站。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众在线检索和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了便利,2004年12月《美国政府出版物目录月刊》保留了网络版并纳入了《美国政府出版物目录》 (Catalog of U.S.Government Publications)。参见张新民、罗贤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发展现状与展望》,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6期。为了实现信息公开便利化,我国政府的各个部门纷纷设立了网站,但政府上网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很多政府网站形同虚设;相当数量的政府网站只是把一些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条文搬到网上;公开的信息数量少,实用性不强;有的网站成为“作秀”工程,没有具体信息;公开内容不具体、不完整或答非所问等。针对上述情况,《新条例》从政府信息发布机制角度,规定可以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公开信息,并专条规定在政府信息公开中需强化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⑥参见《新条例》第8条、第23条和第24条。
此外,《新条例》完善了信息公开的程序性规定,⑦参见《新条例》第51条。并规定行政机关需要为申请和查阅信息的申请人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便民措施。⑧参见《新条例》第25条。
(二)对《新条例》存在问题的梳理
第一,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不明确且范围狭窄。
在我国,有权申请信息公开的主体为“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非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是否有权申请,并不明确。⑨《新条例》第27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国外相关信息公开立法对申请信息的主体资格不加限制,比如美国于1966年制定的《信息公开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括个人(包括外国公民)、合伙、公司、协会、外国与国内的政府机关等。”⑩周汉华主编:《外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可见,美国立法对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没有资格上的限制。在加拿大,有权接触信息的主体范围也很大,包括加拿大公民以及永久性难民,只要其在提出申请时和给予接触信息时同时自然地存在于加拿大就可成为接触信息的申请人,之后又扩大为:出现在加拿大的个人和公司。⑪赵泽君:《中国与加拿大信息公开制度之比较——兼论我国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的完善》,载田平安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论丛(2009年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的国家还包括:韩国、日本、英国、荷兰等。⑫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第6条:人民有权请求公开信息。日本《信息公开法》第 3 条规定请求权人可以是任何人,既可以是日本国民,也可以是外国人。参见日本《信息公开法》第3条关于“公开请求权”的说明。英国《信息公开法》第1条:任何人均有权请求行政机关公开信息。荷兰《政府信息法》第3条:任何人均可以向有关负责的行政当局、机构、服务部门或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查阅与行政事务有关的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
第二,公开信息的义务主体范围狭窄,且在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程序救济方面改进不大,甚至有退化之虞。
我国《新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由于此规定没有对行政机关进行界定,因此,通常的解读是此处的行政机关应当是各级人民政府,亦即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一些具有公共管理职责的单位。但是,依据我国当前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下属的各单位、公司以及一些国有垄断性行业,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电信、供电以及供水等有一定行政性权利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是否有义务公开信息,《旧条例》并不明确,只规定参照执行,⑬参见《旧条例》第37条。而《新条例》将此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事项,交由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文件进行调整,不再参照适用《新条例》,并且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在未能获取信息时如何进行救济的规则,但该条规定只是赋予了申请人对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行为不服的申诉权,而未规定诉讼权。⑭参见《新信息公开条例》第55条。有鉴于此,《新条例》在对申请人获取信息的诉讼程序保障方面不仅改进不大,而且有退化之虞。⑮有学者曾就《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单位信息公开问题就担心有“脱条例化”之险,最终可能会变得“无法可依”。参见彭錞:《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现实、理想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与国外信息公开制度比较,我国公开信息的义务主体范围狭窄。而国外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不仅广泛、明确,而且一般是以列举的方式作出规定。英国2005年实施的《信息自由法》不仅界定了公共机构,并且在目录明细中对公共机构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其公共机构包括中央和地方议会、政府、全国卫生机构、教育机构及接受国家资助的学校、半官方机构和国有企业。⑯张红菊:《英国信息公开制度及其特点》,载《中国监察》2009 年第 2 期。在美国,“信息自由法适用于联邦政府行政机关所拥有的文件。行政机关包括总统行政办公室,内阁各部,军事部门,政府控股公司,独立管制机构以及行政部门设立的其它公营部门”,⑰周汉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3期。但司法机关、私人企业、联邦政府的合同方或受资助方等则不包含在内。在加拿大,披露信息的主体是管理信息的政府机构及其代理机构,其行政机构所涉及的公开义务主体的范围十分广泛。韩国《信息公开法》把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规定为:“国家行政机关、政府投资机关、地方自治团体和其他总统令里规定的机关”,⑱参见韩国《信息公开法》第 2 条中对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说明。还包括“立法机关(国会)、司法机关(大法院、宪法法院等)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等公共机关”。⑲参见韩国《信息公开法》第 5 章补充规则中对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说明。在日本,根据其《信息公开法》第2条、第3条和第8条的规定,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一般行政机关,是指在内阁中设置的机关以及由内阁管辖的机关;第二类是特殊机关,包括府、省、厅、委员省厅直属的机关(比如警察厅、检察院、国立大学)等;第三类会计检察院也属于行政机关。⑳参见常锐:《韩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6期。
第三,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且公开的信息内容存在矛盾。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公开原则写入了《新条例》第5条,并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细化和增加,具体包括: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依法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涉及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的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21]参见《新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16条。很显然,政府信息更加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限很大。
不仅如此,从我国《新条例》的内容中可以发现,公开的信息内容也存在一定矛盾。该条例对应公开的事项作出了列举式规定,[22]参见《新条例》第19条、第20条、第21条。而对不予公开的事项虽然作出了细化,但弹性较大,比如“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23]参见《新条例》第16条。此种列举式规定应公开的事项而弹性地规定不予公开事项的立法模式,预示着可以自由裁量不公开未列举的事项。其结果就会在具体适用中出现矛盾,并且容易引起争议,即在倡导公开政府信息的同时,又为行政机关自由选择不愿公开的信息留下了余地。
与我国相比,因为国外只是从概念角度对公开的信息进行界定,且列举式地规定了不予公开信息的例外,因此,其公开信息的范围比我国公开的范围大得多。比如,在加拿大,接触信息是原则,豁免接触信息是例外,并且必须限定于成文法具体列举的范畴内。[24]加拿大《接触信息权法》第13至26条列举式地规定了不予公开的事项,即除了不予公开的事项,其他事项必须一概公开。参见Canada(Information Commissioner)v.Canada(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1986]3 F.C.63( T.D.)at 69.因此,在加拿大,除了少数信息诸如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外,其他信息均应当公开。不仅如此,在加拿大,对是否应该豁免而发生诉讼,法院对豁免只作限制性解释并且存在回旋余地时,则倾向披露信息而非拒绝披露信息一边。[25]Rubin v.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1988) ,52D.L.R.(4th) 671 (Fed.C.A.) at678;Canadi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arities v.Canada (Minister of Finance) ,(1999) 4F.C.245 (T.D.) at256,additional reasons [1999] 4C.T.C.45 (Fed.T.D.) .
此外,实践中政府公开的信息存在“答非所问”的现象使信息公开制度流于表面化、形式化,由此造成在实践中除了政府通过媒体或者诸如发布公告、布告等方式主动公开信息外,通常情况下申请人通过申请获得信息公开的目的,不容易得到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践效果与公众的愿望如此悬殊,难怪公众对通过信息公开行使参政、议政以及监督政府的权利并不十分关心。对此,不论是《新条例》,还是《旧条例》都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
(三)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1.对政府信息的最终归属权在观念上存在误区且对公开政府信息的作用认识不足
作为由少数人组成的管理社会的政府在其产生、管理以及使用信息中所具有的独立性,使得人们在观念上往往错误地把此类信息的所有权归于政府,并把公开信息的决定权也理所当然地交给了政府。这其实属于人们在观念上的一种误区,在政府具体运作中产生、管理的信息的最终归属权应该属于公民。这是因为政府是从社会中产生,政府信息是公民授权政府在管理社会中产生的,信息本身也是来自于社会和公民,公民理应具有获得此类信息的权利。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有较大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人们对信息公开所具有的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腐败等重要作用仍认识不足。这就导致了信息公开效果不尽如人意,并造成一些非保密文件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及时获取,最终使公民真正想了解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仍是困难重重。
2.信息公开不是从权利与义务角度作出的规定且缺乏责任追究机制
虽然公开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但其既是政府部门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信息的权利。目前的信息公开不是从政府部门履行义务和实现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权利的角度进行的,而是权力主导下以满足行政需要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行政活动。因此,信息公开似乎不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没有对违反或变相违反信息公开制度的责任追究机制。实践证明,缺少责任追究机制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效果会严重受损。《新条例》对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或者“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所规定的责任追究机制,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和制裁追究过于粗疏,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利用率也很低,因为大多数民众对此救济手段不熟悉且所花成本高、时间也长。[26]参见《新条例》第47条和第51条。
尽管《新条例》第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但由于在许多政府部门内缺乏专门的机构来承担政府信息公开的统一规划、部署以及管理,而是由政府中某个部门的人员进行兼职。这也是导致我国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出现各种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对完善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思考
(一)总体构想
1.转变观念
信息公开比较成熟的国家通常从公民权利与政府义务相结合的角度,既规定公民有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又规定政府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在我国,由于当前人们在信息公开的观念上还存在着误区或偏差,《新条例》所确立的信息公开是以权力为核心而非以权利为核心,即是否公布信息、在多大尺度上公开以及如何公开是由政府掌控。此种现象“反映了行政公开浓厚的政策性,具有浓厚的清官意识和不确定性”。[27]皮纯协、刘飞宇:《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与走向》,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因此,此种以政府权力为核心的立法特质与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信息公开的现代观念是相悖的,必须转变。
2.改变我国一贯在制定规则时采取的宜粗不宜细做法
我国有许多有关信息安全权的法律和法规,主要分三个层级:国家根本大法即《宪法》;宪法性法律即《保密法》;行政性法律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和法规均规定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信息安全的义务,而《新条例》第14条也规定:“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换言之,不予公开是解决《新条例》与《保密法》等相关规定冲突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国家秘密、信息安全等与信息公开之间的界限含糊不清。因此,相关法律和法规应该细化信息保护与信息公开之间的界限,并在涉及不予公开信息的类型和具体事项时应尽量明确、具体,避免政府机关以此为借口封锁信息。
3.提高信息公开制度立法的法律地位
就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位阶而言,许多国家尽管也经历了循序渐进的道路,但为了满足民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目前都是由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我国的《新条例》只是一个规定,这势必会影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应提升这部条例的立法层次,在现有的基础上,制定我国的《信息公开法》。同时,国家在制定《信息公开法》时应当与修改《保密法》或者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规定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有利于协调其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关系,而且有利于促进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
(二)具体建议
1.放弃对申请信息公开权利主体资格的限制
各国对于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资格的立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资格不作限制,无论是对本国公民、组织还是对外国公民、组织均采取无差别对待;对申请公开信息的目的没有限制,不论是为了商业之用、学术研究还是为了诉讼之用,均不受影响。[28]张明杰:《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8页。由此看来,对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不作限制是一种趋势。为了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正常行使和在一定范围内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针对我国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不明确和范围狭窄的弊端,未来的应然之举是放弃对申请信息公开权利主体资格的限制。
2.明确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并适当扩大其范围
不论是英美国家,还是韩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其立法所确立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明确、范围广泛,不仅包括了行政机关,也包括了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公共事业单位。我国《旧条例》第2条不仅没有对行政机关进行界定,而且根据其37条,对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所作出的是“参照本条例执行”,[29]参见《旧条例》第37条规定“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使得有一定行政性权利的企事业单位是否有义务公开信息,很不明确。更重要的,修改后的《新条例》删除了“参照执行”,将其改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并授权“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定专门的规定”。[30]参见《新条例》第55条。这种“脱条例化”改革切断了行政主体和非行政主体信息公开制度之间的连接点,并非是推进我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正确方向。[31]彭錞:《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现实、理想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过去10年对第37条的落实情况不理想,并非因为“参照执行”使相关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单位负担过重,恰恰相反,“参照执行”此种不明确的规定造成了实践中的做法并不一致。因此,正确的变革应该是明确把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适用《新条例》的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
3.对信息公开的内容采取概括加例外的方法
如前所述,对应予公开的信息采取概括性界定而对不予公开的信息采取列举细化是国外通常的做法。此种做法有利于扩大应予公开信息的范围。针对我国公开的信息内容存在矛盾和只是概括性地增加、细化了不予公开事项的做法而容易在实施中引起争议并可能出现为行政机关对不想对外公开的信息流下余地等弊端,我国应该增加信息公开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做法是,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应采取概括加例外的方法,即对应公开的信息应采取概括性界定,对不予公开的信息应该列举,而不是相反。
4.建立统一集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体系和统一的网络服务平台
政府的大部分信息被置于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状态是我国当下信息公开的主要特点。许多处于闲置或者半闲置状态的信息公开网站,没有发挥出信息服务的功能,有的网站变成了标榜政绩的“面子工程”。
而国外关于信息公开的法律,经历了漫长而又循序渐进的道路,特别是美国在行政立法方面是较早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国家。美国的信息公开立法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系统的政府信息数据库、政府出版物国家书目库、各联邦政府机构的信息目录及其检索、查阅平台愈来愈健全。为了节省费用、提高效率,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该与时俱进,不仅需要赋予电子信息与纸质信息相同的地位,而且应该在整个行政体系内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其网络服务平台。
四、信息公开制度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之关系及其协调
(一)信息公开制度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之关系
1.域外国家信息公开与证据开示程序关系之解读
按照英美国家的解释,证据开示程序是民事诉讼当事人获取和持有与案件有关情报的方法,[32]Jack H.Friedenthel,Mary Kay,Arthur R.Miller,Civil Procedure,Second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378~379 (1993).其设立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来确定争点、排除无争议的事项进入诉讼以及实现集中审理,更重要的是,授权当事人通过对方当事人获取证据,从而使当事人参与诉讼更具实质意义。
实际上,依据相关信息公开制度获取的信息不同于依据证据开示程序获得的书证信息。提出信息申请可以根据任何理由,也可以没有任何理由,而申请证据开示必须有一定的理由和条件,此其一。其二,法律依据不同:申请政府信息的依据是调整信息公开的行政性法律制度,而申请证据开示的法律是诉讼制度。其三,两者的目的不同:信息权法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获得所需信息以实现实质性地参与民主进程和保障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对公民负责。[33]Per laForest J.in Dagg v.Canada (Minister of Finance),2S.C.R.403 at para.61.最后,获取的方法不同:公众获得政府信息有例外,但例外是有限的、具体的以及对是否公开的裁决应独立于政府进行复查,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或者证人签发传票获取文书而不需要依据有关信息公开法或隐私权法获取。
虽然申请信息公开不同于申请证据开示,但当事人依据相关信息公开法律提出信息申请,有助于其获取诉讼中的文书证据资料,而且信息公开程度影响着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这是因为:
其一,在当事人无法依据证据开示程序获取与诉讼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依据相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来获取政府记录和信息作为证据应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民事与刑事诉讼实践中,信息申请者往往能够成功地以信息自由法的手段来代替或者补充证据开示程序。”[34]同注⑰。在加拿大,若没有相反的规定,依据有关信息公开法律所获取的信息不只限于证据开示程序中的记载资料。[35]The Litigator’s Use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Holly Harris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Canada.
其二,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在主体上适用于所有公民或法人,不只限于诉讼过程中的法院、当事人及其律师,在适用时间上不仅可以适用在诉讼之前,也可以适用于诉讼中。与此不同,证据开示程序仅适用于诉讼中法院、当事人及其律师。加拿大与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一样,虽然允许潜在的当事人在起诉前通过申请证据开示获取信息资料以备起诉之用,但适用诉前证据开示程序是有限的,即诉前证据开示程序不是被用来作为一种确定诉讼案件是否存在的手段,而是其只有在确定诉讼可以成立的前提下才能适用。[36]In Benner v.Walker Ambulance Co.,118 Ohio App.3d 341,692N.E.2d 1053 (1997).
其三,依据信息公开法律所获取的信息是政府机构控制和管理的信息,证据开示程序仅仅向对方当事人和第三人获取其所掌握的与案件相关联的信息资料。因此,如果当事人所要获取的信息,不在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掌控,或者虽在其掌握而基于豁免权不愿开示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依据相关的信息公开法获取该信息。
最后,由于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政府工作,使其更有效、更民主和更负责任,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扩大是一种立法趋势和潮流。比如,加拿大《接触信息权法》第25条就体现了这种立法精神:“不论本法是否有其他规定,在政府机构负责人收到申请接触依据本法规定的档案且因该档案所包含信息或其他材料而有权拒绝披露该档案时,该机构负责人应披露档案中未包含且可以合理地与所包含的上述信息或材料进行分割的档案部分”。也就是说,加拿大信息公开程度较高,虽然部分记录免于披露,但“可以合理分割”的部分必须披露。这无疑有助于扩展和提升当事人证据收集的渠道和能力。
2.我国的信息公开与证据交换关系之解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提供证据,[37]参见《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61条对诉讼代理人收集调查证据权利作出了规定,即“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但上述两条均未具体规定诉讼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底如何行使收集和调查证据的权利,因此,此类规定实际上没有完全被“激活”。
为了增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确立了“证据交换”。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9条和第103条对证据交换又作了修改。证据交换制度是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一种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是当事人行使收集证据权的重要制度。差异在于,证据交换制度没有规定强制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开示其所持有证据的内容。很显然,我国证据交换所具有的收集证据的功能是有限的,当事人享有的取证权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被“弱化”的状态。
不难发现,《新条例》所确立的信息公开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一,两者的目的不同。信息公开制度,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了获取政府信息资源的机会和途径,促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规范和加大政府行政工作的透明度,又促进了公民知情权得以实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证据交换程序的目的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能力与责任、抑制庭审突袭、强化庭审功能以及提高庭审效率。其二,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信息公开制度属于法律制度;证据交换程序属于诉讼制度。其三,两者的适用对象不同。信息公开制度适用于所有公民或法人,不只限于诉讼过程中的法院、当事人及其律师;而证据交换只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只适用于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其四,获取信息的来源不同。通过信息公开制度获取的信息,只能是向生产、掌握和管理信息的政府等机构申请;而通过证据交换获取信息,只能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获取。其五,获取信息的范围不同。根据公民或法人可以申请接触除不予公开以外的所有政府等机构所掌握的信息;而证据交换所获取的信息只能是与诉讼标的或诉讼争议有关的信息。最后,通过信息公开制度和证据交换制度获取信息的程序、限制以及救济途径等也存在很大差异。
尽管信息公开制度与民事诉讼中证据交换制度在立法目的、性质、信息来源以及获取信息的程序等方面存在不同,但信息公开程度与当事人证据收集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条例》有助于诉讼当事人从行政机关等机构收集证据,反过来又促进了证据交换。与其他国家比较,由于我国《新条例》本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这些并不利于改善我国当事人证据收集能力。
(二)未来对我国《新条例》的修改及其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的协调
从完善我国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的视角看,未来修改我国《新条例》时如何协调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之间关系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其一,有必要制定《信息公开法》并对政府信息的表现形式、信息公开范围以及信息公开与豁免之间的界限作进一步的界定。
在我国,究竟什么是政府信息?政府信息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如何界定和协调信息公开与豁免之间的界限等?这些基本问题在理论上仍然不是十分明确。
我国《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但是,该条未明确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职能弱化和当事人取证权利虚化的情况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收集与案件争议有关的政府信息时,很难避免政府机关以此为借口封锁信息,或者更有甚者为了使文件难以被发现或为了否决申请人获得文件而可能出现故意毁损、改变或隐匿记录的情况。我国学界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论述中,大多数学者主张,除了法律规定保密信息以外的所有信息均应一律公开。然而,此种观点仍然没有回答究竟哪些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哪些政府信息,[38]韩大元、杨士林:《论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制度》,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特别是《新条例》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细化和增加了的情况下,针对政府信息的表现形式、公开信息的范围问题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强化和扩大对拒绝公开信息的行为进行司法救济,在理论上需要作出回应。从此角度而言,至少《新条例》不应该让公共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密切相关的信息公开行为豁免司法审查。[39]其实,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已有大量案例认可了对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行为不服,申请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外,为了有效保障公民申请信息公开权,民众要树立权利意识,立法应该对政府等有关单位不履行公开信息义务的行为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而司法监督机制尤其重要。
其二,有必要修改《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使其与《新条例》在涉及获取相同信息时能够相互衔接和配合。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对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规定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另一种是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40]参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但《民事诉讼法》对何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何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并未进一步明确。《证据规定》第17条和第15条分别对此进行了解释,即“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主要是指“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等,[4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而“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或者“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民诉法解释》第94条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所作的界定和细化,基本沿用了《证据规定》第17条的规定。《民诉法解释》第96条沿用了《证据规定》第15条的思路,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将“可能有损他人合法权益”修改为“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并增加了“涉及身份关系的”和“涉及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诉讼的公益诉讼的”情形。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法官调查收集证据范围的规定,即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需要的证据的范围”和对于“客观原因”的范围和条件的规定,与我国《新条例》中的某些内容发生抵触和冲突,即我国《新条例》涉及政府机关保存的档案材料有可能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范畴之列,因为当事人或其律师可以据此自行获取此类信息材料,无需申请法院调查。但是,我国信息公开制度才刚刚起步,当行政机构对申请人所请求披露的与诉讼相关的档案信息不予披露时,申请人只能由主管部门提出督促整改或者通报批评或者只能采取投诉、举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43]《新信息公开条例》第47条和第51条。这对在诉讼中当事人而言往往是因时过境迁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最终会导致当事人在收集证据问题上处于两难的境地,即自行收集难和申请法院收集调查难。换言之,我国《新条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目前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这种对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提高只是一种量的改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更何况,依据《新信息公开条例》获取信息的权利属于宪法性权利,即公民的知情权,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证据信息而享有的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属于诉讼权利。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建立比较完备的当事人证据收集机制之前,不能以诉讼中所涉及证据信息可以依据《新条例》获取的信息相同为由,就剥夺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此类信息材料的权利。这就需要修改《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以避免其与《新条例》涉及相同信息时出现理解上的冲突和矛盾。具体修改意见是,在界定“因客观原因”的《证据规定》第17条和《民诉法解释》第94条中增加一款,即不能因为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依据《信息条例》查阅调取而剥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权利。
其三,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是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就信息公开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和调查之关系而言,两者虽然不能等同或互相取代,但正如前文所述,《新条例》确立的信息公开制度有助于减轻当事人收集证据时对法院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会缓解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困难。这是因为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收集证据权受到了限制。因此,为了打破当事人举证对法院的依赖性,扩充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的渠道,修改《新条例》或制定《信息公开法》时需要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从而使立法上所确立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能够被“激活”。
五、结语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既是开放政府的制度基础和发展趋势,也是落实公民知情权此种宪法性权利的必然要求。与域外国家的信息公开制度相比较,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我国信息化发展和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需求的不断增长,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会逐步增加。因此,《新条例》在未来修改时可以先选择性地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然后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公开制度,这是健全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必由之路。
尽管信息公开增强了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与此相关,在收集证据主体上,当事人依赖法院收集证据会逐渐退出历史,即由当事人依赖法院收集证据向当事人拥有独立收集证据权转变,但《新条例》只授权申请人获取行政机关所持有的信息,且我国信息公开程度不高,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和改变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在立法上还缺乏充分的程序性保障,要改变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虚化状态,在收集证据方法和手段上需要实行多元化。因此,为了避免对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客观原因”在理解和适用上发生歧义,立法上应该规定,不得以所需要证据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之列为由而理解为不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畴,从而剥夺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