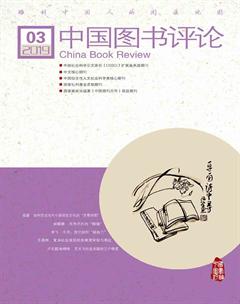“真实眼泪”的戏仿
田争争
套用齐泽克引用拉康时惯常的戏剧化手法,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说:书不存在,因此书评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评论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违章建筑,是在现有的房顶(如果书可以被视作一个合理存在着的建筑的话)之上加盖毫无章法、不堪入目的废料。如果我们将一个文本视作对象的话,那么与它遭遇的过程就是打开一个文本—他者的“真实”存在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本身就处在构成性的悖论中:文本的主体性处于诞生时就注定的缺乏之中,它有待读者参与到其自身的完成中;但同时,对于任何阅读的主体来说,文本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如其所是的现象,它打开了我们与文本之“真实”的遭遇,主体同时又重新将其缝合入象征秩序之中,使其沦为阅读的快感。我们如何可能真正评论一本本身就是未完成的、复合了多重目的,甚至是我们自身主体性之象征秩序投射其上的书呢?
齐泽克的《真实眼泪之可怖》是未完成的,也是不可完成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正如每一本书那样提出了自指涉的、恼人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更重大的秘密在于: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对其写作目的的戏仿。
正如副标题“在理论与后理论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提示我们的,这本著作本身就是齐泽克为“大理论”的合法性所做的(非)辩护。那么问题接踵而至:什么是“大理论”?它对基耶斯洛夫斯基做了什么?是谁在指控它?它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又要齐泽克来辩护?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和诺埃尔·卡罗尔(NoelCarrol)在其《后理论》(PostTheory)一书的导言中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社会批判/文化研究等路子”称为“大理论”。而两位作者试图完成的任务就是用后理论来反对“大理论”,即想要证明,“无须借助统治电影学术界的精神分析框架,照样可以进行研究”[1]。我们不应当怀疑,作为严肃的研究者,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对电影学术界的诸多分析理论(行话)有着充分的理解;也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他们反对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的诸种文化批评体系不过是为了标新立异。那我们如何同情地理解他们拼命树立起“大理论”的靶子(且不论这样的靶子本身是否能站得住脚,这些所谓的“大理论”不曾经也是少数派的理论并被用来反对陈旧的电影分析话语吗?),提出与之不同的分析模式其背后的目的?
不妨先引用一下齐泽克自己在序言中所说的例子:在参加一个关于艺术的圆桌会议时,齐泽克受邀评论一幅第一次见到的绘画。他在毫无感想却又不得不谈些什么的尴尬局面下,说了一堆关于画框的“胡话”:“除了这个眼前可见的画框之外,还有一个由绘画的结构暗示的画框,它框定了我们对绘画的感知,而这两个画框并没有重叠———二者之间被不可见的裂隙所分离。绘画的关键内容并非由它的可见部分所传达,而是在于两个画框之间的这一断裂,处于分离二者的裂隙之中……一旦我们丧失了洞悉这一裂隙的能力,任性的决定性维度就也会丧失……”[2]让齐泽克惊讶的是,这样一番“胡话”竟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并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我再次遭遇的,并不仅仅是胡话产生功效,而是存在于今日文化研究核心之处更彻底的冷漠。”[2]9也许波德维尔等人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大理论的陈词滥调:我们当今的文化研究理论似乎逐渐地失去了其诞生之初对既有话语场域的颠覆和不断解域的作用,反而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批评家们通过不断地写作构建出的“理论场”专注于构建一个坚固的行话体系,不再真正地让主体与作品中所揭示的“真实”发生遭遇。并且进一步地,让波德维尔等人清醒地感到悲哀的(也许是悲哀的?),是大理论对自身的吞噬:大理论曾经作为理论武器,让我们能够反抗资本主义文化所输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它曾经以一个颠覆性的激进姿态暴露出了作为霸权的文化生产体制中仍然有少数派的存在,仍然能在其中看到革命的可能性(女性的、解构的)。然而这样一种曾经刺激了我们对于文化霸权之反抗的激情,如今却吞噬了自身存在的根本理由,代之以学术体系内二律背反式的双重冷漠,对理论的现实和作品及社会的真实同时视而不见。齐泽克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其看似玩笑般的“胡话”就是提醒我们,理论正逐渐失去自身和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一切产品之间的必要裂隙———而这个裂隙,恰恰是理论在诞生之初所要揭示的,也就是其批判功能的核心。
然而当下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为理论做出振聋发聩的呼喊,让我们意识到重新找到这样的裂隙有着如何如何的迫切性———真正的问题远比这样的现象来得复杂。齐泽克同样知道,理论本身有着其独特的场域,我们在理论的场域中使用理论的行话,进行理论自身的生产和增殖,使其成为自身的多重身。然而悖论的是,理论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完成了的主体。在理论的建立过程中,它不得不面临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原初性的缺失:理论本身是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哲学思潮,但在其与具体作品不断嫁接的过程中,面临的是作为理论之存在背景的思想体系和总体语境的必然缺失。文化研究理论的诞生就是一个话语共同体—主体从子宫中(哲学或思想史的潮流和发展脉络)诞生,妄图通过与作品的结合获得关于自身之命名的方式来确定作为主体的自身。然而这样的确定性本身就是对其缺失本质的误认:符号和实在并不重叠;没有一个能指或者现实的客体能够为它带来确定的名称。
那么让齐泽克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并非理论自身的永恒缺乏,恰恰是其与分析对象间的过度自恰。过分自洽意味着,我们的理论生产本身被树立成了一个新的大他者,胁迫着一切批判的范式進入到理论的话语中。因此,齐泽克一番所谓的“胡话”并非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点想法也没有”,而是可以被理解为齐泽克无意识中最想说的那些话。这样的“胡话”正是因为没有迎合理论场的讨论范式,而变成了在艺术批评的共同体中撕开一道裂缝的企图,即对“真实眼泪”的召唤。然而悲哀的是什么呢?任何打开裂隙、让真实遭遇的企图都会瞬间在一个强势的“大理论”话语中被重新缝合,重新回归象征秩序中温软、湿润、安全的领域。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为什么齐泽克要专门选择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作为回应批判的手段。“现实的‘整体是不可能被感知/接受为现实的,因此我们为‘正常地立身现实之中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有一些东西要被排除出现实:原初压抑的空洞必须用幽灵般的幻想来填补或‘缝合。而正是这条裂缝贯穿了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的核心。”[2]95谈到从纪录片转向剧情片的问题时,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被描述。这正是纪录片的最大问题。这就好像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一般……我注意到在拍摄纪录片时,我越想接近一个人,他那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越发消失不见……我可被真实的眼泪吓坏了,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利去拍摄它们。”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的秘密正是现实的不完整性,我们越是试图去理解使现实成为现实的根本核心,我们越是觉得这样的核心不存在,是依靠我们过度的想象来填补、缝合的;而一旦这样的象征界机制缺乏了,真实展现的就是其可怕的入侵者的面目。进一步的,这样的缺乏迫使我们认识到的是真实本身的不真实性:真实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将我们局限在一个当下的、唯一的处境中,真实并没有把其他可能的结果排除,而是把它们作为事件的幽灵缠绕着我们当下这看似唯一的“真实”现实。真实的可怖在于,即便它是如此的真实,但它仍然只是多重可能性中的一种。
我们终于在这样的对比中看到一个同质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大理论与现实经验间断裂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主体无法真正遭遇真实的问题。而其逻辑关联是,二者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后者是理论在理论阐发中对自身的揭露;从写作策略上说,后者正是为了论证前者而写作的。序言里所讨论的是大理论与当代生活的经验之间发生的分裂。齐泽克首先强调了我们当今对二律背反的“冷漠”:“康德走出这一认识论震惊的道路是走向实践理性:一旦我进入伦理行为,我就在实践中解决了二律背反并展现了我的自由意志。今天,我们的经验仍然面对着一套不同的二律背反,但这些二律背反失去了使我们震惊的能力:对立两极就这么简单地共存着。”[2]9为什么我们不再震惊?其理由就在对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的分析中,以一种复调的方式得到了阐发:似乎由精神分析(大理论)所揭示出的二律背反(“真实的眼泪”)就是那个裂隙,就是迫使我们进行缝合的入侵者。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初缺乏,我们因为无法承受“真实”,我们必须依靠缝合的方式在电影中表现一个正常的主体(即便这个主体在面临真实之后不可避免地被其幽灵缠绕着)。如果我们把电影分析中的主体代换为理论,那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齐泽克的策略:甚至我们在使用理论来分析作品的那个时刻开始,理论本身就已经在不断缝合自身与真实的遭遇了;任何借助理论分析作品之真实的企图在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对这一裂隙的缝合。真实的可能性在被打开的同时就不断地在关闭,因此我们才会觉得如今的理论走到了自身的反面,波德维尔等人才会反对这样的大理论而以后理论取而代之,才会发现理论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不可弥合的断裂经验。
那么理论的写作是否可以停止呢?齐泽克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反而是在全书的最后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电影版中,可能性是敞开的。结尾看起来一切都仍然可能,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一切都不再可能。这不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式多重世界的终极悖论的最简洁版本吗?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最终选择(其实是非—选择),不就是在《爱情短片》的两个版本之间的选择吗———是选择已错过的相遇,维持裂缝,还是保持幻象的封闭循环,填补裂缝?”[2]243齐泽克同样把这個问题提给了大理论自身:我们真正拥有的不是在两个版本之间选择的权利(非—选择),也就是说,选择一个直面裂隙的革命性理论或者令人悲哀的缝合裂隙的大理论。不,真正的二律背反从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或此或彼,既非此亦非彼的真正的两难,是无法选择的选择,是与“真实”遭遇时必然面临的两难。那么理论的写作本身就是这样的悖论:理论的写作不能停止,大理论不能被抛弃,但也不能就一直保持现状地使用下去,而唯一能借助的终极策略就是通过使用大理论来分析作品的方式,完成对大理论自身困境的戏仿———一种本雅明所谓卡夫卡笔下桑丘·潘沙式的人物(一位镇定的小丑和笨拙的助手,打发他的骑手冲锋陷阵[3])。齐泽克似乎狡黠地躲在这本未完成的,也无法完成的书的背后,来指使着他的对手们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一切无比严肃地企图摆脱大理论来进行文化研究的努力(“看啊,我不借助大理论,照样能研究!”),都显得像是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注释
[1]大卫·波德维尔与诺埃尔·卡罗尔.“导言”.收入《后理论》(PostTheroy,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6),第xvi页.
[2]齐泽克.真实眼泪之恐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8.
[3]本雅明.弗朗茨·卡夫卡[A].选自本雅明文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7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