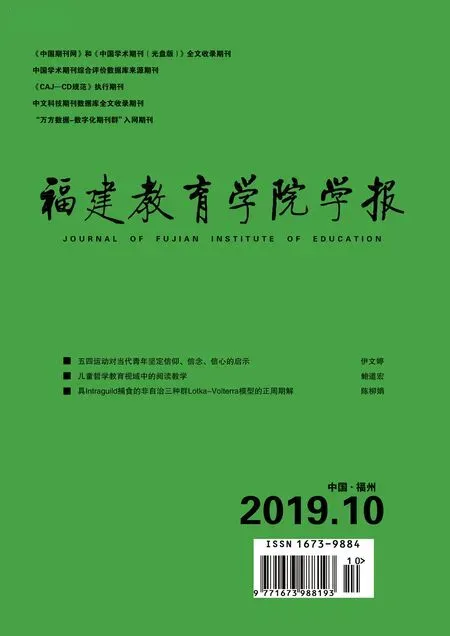生态保护意识:唐禁屠令中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探析
翁洁仪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禁屠令是指统治者在特定的某些日子中,禁止全国百姓宰杀与食用肉类,撒网捕鱼钓虾的强制性政策。唐代禁屠令颁布频繁,每年约近1/3的日子需要“断屠”,政策贯穿唐朝始终。目前对于唐代禁屠令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宗教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或从历史角度对禁屠令的渊源、变化演变、具体内容及实施状况进行分析;以生态环保为角度切入的则多集中于生态平衡、断屠与灾荒之间的关系研究上。本文亦是从生态角度入手,但着重探讨从秦汉时期的“日书”“月令”到唐代“禁屠令”中一脉相传的生态平衡思想;同时从生态与经济角度分析了唐代不同阶段的禁屠令颁布原因。
一、影响唐禁屠令的历史因素
(一)宗教因素及其护生思想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禁止杀生的教义的广泛传播,“禁屠”思想开始逐渐影响国家政策。六朝时期,祈雨仪式中开始出现“禁屠”的身影。文献中最早可见的“禁屠”是在《魏书》卷八《宣武帝纪》的永平二年(509年)五月条:“辛丑,帝以旱故,减膳撤悬,禁断屠杀。”[1]由于北魏宣武帝在位期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于是下令减少膳食和娱乐,并且禁屠。而祈雨仪式流程的正式确立是在隋代,从隋代起,“禁屠”开始成为祈雨仪式中的固定仪式之一。
不仅如此,隋代还将佛教的三长斋月推广至国家层面,成为全国性政策。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下旨:“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其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远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2]即于每年的三长月禁屠,时长为每月八至十五日不等。三长月来源于印度佛教,其把每年的正月、五月和九月看作是万物萌生,成长的关键时段,因而信众应当在三长月的每月前十五日避禁持斋。[3]受到佛教这一护生观念影响的隋代统治者,开始将原本仅需信众践行的禁屠扩大到全国范围。
到了唐代,由于李唐皇室尊崇道家始祖李耳,因而在继承了隋代以来的崇佛禁屠的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地将道教的十斋日融入其中。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初,即颁布断屠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4]除此之外,唐代的禁屠还吸收了儒家思想,在皇家忌日,皇帝诞日、春秋社日等也实行禁屠。
(二)月令与日书及其生态平衡理念
但“禁屠”行为并非外来之物,并非随佛教一同东传而来,而是秦汉时期便已有之,且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宗教性的三长月、十斋日、三元日等没有被推广为全国性的禁屠日,但非宗教性的国家层面的禁屠行为也是存在的,如《魏书》卷八《宣武帝纪》永平二年(509年)十一月条:“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北齐书》卷屯《武成帝纪》河清元年(562年)正月条:“诏断屠杀以顺春令。”其中,顺春令中的春令应该指的是春季的月令,即《月令》中所划分的十二时节,其中孟、仲、季三个时节为一季,每一季中都包含相关的规范和禁忌,将此称为春令、夏令、秋令和冬令。如果春季行春令,则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如果在春季行夏令、秋令、冬令带来天灾人祸的恶果。另外,在在《月令》中也有不杀含孕的记载:“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不仅不能杀已经怀孕的动物,处于幼年的鸟类幼兽也都不能杀。”[5]除月令外,秦汉时期还有把各种事宜按历日进行排列的择日的书——《日书》,该书吸收了天文、历谱、时令、阴阳五行、杂占等知识,形成了一套用以占测吉凶选取时日的习俗,该书中也有在四季固定时间段不可进行屠宰牲畜活动的记载。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
杀忌
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杀,天所以张生时。
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杀,天所以张生时。
秋三月庚辛,不可以杀,天所以张生时。
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杀,天所以张生时。
此皆不可杀,小杀小央,大杀大央。[6]
《日书》与《月令》都是劳动人民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认识并总结出来的自然生长规律,从二者的按时令禁杀,不杀含孕等记载,可以看出它们是与动物的生长周期、四季天时相对照一致的。在生产力较低的社会中,实行“禁杀”“禁屠”是为了利用规律以保护社会再生产,它要求人们根据动物生长规律有节制地宰杀动物,在消费的同时能够保证下一轮的繁衍循环。因其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巩固统治,《月令》开始被上升为“王术”,作为政令及律法推行,如秦简和汉简中出土关于《田律》的简赎中载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惿水不〈泉〉。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谷,毋□□□□□□四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即春二月禁止砍伐山林木材和阻断水流,夏季时禁止取草烧灰作为肥料,禁止取未成熟的荡草,禁杀幼兽和幼鸟,禁毒杀鱼鳖,河海中置网捕鱼要到七月份才能开禁。这体现了四时生杀的思想,脱胎于传统的月令,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与增删的“四时之禁”。
秦汉以后,这些“时禁”思想被历朝历代一脉相承地继承下来,至唐代亦是如此,且与宗教“禁屠”结合起来,如前文引述的武德二年正月时唐高祖颁布的诏令便有对于“月令”与“时禁”的继承,“四时之禁,无伐麛卯。三驱之化,不取前禽。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兹道。朕祗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亭育,无忘鉴寐。殷帝去网,庶踵前修。齐王舍牛,实符本志。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4]显然,“禁屠令”除了受到宗教因素因而影响了具体日期以外,还受到秦汉时期四时生杀思想的影响,以保护动物繁殖与生态平衡。
二、影响唐禁屠令的社会因素
纵观唐代的禁屠政策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禁屠政策的颁布,宗教都并非主要目的,更为主要的是,遵循动物的生长规律,以便根据具体的社会状况来调整动物的数量,恢复与发展生产力。
(一)初唐时期:以唐高祖为例
唐初期,由于唐初战争频繁,先后镇压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王世充、丘师利、辅公袥等起义军及割据势力,杀伤众多,社会动荡,“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7],社会生产力尚未恢复。因此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由于“国初草创,日不暇给”,[8]下令“其祭圆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8]并且说明“待时和年丰,然后克循常理。”[8]即祭祀时改用少牢(羊、猪),而不用太牢(牛、羊、猪)。这是由于牛对于粮食生产及农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因而需要在生产力严重破坏的建国初期,着力保护耕牛的数量,等到经济状况基本能够稳步发展时,再遵循旧礼,恢复用太牢祭祀。
武德元年至武德三年间,禁屠令开始逐渐扩展与固定,由最初的仅祭祀禁屠牛到长时段、多种类的禁屠,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该时期唐朝政府还未能直接有效地控制东部与江南地区,来自东部的粮食无法通过运河输送至长安,[9]因而该时期长安及关中地区缺粮严重,导致该地区粮食价格飞涨,对于初立不久的唐政权危害极大。以武德元年为例,“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10]当时的唐政府已经需要向进关的车马抽取米谷作为关税,才能保证长安军民的粮食需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政府更须保护牲口,以促进生产;禁止饮酒以缓解粮荒、谷价昂贵等问题。唐朝政府在武德二年(619年)开始禁止关中地区的屠宰与饮酒,“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谷不登,市肆腾踊,趋末者众,浮冗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其费,去弊之术,要在权宜。令关内诸州官民,且断屠酤。”[7]并于武德三年(620年)以“非惟务在仁爱,盖亦示之俭约”为由,再次下诏“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更为条式”。”[4]将断屠定为永制。
由此可见,唐初期的禁屠令推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与发展生产力。但由于佛教的三长月的禁屠政策在前代已有实行,已有一定历史基础,因而借宗教之名推行禁屠政策能更好地保障其实施状况,在推行上也能减少阻碍,更有效地保障生产力。
(二)盛唐时期:以唐玄宗为例
玄宗时期是唐代颁布禁屠令最为频繁的时期,多达25道,平均每三年便颁布一道。该时期所颁布的禁屠令开始出现了对具体动物的禁屠,这些动物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日常食物相关的鸡、鸭、鹅、鱼等肉类;一类是祭祀相关的牛、羊、猪;另一类是有助于生产的马、驴、骡等。
首先,对日常事物相关动物的禁屠可能与唐人饮食习惯有关。该时期饮食行业发达,肉类消耗巨大,更衍生出了如运输、屠宰业等一系列产业。[11]盛唐时期,唐代肉市发展迅猛,应运而生了一大批专职屠宰的人员,屠肆繁荣,在武则天时期,便有“屠钓关柝之流,鸣鸡吠犬之伍,集于都邑,盖八万计。”[7]从业人数众多,可见肉类消费之大。日常饮食中,唐人最为喜爱,食用最为频繁的莫过于鸡肉,几乎家家户户均养鸡。[12]玄宗时期,人们对于食用鸡肉的热忱更甚,与酒相配更是常见的食法,从当时的不少诗作中可见一斑:“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13]“檐前举醇醪,灶下烹只鸡”[14];鸡肉亦是普通农家待客的常见肉食:“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14]而南方地区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则以渔为命。淮河、汉中以南的广大区域均是水产资源丰富,“地富鱼为米”[14]的地方,因而鱼虾是该地百姓最主要的饮食。该时期南方地区渔业之发达显示在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大量的劳动者从事渔业以谋生,且分工细致。有专业的捕捞人员,“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15]亦有专门的贩鱼人员“宣城郡当涂民,有刘城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15];第二,捕捞贩鱼业的兴盛孕育出了繁荣的鱼市。南方地区鱼市尤为繁荣,从交通要道,到县邑村野,无不鱼市遍布,江河湖海边更是如此,[16]虚中《泊洞庭》中曾载:“浪没货鱼市,帆高卖酒楼”;第三,鱼类副食品产业发达。捕获量的巨大促进了鱼类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根据前人研究,唐代鱼类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类:鲊、干脍、含肚、海虾子梃及糖蟹等[12]。与此同时,繁荣的鱼市上不仅贩卖新鲜的鱼虾,也出售许多深加工的鱼类产品,如“池州民杨氏,以买鲊为业。”[15]大量的肉类鱼类需求促进了肉市屠肆鱼市的繁荣,但也难以避免鸡鸭鹅鱼虾的大量消耗,打破了自然界的动物数量平衡,进而导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顺应天时”、顺应动物生长规律,有规律地禁屠禁捕,便成为了最有效的保护举措。因而这一时期,禁屠诏令中开始明确指明对日常食物有关的动物的禁屠。正是希望借以佛道教的禁屠护生思想来保障自然平衡不被打破,在遵守动物生长规律的前提下获取饮食资源。
其次,禁止屠杀牛羊猪以祭祀的政策可能是由于天下州县在春、秋社祭中所屠的牛、羊、猪过多。《文献通考》称北魏“孝文时,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头”,分裂时期的北魏尚且如此,何况是已统一全国的唐代!其使用数量可能已造成牲畜供给的巨大危机。但由于祭祀同国家象征相关联,血祭作为国家祭祀的重要仪式,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存在的象征。因而这一政策自推行以来便不断在禁屠与开屠中反复。
最后,对于马、驴、骡的保护可能由于盛唐时期对外战争导致战马消耗大,需要对其保护以便促进数量增长。太宗至玄宗时期虽然是唐代社会经济向上攀升的时期,但并未减少对外征伐。高宗时征吐蕃,武后时征突厥、契丹,皆发大军前往,动辄十数万,战马消耗应不在少数。因而这一时期,对牛马骡的禁屠令中开始出现了违者责罚的内容,先天二年(713年)六月,玄宗颁布“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7]的诏令,唐政府对牛马骡的重视程度开始提高,并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种禁屠动物。断屠政策从劝导转变为了强制性的政策,并且此类政策最后被纳入法律,《唐律》有“牧畜产死失及课不充”或“养疗羸病畜产不如法”等,是官方畜牧业中因负责官员失误而导致官牛、官马死伤的规范;“故杀官私马牛”“杀亲属马牛”[18]等则是以非官方畜产为对象的相关规范。
综上,虽然唐玄宗时期的禁屠政策有部分的确出于宗教目的而颁布,但纵观其所颁布的所有禁屠令可知,不论是对于祭祀禁屠政策的反复摇摆,还是对于具体动物的禁屠,都是以社会资源状况为出发点,以保护动物数量及生产力的。
(三)晚唐时期:以唐宣宗为例
在唐代,牛对于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关系整个国家的存亡,“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19]。不论何种耕作方式都离不开牛耕,在南方更是如此。水田耕作对于牛耕有着更高的要求,其单位面积所需的牛力接近旱田的两倍,[20]“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舆”,[7]牛不仅是重要的农业物资,同时也是常用的交通工具。
唐代始终重视对于耕牛的保护。但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政府的陇右与河西监牧区皆失陷于吐蕃,这不仅导致了战马来源紧缺,更重要的是,监牧区所还饲养有牛与羊等,监牧区一失,官方的畜牧业便难以维持,只能依靠边境地区的畜牧业支持,或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向回纥或吐蕃取得耕牛。这种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愈加严重,如在德宗时期,国内的耕牛仍然可以在区域间流通、相互供应,但到了宝历元年时,已无法从内地取得耕牛,必须取之于“河东、振武、灵盐、夏州”等西北边区,[9]短短四十年间,唐帝国内地已无法自行供给耕牛,畜牧业逐渐式微。
除了畜牧业日渐薄弱外,该时期唐王朝内部农业发展情况亦是每况日下。一方面是由于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对运河的控制与阻碍,导致南北粮食漕运几乎难以展开。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是该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自唐文宗至唐宣宗即位前的19年间,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发生了41次,大大影响了农业发展及粮食生产力;而唐宣宗在位的12年间,饥荒更是成为了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共发生了3次,以湖南地区饥荒最为严重,淮南地区最为频繁,三年间反复发生了两次。①因而恢复农业生产力,确保粮食产量成为了首要问题,耕牛作为“耕之所资”,在畜牧业式微的背景下,更是保护的重点,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的关键物资得以保障,才能确保不论灾年丰年粮食都能稳定生产,不至饥年频发。
因而我们可以在该时期的政策中看出,虽然禁屠政策相较于之前减少许多,颁布的频率也远远低于之前几个时期,近八十年间仅颁布五道禁屠令,但其中就有两条是明令禁止屠牛的,都颁布于唐宣宗时期。分别是大中二年(848年),禁止屠杀耕牛,且重申了屠牛的后果“有牛主自杀牛并盗窃杀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决六十,然后准法科罪”[17];三年后,即“湖南大饥”[10]的大中五年,下令“两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后,三年内不得杀牛享祀合用者,如郊庙享祀合用者,即与诸畜代”,[10]三年间不许杀牛,就是是祭祀这样重要的仪典,也不例外,可见当时耕牛数量紧张的状况。
综上,由禁屠牛政策及屠牛刑责的一再重申,可以看出晚期的唐帝国内部,牛只需求同牛只供应的不平衡,帝国内部无法维持正常的供给量,因此必须以强硬的手段进行保护,只有保护了农业根本——牛,才能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因而晚唐时期的禁屠令已基本同宗教无关,其颁布与推行都是出自生态现状与经济状况的考量。
三、总结
禁屠令并非是宗教独有的产物,它与秦汉时期早已实践的《日书》《月令》中平衡生态,取之有度的思想不谋而合。虽然在唐代,禁屠的日期可能更多地受到了佛道二教的影响,但透过其宗教的外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唐代,基本上所有的禁屠政策都指向一个目的——即保障物种数量。
以此为出发点的政策在唐代不同时期,也常常出现补充、重叠乃至抵触的现象。但不论是补充、重叠还是抵触,都脱离不了现实生态环境乃至经济因素的限制。补充可能是应现实环境所需而增加断屠的时间与地区、断屠的牲畜种类。如初唐时期,由于未有效控制东部与江南地区,关中粮食问题日益严峻,因此需要长时期、多种类地限制祭祀与饮食宰杀牲畜及禁止饮酒。重叠则可能体现了生态平衡破坏之严重或肉类消耗之大急需国家以不断重申政策予以保护,如盛唐时期,居民饮食习惯与饮食行业的兴隆,祭祀的大量消耗以及对外战争的频繁使得政府需要通过禁屠来规范稳定日常饮食、祭祀及战争所需牲畜的基本供需,在消费的同时能够继续保障新一轮的物种繁衍循环;以及安史之乱后,由于唐王朝失去西北畜牧区及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不足,牲畜来源日渐短少,到了晚唐时期已无法维持正常需求的供给量,加之自然灾害与饥荒频发,急需恢复与发展农业,因而需要政府以强硬手段对牛犊耕牛进行保护与断屠。而抵触可能由于根深蒂固的“血祭”思想难以撼动,因而禁屠政策执行不佳。
禁屠政策各有特点,但不离恢复物种平衡,保护其数量的目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业报与杀生关系的思想,宗教氛围浓厚,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禁屠政策,更有助于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②借神力保障政策的效力,有利于政策背后“保护与恢复物种数量”的生态保护思想的实现。因而禁屠令不论是从历史渊源来看,还是从实际实施背景来看,生态平衡都贯穿其始终。
注释:
①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卷八、卷三四至三六;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十七下、卷十八下、卷三十七。
②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一三载:“吴道子画此地狱变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第8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