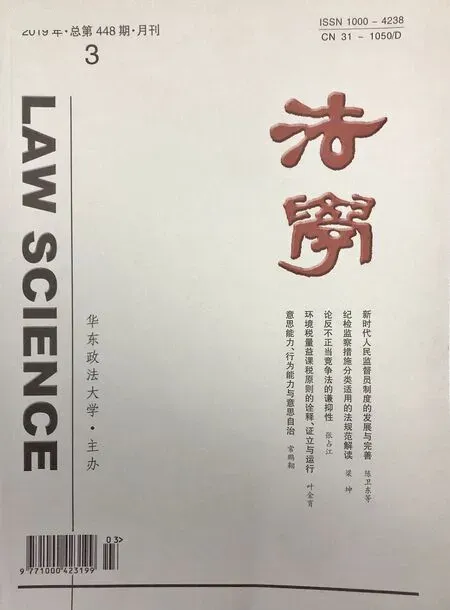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
●张占江
一、问题的提出
“竞争”原则上是私人事务,对其进行干预本属于市场经济的例外,但是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的一般条款在确保规制周延性的同时因适用标准上的模糊,〔1〕依学界通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确定了市场交易行为须遵循之原则,并对“不正当竞争”予以概括界定,称为一般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海带配额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出,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是一般条款的核心,其中“诚实信用原则主要表现为公认的商业道德”。但究竟该如何解释“公认的商业道德”,是采取基于竞争效果本身的解释,还是采取抽象的道德解释,抑或是侧重竞争优势“权利化”的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分歧明显。经常逾越其应有之界限,把正当的竞争行为贴上不正当竞争的“标签”。
(一)不正当竞争认定中的过度干预
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言,依“反法”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思路主要有如下两种:(1)一般竞争利益的权利化,以权利保护的方式适用法律。此点在适用一般条款处理涉互联网的软件干扰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根据法院内部的调研统计数据,从2002~2017年各地法院共审理了大约141件相关案件,自2005年后年均在10件左右。(参见“中国知识产权新年论坛:新反法互联网专条的司法适用”会议,2018年1月27~28日,于北京粤财JW万豪酒店)。法院对这类案件裁判皆以竞争优势受到的损害为论证基础,明显带有权利侵害式侵权认定的痕迹。相关裁判采用权利侵害式的侵权法思维,先确定一种受保护的合法权益,如先论述特定商誉、商业模式(如“免费视频+广告”)等受法律保护,再从权益受损推论侵害行为的不正当性;或者以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作为论证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仅作摆设性、象征性或套路式的论述,对认定其正当性的相关元素并无实质性考量。〔3〕相关分析,参见孔祥俊:《〈民法总则〉新视域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刘维:《论软件干扰行为的竞争法规制——基于裁判模式的观察》,《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周樨平:《竞争法视野中互联网不当干扰行为的判断标准——兼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法学》2015年第5期。法院甚至还发展出专门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强调除非基于公共利益否则不能损害在先经营者之营业利益,并作为一项重要的裁判规则被广泛适用。〔4〕“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最初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审理“百度与360插标不正当竞争案”中提出,强调非因特定公益(如杀毒)的必要,不得直接干预竞争对手的经营行为。(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该原则在之后的系列案件中得到适用,例如,“猎豹浏览器屏蔽优酷网视频广告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3283号民事判决书)和“极路由视频广告屏蔽不正当竞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4)京知民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就备受瞩目的广告屏蔽类案件而言,笔者在威科先行数据库中通过对“广告屏蔽”“屏蔽广告”分别进行标题与全文精确搜索,又在案由为“不正当竞争纠纷”的案例中通过搜索“广告”进行补充检索,共计检索出20份已结案件的司法文书(检索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其中18个案件采用了权利侵害式侵权法思维或者适用“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认定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只有2个案件基于竞争本身的效果通过综合利益衡量认定屏蔽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参见“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0786号民事判决书;“快乐阳光公司诉唯思公司案”,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这等于是将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商业利益在事实上上升为权利加以保护。(2)竞争行为评价道德化,将“搭便车”“不劳而获”作浅层的理解,简单地将其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画等号。〔5〕参见蒋舸:《关于竞争行为正当性评判泛道德化之反思》,《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其实,“模仿是竞争的天然血脉”,〔6〕Bonito Boats,Inc.v.Thunder Craft Boats,Inc.,489 US 141(1989).竞争离不开对他人成果之使用,将“搭便车”“不劳而获”等一般商业伦理观念当成具体判断标准,极易不适当地扩张专有权的范围。而且,注重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判断行为的不正当性还可能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7〕同前注〔5〕,蒋舸文。在与技术有关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被告双方都会高举道德旗帜,〔8〕例如,在广告屏蔽类案件中,被屏蔽方强调其行为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免费视频,而屏蔽方则主张其行为使消费者免受不受欢迎的广告的滋扰。但抽象的道德考量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多数时候,其不过是为公权力偏好干预和管制市场价值的“家长式”情怀提供法律和道义上的支持罢了。〔9〕同前注〔3〕,孔祥俊文。
上述两种思路的共同指向都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将竞争利益权利化等于是将竞争静态化,以保护竞争的名义阻碍竞争,保护了特定竞争者而不适当地限制了不特定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而以道德名义将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还可能增加企业市场行为的风险,于是避免类似行为便成为企业降低风险的唯一路径,最终将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激励,压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空间。
(二)被忽视的“反法”谦抑属性
导致产生上述问题的本因在于理论与实践都严重忽视了“反法”内在的谦抑性。谦抑性最初在刑法领域被反复提及。例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法(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有效的预防或者控制犯罪。”〔10〕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它主要强调在立法环节的去刑罚化和法律实施环节的轻刑罚化。近些年,谦抑性的概念才被明确引入经济法的话语体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作为一种理念的经济法的谦抑性,“是指在自由主义和市场竞争基本假设下的私法能够发生作用的范畴内,经济法应保持必要的谦恭和内敛,让位于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而不轻易使用国家干预,令经济法作为一个补充性和最后手段性的机制而存在,杜绝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泛干预主义’倾向的发生。”在其看来,“谦抑干预应当成为统率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11〕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
在本质上,“反法”是一种对竞争自由的限制,而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效率和繁荣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须保持谦抑,避免将正当的市场行为归入不正当竞争的范畴,故其制度构造源于一种“法无禁止即自由”之理念,围绕限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边界展开,从而为企业在广泛空间内留有竞争自由。针对“反法”一般条款适用标准的不确定性,谦抑性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分析范式。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不正当竞争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是直接论证“行为为什么是不正当的”,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干预的思维,而非在优先考虑“为什么不是”(即竞争冲突的市场可调节性)的基础上再进行判断的谦抑思维,导致了一种盲目的或“家长式”的干预。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拟在弥补这一缺憾,在厘清“反法”介入竞争正当性、合法性基础之前提下,构造一种市场优先的不正当竞争认定理念,以及在比例原则支撑下的不正当竞争认定的技术框架,从而确立“反法”的内在谦抑性。
二、理论基础:法律何以介入竞争
(一)私法自治的保障与限制的均衡
发挥市场经济优势的关键在于确保私法自治。〔12〕参见刘凯湘、张云平:《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分析》,《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从而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证实,保证个人自主决定实现的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制度,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制度;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自主决定是调节经济过程的一种高效手段。〔13〕参见熊丙万:《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竞争自由所强调的竞争不受限制或扭曲,是私法自治所强调的主体“自决性”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延续。不受扭曲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尽管竞争自由不一定在宪法规范上进行直接表述,但其可从基本权利的指导性效力上推导出。基本权利的功能就包括确保经营者自由营业的空间。〔14〕参见[德]罗尔夫·施托贝尔:《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谢立斌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1~116页;[德]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欧洲与德国经济法》,张学哲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作为客观法的基本权利所确立的价值秩序构成了国家各项制度构造必须遵循之原则,〔15〕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这就使得私法自治不仅是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而且统领整体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
但是,绝对的私法自治面临着社会整体正确性之责难,〔16〕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故很难完全得到实现。一方面,竞争天然地蕴含损害竞争(不正当竞争、垄断)的因素,完全自由必然导致对整体秩序的损害;另一方面,自治观念应该是指在完全、充分地意识到所有的可得机会,掌握了所有相关信息,或最一般地说,在偏好形成过程中甚至没有受到任何非法限制的情况下而作出的决定。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这些因素并不一定完全具备,私人决策在多数情形下其实只是无奈和无知之举。也就是说,私法不能不借助于公法而独立存在,〔17〕参见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表面上不受干预的决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决策。故此,法律始终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以私法自治为出发点的同时又尝试对其加以限制;而为了避免过分压缩自由之空间,限制本身同样受到严格之约束。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显然有些操之过急,缺少一种控制干预的机制以确保均衡的实现。
(二)竞争自由与竞争秩序的兼容
政府干预的正当性既在于弥补私法自治之局限,消除不正当竞争及垄断,又在于保障和拓展私法自治。规制法学的旗手桑斯坦(Sunstein)强调,恰当的规制在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同时又增强了行动能力,促进私人的选择。〔18〕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通过规制改变可得机会和信息等限制条件,往往可以改变在不合理条件下形成的私人偏好,从而促进偏好形成过程中的自治。规制在此情形下“不是真的要迫使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反而是通过强制来使他们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9〕同上注,第3页、第56页。德国学者同样也意识到,缺少政府干预因素的支持与补充,私法自治制度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作用。〔20〕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书,第138页。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的规制才属恰当,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从宪法上言,基本权利所确定的行为自由也要受到限制,但只能基于一种更普遍的自由的实现。〔21〕如罗尔斯所言:“限制自由的理由来自自由原则本身。”[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页。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基本权利,无论是基于其他基本权利,还是基于公共利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最终归结于基于实现更普遍的自由。这种更普遍的自由就是经济竞争秩序。因为只有竞争秩序才能赋予所有企业通过与市场兼容的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的机会,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需求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整个社会才能在竞争的推动下不断取得进步。换言之,竞争秩序是所有市场参与者主权(共同利益)实现之基础,它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自由兼容。是故,规制正当性的逻辑阐释为:竞争自由是宪法基本权利及其对行为自由保护的必然结果,反之,只有基于构造竞争秩序实现更普遍的竞争自由,才能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
但在事实上,缺少了政府的介入,竞争秩序也不可能存在。竞争既可提供给每个人在市场中胜出的机会,又可能使其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导致市场主体对竞争的态度充满矛盾,当竞争对己有利时举双手赞成,对己不利时就设法破坏或规避。一旦将构造、维护或服从竞争秩序的愿望留给私人自由决策只会造成混乱无序,只有通过政府对私人行为的谨慎干预才可能实现竞争秩序。〔22〕参见邱本:《论市场竞争法的基础》,《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从整体上看,一来无限制的自由本身就不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很好地实现,二来对自由的限制必须受到严格约束,因为离开对自由的确认和保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机制的实现也就是政府只能基于竞争秩序限制私人的行为自由,或者说,确保私法自治以有利于竞争秩序的方式实现,这正是经济法本身的精髓所在。经济法的特殊价值是整体经济的正确性。〔23〕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书,第28页。
经济法基于竞争秩序才能干预市场主体自由的机理与宪法保留原则一致,使其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民法和经济法在此点上紧密地衔接在了一起。王轶教授强调,唯有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成为民法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根据。它们明确民事主体自由的边界,这个边界同时也是国家可以发动公权干预私人生活的界限。〔24〕参见[英]迈克·费恩塔克:《规制中的公共利益》,戴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6页。
作为一种典型的干预机制,“反法”对特定主体竞争行为的禁止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普遍的竞争自由,而且对特定主体自由的限制只限于保护竞争秩序之需。或者说,只有行为损害了竞争秩序才能纳入“反法”的禁止范围。由此,“反法”的构造一方面是个人以及赋予其权利的私法自治问题,另一方面是作为公共产品的竞争秩序的供给问题。从更一般的角度观察,立法是保障“法治国之自由的一种形式”。只要立法者本身不进行干涉或者不具有干涉的权限,则存在普遍的行动自由,尤其是从事经济活动,创造经济价值以及竞争的自由。〔25〕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书,第217页。在经济法领域,法律保障自由功能的出现远早于其保护基本权利的功能,该功能在实践中被充分遵守,立法者必须作自我克制。政府干预相对于个人自由的整体实现而言,必须处于辅助地位,这不仅是一种对政治道德的要求,而且更多地涉及一个宪法国家的结构性原则,它通过“自由优先于国家的理念而获得正当化”,是“真正的自由”。〔26〕同上注,第218页。
(三)正当性定位:内嵌谦抑属性的法律规制
私法自治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制度,政府干预被限定于弥补私法自治的局限和确保私法自治的实现,或者说,立足于将竞争自由融入竞争秩序的建构。归根到底,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建立在将谦抑品格内在地嵌入其适用逻辑之上。
其一,在任何经济领域都应当优先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或者说竞争秩序受到损害而市场自身无法纠正时,国家干预才具正当性。这样的干预被限定于穷尽市场救济的情形,属于市场调节失效后的“二次调整”,〔27〕同前注〔11〕,刘大洪、段宏磊文。即当一人的行为损害了另一人基于竞争(秩序)享有的利益,而建立在私人自治基础上的机制又失灵时,规制才是必要的。〔28〕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书,第312页。
其二,即使于市场失灵之场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必须适应市场固有之逻辑,旨在恢复而不是取代或颠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29〕或者说,国家的经济干预不是颠覆私法自治的框架。同上注,第219页。于此意义上言,规制是辅助市场发挥作用,故被称为间接干预,以区别于代替市场作出决策的直接管制。沿此逻辑,政府对竞争干预本身只是为竞争创造条件,绝不可厚此薄彼。竞争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就是每个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不受扭曲,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拥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展开竞争和获取竞争收益的权利,这也是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延续。给予在先商业模式权利化的保护而忽略其他不特定经营者的商业创新的权利等于从根本上破坏了竞争。
其三,在既有经验和理性无法判断某一领域的市场是否失灵时,应优先假设市场未发生失灵,暂不进行国家干预。竞争本身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究竟在哪些方面创新、究竟采取怎样的商业模式、究竟谁会胜出等都无法事先作出准确预判。尤其是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的技术与经营上的冲突、对立不可避免,单凭道德直觉难以对其进行评价。在缺乏足够经验和共识的前提下,鲁莽的竞争干预反而可能恶化市场的竞争状况。为了扼守谨慎干预的界限,原告需要承担较高的证明责任,司法者也需要有充分的说理义务。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基本原则的认可导致任何对此原则的偏离都需有足够充分正当的理由〔30〕同上注,第69页。来证明市场和私法都无法纠正对竞争秩序的损害。
三、观念内核:竞争冲突市场调节优先
市场优先是经济法谦抑性理念在基本原则领域的映射。〔31〕参见刘大洪:《论经济法上的市场优先原则:内涵与适用》,《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最大程度地发挥私法自治的作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目前对“反法”的解释和适用恰恰因为没有充分虑及市场的优先性,才导致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过于宽泛。市场经济的“统治者”是技术和偏好,分别对应供给侧经营者之间的技术创新(对抗)和需求侧消费者的选择。而技术上对抗很可能导致商业模式上的冲突、竞争格局的变动,由此引发竞争损害。故此,下文分别从技术对抗、竞争损害和消费者选择三个维度来说明市场调节的优先性。为了说理更具针对性和细致性,笔者主要借助充分体现技术竞争特性且备受关注的系列广告屏蔽案的处理展开论证。
(一)技术对抗空间的预留
技术创新、技术对抗是现代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法律对竞争的保护必然意味着对技术使用行为正当性的评价要为技术创新预留空间。换言之,对技术有关的不正当竞争争议的处理需以承认技术中立性为前提,不能仅因技术功能之间的冲突就加以责难,而应立足于技术所产生的整体社会效果进行评价,从而为经营者开发新技术产品和探索新的经营模式提供机会。〔32〕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的基本范式》,《法学家》2018年第1期。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只具评价意义而不具主体意义,故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中,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源于不受扭曲竞争带来的创新利益。
就广告屏蔽案件而言,广告屏蔽技术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广告屏蔽软件是内容服务商“免费内容服务(诸如视频、新闻等)+广告”商业模式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另一方面,广告屏蔽软件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护用户的利益。〔33〕屏蔽软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避免了广告对用户的损害:(1)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注意力。对于用户获取信息来说,不同形式的网络广告存在程度不一的干扰。尤其是大量出现的横幅广告对用户造成了严重的干扰。(2)影响用户的良好体验。弹窗广告需要加载或运行第三方程序,占用带宽和降低网速,并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3)侵犯用户的数据隐私。Digital Content Next公司的调查发现,高达68%的用户担心广告定向追踪能够跟踪他们的互联网行为,泄露个人隐私。(参见韩红星、覃玲:《广告拦截的发展及对媒介生态的影响》,《当代传播》2017年第1期。)事实上,美国移动安全公司Lookout在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激进网站未经用户允许便搜集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或手机号码,有些网站还会直接安装跟踪应用,并向用户推送广告,严重侵犯了用户的个人隐私。(参见张小强、黎婷婷:《广告屏蔽应用对数字传媒业的冲击与应对策略》,《传媒》2017年第20期。)正是因为其对消费者福利有改善之效,所以广告屏蔽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34〕2016年,有将近7 000万美国人使用广告屏蔽软件,有超过2亿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使用屏蔽广告的移动浏览器。See Max Willens,How Many People Use Ad Blockers? That Depends on Whom You Ask,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http://www.ibtimes.com/how-many-people-use-ad-blockers-depends-whom-you-ask-238 4864 ,last visit on June 21,2016.例如,美国苹果公司2015年发布的iOS9在Safari中开放了广告屏蔽应用,多款收费广告屏蔽软件在苹果应用商店瞬间登顶即是一个典型例证。〔35〕参见杰罗姆:《广告拦截崛起:一个免费互联网时代的终结?》,https://www.jianshu.com/p /05e452381b03,2018年12月20日访问。
“免费内容服务+广告”商业模式面对屏蔽软件的“劣势”完全可通过技术上的改进加以扭转。其一,研发针对屏蔽行为的反制技术。屏蔽软件对视频网站广告的拦截主要是通过改变浏览器与视频网站软件之间的调用条件,在软件运行中拦截、修改、增加或屏蔽本地客户端和远程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信息,实现改变视频网站在浏览器上展现广告的能力。但这并未改变视频网站本身,视频网站完全可采取技术手段对浏览器的内容侵权进行拒绝,或者拒绝浏览器浏览网站。其二,改进广告的形式。广告旨在追求商业利益,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广告存在与否,而是广告的推送是否最大程度地兼顾到用户的体验。原生广告因为与内容、环境高度融合,注重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和有价值的内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有道词典与宝马公司合作,推出独具特色的原生广告形式,利用既有的“每日英语”栏目进行广告宣传,并就宝马1系列车推出英语在线问题,用户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广告的影响,将广告信息转化为对受众有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获得了良好的推广效果。〔36〕参见廖秉宜、何怡:《原生广告的概念辨析与运作策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7年第5期。其三,提供用户需要的广告。美国互动广告局发布的《广告拦截:谁在使用?为什么会被使用?如何再次赢得用户的心》报告显示,如果发行商在用户浏览网站时能为用户提供符合需求并有价值的内容,那么三分之二的美国地区用户都愿意关闭广告拦截。〔37〕See IAB Ad Blocking Report: Who Blocks Ads,Why,and How to Win Them Back,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7/IAB-Ad-Blocking-2016-Who-Blocks-Ads-Why-and-How-to-Win-Them-Back.pdf,last visit on Dec.12,2018.
可见,应对广告屏蔽行为的巨大技术创新空间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企业运营商的市场前景依然广阔。例如,谷歌公司开发的Chrome浏览器一直开放广告拦截插件的使用,其拥有高达56%的桌面浏览器市场,但其广告收入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数据显示,其广告收入从2004年的31亿美元稳步增长至2014年的596亿美元。〔38〕See Ankit Oberoi,The History of Online Advertising,https://www.adpushup.com/blog/the-history-of-online-advertising/,last visit on Dec.12,2018.又如,德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715万欧元增加到2017年的844万欧元,仍将持续增长之势头。〔39〕Vgl.Statista,Nettovolumen in den einzelnen Segmenten des Online-Werbemarktes in Deutschland in den Jahren 2015 bis 2017 und Prognose für 2018 (in Milliarden Euro).转引自张飞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广告屏蔽软件的合法性问题》,《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7期。
然而,对“免费内容服务+广告”商业模式的庇护扼杀了上述技术创新的可能,发达市场经济体早已摒弃了权利侵害式侵权法思维,转而将技术问题交由技术来解决。在著名的德国“电视精灵案”中,原告是一家以在播放的电视节目中投放广告为盈利方式的电视台,被告生产和销售被称为“电视精灵”的一种广告屏蔽装置。用户通过在选定的节目广告播放时间内向安装该装置的电视机或录像机发出指令信号,跳转到其他节目,并在广告时间结束时返回原频道。原告认为被告推广、销售“电视精灵”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德国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理由主要是,原告自身具有针对屏蔽行为的应对和自救能力。“传媒企业也必须接受市场的挑战,而市场的生命力就在于商业活动自由和创新。”“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与广告经营者一起努力激发并维持观众对广告节目的兴趣,或者主动采取技术革新来解决广告屏蔽的问题。至于到目前为止是否存在这样的技术手段以帮助原告避免被告产品对其经营活动造成的生存威胁和影响与本案的法律问题认定无关。”〔40〕BGH,Urteil v.24.06.2004,Az.I ZR 26/02.与这一裁判思路一脉相承,德国法院在“白名单广告案”中再次强调原告除了加入白名单外,还可以有多种选择方式,“既可以拒绝屏蔽了广告的用户进入网页;又可以做出技术上的改进以防止广告被屏蔽。况且,在线广告只是在线新闻行业多个融资模式中的一个。”〔41〕416HKO 159/14.德国上述经典判决明显秉持了“市场的归市场”“技术的归技术”的理念,依靠市场和技术解决竞争纠纷,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竞争问题,重点考量原告是否具有市场的和技术的应对能力,从而避免将技术创新引发的冲突动辄就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此一做法无疑更有利于商业创新和技术进步。〔42〕同前注〔32〕,孔祥俊文;同前注〔39〕,张飞虎文。
反观在我国备受关注的“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案”二审中,法院的裁判(包括所引入的专家分析意见)对屏蔽行为对被屏蔽方影响的分析中一个致命缺陷就在于,未能考虑到上述可能的应对方案,由此得出的视频网站因为广告被屏蔽而转向在视频服务中收费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结论,或者视频网站无法维系运营的结论,皆无法令人信服。〔43〕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558号民事判决书。最终,对屏蔽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因抑制技术创新而损害了动态竞争。
(二)市场损害中性原则的厘清
竞争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一方优势的确立即意味着另一方劣势的产生。竞争造成的损害是中性的,损害本身并不具有是与非的色彩,不构成评价竞争行为正当与否的倾向性要件,充其量不过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一个考量因素。〔44〕同前注〔32〕,孔祥俊文。
普通法上的一项坚实的侵权法原则就是“竞争损害并非侵权”(competition is not a tort)。〔45〕Shank v.William R.Hague,Inc.,192 F.3d 675,687(7th cir.1999); ABA Section of Antitrustlaw,Business Tor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Handbook,ABA Publishing,2014,p.22.在美国享有巨大影响力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第三版)》第1条规定,除非符合特别规定,“凡是从事商业或者贸易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不需要对该损害承担责任。”换言之,“竞争自由默示一种可以诱使潜在客户与其本人而不与其竞争对手从事交易的‘竞争特权’(a‘privilege’to compete)。”英国法官Robin Jacob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夺取他人的市场或者客户一般不构成侵权。无论是市场还是客户都不是原告自己的。”〔46〕Hodgkinson Corby Ltd.v.Wards Mobility Services Ltd.[1995]F.S.R.169.See Christopher Wadlow,The Law of Passing-off:Unfair Competition by Misrepresentation,Sweet & Maxwell,2011,pp.5-6.
商业模式的更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由此造成的损害不能直接得出行为不正当性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就曾指出:“竞争对手之间彼此进行商业机会的争夺是竞争的常态。对于同一交易机会而言,竞争对手之间一方有所得另一方即有所失。”所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一种利益应受保护并不构成该利益的受损方获得民事救济的充分条件。”〔47〕同前注〔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可惜的是,在此点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在之后的“腾讯诉360案”中,法院强调“正当的商业模式必然产生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商业利益”,〔48〕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明显是开了倒车。
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中,对竞争损害的考量以竞争者的生存不受威胁为底线。法律之所以将“损人利己”界限划在是否导致竞争对手无法生存之上,是基于增强市场竞争的对抗性,提升市场竞争的张力、韧性和强度的考虑,〔49〕同前注〔32〕,孔祥俊文。避免任何与在先商业模式产生冲突的行为动辄得咎。在“电视精灵案”中,德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指出:“被告的广告屏蔽装置的销售虽然加重了原告的经营负担,但并未威胁其生存。”但是,如果禁止被告生产和销售“电视精灵”,那么“则会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因为广告屏蔽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50〕同前注〔40〕。在“白名单案”中,德国法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原告并未证明正面临被市场淘汰的情境”,若其“提供的新闻服务不再仅仅通过广告筹集资金,其经营活动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观”。故此,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屏蔽真正地危害了原告生存”。〔51〕同前注〔41〕。
在实证法上,德国曾经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直接以对竞争者自由构成“显著损害”(Spürbarkeit)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门槛(§3I,UWG,2008)。为了与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UCPD)保持一致,《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UWG,2016)删除了这样的表述,但并未放弃这样的要求,而是将其纳入到对“不正当”的解释之中。〔52〕Vgl.Christian Alexander,UWG 2015-Ende des schwierigen Weges zur Richtlinienkonformität?,Betriebs-Berater,BB 5.2016.S.1.按照“电视精灵案”的判决,“显著损害”就是“导致竞争者任凭自己的努力都无法将自己的业绩在市场上合适地展示”,破坏了凭借真本事争胜的竞争秩序。
法律对竞争损害的态度决定了竞争发挥作用的空间。仅仅因为导致竞争损害就认定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打着保护竞争的旗号阻断竞争的过程;而对竞争损害的宽容,则给予了更多的竞争自由。目前我国采用的权利侵害式侵权法思维(尤其是“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或抽象的道德评价标准天然地有利于主张正当商业模式的一方,任何与之冲突的商业模式都被认定为“干扰”或不正当竞争,这显然是落入了“竞争者保护”的逻辑,仅仅因为原告受到损害就草率地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53〕需说明的是,作为不正当竞争认定依据的竞争损害并不只是着眼于行为对竞争者的影响,还包括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竞争相关者利益整体权衡后的结果。能够作为竞争行为判断依据的只能是对竞争秩序的损害,而不是对竞争者的损害。“致使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门槛降低,使不正当竞争的范围易于事实上扩大化。”〔54〕同前注〔32〕,孔祥俊文。
(三)消费者自由决策不受扭曲标准的确立
在技术创新之外,竞争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决定了竞争的结果。同样以屏蔽广告案为例,一方面,“免费内容服务+广告”盈利模式的好坏由网络用户来决定。美国的网页广告模式就是依据用户体验成功地实现了转型。这一领域的巨头YouTube在2010年推出“True View”服务,用户可以选择是否跳过广告以及广告呈现的方式,甚至可选择在视频特定位置观看某广告。另一方面,即使屏蔽方与被屏蔽方合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用户。著名的广告屏蔽应用AdBlock Plus软件商曾多次与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平台企业谈判,在收取一定的费用后将其广告纳入某“白名单”,使其免受拦截。〔55〕同前注〔33〕,韩红星、覃玲文。“白名单”的设定本身必须满足一些旨在确保消费者利益(诸如不追踪用户隐私、不发送弹窗)的硬性标准。
“消费者偏好”要在竞争机制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竞争过程中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即消费者的自由决策机制不受扭曲。〔56〕See Tim W.Dornis,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onflicts: Historical-Comparative,Doctrinal,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pp.287-295.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消费者自由决策的机制不被扭曲,一般就不会认定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如在“电视精灵案”中,德国最高法院的裁判就再三强调“认定是否构成对竞争者广告营销的阻碍关键是看该阻碍行为是否剥夺了消费者的自主决定权。”因为电视观众完全有权决定是否选择使用“电视精灵”,所以“被告只是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一个技术帮助让他们离开其本来就不想看的节目”而已。〔57〕同前注〔40〕。
我国在“反法”修订过程中,学者对消费者利益能否成为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认定标准一直存在争议,虽然持肯定意见者不在少数,〔58〕参见李友根:《论消费者在不正当竞争判断中的作用——基于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案的整理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定位》,《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吴峻:《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模式》,《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周樨平:《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消费者保护功能》,《竞争政策研究》2017年第2期。但仍有人拒绝将消费者利益作为不正当认定的独立标准。〔59〕参见焦海涛:《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而法院一直倾向于将消费者利益作为证明经营利益受损的一个工具,不具有独立评价的地位。此种情况在最新的两起广告屏蔽案件的裁判中有了明显改观,法官在这两起案件中因消费者利益改善而拒绝认定被告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60〕同前注〔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需明确的是,竞争过程中的消费者是一个整体形象,对消费者的自由决策的“实质性扭曲”,〔61〕与对竞争者利益的“显著损害”含义一致,对消费者决策的“实质扭曲”也强调的是消费者基于竞争秩序享有的利益受损的程度,这是一种在正常市场风险之外所遭受的非市场损害。指的是企业因此不合理地获得了竞争优势的行为,而不是侵害消费者个体利益的个别行为。行为“足以影响交易秩序”是其纳入“反法”而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界限,这也正是“反法”作为经济法所具有的公共属性的体现。对“足以影响交易秩序”的考量集中在受害人数的多寡、造成损害的范围及程度、是否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警惕效果及是否为针对特定团体或组群所进行的欺诈或显失公平的行为等因素,但不以其对交易秩序已实际产生影响为限。〔62〕参见杨宏晖:《欧盟不当交易行为指令与德国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的新变革——以消费者保护的强化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2010年第2期。
四、法律技术:比例原则对干预边界的限定
市场调解优先除了意味着优先发挥市场在解决竞争冲突中的作用外,还意味着依据竞争本身的属性和客观效果认定行为的不正当性。竞争的过程是动态的利益均衡的过程,作为利益衡量工具的比例原则在限定不正当竞争边界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它被视为对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更好的结构性规范”。〔63〕同前注〔24〕,迈克·费恩塔克书,第286页。过度规制或规制不足很大程度上源于“未向社会和经济规制中引入比例原则。”〔64〕Sunsteine,C.R.,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81.
(一)作为“对规制限制”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在本质上是一个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与协调的工具及具有普适性的判断行为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其通过考察不同方式(行为、手段)对两个相冲突利益(原则、目的、价值等)的各自影响,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上同时兼容两种利益的方式。〔65〕参见兰磊:《比例原则视角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解释——以视频网站上广告拦截和快进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例》,《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该原则最初滥觞于行政法领域的警察法之中,后逐渐上升为一项宪法原则,最终扩展适用于整个法律秩序。〔66〕转引自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在构成上,比例原则一般包括三个子原则:一是妥当性原则,即所采取的措施可实现所追求的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即除采取的措施外,无其他给关系人或公众造成更少损害的适当措施;三是相称性原则,即采取的必要措施与其追求的结果之间并非不成比例(狭义的比例性)。〔6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妥当性原则关注手段与目的的联系,比较容易查明,而且即使相关行为只是部分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仍可满足。当然也确实存在某些行为仅仅以追求某个目的为借口,实际上完全无助于该目的的实现。必要性原则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存在多个能够实现目的的行为方式,否则必要性原则无适用的余地;其二,在能够同等实现目的的诸方式中,选择对第一种价值侵害最小的一种。由于技术的复杂性,要求被告在行动时逐一考察各种可选方案并选择其中侵害最小的方式显然是一种苛求。实践中通常会给予被告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只要求不存在侵害性明显更小的替代方式即可。〔68〕同前注〔65〕,兰磊文。狭义比例原则强调的是利益平衡的方法,权衡追求目的所要达到的利益(收益)与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对相冲突利益造成的损害(成本)之间是否成比例,这一平衡过程并不是通过精确地计算两个变量的数值大小然后加以比较,而是较为粗略地比较两个变量。〔69〕同上注。只有当损害明显大于收益时才构成对狭义比例原则的违反;如果造成的损害与所实现的收益相比并不明显失衡,则认定行为合法,从而给行为人留下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动辄违法。〔70〕同上注。
在性质上,比例原则是“一种规范”,违反此规范将遭受制裁,也是“一种审查工具或手段”,〔71〕陈淳文:《比例原则》,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8页。为执法者提供制裁的理由。这两种性质体现为比例原则的“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前者指的是作为公民“自由权利不受公权力不当限制与侵害之准绳”,〔72〕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7页。“任何国家公权力之行为违反了这个原则,会导致违宪的后果。”〔7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页。后者指的是其提供一套可供理性操作和论辩的思维工具,为最终的结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理由。〔74〕同前注〔66〕,郑晓剑文。
(二)在不正当竞争认定中适用的正当性
比例原则最初适用于传统的公法领域,一方面确认公权力基于公共目的可以限制私权利,另一方面又将其限制在必要限度之内。随着权利与权利、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频现,比例原则从一个处理政府与私人利益冲突的原则转化为一个处理私人之间利益冲突或者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原则,逐渐拓展至私法、经济法领域。
经济法以私法自治为其构造的逻辑起点,旨在弥补私法自治的局限,保障和拓展私法自治的作用空间。而对私法自治构成威胁的一是国家公权力过度干预,一是私权利的滥用。在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施加某种限制的情况下,比例原则可以发挥其所具有的“限制之限制”的功能,即要求此种限制须服务于一个价值更高的正当目的(如实现公共利益);所采取的限制手段须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在有多种手段供选择时,需要采用最为和缓的干预手段进行限制;该最为和缓的干预手段对利害关系所产生的负担与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在效果上要相均衡。如此,既可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又可维护私法自治不被过度介入和干预。在一方不当地获取或维持竞争优势的情形下,也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对此种过度的自由进行限制,恢复竞争约束之下的均衡。因为,对私法自治的限制,不仅在于禁止恣意,还在于禁止过度。反对极端“禁止过度”是比例原则之精髓。〔75〕参见郑晓剑:《比例原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
具体到“反法”领域,比例原则适用的正当性包括如下三个层次。
其一,比例原则的适用切合“反法”利益平衡的制度机理。现代意义上的“反法”对不正当竞争的认定“越来越具有利益平衡的意蕴”。〔76〕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代化》,《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反法”通常具有保护经营者(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三叠加的保护目标。〔77〕相对于旧法而言,2017年11月4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置于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之前,意味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首先要考量市场竞争秩序,也就是竞争机制和公共利益意义上的损害;其次引入消费者利益,使利益衡量法律结构更加完善。至此,从法益保护的角度看,新修法实现了“公共利益”“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三叠加的保护目标。参见孔祥俊:《论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时代精神》,《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竞争享有不同的利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就必然是对这些相关冲突的利益进行衡量。
利益衡量的方法无非有二,一是参考权利位阶,一是诉诸比例原则。〔78〕参见梁迎修:《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如果权利位阶存在高低之分,那么位阶高的权利通常会被视为具有更高的价值并得到优先保障。但是,经营者的营业利益无时无刻不与自由竞争相冲突,这两种冲突的利益无所谓谁更“高阶”,没有哪一方必须在冲突中获胜,〔79〕参见于飞:《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故此,只能采用比例原则在个案中确定哪种利益更值得保护。
比例原则相对具体的规范构成及判断方法可以在司法层面进行展开和操作,从而为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或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提供指南。将其作为利益衡量的指导和参考框架,既可妥当地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又能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较为明确的预期。〔80〕同前注〔66〕,郑晓剑文。或者说,既符合竞争有优势的利益属性和保护需求,又避免了抽象道德的不确定性。
其二,比例原则的逻辑、适用结果与市场竞争的本质高度契合。竞争是一种争胜过程,是在不同利益主体相互约束、激励和反制的互动下不断推出、改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这种约束、激励和反制本身就体现为对既有利益的损害和对新型利益的创造。只有允许对既有利益的适当损害才可能为新型利益的发展腾出空间,也才能刺激既有利益的不断改进。〔81〕同前注〔65〕,兰磊文。基于比例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逻辑可以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的商业道德标准转换为一个依据竞争效果展开的客观的利益权衡的框架,排除对某种特定权益的专门保护,最大程度地实现各种利益的协调与兼容。
在“淘宝诉载和、载信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对一项竞争行为是否予以规制,应综合考虑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的利益,并对其他经营者因被诉行为遭受的损害与停止被诉行为对行为者利益造成的损害进行衡量。竞争的利益均衡的功能特性决定了无论哪一种利益都不具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优先地位。该案的二审法院在进行更精细的利益衡量后特别指出,消费者在竞争过程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可以提升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不能当然被排除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外,仍要就被控行为的正面效果与对被干扰者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衡量”。〔82〕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终198号民事判决书。
其三,比例原则的适用是法治框架构建的必然要求。以一种更为连贯的视角来看,基本权利所确定的行为自由要受到合宪性制度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满足比例原则。〔83〕同前注〔14〕,弗里茨·里特纳、迈因哈德·德雷埃尔书,第145~146页。比例原则被视为对规制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更好的结构性规范”。〔84〕同前注〔24〕,迈克·费恩塔克书,第286页。作为一种典型规制,“反法”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普遍的竞争自由而对特定主体的行为自由进行限制,其划定企业竞争行为的负面清单,同时也将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限定在这一范围内。由此,与其说“反法”是对干预的授权,毋宁说是对干预本身的限制。
总之,从本体论意义上言,比例原则在“反法”中的适用切合了“反法”本身的制度机理,与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弥补市场局限和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的制度逻辑相适应。它实际上筑起了维护私法自治的两道屏障:对外抵御国家公权力对竞争的过度介入;对内确保私法自治不被竞争者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损害。从方法论意义上言,比例原则为涉不正当性的判定提供了一个更具可操作性的框架与思路,使裁判更加具体化与规范化,降低了过度干预的风险。
(三)不正当性判定中的利益考量框架
比例原则的教义学功能就在于其可以使权衡过程合理化和权衡内容具体化,〔85〕Vgl.Val Hans Hanau,Der Grundsatz Verhältnismäßigkeit als Schranke privater Gestaltungsmacht,Verlag Mohr Siebeck 2004,S.95.从而使诸种相互冲突的法益和谐均衡。〔86〕转引自前注〔66〕,郑晓剑文。其适用的最大价值正在于与摒弃权利侵害式的侵权法思维和抽象道德判断的需求相吻合,最大程度地限定政府干预竞争的边界。很多依据“反法”一般条款认定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引发的争议在根本上是源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完整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导致一些案件在利益考量因素上顾此失彼,或存在结构性缺失,或逻辑混乱。
在现代“反法”体系内,所有市场参与者均受保护。〔87〕Vgl.Emmerich,Unlauterer Wettbewerb,7.Aufl.,2004,C.H.Beck.,S.29.对于竞争者的保护主要是保护其基于自由竞争所享有的利益;对于消费者的保护主要是保护基于自由决策不受扭曲所享有的利益;对于社会公众的保护主要是保护其基于不受扭曲的竞争所享有的利益。这些利益权衡要素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中并无固定的价值位阶和权重,行为正当性与否则取决于其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相关利益的兼容。
权利侵害式的侵权法思维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几乎将在先商业模式作为一项权利加以保护,赋予特定经营者免于竞争的特权;将竞争正当与否的判断局限于在先经营者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忽视了其他经营者竞争的自由以及消费者利益的独立判断价值。被广泛适用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该思维的延续,虽然将“公益”作为干预的唯一正当化理由,从表面上赋予了公共利益很高的权重,但实际上却会因阻断竞争、限制创新而最终损及公共利益。
此前的大多数广告屏蔽案件将屏蔽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就是基于此一思维。例如,在“大摩与乐视广告屏蔽案”中,二审法院的判决虽然向前迈进了一小步,确认“反法”保护的是原告依托“免费内容服务+广告”商业模式进行经营活动所获取的合法权益,而非商业模式本身,但其裁判仍未能跳出“劳动成果权利化”的桎梏。法院特别强调:“竞争必须是经营者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而进行的正当的竞争。”“大摩公司利用用户存在的既不愿支付时间成本也不愿支付金钱成本的消费心理,推销屏蔽软件,目的在于依托乐视网公司多年经营所取得的用户群,为大摩公司增加市场交易机会,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属于不当利用他人市场成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来谋求自身竞争优势,”〔88〕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75号民事判决书。所以判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无不当。直至最新的两起广告屏蔽案,法院的态度才发生了转向,认定屏蔽行为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此际,法院判决的说理才具有了比例原则分析框架的雏形。详言之,其一,在妥当性层面,法院都注意到了屏蔽行为有助于消费者免受不受欢迎的广告滋扰。其二,在必要性层面,法院特别强调屏蔽软件给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空间。尤其是在“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案”中,法院判决在此点上说得非常详细。首先,世界星辉公司广告屏蔽软件并非直接和无选择屏蔽任何广告,而是只有用户选择勾选“强力拦截页面广告”选项时才能实现广告过滤功能。其次,从屏蔽项的设置看,在所设置的四个选项中,以不屏蔽任何广告为首选,默认屏蔽项只限于针对色情、赌博等不良广告,即屏蔽软件是否使用、如何使用,最终均由用户决定,最大程度地考虑了对内容提供商的影响。其三,在相称性层面,法院着重论证了屏蔽对内容提供商并未造成实质性损害。在“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案”中,法院指出,会员制与非会员制用户的存在以及财务报告的分析都可说明广告收入并非原告唯一的收入来源,屏蔽行为不会对其产生“根本性影响”。虽然判决未能像“电视精灵案”中德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那样详细列举内容提供商各种应对屏蔽的可能(如在正片情节中融入广告或者与正片内容进行分屏显示进行改进等),但是法院还是提到了视频网站可通过进一步改善自身的经营和服务来谋求发展。〔89〕在“快乐阳光公司诉唯思公司案”中,法院在此方面做得更为出色,该案的判决详细论证了原告应对屏蔽行为的诸多技术方案。
仍显遗憾的是,法院判决在说理上将三个层次的内容交织在了一起,缺乏一个清晰的逻辑。在此方面,“大众点评诉百度公司案”的二审法院的判决有了很大改观。〔90〕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审理该案的法院全面考量了信息爬取行为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既考虑到信息获取者的财产投入、信息使用者自由竞争的权利,还顾及到公众自由获取信息的利益,以及信息和互联网发展所必须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特点。〔91〕该案的一审(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书)与二审的裁判结果虽然一致,但是在理念和思路上却有了很大差别。一审法院主要立足于汉涛公司基于收集、整理、加工对大量信息所产生的商业利益的保护,缺乏对整个信息产业的信息传播、其他经营者合理使用信息、消费者获取更多信息利益的考量。裁判建立在“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劳动成果”的逻辑上,以“不劳而获”“搭便车”为主要依据,这一方面陷入了道德判断的泥沼,另一方面事实上创立了一种“劳动成果权”。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保护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的思路,是“权利侵害式侵权”而不是比例原则下的“利益衡量”思维。最重要的是,在行为正当性判断上清晰地体现了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的分析脉络。其一,就妥当性而言,二审法院确认了百度公司将从大众点评网上爬取的点评信息用于百度地图,用户在搜索到商户位置的同时,还可了解其他消费者对该商户的评价,这种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用户体验,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具有积极的效果。其二,就必要性而言,由于存在明显对汉涛公司损害方式更小的方式而未采取,可认定百度公司对大众点评数据的使用方式已超过必要限度。如法院判决所言,它本可以采取一种对大众点评网损害更小的少显示或部分显示点评信息的方式,在基本保证用户体验的情况下降低对大众点评网的损害。其三,就相称性而言,百度公司的爬取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与对大众点评网的损害相比并不相称,对大众点评服务产生了实质性替代。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还可能使得其他市场主体不愿再就信息的收集进行投入,破坏了正常的产业生态,对竞争秩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进入这一领域的市场主体减少,消费者未来所能获知信息的渠道和数量亦将减少。因无法满足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故百度公司的爬取行为才被法院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五、结论
美国著名竞争法学者霍温坎普教授曾深感忧虑地指出:“反垄断政策经常基于对竞争损害的夸大担忧,发展出一些具有过度保护性的规则,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使无效率的企业摆脱竞争的约束。”〔92〕Christina Bohannan,Herbert Hovenkamp,Creation Without Restraint: Promoting Liberty and Rivalry in Inn- ov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XI.同样地,在“反法”适用过程中发展出的权利侵害式侵权法思维、过于宽泛的道德化判断,严重低估了竞争本身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将竞争损害等同于不正当竞争,或者将对他人成果的合理使用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过度保护了竞争者。这种对私人竞争关系的不合理介入和过于宽泛的不正当竞争认定方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其限定企业竞争行为“负面清单”的意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企业自由竞争的基础。
“反法”的谦抑性源于一种法治化的要求。尊重市场的权威、尊重私法自治的原则是由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所决定的,也是民法与经济法相互衔接、相互支援的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竞争具有复杂且不可预测性,若对竞争行为过多地指手画脚,很可能损害企业的竞争自由。也就是说,在错综复杂和具有内生性的市场竞争面前,法官对于不正当竞争的判断必须保持足够的谦抑。〔93〕同前注〔32〕,孔祥俊文。极端私法自治无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哈耶克也不否认政府干预的价值,只是他将公法的边界限定在为自生自发秩序的作用的发挥提供必需的框架,反对以公法扭曲或替代私法。〔94〕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从结构上讲,“反法”确保私法自治优先发挥作用,对竞争关系的介入以私法自治无法发挥作用为前提,以维护竞争秩序为限;并且这种干预不是取代或扭曲私法自治,而是旨在弥补其不足或者为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反法”的谦抑性还源于自身的制度逻辑。它是为实现更普遍的竞争自由而介入私人竞争关系,融合了私法和公法,最终体现了经济法的特性。民法自身无法克服私法自治的局限,需要政府干预,而这种政府干预又必须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确保真正的私法自治的实现。作为这种对私权与公权的双重限制,内在嵌入了谨慎的干预思维,而强烈干预的“家长”式情怀本身就是对这种谦抑性的背离。
“反法”的谦抑性强调的是其作为一种干预而建立在市场调节失效之后的后发性、恢复市场作用的辅助性,以及与市场逻辑保持一致的适应性之上。就后者而言,意味着对不正当竞争界定的标准是基于竞争本身。欧肯早就提及,对“不正当”的定义通过“不受扭曲的竞争”获得。〔95〕参见范长军:《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不受扭曲的竞争”是各方利益的均衡,比例原则是利益平衡的工具,故此,对不正当竞争的认定必须在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下展开。该框架的客观性可最大程度地避免因权利侵害式侵权法思维和商业道德判断所致的过度干预风险,将政府对竞争的干预限定在应有的范围内。在全球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勃兴的今天,对在市场上诞生的创新型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不应动辄就采取行政干预或动用司法资源,而应更多地留待市场自身来解决。〔96〕参见郑友德、王活涛:《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探讨》,《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