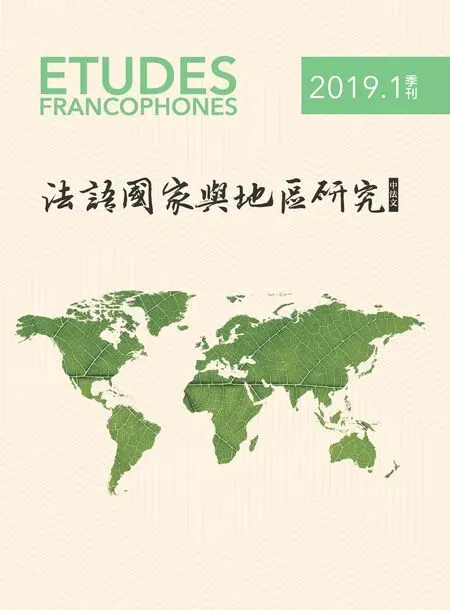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高端论坛简报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高端论坛”(Séminaire francophone)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举办的区域国别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由中心主任丁一凡教授主持。论坛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就国际国内热点问题发表学术报告,是国内唯一以国际政治经济和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为主题、以法语为工作语言的学术论坛。以下为2018年6—11月的论坛简报。
第四十讲:外语课堂的文化教学:理论与实践
6月11日下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教授托马斯·森德(Thomas Szende)应邀做了题为“外语课堂的文化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讲座。
森德教授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享了外语课堂的文化教学研究。他认为,词汇承载着一个群体共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是我们认识和了解目的语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他鼓励教师从影射目的语群体思维模式和精神面貌的词汇入手来进行文化教学。同时,与某一文化相关的词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比如结婚、市政府与教堂。在进行文化教学时,教师应尽量全面而充分的讲解相关词汇,让学生对此文化现象有更完整而深刻的认识,这种由文化捆绑的词汇也有利于学生记忆。在讲解词汇时,教师还应明确一个词语的相关属性,比如文学词汇还是口语,褒义还是贬义,古语还是新词,方言还是官话,是否只用于特定领域等,以便学生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词汇。
一些词语由于文化的积淀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文化教学中也应当予以重视,比如隐喻词、基于公众刻板印象的词、具有象征意义的词、固定表达和成语等,这些词通常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且体现出一定的情感价值观。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意义丰厚的词更难翻译,通常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词与之对应。因此,译者不应当拘泥于字词本身,而应该在目的语文化背景中找到能传达相同意义和情感的词语来翻译。
日常交际用词也不容忽视,这些词由于在表达时通常涉及到动作、语调和神态,比如礼貌用语、餐桌礼仪用语等,体现出了相当丰富的文化意义。
最后,森德教授指出,外语课堂是不同文化接触与碰撞的地方,听众应当在接受这种相异性的基础上,最大化地认识和了解目的语文化。
(徐源源 供稿)
第四十一讲:法兰西共和模式还有生命力吗?
10月9日上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教授弗里德里克·布拉阿米(Frédéric Brahami)应邀在北外做了题为“法兰西共和模式还有生命力吗?(France : la promesse républicaine est-elle encore vivante?)”的主题讲座。
法兰西共和模式指一种追求高度均质化的同化政策,是通过在学校推广法语、重构国民历史叙事展开的,使得人们脱离原有的地域认同,而实现新的国民认同。法兰西共和模式的同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纸张上成为公民,即获得法国国籍,而是从心底成为公民,即脱离原有的文化认同,转而认同法兰西的共和价值观,即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成为百分之百的法国公民。
这一同化政策一度是有效的。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对地域的认同还超过对国民的认同。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人们对于国民认同的情感已经高于地域认同的情感了。但近来这一同化政策却遭遇到了危机。其中的原因之一,即近年来的移民大多为阿拉伯穆斯林,历史上关于殖民主义的创伤使得穆斯林移民与本土法国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的拒斥:从穆斯林移民的角度看,他们感到没有在法国得到很好地接纳,他们很难在法国找到工作与居所;而从本土法国人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加之恐袭之后对穆斯林世界的恐惧,使得他们拒斥穆斯林移民。这使得共和国曾经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承诺遭到了质疑。
此外,法兰西共和国的同化模式也从理论上遭到了质疑。法国希望按照统一的模式塑造公民,让人们成为“均质”的法国人,这似乎显得真诚而慷慨。然而,这同时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在放弃其原有的文化认同之后,才能被接纳为法国人。法国可以慷慨地接纳阿拉伯人、黑人、犹太人、中国人等等,但禁止他们在公共领域展示其特定的文化归属及对其原属社群的忠诚,虽然这一切在私人领域当中都是允许的。事实上,政教分离不仅把国家与宗教分开,还把公民身份与其文化认同分割开来。组成法兰西民族的,是自由而平等的个体,而宗教的、文化的、伦理的团体却并不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法国长久以来关于伊斯兰头巾的争议恰恰能体现法兰西共和模式的危机与悖论。共和国宪法捍卫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意味着国家从宗教事务中分离出来,保持中立,不干涉人们的信仰,也不干涉人们的信仰,而佩戴头巾也并不会对他人造成危害,这似乎意味着种族主义和对伊斯兰的仇恨,也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那么为何要禁止伊斯兰女性佩戴头巾呢?共和派论证了禁止佩戴头巾的合理性:1.法律只允许在公共场合佩戴低调的宗教标志,而头巾太过张扬;2.伊斯兰教带有强烈的劝人改宗入教的热忱,这有悖信仰自由的原则;3.女性佩戴头巾有悖男女平等的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女性须服从于男性。
总之,赞同禁止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法案的共和派认为,这一特定团体的风俗有悖基于均质化基础上的国民认同,而反对这一法案的则认为这意味着种族主义的歧视,这甚至体现了法兰西共和模式的虚伪之处。因为人们只有放弃其特定的文化认同,才能被吸纳为法国公民。而盎格鲁—撒克逊的社群主义则是另一种模式。享有权利的并不仅仅是个体,还有具备特定认同的各类团体。这一理念意味着国民这一团体不能凌驾于各种宗教的、伦理的、文化的团体之上。在法国,穆斯林只有作为法国公民个体才能享有权利;而在美国或加拿大,宗教团体也能享有权利。我们很难说法国会向哪个方向演进,公众意见分歧很大,关于头巾的争议只是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原则的模糊性与其内在的悖论性,因为一个真诚地信仰共和原则的共和派既能据此反对佩戴头巾,也能支持佩戴头巾。
一方面,法国自诩是一个宽容的国家,人们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自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法兰西共和国似乎仇视一切宗教,把宗教视为自由平等的敌人,将宗教完全压缩到私人领域中。“反教权主义”是法国一个深厚的传统。在欧洲,法国是唯一对宗教和文化认同持有这一态度的国家,这也触及到法兰西共和精神特性的实质,而这一特性与法国大革命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的奠基性事件,它塑造了迄今为止法国政治辩论的特性。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法国大革命都是最富争议性、最具热点性的辩论议题。
法国大革命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人权宣言的颁布。宣言赋予个体和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在革命当中,这一自由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恐怖与专制。19和20世纪,人们努力探索自由与专制之间悖论的原因,有人归咎于内忧外患的战争形势,有人则认为应当反思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其批评精神与抽象原则。启蒙哲学意味着解放人的精神,尤其是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论断,在狄德罗(Diderot)、埃尔维修(Helvétius)等启蒙哲人的思想当中既已存在。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宗教获得其神圣性与权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古老传统的尊崇。因此自由精神最为根本的敌人,还不仅仅是宗教,而是对既往传统的尊重。因此,自由意味着隔断与过去的联系。《国际歌》歌词中“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实并非共产主义的原创。
革命者希望塑造新人、新的共和历、新的行政区划和新的立法原则,即依据以启蒙哲学为基础的模式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人是理性的、普遍的、抽象的。然而,正如迈斯特(de Maistre)所言:我能看到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普遍的抽象的人,我从没见过,这是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的悖论恰恰在于,革命后的法国不再通过其历史和地域来界定自身,而是一个由普遍的、抽象的、超越历史的个体组成的国度。法兰西民族不再因为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而界定自身,而是通过认同抽象而普遍的哲学原则来界定自身。而法国革命的使命也是普遍性的,《人权宣言》声称:所有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所有人”,就意味着不仅仅是法国人,而是超越一切民族的、宗教的、文化认同与归属的抽象而普遍的人。
这一悖论必将造成诸多困扰,在一些文化、宗教与社会语境中,男性与女性、老年人与年轻人并非完全平等,而法国却希望推行一种普遍性的人权,这自然会在这些文化语境中引起冲突。卢梭曾言,要强迫人自由,那么是否意味着要将人从其特定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归属中解放出来?在原则上无法找到走出这一悖论的途径。这一悖论不仅仅是理论性的,也在实践中造成了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恐怖正是不顾一切既定社会文化现实将普遍性的权利付诸实行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革命后19世纪的法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放弃这一普遍性的使命,还是依据法兰西共和模式的理想,塑造博爱且拥有人权的新人?第三共和国尝试了一种与恐怖时期塑造新人不同的模式,即通过学校教育塑造新人。一开始,第三共和国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工人多为社会主义者,农民则是波拿巴派,资产阶级则为奥尔良派。在1870—1880年间,共和派是少数。在这一情况下,共和派创建公立的世俗学校,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来培养新一代支持共和制的公民。这确实成功了,到1914年,绝大多数人都是共和派。通过第三共和国的共和道德教育与历史叙事重塑,革命后的法国又与曾经的法国联系在一起:如果说1792年的法国通过否弃君主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认同;那么在1880年,共和教育的历史叙事却认为自高卢人到路易十四,是国王创造了法兰西民族。此外,这些共和派还是法国在北非及黑非洲等地殖民的支持者,认为共和国赋有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最终,共和派基本上成功塑造了一个认同普遍性人权的法兰西民族。
事实上,共和主义思潮在法国始终是比较弱势的,它一直在两股更为强势的思潮,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在欧洲,由于法西斯、纳粹、殖民历史的残暴,爱国主义似乎一直是个负面的词,似乎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战争。而民族主义抑或爱国主义是与共和国紧密相联的,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在许多方面彼此对立,但它们都反对民族主义。在布拉阿米教授看来,或许今天法国最为实质的问题,就是进步主义者不愿谈论民族,而普通民众、右派、保守主义者却眷恋着民族。或许法兰西的共和主义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确实能激发我们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彼此紧密团结、却并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们或许可以回溯到共和主义的思想源流当中去探寻。
(潘丹 供稿)
第四十二讲:全球化的未来:面对单边主义的中欧关系
10月12日下午,欧盟新任驻华大使郁白阁下(Nicolas Chapuis)应法语系邀请在北外做了题为“全球化的未来:面对单边主义的中欧关系( L’avenir de la mondialisation : la relation euro-chinoise facel’unilatéralisme )”的主题讲座。
郁白首先提及了中国和欧盟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他表示,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而欧盟则在经历了诸多挑战后,面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欧盟在货币、经济、农业、安全、海关、对外政策等方面实现了高度一体化。但欧盟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和困境也无法忽视。在谈到中欧关系时,郁白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应将欧盟视作带来富饶、发展、和平的世界一极。中欧双方都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将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困难。
郁白曾多次被派驻中国,曾担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法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等职,并曾担任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副司长,历任法国驻蒙古大使、法国驻加拿大大使。他是法国知名汉学家,曾把杜甫、钱钟书等的作品翻译介绍到法国。2018年9月就任欧盟驻华大使。
(许赞超 供稿)
第四十三讲:以文学的方式追述历史
11月2日下午,法国作家、评论家、记者及编剧奥利维耶·盖兹(Olivier Guez)应法语系邀请在北外举办了名为“以文学的方式追述历史——探讨历史调查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讲座。
盖兹在讲座中主要讲述了他创作《魔鬼医生的消失》(LaDisparitiondeJosefMengele)的过程。该作品于2017年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le prix Renaudot),叙写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医生门格勒(Josef Mengele)的战后逃亡生涯和心路历程。
作家着重介绍了该作品创作准备过程的三个阶段。首先,必须决定作品将着重书写门格勒人生中的哪一个部分。门格勒医生的一生分为两大阶段:作为纳粹医生,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杀害犹太人并以人体进行生物和医学实验,犯下滔天罪行;作为战争犯和逃亡者,他辗转躲藏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等拉美国家,逃脱追捕,生活充满跌宕起伏。盖兹对门格勒后半生更感兴趣,不仅因为门格勒的逃亡人生如同侦探与谍战故事般扣人心弦,还由于这个魔鬼医生在逃亡中复杂的心路历程更值得人们思索。虽然门格勒最后没有被捕获和审判,但是在长达三十年的逃亡生涯中经历了种种精神折磨,受到了生命自然历程的惩罚。
第二阶段是积累史实资料。他为创作此书搜集了大量文献档案,这些资料涉及门格勒本人、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医疗系统、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以及德国、阿根廷、以色列等多个国家。此外,他为积累资料做了大量旅行考察,去门格勒曾经躲藏的南美各地亲身体验其逃亡生活。
第三阶段是文体选择。他认为当时有三种选择:史学著作、调查报告或是小说。由于涉及门格勒的档案涉及多个国家且很多尚未公开,因而很难将其创作为史学著作。盖兹先生认为调查报告惯常使用的第一人称会影响叙事节奏,所以放弃了这一选择。因此,他最终以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进行写作。
盖兹先生对于读者关注的史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以文学的方式追述历史时,一方面,作者必须严格遵循史实,基于真实可信的史料进行创作,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许多具体细节与场景难以知晓,作者在这方面可以进行想象,从而拥有创作空间,虚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历史留下的空白。
最后,盖兹先生强调,他并非作为一名法国人来写一个德国故事,而是作为一个欧洲人来写一个欧洲故事。一战和二战使整个欧洲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常常从社会的角度对此做出反思,而他则以个体的视角对欧洲文明进行反思。此外,门格勒的人生经历既是历史潮流的裹挟,也是个人意志的选择,二者的结合决定了个人命运,他的人生道路给后人留下了警示。
(沈逸舟 供稿)
第四十四讲:《阿摩司·达拉贡》的作者布莱恩·佩罗谈创作
11月5日下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著名法语青少年读物作家布莱恩·佩罗先生(Bryan Perreault)应邀来北外做了关于其知名系列作品《阿摩司·达拉贡》的创作历程的演讲。
演讲开始前,魁北克省政府驻华办公室文化与教育专员汤米·哈梅尔先生(Tommy Hamel)向在场观众介绍了布莱恩·佩罗先生的个人成就。布莱恩·佩罗,1968年6月11日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既是加拿大知名的作家,又作为演员、编剧活跃于舞台上。2003年推出了青少年系列读物《阿摩司·达拉贡》,成为加拿大法语地区最畅销的系列之一。之后该系列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在26个国家发行,读者遍布全球,布莱恩·佩罗由此成为魁北克读者群最广的作家之一。
布莱恩·佩罗先生以《阿摩司·达拉贡》系列的创作目的作为主题引入。许多书籍、影视作品似乎都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善即恶”的世界里;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都有着一个相似的走向,即好的一方对抗坏的一方。但在《阿摩司·达拉贡》系列中,他力图构建一个“平衡的世界”,并告诉读者们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一个没有绝对的“黑”与“白”,而是存在着大片“灰色”区域的地方。
佩罗先生谈到了自己写作的动力和灵感源泉:对于神话的热爱。他与在场观众积极互动,引导大家说出神话的四个重要元素:神灵、传说中的奇异生物、民间故事与传说、英雄人物。除了不时举例帮助大家理解,佩罗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这些神话元素的解读与理解。
佩罗先生还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从24岁时初试写作,再到如今闻名遐迩,这一路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坎坷曲折。喜剧演员出身的他,曾经写过三部舞台剧本,但皆未引起反响。但正是这些剧本,激起了他对于写作的热情。在26岁时,他出版了耗时一年时间撰写的人生第一部小说《土拨鼠》,这本小说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售绩惨淡:仅卖出53本。在市场和受众范围有限的魁北克,想要凭借写作谋生无疑异常艰难。他的前十年写作生涯里共出版了三本小说,但一共只卖出了不到一千册。他只能依靠自己教师的职业来谋生,将写作当做兴趣和爱好。直到2002年,有出版商邀请他在一年内完成三部作品,并允诺预付钱款,佩罗先生才真正开始了全职写作生涯。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三部小说大获成功,首印三万册在短短半年内就销售一空。而圣诞节时出版商给他打来的电话,也打消了他心中对于失败的担忧。至此之后,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教师、剧作家,变成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青少年读物作家。
在总结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时,佩罗先生感慨道,要是没有“浪费在前几本书上的时间”,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他也借此勉励在场的同学们:人生有如爬山,有不同的阶段。太仓促的成功容易跌落谷底,只有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才能平稳到达顶峰。
(许赞超 供稿)
第四十五讲:欧洲民粹主义抬头是否值得担忧?
11月14日下午,国家外国专家局聘请的高端外国专家、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前学生事务副校长、社会学与政治学院前院长、政治学教授让-米歇尔·德瓦勒(Jean-Michel De Waele)先生应法语系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中心邀请在北外做了名为“欧洲民粹主义抬头是否值得担忧?”的讲座。
作为民粹主义问题研究的专家,德瓦勒先生首先简单回顾了民粹主义的历史,然后深入阐述了他对当今民粹主义的定义,并分析了当今民粹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最后对中国应该怎样理解与看待当今西方民粹主义提出了建议。
德瓦勒先生认为,在历史上总共涌现过四次民粹主义浪潮。第一次浪潮兴起于19世纪的俄国;第二次民粹主义浪潮即20世纪20至30年代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第三次民粹主义浪潮以战后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为代表;而第四次即当今西方面临的民粹主义,它的形式与内容非常多样化,法国极右翼领袖玛琳娜·勒庞、法国极左翼领袖让-吕克·梅朗雄、当今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等等都是其代表人物。
德瓦勒先生说,政治学家们对民粹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而他本人首先用两个“不是”来定义民粹主义,即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民粹主义也不是一种理论学说。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形式与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带有各国历史文化的烙印,并且它既可以属于左派也可以属于右派。
德瓦勒先生同时也认为,虽然民粹主义十分多样化,但是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所有的民粹主义都将人分为平民与精英,认为平民都是诚实的而精英都是腐败的。民粹主义者们都声称自己是遭受苦难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对抗的是腐朽的精英阶层。其次,民粹主义者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极为简单与直接,他们往往无视当今全球化时代各类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因此,民粹主义者都以弱势群体的代表自居,但其主张的解决方案带来的后果却往往与弱势群体的利益背道而驰,最终付出代价的也往往是弱势群体。
随后,德瓦勒先生分析了当今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当今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他将全球化称为继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革命。他认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介于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一方面,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各地联系日益紧密,一个“地球村”正在逐渐形成。另一方面,许多旧事物被打破的同时,许多新事物却尚未形成。全球化和所有革命一样,会产生胜利者与失败者。对于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全球化是一种机遇,而对那些生活在农村与小城市且并未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失业。这些失败者往往会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同时,由于新世界样貌的不确定性,即使是未受到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地区与人们也易产生一种不安感,这就是为什么移民人口少、失业率低的地区往往会有更多的人投票支持极右翼势力的原因。总之,全球化带来的悲观主义是造成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
此外,德瓦勒先生还认为,媒体也是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媒体很少关注那些受全球化影响而陷入困境的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使得他们产生一种被遗弃感,被推向民粹主义。另一方面,电视、广播媒体在社会议题的讨论上有一种简单化倾向,严肃议题也逐渐被花边新闻所替代,而互联网的发展又极大地方便了仇恨言论以及假新闻的传播,这些都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壮大。
德瓦勒先生对中国应该怎样理解与看待当今西方民粹主义提出了他的建议。首先,他建议我们在分析研究西方民粹主义时分辨各种不同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因为民粹主义不仅仅指极右翼势力,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反体制,也可以是建制派;其次,他建议中国应警惕西方民粹主义,认清民粹主义的实质,因为所有民粹主义都有两个共同观点,一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第二个就是往往会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把中国树立为敌人,将中国指责为西方国家某些问题诸如失业等的来源。
最后,德瓦勒先生强调,我们在警惕民粹主义的同时不应害怕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的目的就是传播悲观与恐惧。他认为应该对全球化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全球化帮助中国以及许多亚洲国家极大地减少了贫困人口和文盲率,并且极大地撼动了西方的中心地位,促进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和多元化发展。因此他鼓励青年们承担起责任,拒绝民粹主义,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