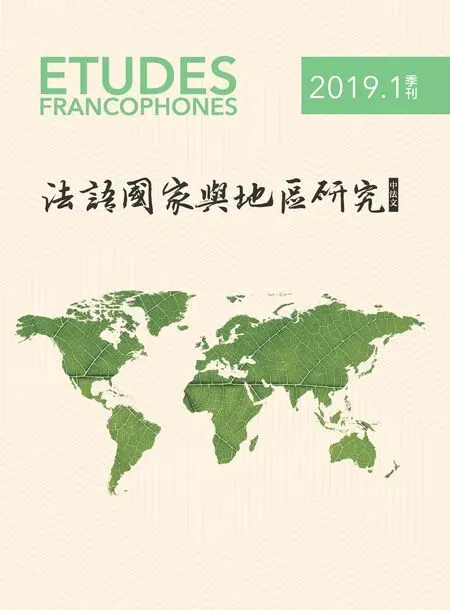苏非兄弟会在塞内加尔社会契约中的角色研究
方圣兰
内容提要 塞内加尔苏非穆斯林兄弟会对社会契约的影响主要建立在其对穆斯林人民的高效治理,及其与政府权力的合作关系上。苏非兄弟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中,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救世主”树立威信后,兄弟会继续在精神教育与物质帮助的过程中获得教徒对其的依附。但兄弟会选择对政府进行权力让渡:它们利用自己与穆斯林人民的联结,积极配合政府发挥巩固统治、推进政策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纽带作用;作为交换,政府赋予兄弟会大量政治经济特权,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引 言
作为一个穆斯林人口比例高达95%的多民族国家[注]塞内加尔境内共有2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沃洛夫族、谢列尔族、富尔贝族、图库洛尔族、曼丁哥族、摩尔族等。参见ANSD,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et de l’Habitat 2002.,塞内加尔在西非国家中始终以社会稳定与民主规范著称。法国殖民时期,它是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国独立运动的温和派。自1960年获得独立后,塞内加尔的政权交替和平进行,始终保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局势。根据《经济学人》发布的民主指数,塞内加尔已于2012年进入“部分民主”(flawed democracy)国家行列,这在非洲国家中屈指可数。[注]The Economist, Democracy Index 2012—2017.事实上,在塞内加尔政府与人民之间高度协调的社会契约关系中,以苏非兄弟会(Sufi brotherhood)为主导的宗教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又保持着国家世俗性原则与宗教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
苏非兄弟会并非塞内加尔伊斯兰教的最初形态,而是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实现平民化的标志。伊斯兰教最初于公元11世纪时从马格里布地区经由毛里塔尼亚进入塞内加尔,即当时的塔克鲁尔王国(Kingdom of Takrur),经历了加纳帝国(700—1240)和马里帝国(1240—1488)时期王室内部的大力推崇和随后的低潮。随着1776年富塔-托洛地区(Fouta-Toro)建立神权国家,伊斯兰教开始逐渐在民间传播。19世纪初,伊斯兰宗教领袖马拉布特[注]马拉布特(marabout),最初指王室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后大批致力于伊斯兰教的平民化,成为宗教领袖。哈吉·奥玛尔·塔尔(Hajj Umar Tal)发起圣战反抗传统王权,抗击西方殖民者,并使伊斯兰教传播至今天塞内加尔的大部分地区。马拉布特运动与苏非兄弟会正是在旧封建王国秩序被摧毁和新西方试图建立殖民体系的这一交界点进入历史舞台。
1. 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的诞生
在王国内部,传统王权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地方贵族间的敌对情绪加剧了社会动荡。在具有伊斯兰圣战传统的富塔-托洛地区,社会阶层分化与部族政治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权力,地方贵族崛起,通过土地控制农民,苛征杂税,激起农民的频繁暴力抗争。在沃洛夫地区,封建君主倚仗的武士阶层(ceddo)权力扩张,社会原有的稳定秩序遭遇严重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压迫和动荡。在外部影响上,法国对塞内加尔事务的干预使国家陷入分裂危机。1844年,富塔地区的法国总督布埃-维劳梅兹(Bou⊇t-Willaumez)在与航海部部长的通信中明确提及“分裂富塔”的计划;[注]Lettre de Bou⊇t-Willaumez au ministre de la Marine. 6 sept. 1844 : A.N.S., 3 B 89; cité dans Chritian Coulon, op.cit., p.25.迪马尔(Dimar)、托洛(Toro)和达姆加(Damga)地区先后于1858年和1860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地”。[注]Chritian Coulon. op.cit., p.25.与此同时,黑奴贸易得到塞内加尔当地政府的默许,造成社会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破坏,并导致相邻部族间冲突不断。在内忧外患之中,马拉布特作为伊斯兰先知,成为农民阶层眼中“当局的对抗者”和“唯一的暴政抵御处”。[注]Ibid., p.60.肩负抗击殖民者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双重使命,马拉布特迅速填补了传统贵族合法性衰落留下的社会权力空白。他们倡导平等与正义,传播苏非主义,创建苏非兄弟会。这些兄弟会将广大伊斯兰民众组织起来,置于马拉布特的保护之下。为了加强组织的有效性和延续性,马拉布特试图超越救世主的单一形象,为兄弟会建设系统性教义,但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已经预示着这一教义的务实性将甚于其宗教意识形态色彩。
2. 苏非兄弟会教义
苏非主义强调“无我”,倡导博爱。学者指出,虽然塞内加尔的伊斯兰教从一开始便表现出政治化的特点,但各宗教团体和兄弟会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同样是其重要特征。[注]Mountaga Diagne. 《 Pouvoir politique et espaces religieux au Sénégal : la gouvernance locale Touba, Cambérène et Médina Baye 》. Montréal (Québec, Canada), Université du Québec Montréal, Doctorat en science politique, 2011, p.55.苏非谢赫(cheikh)教导信徒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交流以促进社会改良。[注]Ibid.这种宽容和开放的精神还体现在兄弟会的非排他性。据记载,提加尼兄弟会(Tijaniyyah)的创始人之一西迪·阿赫默德·提加尼(Sidi Ahmed Tidjni)长期同属其他兄弟会,穆里德兄弟会(Muridiyya)创始人阿马杜·邦巴(Amadou Bamba)也极可能是提加尼兄弟会成员。[注]Vincent Monteil. 《 Une confrérie musulmane les Mourides du Sénégal 》. In : 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no 14, 1962, p.87.宽容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内部以及各兄弟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联系苏非兄弟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教义的另一特点在于实用主义。兄弟会内部最高领袖马拉布特称为哈里发(khalife),其下属马拉布特为各地方谢赫,管理各自区域内的教徒(taalibe)。如前提到,马拉布特的威信一方面来源于其丰富的宗教知识,另一方面建立在对穆斯林民众的保护基础上,因此马拉布特必须保证与教徒之间的“庇护关系” (clientelism)。这种物质性、功利性的联结赋予了谢赫有条件的绝对权威,很多教徒甚至可以“无视穆罕默德先知的存在”。[注]Ibid., p.86.正因如此,塞内加尔的苏非兄弟会常常受到来自穆斯林改革派“蒙昧主义”和偏离伊斯兰正统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塞内加尔的四个苏非兄弟会成为一种十分高效的宗教组织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3. 塞内加尔的四个苏非兄弟会
按照建立的时间顺序,塞内加尔现有的四个苏非兄弟会分别为卡迪里兄弟会(Qadiriyya)、提加尼兄弟会、穆里德兄弟会和拉耶纳兄弟会(Layène)。其中卡迪里兄弟会和提加尼兄弟会皆为外源型和全球性兄弟会,穆里德兄弟会和拉耶纳兄弟会为塞内加尔本土兄弟会,活动范围集中在今天的塞内加尔境内。
卡迪里兄弟会于11世纪建立于中东地区,其创始人是谢赫阿卜杜勒·卡德尔·阿尔·吉拉尼(Abdel Khadr Al Jilani)。它也是第一个被西非穆斯林所接受的兄弟会。18世纪中期,摩尔人(Maure)将卡迪里兄弟会传播至塞内加尔境内,然而其历史上的贵族根基与外来性限制了它的发展,其在塞内加尔的影响范围以今天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Casamence)地区为中心,圣城位于恩迪亚桑(Ndiassane)。
提加尼兄弟会于18世纪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在哈吉·奥玛尔·塔尔、哈吉·马立克·西(Hadj Malik Sy)和哈吉·尼亚兹(Hadj Niass)的推动下广泛建立于塞内加尔各地区,成为今天塞内加尔第二大苏非穆斯林兄弟会,覆盖全国33%的人口,[注]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Pride, Faith, and Fear: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7.圣城位于西部城市蒂瓦万(Tivaouane)。提加尼兄弟会内部支派众多,因此整体组织性较弱。与其他兄弟会相比,提加尼兄弟会更注重践行伊斯兰教义而非培养教徒对谢赫的个人忠诚,且吸收大量中产阶级。克里斯蒂安·古龙指出,这种“教育性”和“中产性”使提加尼兄弟会的发展更具理性。[注]Christian Coulon. op.cit., p.89.
穆里德兄弟会是塞内加尔规模最大的兄弟会,其成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约为50%。[注]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cit., p.97.穆里德兄弟会创始人为塞内加尔历史上最有名望的伊斯兰先知阿马杜·邦巴,同时他还是一位享有世界盛名的诗人。他建设村庄,为动乱中流离失所的农民提供避难所,其对法国殖民者的激烈抗争和因此遭遇的12年流放更为他在穆斯林——尤其是农民中赢得了极高声望。1886年,阿马杜·邦巴建立穆里德兄弟会的圣城图巴(Touba),如今已成为塞内加尔的第二大城市,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穆里德兄弟会的发展与其内部严格的组织和等级体系密切相关,强调教徒对谢赫的绝对忠诚。尤其在农村地区,兄弟会几乎享有绝对权威,深入地参与到穆里德教徒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拉耶纳兄弟会是塞内加尔规模最小的兄弟会,且教徒集中在勒布族(Lebou)中。拉耶纳兄弟会由塞迪纳·利玛胡·拉耶(Seydina Limanou Laye)创建,今天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最西端的佛得角半岛(Cap Vert peninsula)上。其宗教中心为约夫(Yoff)。在教义方面,拉耶纳兄弟会注重平等原则,并和提加尼兄弟会一样,强调对伊斯兰教义的严格遵守和实践。
二、苏非兄弟会对塞内加尔穆斯林群体的影响力
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从建立伊始便直接影响人民利益,对接人民诉求,因此它在社会契约中的作用首先建立在其能够对广大穆斯林民众产生绝对影响力的基础上。这种权威主要来自两方面:精神引导与物质利益。
1. 精神引导
苏非兄弟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将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作为其主要宣教方式。
兄弟会的宗教教育主要在德阿拉(daara)和德赫拉(dahira)这两种机制下进行。德阿拉最初是农村未婚兄弟会教徒团体,其成员在谢赫的土地上进行农业劳动,将农作收入用于建设教育中心,接受技能培训和谢赫的精神教导。[注]Mamadou Mane. Les valeurs culturelles des confréries musulmanes au Sénégal. Dakar, BREDA, décembre 2012, p.29.后发展为兄弟会开设的古兰经学校。截至2012年,塞内加尔已开设约6000所德阿拉。[注]Ibid.随着塞内加尔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中的教徒组织——德赫拉逐渐建设起来,如今已经实现制度化和网络化。在德赫拉中,马拉布特定期组织集体祷告、唱诗会、宗教时事讲座、伊斯兰先知思想解读课甚至麦加朝圣。[注]Ibid., p.31.同时,德赫拉收取一定的会费,组织成员进行营利性工作,所得用于支持日常活动,同时也构成马拉布特的收入。这两种组织并不仅限于宗教学说教育,而是致力于帮助教徒更好地融入现世社会。历史学家指出,德阿拉注重将教徒培养为“有知识、受教育的公民”,使其拥有“社交性、正义感、公正精神”,尊重“家庭权威、社会权威和国家政府权威”,从而认同一个“秩序性、和平、稳定、公正、团结、博爱的社会”。[注]Iba Der Thiam. 《 Les Daaras au Sénégal : rétrospective historique 》. www.Asfiyahi.org, 2010. Cité dans ibid. 访问日期:2018年1月17日。另一方面,德阿拉与德赫拉为教徒与马拉布特提供了思想互动的平台,并在教徒中建立和谐、团结、集体和忠诚等价值共识,同一组织内教徒的宗教归属感可以弥合部族与地域差异,由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歧视和冲突。[注]Mamadou Mane. op.cit., p.31.
除宗教教育外,宗教仪式对于树立苏非兄弟会权威、加强马拉布特与教徒之间的联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塞内加尔,穆里德兄弟会的大马加尔节(Grand Magal)与提加尼兄弟会的穆罕默德诞辰日(Gamou)是规模最大、地位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宗教仪式,用于纪念伊斯兰先知或兄弟会重要历史事件。仪式在兄弟会的圣地举行,通常由哈里发负责筹办,为前来参加的教徒准备丰盛的宴席和各种娱乐活动,开放大型集市为教徒提供商贸交易场所。仪式同时也设置展览、表演和其他文化活动。高度多样的活动安排一方面凸显出组织者的重视程度和背后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调动,因为宗教仪式能够直接更新教徒对其所属兄弟会秩序与实力的认知体会,加深教徒依附兄弟会的受益感。[注]Leonardo A. Villalón. op.cit., p.167.另一方面,从穆斯林教徒的角度来说,宗教仪式是表达对马拉布特忠诚的重要机会。为了加强与马拉布特之间的联结,每年数十万苏非兄弟会教徒通常以德赫拉为单位赴宗教圣地参加宗教仪式,拜访马拉布特,排队数小时以接受马拉布特的教导与福音。
2. 物质福利
事实上,除精神影响力以外,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对穆斯林教徒的控制从根本上来说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教徒对苏非兄弟会的经济依附性是这一关系形成的基本条件。
首先,在塞内加尔农村地区流行一种马拉布特隶农制。从殖民时期开始,各地方马拉布特在法国殖民政府推广的花生种植浪潮中大范围开垦荒地,由教徒自愿无偿耕种,农产品所得归马拉布特所有。以穆里德兄弟会为首的各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一进程中建设村庄,积累了大量土地资源。穆里德兄弟会推崇的“劳作主义”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制度的形成。根据多位学者的记述,阿马杜·邦巴的许多言论表明其对“劳作”这一概念的重视,认为劳作甚至可以取代祷告:“为我劳作,我则为你们祷告。”[注]Lucy E. Creevey. 《 Ahmad Bamba 1850—1927 》. in John Ralph Willis. (ed.) Studies in West African Islamic History, vol. 1: The Cultivators of Islam. London: Frank Cass, 1979: 281; cité dans Kota Kariya. 《 The Murid Order and Its ‘Doctrine of Work’ 》.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no42, 2012, p.56. 法语原文为“Travailler pour moi et je prierai pour vous”.“劳作是宗教的一部分。”[注]Donal B. Cruise O’Brien. The Mourides of Senegal: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n Islamic Brotherh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90; cité dans ibid.. 法语原文为“ Le travail fait partie de la religion”.“劳作即祷告。”[注]Brochier J. La diffusion du progrès technique en milieu rural sénégalais. I.S.E.A., Dakar, 2 vol. (multigr.), 1965, p.142; cité dans Philippe Couty. 《 La doctrine du travail chez les Mourides 》. In : Maintenance sociale et changement économique au Sénégal : 1 — Doctrine économique et pratique du travail chez les Mourides, Paris : ORSTOM, (15), 1972 : 71. 法语原文为“Travailler c’est prier”.“劳作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教徒通过劳作获得物质独立从而追求精神独立;二是将劳作视为教徒效忠马拉布特的方式。在这一逻辑引导下,教徒往往自愿为马拉布特贡献劳动。根据库隆的记载,在德阿拉中,父母令子女受马拉布特全权指挥,献出全部自由,通常直到马拉布特为其找到配偶为止,年轻教徒身心都服从于马拉布特。[注]Christian Coulon. op.cit., p.124.更重要的是,由于马拉布特负责土地分配,教徒也有通过为其劳作得到更多土地的目的,虽然他们依然将个人所有土地的部分所得贡献给马拉布特。研究显示,一位高级别马拉布特可从教徒的私有土地中获得年收入3000—4000万西非法郎(约合36—48万人民币),一位中等级别的马拉布特土地年收入也可达上百万西非法郎。[注]田逸民, 杨荣甲. 《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的影响》. 西亚非洲,1983(5):47-50.学界对这种马拉布特隶农制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榨取教徒劳动成果的“地狱机器”;[注]Jean Copans. Les Marabouts de l’arachide: La confrérie mouride et les paysans au Sénégal. Paris : Le Sycomore, 1980; cité dans Leonardo A. Villalón. op.cit., p.186.而另一些则指出教徒的贡献其实并不会超出合理范围。[注]Leonardo A. Villalón. op.cit., p.189.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兄弟会虽然掌握着土地资源,其权力并非绝对专制。相反,由于教徒有自由选择和更改其所效忠马拉布特的权利,且教徒的数量直接决定马拉布特和兄弟会的影响力,为了加强权威和竞争力,马拉布特不仅需要树立领袖威信,更需要切实保障教徒的物质福利。这些物质关怀不仅来自马拉布特个人,还有兄弟会整体福利体系的保障。穆里德兄弟会的核心机构扎维亚(zawyia)同时是其救济中心、社保机构,并负责农业收入再分配;在德赫拉中也设有互助机制用于资助教徒朝圣、丧礼等重大宗教事件;此外,穆里德基层德赫拉每年定期向兄弟会领导层递交帮扶贫困户名单,由后者与政府部门沟通,商定并落实救济方案。除经济资助外,马拉布特对教徒的帮助可以准确地渗透进个人日常生活,如为单身教徒介绍结婚对象;[注]Christian Coulon. op.cit., p.112.同时也能成为精英事业的重要助力:塞内加尔的所有重要商人几乎都与其所属兄弟会高层马拉布特保持密切关系,因为后者常常能对其打开公共市场发挥关键作用。[注]Ibid., p.114.
此外,苏非兄弟会维护教徒的切身利益。上世纪70年代,塞内加尔的第一个农民自治工会便诞生于穆里德兄弟会。[注]Monika Salzbrunn. 《 Leaders paysans et autorités religieuses comme courtiers du développement en milieu rural sénégalais 》. Bulletin de l’APAD [En ligne]. 1996, mis en ligne le 3 juillet 2007, adresse URL : http://apad.revues.org/801. 访问日期:2018年2月26日。在农村地区,马拉布特一直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与政府部门定期会晤,更多地为农业问题而非宗教事务建言献策。上世纪70年代塞内加尔发生严重旱灾,马拉布特代表农民向政府部门施压,要求上调花生价格;80年代穆里德哈里发在与桑戈尔总统的会谈中也反复强调“政府是农民的依靠”,希望国家关注民生。[注]《 Documents. Paroles mourides : Bambam père et fils 》.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 décembre 1981, p.109.在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下,苏非兄弟会往往成为事实上的社会管理部门。
三、苏非兄弟会与塞内加尔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
塞内加尔的政教关系是较为和谐、互利互惠的。苏非穆斯林兄弟会借助于自身对民众的影响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选举、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中。政府也乐于通过苏非兄弟进行社会管理与权威建设。这种合作模式从殖民时期延续至今,对稳定塞内加尔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殖民时期
在塞内加尔,法国殖民者与马拉布特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妥协的过程。历史上许多苏非兄弟会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者都曾因领导抵抗运动而遭受法国殖民当局流放。但随着殖民秩序的确立,兄弟会和殖民政府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显现,二者逐渐实现了和解甚至合作。
在政治方面,法国殖民者意识到马拉布特在被统治民众中的地位难以撼动后,便转向务实主义的统治策略,意图利用马拉布特的影响力实施一种“间接统治”。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后者的认同。马拉布特在公开讲话中呼吁教徒服从法国殖民者,称赞殖民政府的“仁慈与正义”和对伊斯兰教的尊重。[注]Mouhammadou Mansour Dia. Les daara et leur taalibe : contribution l’étude du problème de la mendicité dans la ville de Dakar. thèse de doctorat, Dakar, UCAD, ÉTHOS, FLSH, Département de Sociologie, mai 2012, p.154; cité dans Mouhammadou Mansour Dia. 《 L’administration coloniale française et la consolidation de l’Islam confrérique au Sénégal 》. Histoire, monde et cultures religieuses, no 36, avril 2015, p.112.相应的,殖民政府也在公众面前刻意抬高马拉布特的地位,并频繁拜访兄弟会重要成员,加强教徒对其所属兄弟会的信心。此外,马拉布特能够帮助收缴赋税、解决土地争端、安抚民众情绪,甚至募军——一战期间,仅穆里德兄弟会创始人阿马杜·邦巴一人便发动了1400名教徒加入法国军队,并因此于1919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注]Ibid., p.180.
如果说马拉布特在政治上的服从更加符合殖民者的利益,那么二者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则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自1840年开始,法国本土对植物油的需求大涨,殖民政府认为塞内加尔的自然与技术条件非常适合推广花生种植以提取花生油。[注]Philippe Couty. op.cit., p.69.各苏非兄弟会纷纷利用这一机会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拥有当时国内70%劳动力的穆里德兄弟会,[注]Vincent, Monteil. op.cit., p.94.积极发动教徒大范围种植花生,以实现农业收益最大化。事实上,塞内加尔将大部分花生产出都供应给欧洲贸易公司,1885年出口花生2.5万吨,1900年出口量倍增至14万吨,1930年达50.8万吨。[注]Christian Coulon. op.cit.,p.71.除农业生产外,教徒也在兄弟会的指挥下大量服务于修路、钻井等其他工程项目。作为回报,法国殖民政府为几乎所有高级别马拉布特都特供一块“秘密土地”,并根据兄弟会中的马拉布特等级决定花生生产合作社社长的人选。合作社用于生产现代化的经费常常大量被马拉布特私人侵用,而殖民者一直默许任人唯亲和腐败的现象,希望通过拉拢马拉布特推动新土地开发。
在文化方面,法国殖民政府虽然一直对伊斯兰教持蔑视和质疑的态度,但选择采取宽容的政策。当局允许穆斯林保留信教的权利,为建立古兰经学校与清真寺提供资金支持,为非洲公务员参加宗教仪式设置专门假期,甚至建立伊斯兰法庭、尊重伊斯兰教法。[注]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 A Secular Age and the World of Islam 》. In :Tolerance, Democracy and Sufis in Senegal, ed. Mamadou Dio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4.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塞内加尔伊斯兰教的延续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这些利益交换,马拉布特对殖民当局的妥协并未损害其在教徒中的威望,相反,由于马拉布特的让步换取了殖民者相应的利益保障,教徒的受益感加强了其与马拉布特之间的“庇护关系”。对他们来说,服从与合作只是换取更多利益的方式。随着合作模式的加深,苏非兄弟会更加认可法国殖民统治下稳定的社会状态,并通过游说对1958年塞内加尔全民公投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使塞内加尔继续留在法兰西共同体中,直至1960年才获得独立。
2. 独立时期
独立以后的塞内加尔采取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但其政教合作依然表现出相当的延续性。面对建立国内新秩序的困难和心存疑虑的民众,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edar Senghor)采取庇护主义政策,通过宗教力量巩固政府权威,1960—1968年是这一政策发挥效用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政府给予苏非兄弟会马拉布特尊贵待遇并赋予大量特权。首先,宗教仪式被视为行政事务的组成部分,政府提供大量资金与物资,增设朝圣专列,派遣安全人员维护现场秩序,并派相应级别官员出席仪式,通知媒体进行大范围宣传报道以显示对宗教事务的重视。第二,马拉布特及其教徒享有一定的“豁免权”。据记载,图巴的部分区域禁止政府人员和警察进入,却对宗教人士敞开大门。[注]Mountaga Diagne. 《 Décentralisation et participation politique en Afrique : le rle des confréries religieuses dans la gouvernance locale au Sénégal 》. ARUC-ISDC, Recherches, no 18, 2008, p.17.苏非兄弟会高层马拉布特便可利用此类特权在教徒犯罪时对其加以庇护,尤其是走私罪。桑戈尔总统的亲密盟友法里卢·穆贝克(Falilou Mbacké)担任穆里德兄弟会哈里发期间,图巴的走私问题达到顶峰,甚至有民间传言“所有被警察追捕的商贩进入图巴就会得救”。[注]Momar, Coumba Diop. 《 Les affaires mourides Dakar 》.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 décembre 1981, p.91.此外,马拉布特拥有重要经济特权。1964年塞内加尔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然而事实上大量土地依然被划归马拉布特所有。[注]Christian Coulon. op.cit., p.241.农产品销售中,马拉布特也拥有特殊渠道以获取更高利润。在城市里,商人与马拉布特往往关系密切,利用后者在政府部门的影响为行政手续创造便利,甚至进行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作为交换,苏非穆斯林兄弟会是巩固政权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支柱性力量。首任总统桑戈尔虽为天主教徒,却成功与兄弟会的重要马拉布特,尤其是哈里发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宗教领袖曾在50年代桑戈尔与拉明·盖耶(Lamine Gaye)的政治斗争中给予桑戈尔有力的支持。1962年,桑戈尔与总理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的对抗构成塞内加尔独立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危机。虽然迪亚本身是提加尼兄弟会教徒,但由于桑戈尔温和的经济政策更加符合马拉布特的利益,穆里德兄弟会哈里发和提加尼兄弟会的重要家族均选择支持桑戈尔,最终议会投票通过对马马杜·迪亚的不信任案,称其策动政变,将其逮捕,结束了这场政治风波。在政府合法性构建方面,兄弟会能够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80年代末以前的选举中,马拉布特往往对教徒直接下达明确的投票指令。[注]Ibid., p.212.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指令几乎确保了社会党桑戈尔及其接班人阿卜杜·迪乌夫(Abdou Diouf)的连选连任。[注]Cruise Donal O’Brien. 《 Le “contrat social” sénégalais l’épreuve 》.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5, mars 1992, p.17.
2000年塞内加尔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后,新任民主党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依然十分重视与苏非兄弟会的关系,与其所属的穆里德兄弟会哈里发来往尤其密切,并特别承诺促进图巴的发展。其接班人也从无神论者改宗为穆里德兄弟会教徒,据此有学者预测未来选举中会出现“根据兄弟会投票” (vote confrérique)的现象。[注]Leonardo A. Villalón. 《 Senegal : Shades of Islamism on a Sufi Landscape 》. In: Political Islam in West Afric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ransformed, ed. William F.S.Mile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174.同样,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苏非兄弟会是政府与民众冲突中的缓冲剂。1968年塞内加尔首都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兄弟会所有高层马拉布特纷纷发表讲话,命令教徒保持冷静;穆里德兄弟会哈里发则直接派遣700名教徒至达喀尔“保护政府”。[注]Cheikh Anta Babou. 《 The Senegalese “Social Contract” Revisited 》. In : Tolerance, Democracy and Sufis in Senegal, ed. Mamadou Dio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31.
3. 新时期的社会契约转型
然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大量穆斯林向城市和国际范围转移,动摇了大部分原以农村地区为权力中心的苏非兄弟会的权威基础;随着兄弟会内部和国家整体的代际交替,新一代掌权者和年轻群体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与认同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社会党在大选中的落败显示马拉布特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已经大为弱化。事实上,早在1988年,迪乌夫总统颇具争议的连任已经引发塞内加尔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在逐渐自由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继桑戈尔总统之后的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先后针对兄弟会问题表示要与“惰性、保守、倒退等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决裂[注]Christian Coulon. 《 La démocratie sénégalaise : bilan d’une expérience 》. Politique africaine, no 45, mars 1992, p.3.、推动“变化”[注]瓦德总统2000年大选的竞选口号,沃洛夫语为sopi。。现任总统麦基·萨勒(Macky Sall)虽不避讳其穆里德兄弟会成员身份,但已越来越注重在个人宗教信仰与政治决策之间划清界限。而在苏非兄弟会层面,塞内加尔两大兄弟会的新一任哈里发都表现出远离政治的态度。[注]Lucy E. Creevey. 《 Muslim brotherhoods and politics in Senegal in 1985 》.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no 4, 1985, p.720.更有谢赫表示与政府关系过密的马拉布特已经越来越难吸引新的教徒。[注]Cheikh Anta Babou. op.cit., p.140最终,1988年大选事实上也成为各兄弟会哈里发最后一次对教徒发布投票指令的选举。但值得注意的是,苏非兄弟会作为穆斯林人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并未动摇;另一方面,苏非兄弟会内部出现分化趋势,一些马拉布特开始成立政党,正式进入政治领域。因此不能排除苏非兄弟会和塞内加尔政府间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正在酝酿之中。
结 语
塞内加尔苏非兄弟会的实践表明,伊斯兰教作为人民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政府权威的修护工具,在塞内加尔社会契约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为人民与政府之间搭建了有效互动的桥梁。宗教对人民的影响不仅依托于精神信仰,更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政府借助宗教力量维系统治,则以各种形式的特权作为回报,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可以看出,苏非兄弟会从殖民统治初期社会运动的主导者转型为社会治理的辅助者,如今仍进一步收缩其政治影响力。兄弟会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获得利益回报,但不可否认地为塞内加尔的社会契约与稳定秩序的维护做出重要妥协。随着新时期塞内加尔伊斯兰世界内部进一步分化,原有的社会契约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但苏非兄弟会尊重世俗权力、重视与政府对话及妥协精神的传统如宗教影响力一样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也将帮助它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