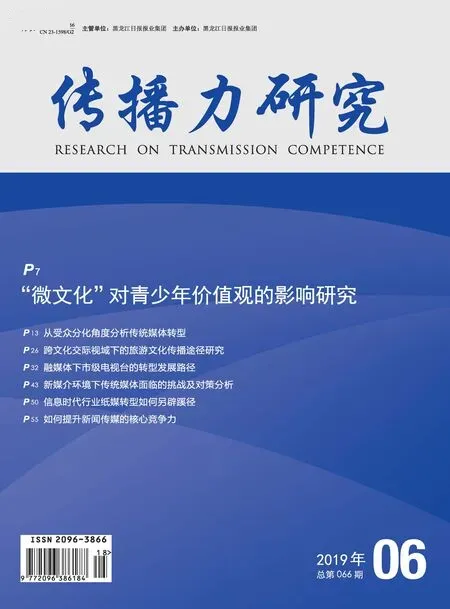“树典型”之研究综述
田丰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一、相关概念
典型原意是铸造用的模具,后来衍生出“模范”的含义。中国在历史上通过表彰“忠”“孝”“节”“义”的典型人物来进行教化,以达到自身执政目的。毛泽东于1943年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将树典型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来阐述。
二、社会学取向下的“树典型”研究
目前的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被引用最多的是学者刘林平、万向东所著的《论“树典型”——对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模式的社会学研究》。他们认为,树典型和民族心理中的群体主义取向有关,和计划体制下的政治本位、领导本位的价值取向等因素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治者通过教化和奖惩把施政理念内化为被统治者的行为动机。采用树典型能节约经济激励费用、节省管理成本和起到“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1]
学者黄鹏进则从乡村治理角度,对树典型策略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树典型”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德治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技术”[2],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集体化动员的一种娴熟的技巧性艺术”[3]。这背后的逻辑是“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式。研究者同时也指出了“典型”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异化”,失去了树立典型的政治初衷。
学者苗春凤从社会评价论的视角,认为典型是权威评价活动的产物,有助于权威机构加强对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在当代社会中,权威机构仍然需要树立典型提倡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社会整合,但必须坚持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相结合。[4]
学者郭晓宁则以来自军队的两个案例为例,对转型期的所面临的国情和多元文化涌现后,带来的政治权威与民间大众的结合,促进典型影响力增强进行了阐述。[5]
学者韩志明、顾盼以“典型政治”及其运作为例,研究了价值分配的国家逻辑,认为树典型是一项国家治理技术,其实质是围绕伦理价值而建构起来的权威性分配行动,主要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需要。相对于由法律法规所建立起来“硬”性惩戒体系,典型政治具有调控社会行为的“软”功能,并主要通过优劣对比机制、简单重复机制、双向选择机制和宣传学习机制等来运作。[6]
三、传播学取向下的“树典型”研究
“树典型”行为其实质就是一个传播行为,是主流价值符号塑造和传播的过程。
学者苗春凤结合当下日益多元的传播环境,提出要引入互动仪式链,通过建构典型的符号,来构建和引领社会公认的价值观。[7]他呼吁要注重传与受的“互动”,将树典型带入到具体的情景中去,重塑社会认同、符号认同和价值认同。
学者张杨波分析了广东省妇联开展的“好丈夫、好妻子”评选活动的传播效果,研究结论不仅扭转了人们以往认为典型在树立之后肯定会产生预期效果的传统观念,而且部分证实了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回飞镖效应的存在。[8]
四、总结与讨论
社会学取向下的“树典型”研究对于社会治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具有指导意义。政治权威越来越注重大众评价,这将带来政治行为模式的改变。传播学取向下“树典型”研究则从传播五要素着手进行了梳理,开始有学者注重效果评估,开始研究受众,这是传播学科引入的一大优势,对于更好的进行“树典型”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已有的文献多采用质化分析,对“树典型”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的引入、现状的概述上,鲜见采用量化分析,研究还未深入,对当下信息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和价值观多元的研究还很欠缺。
当今社会,树典型依然是社会治理、企业(组织)凝聚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技术路径,随着消费社会的浪潮继续深入发展,异化后人们会产生“返祖”现象,他们呼吁人性的回归,他们需要符号的价值和价值观的引领,将多元价值观、碎片化的个体重新聚合在一起,寻得“心灵的安宁”,这将成为社会治理和组织发展的稳定基石。
未来,“树典型”要更加注重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借助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借助大数据的优势,从典型的选取、诞生、塑造、宣传和维护整个流程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和受众的需要,使得“树典型”这一古老的治理模式“老树发新芽”,焕发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