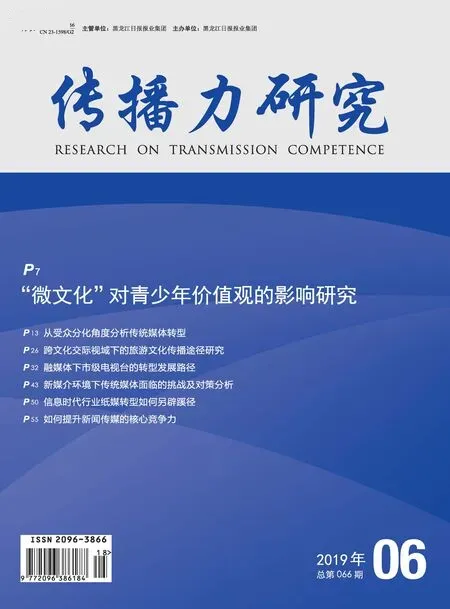纪录片与真人秀的类型融合
——从《奇遇人生》看真人秀节目的新表意实践
刘相如 湖南师范大学
一、引言
里芬斯塔尔认为,“艺术就是感知真实状况的本质,并且把那个真实时刻的形成、内容与意义转化成电影。”[1]这成为广义纪录片的基本信条。可见,纪录片与真人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试图将具有“真实”本质的内容传达给观众,以完成其意义的表达。但是,对“真实”与“虚构”两者比例拿捏的不同使真人秀与纪录片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了本质区别。
《奇遇人生》是腾讯视频推出的国内首档明星纪实真人秀节目,在全球范围内,阿雅与十位明星好友在节目中分别展开十次旅行。基于嘉宾对自我与人生的感触和向往,为其专属定制一次“诗与远方”的体验之旅。在这个过程中,嘉宾们向外丈量世界的长度,向内探究心灵的深度,以感悟人生,认知自我。作为腾讯视频推出的“创新化产品”之一,《奇遇人生》在具备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创作元素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纪录片的拍摄方式,是对纪录片与真人秀类型融合的一次巧妙尝试。那么,这种新表意实践为当代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增添了何种可能性想象?对《奇遇人生》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心理机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寻找到答案。
二、纪录片之纪实美感
从《幸运52》等益智博彩类真人秀,到《爸爸去哪儿》等户外体验类真人秀,真人秀节目形式不断演变。与纪录片的类型融合并非《奇遇人生》之首创,创新之处在于,它一改过去真人秀节目的作“秀”之态,是一次在真实基础之上的新表意实践,明星、剧本、目标在《奇遇人生》里不再是制造噱头与冲突的手段,而是为客观真实服务,大大削弱真人秀本身具有的肤浅的娱乐性,这份从容怡然的情感基调使《奇遇人生》在众声喧哗的电视节目中得以脱颖而出。
《奇遇人生》的创作初衷是增进对世界的理解与自我的认知,在这种向外探索与向内认知的二元架构下,宏大与个体之间碰撞出的强烈张力内化为如诗般的情感体验。与展现地理风貌或风土人情的传统自然人文纪录片不同,《奇遇人生》以个人的脚步丈量世界,走进自然,在每段旅行中向外观人生百态,向内见心灵波澜。第一期非洲看大象可以看到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多重情感;第二期追逐龙卷风告诉人们要享受过程,也要顺应规律;第三期印尼攀峰,是有舍也有得,放弃不一定意味着失败。在剧情与情感的铺陈中,自然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山川湖海,而更添一份真实与可贵。通过个体与自然、内心与外界的相互观照,观众会不由得萌发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之感,“想象共同体”便瞬间得以建构。
节目开篇词说到:“地球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人类七十四亿四千万。当我们凝视世界时,世界也凝视我们。当我们遇见他们时,我们也遇见了自己。只有出发才是一切的开始。”《奇遇人生》每期都会依照嘉宾特点与个人喜好选择“奇遇”的内容,以一段旅行作为线索,并以崇尚纪实风格的“真实电影”的拍摄方式进行纪录。每段“奇遇”都是一次对“我是谁”、“我去往何处”的答案追寻,这两个抽象的哲学思考在旅行中化为具象的行为与情节,而在这一次次记录中,记录者不会对被记录者的选择与表现加以干扰,人物的行为都是其内心真实的映现。也就是说,节目不止关注嘉宾对“我是谁”、“我去往何处”的思考,也关注对“我如何思考‘我是谁’、‘我去往何处’”的记录。在第六期节目中,朴树与阿雅一起前往古巴,当哈瓦那的东道主在跟大家聊他家庄园的事情时,朴树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觉得非常无聊,摄影机利用多角度特写捕捉到朴树面部细微的反应。这种将不完美毫无保留地呈现于镜头前的纪实感,使得被记录者的行为、言语变得格外真实、生动。正如让·鲁什所认为的那般,“真理纪录片”的功能就是:“人们都被激发表现出了他们虚构部分;同时,它又绝不仅仅是一部故事片,因为它所展现的虚构部分都是真实的。”[2]
三、真人秀之审美期待
虽然纪录片也是有拍摄计划的,但并不会规定被记录者的行动去向。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奇遇人生》同样根据当事人的特点为其提供了情境、设定了任务——展开一段旅程。在节目推进中,在将被记录者的所去之处、所见之人这些“已知”一层层展现的同时,旅程中的“未知”也在悬置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期待。在第二期节目中,阿雅与春夏一起去追逐龙卷风,在常规节目设置里,追逐的最终结局必然是追到。节目在一次次追逐中不断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这种常规积累,观众可以在追风者们的一次次欢欣鼓舞中达到追寻的价值体验,而当最后没能追到龙卷风时,打破了观众的期待惯性,但追风向导马丁所言“虽然我们追不到龙卷风,但是在风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色”,“它就像一道自助餐,看你享用什么”也唤起了对自然的尊重和对过程的重视,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绪起伏也调动起观众的独特审美体验。追风人春夏从没追到的失落到被开导后豁然开朗并说:“生活中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你想要的,和你拥有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你曾经那么接近过那个目标,但你就是碰不到。”至此,节目在已知情境的“顺向相应”和安抚“逆向受挫”的审美期待后完成了内涵与意蕴的升华,颠覆性叙事使观众得以脱离故事本身,在“得到”与“放弃”、“过程”与“结果”的选择中获得全新感悟。
除了个体与自然、内心与外界的相互观照使观众感同身受而建构起“想象共同体”外,通过社会自然风貌的展现,《奇遇人生》完成了观众集体认同的建构,又通过不同明星的参与,完成了个体认同的建构。从台湾知名主持人小s、脱口秀红人李诞、到创作歌手毛不易、音乐人朴树、歌手白举纲、“小魔女”范晓萱,再到个性女演员宋佳、金马奖影后春夏、魅力演员窦骁,《奇遇人生》选择了主持界、音乐界、演艺界的不同知名人士,这些人物组成了一个由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所形成的小社会。明星选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收视率高低,而知名度只是众多考虑因素之一。理查德·戴尔提出了明星与观众的四种关系模式:情感喜好、自我认同、模仿、投射。[3]在对明星荧幕形象的熟悉喜爱的基础上,从明星的行为与情绪中去感受、体悟,是形成认同的关键一步。第一期节目中阿雅与小s去到大象养殖基地,拍摄中途突然得知有两只小象走丢,小s从小象走丢联想到自己的小孩不见,两人蹲在地上不能自已地潸然泪下。此时的小s与阿雅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她们回归质朴,真情流露,观众与褪去明星光环的小s与阿雅达成个体认同,完成了个体对明星的身份想象,同时更能深刻体会到小象之于动物保护者们的重要性。而当节目中武装侦察队前往秃鹰盘旋的地区,拍摄到一头被杀取走象牙的大象尸体,象鼻被像垃圾一样丢弃在一旁时,观众也会经历与小s同样的震撼,会对保护动物、尊重自然产生强烈的认同。在观众与银幕形象建构起的个体认同中,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被认可与强调,这或许是《奇遇人生》的深层意义。
四、结语
真人秀本身就是纪实与娱乐的结合,虚实相生,浑然一体,打造出其独特魅力。随着真人秀“纪录片化”的趋势愈加显著,真人秀也在探索的道路上朝着一种新的表意形式不断演进。《奇遇人生》将记录片的纪实之美与真人秀的审美期待巧妙融合,形成了一种介于纪录片与真人秀之外的独特叙事语言,带给观众以精神和心灵的启迪和思索。这种新的表意实践,或许能为真人秀节目的良性发展打开新思路,而对节目制作者来说,对“真实”和“虚构”的理解,对两者比例的权衡,则需要具备更多的智慧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