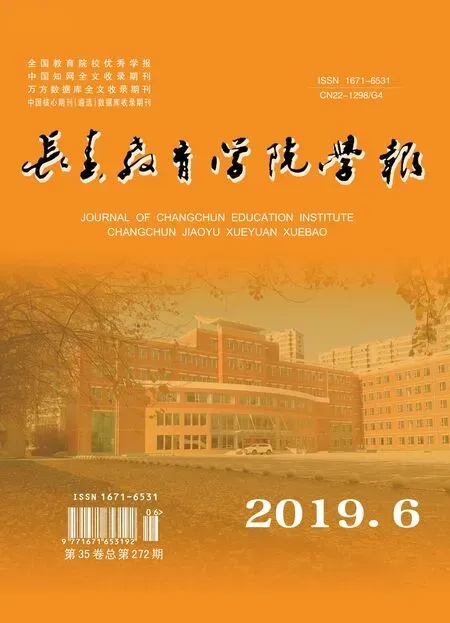时代与人性背后的自我反思
——论《芳华》的悲剧人物形态
谢 秋
在严歌苓的小说《芳华》中作者以局外人萧穗子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那一代人难以忘却的青春回忆,一群满怀理想的青年男女在军队文工团这一大集体中经历着情感的启蒙与难以掌控的人生命运。有着文艺兵经历的严歌苓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讲述的那段逝去的故事,有着自叙传的色彩。同时叙述人与我的游离、变换使得小说不仅在叙述手法上有了新突破,也在这种虚实之间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的真实。其以刘峰的“触摸事件”为中心,呈现了个体不同类型的悲剧,英雄的悲剧、性格悲剧、欲望导向下的婚姻悲剧,在其背后映射出欲望的追求与人性的弱点。在严歌苓的反思与忏悔中,“芳华”这两个字并不是一种讽刺,也不是一种歌颂,它是岁月终归平静的温柔。
一、理想主义光环下的英雄悲剧
刘峰是这场“芳华往事”的核心。在伊甸园式的文工团里他是起模范作用的“活雷锋”,在屠宰场式的战场上他是人们心中的英雄,他的存在印证了平凡即伟大的时代价值取向。又名“雷又峰”(又一个雷锋)的他是文工团里公认的好人,无论是谁的事他都乐意帮忙。大到给结婚的炊事班长打沙发、帮助外号“括弧”的残障孤儿挑水、开导恋爱受处分的萧穗子、主动为受人排挤的何小曼伴舞……小到自觉吃烂饺子、帮女兵找落在棉被里的缝衣针等等,“这个自知不重要的人,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1],成为大家心中的活雷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唯一首要之点,是性格必须善良……意向的善良,性格亦善良”。[2]从一件件平凡普通的小事情中,我们感受到刘峰的善。也正是这种善使刘峰一步步完成理想人格的建构,使他从本能的“自我(Ego)”人格走向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人格。换言之离“超我”越近,也就离完美越近,离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来越远。当然刘峰人性光辉的闪耀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场域,孟繁华在评《芳华》时曾说:“这是一部今天与过去对话的小说,那是一个简单、透明、单纯和理想的时代。”在那个特殊的理想化历史语境中,向完美人物的靠拢成为社会的主流,人性本善的自我显现不仅让他成为英雄典型走向神坛,也在无形中也使他成为政治话语符号的代表。
但是在这种理想主义的光环下,乌托邦式的美好与现实生活之间并不存在“同构关系”。在众人眼中近乎完美的刘峰“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人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错什么的。”[3]个体的善良与集体无意识领域的嫉妒在时代的底色中不断斗争着,这种“善”与“恶”的冲突以“触摸事件”为标志,将人性的复杂多变展现得淋漓尽致。天生自带娇嗔的上海女孩林丁丁唤醒了“活雷锋”内心的柔软,在爱的启蒙下发生了“触摸事件”,这给众人一个借口、一个契机让他们把刘峰拉下神坛,人性中的卑琐冲撞着崇高,昔日的英雄在集体的重压下被吞噬,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如果说前半段助刘峰走向神坛的自我意识为他贴上“活雷锋”的标签,那么这也成功摧毁了他。因为任何一种标签都是一种阉割,“活雷锋”是被阉割的男人,雄性荷尔蒙自带的攻击性与青春期的爱、欲望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都要受到压抑,一旦出现就要被阉割。这个被异化的如千斤巨石般的标签一直约束着刘峰,使他只能按照圣人的模式去生活,稍有差池便为千夫所指。冲动与压抑、本能与理性在刘峰身上不断分裂,他“不能体验自身是自身的核心……分裂化的人找不到自我,恰如他找不到他人一样。”[4]刘峰为标签所绑架,他的自我人格无处安放、无法表达,唯有抗争、超越才能实现自我意识的表达,所以那压抑的灵魂驱动肢体对林丁丁发出了那一记触摸。看似偶然的触摸背后暗含着其发生的必然性,因为随着自我意识的深化和理性主义精神的强化,“人的精神已经跟旧日的生活与观念的世界决裂……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5]。黑格尔将悲剧这种表现历史必然性的本质称为永恒的伦理力量。“活雷锋”标签下的刘峰在异化的生存空间上备受挤压,他不断寻找着自我的主体意识,于是他独立的个人意识与普遍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悲剧性的冲突。在不可预期、不可靠、变幻无穷的人性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换来林丁丁一句“救命!”“批判者从中国传统道德角度、从军队的组织纪律出发把这件事定义为作风问题而加以批判”。[6]但是对于从本性出发的刘峰而言,这是无意识领域里的行为,“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力量的否定和损害予以实现,结局就是它们在伦理意义上,并且通过伦理意义来看,它们都是有罪的”。[7]这两种普遍的永恒力量之间的斗争不断继续着,最终刘峰在那场任人宰割的批斗会上屈辱地低下了头颅,辛苦多年铸造的自我意识被毁灭成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也正是人在实现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体现出悲壮”[8]。刘峰个人虽然遭受到毁灭,但是他所代表的人性之善与人类的自我意识却得到了历史的认可,永恒的正义正是在个人的毁灭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本性善良的刘峰在摔下神坛后依然不改初心,残酷的战场成为磨练自我最好的舞台。在生死之间他毅然选择牺牲,为驾驶员带路先送补给。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那只曾经触摸过林丁丁的手,成为英雄。“截肢”这一事件颇含隐喻,在失去“犯过错误”的手臂后,战斗英雄刘峰南下卖过盗版图书,与妓女小惠有过短暂的温暖回忆。这些行为看似是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背离,但是不完整的刘峰反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满人格,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9]他超越了“雷锋式”的时代英雄,拥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魅力。但是命运的罗网再次出现,社会底层讨生活的刘峰在经历妻子的抛弃后竟身患绝症。好人刘峰的遭遇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0]对于刘峰而言,善是本能更是一种选择,集体的背叛、生活的苦难依旧未曾改变他的本心,这是人性的闪光点;对观者而言,在面对不应遭殃而遭殃的刘峰时会产生哀怜,这种强烈的刺激给观者一个机会,不仅能使其认识自我,也给现实生活中遭受苦难的观众提供一个正当发泄的机会来疏解其压抑的心理;另一方面遭殃的刘峰因为和我们类似,才更能引起恐惧。我们见证了因小错误而引起一连串巨大灾难的英雄刘峰陨落的全过程,虽然情感在泛滥,但是人生的痛苦在艺术描写中不断被升华,最终在恐惧中使情感与理性得到净化与重生。从林丁丁、萧穗子到郝淑雯,无论是当事人、批判者还是旁观者,其中的罪与罚都在这场被阉割的青春中被不断反省着、忏悔着,生存与死亡、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些困扰着人类心灵的内容也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伸张正义、舒展人性的光辉。
二、环境影响下的性格悲剧
《芳华》的英文名是“You touchedme”,这里“触摸”一语双关,如果说触摸让刘峰身败名裂开启了英雄的悲剧,那么它同样挽救了何小曼,开启了人性的救赎之路。小曼的故事开始于她的父亲,那个一生善良最后终于善良的男人,她的故事完结于刘峰,那个一生善良最后依然善良的男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右倾主义者女儿身份出生的何小曼生来就带有原罪,后来亲生父亲畏罪自杀,她像“拖油瓶”一样跟随改嫁的母亲依附于继父,由此开始了她的悲剧人生。性格执拗的何小曼在新家备受冷落,对母爱的渴求成为支撑其成长的唯一动力。现实的境况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她发现那个为了女儿能够有优越生活而牺牲自己的母亲已经不再是亲妈了,而那个看似沉重的牺牲,也只是女人寻找更好庇护的便捷途径。她本身的导向就是自私的,伏低做小也只是为了给自己换取更多的利益。破旧的衣服给小曼、破了皮的饺子给小曼……这些打着爱、牺牲的名义深入生活的冰冷细节逐渐浸润着何小曼。在对爱的渴求与畏惧,对母亲的期待与愧疚,对家庭的失望与恐惧之中何小曼的性格被扭曲,她的希望不断被摔打、被挤压、被蹂躏得体无完肤。这使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卑微,这种自卑的性格不仅给她的生理、心理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决定她对未来行为的选择,是其悲剧性人生的彰显。
渴望与匮乏是成正比的,失去情感支撑的何小曼离开了那个为她左右为难的母亲,以及继父组建的与她无关的家庭,带着卑微与脆弱投奔到三千里外的文工团。看似放弃、妥协的离开,其实是何小曼对原罪人生做出的第一次反抗,她放弃家庭转向寻求集体的认同,渴望集体这一避难所能帮助改变其卑微的命运。但是那敏感自卑却又极度渴望爱的性格让她难以在集体中生存,美好的文工团在给了她短暂的庇护后亦造成了她的悲剧性命运。当众人发现“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等”[11]。这些小毛病在女兵里普遍存在,并没有被看成真正的毛病。童年时期的那些悲惨经历给她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以往的行为养成人的性格,而已养成的性格又决定着人对未来的行为方式”。[12]所以,那些怪异的行为是其生理病态与心理病态的延续。因为在那个所谓的“家”里,冷漠的继父、取悦他人的母亲、没有血缘的弟弟妹妹都不曾给她任何温暖,被忽视、被倾轧的小曼在这种环境下逐渐被异化。她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去厨房偷吃的又或者人前将肉杵起来,人后再一点点啃。正如保姆所说:“小曼就像村里的狗,找到一块骨头不易,舍不得一下子啃了,怕别的狗跟她抢,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以上种种不仅仅映射着小曼贫乏的物质生活,更暗含着是其心灵深处对亲情的渴望。毛衣事件中,她拆掉母亲心爱的红毛衣,将其染成黑色又重新织成新毛衣,就是在向母亲宣告“你的本来就该是我的”。眼看着就要彻底失去母亲的她干脆把自己浸在冷水盆里,因为只有生病才能分得母爱的一瓢羹,所以萧穗子曾多次说过热爱生病、热爱危险、热爱伤痛的何小曼在潜意识里是求死的,这种向死而生的状态对何小曼的生理与心理都产生不小的影响。进入文工团的何小曼重蹈着被忽视、被厌弃的覆辙,那个欠缺青春发育为了女性自尊而在乳罩上填塞海绵的小曼陷入了被众人围堵责辱的窘境。对美的追求是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这不仅仅是自卑的小曼一个人的潜意识,更是红楼中一群女兵乃至全体女性上千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但是在文工团的高压环境下,爱美是一种罪恶,这何尝不是对女人的人性阉割。严歌苓说过:“我为小曼的行为着迷,为她许多不可理喻的行为感到难为情,但更为形成她那些行为的社会和我们这个集体感到难为情。”[13]在集体与社会的生存空间中,这种偏见不断蔓延致使她被舞伴嫌弃。面对众人的冷漠与讥笑,刘峰如暖阳一般,主动要求托举她,“他托举起的不仅是何小曼的身体,更是她一向敝帚自珍而他人熟视无睹的人格尊严”,[14]为处在痛苦与毁灭边缘的何小曼带来希望。这是对个体意志与人格尊严的重新确证,显示出生命的永恒力量。随后发生了触摸事件,刘峰的被迫离开彻底让小曼对集体寒了心。所以在高原慰问演出中她以发烧来反抗集体迟来的关注与赏识,但真相大白后她落得与刘峰一般被处理的下场,成为集体的弃儿。刘峰的悲剧颠倒了顺序发生在她的身上,小曼于战场上的无意之举在被集体放大后使她成为新一轮的思想标兵,一个始终被集体忽略、被集体排除在外的人,突然间成为集体的英雄。她和刘峰一样都经历了神坛的起伏,登高跌重的“活雷锋”陨落了,揠苗助长的何小曼也疯了。弗洛伊德认为:“人类防御机制的过度使用与神经症(neuroses)联系在一起,神经症是与过度控制本能有关的变态行为的焦虑驱动模式。”[15]而在歇斯底里的精神中症隐藏着“一个人通过失调的症状来避免一些对意识而言太痛苦或者太令人恐惧的体验”。[16]忽视与关注、歧视与荣耀都出现在何小曼的身上,巨大的反差令她恐惧,最终精神崩溃。这样一个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珍视善良。在崩溃中自愈的何小曼找到生病的刘峰,照顾他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何小曼于脆弱与卑微的性格中经历着毁灭与希望、畏惧与渴望。最终恶被驱逐,善在无形中被传递,所以何小曼的悲剧性成长历程正是对善的谢恩。
在何小曼无奈而尴尬的成长历程中,父亲的逝去、母爱的缺失让这个幼小的心灵过早体会到世间的冷暖,物质与精神空间的重压造成难以弥补的生理病态与心理病态。正如布拉德雷所认为的那样,“悲剧的结局源于主人公的行为……而行为的过失是由性格所决定的”。[17]在寻找亲情乃至集体认同的道路上,脆弱自卑的何小曼在讨好的过程不仅仅割舍了人的尊严,更是丧失了自我。在这种获取与丧失的恶性循环中刘峰的出现让她骤然醒悟,于是在生活的阴暗与命运的捉弄面前,何小曼以拯救的本能实现了自我的重新确证。从心底感受到“由人类的尊严而生的振奋之感”。[18]这正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悲剧的本质。
三、欲望追求下的婚姻悲剧
相较于不受重视的何小曼,天生自带三分病的上海女孩林丁丁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首长的掌上明珠。但在人性与时代的较量中,那个“单纯”“天真”的林丁丁终究成为老友嘴里“一只假手都不愿摸”的笑料。将嫁入高官家庭当成人生终极追求的林丁丁,总能够迅速吸引并撩动男性简单粗暴的荷尔蒙,而她自己的荷尔蒙却是冷的。在两性的修罗场上,把婚姻当成筹码从而摆脱现状的欲望和冲动一直左右着她,因此挣扎的痛苦也与其相伴,所以“触摸事件”中林丁丁对刘峰落井下石也不难理解。在时代的转变与人性的压抑中,林丁丁于渴望与失败的痛苦之间摆动,展现了这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欲求与挣扎的全部本质。欲望是她的不竭动力,也是将她推向深渊的黑手,她在欲望的驱使下上演着婚姻的悲剧。
在人性压抑与特定时代发展的矛盾冲突背景下,林丁丁以人性与时代二重奏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人其天性就是利己主义,人的天性或者说人的生命意志若不加以道德的约束最终会成为悲剧的根源。她一早就懂得生得好不如嫁得好,因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一心嫁给高官子弟做豪门阔太的欲求成为林丁丁全部的生命意志。“就欲望这个话语概念本身而言,它是生命生存和延续的必要条件,是生命的本质属性”。[19]虽然欲望的实现伴随着主体价值的确认,但其实现的过程却时常对抗着道德、理性,因此欲望的实现方式是必须要考量的。温暖善良的刘峰太过平凡,权利与金钱等实际利益的缺乏使他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得到林丁丁的青睐。刘峰被她理想化的人格所蒙蔽,所以她们的感情从始至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那一记触摸换来的是林丁丁在组织逼问下为求自保的出卖。缺乏道德约束的意志助长了她的生命冲动与欲求,但是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由于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与冲动,因而痛苦也就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只是永恒痛苦中短暂的间歇,并且正是人生的致命伤”。[20]主体因此就在欲求—满足—新的欲求中不断尝试,这种缺乏理性约束的欲望带来一系列的恶果,所以这种欲望越是强烈,主体的痛苦也就越明显。在欲望的驱使下抛却良知,又经过千万番努力如愿嫁入“豪门”,成为首长儿媳的林丁丁在获得短暂的满足后,意志中的可欲之物随即消除,缺少了欲求对象后可怕的空虚与无聊席卷而来,因此在文工团养成的嗑瓜子、吃零食的习惯越来越严重。事业无成柔弱娇巧的林丁丁被夫家嫌弃,学历低下的她在妯娌的嘲讽下逼迫自己紧跟时代潮流念了函授大学,但进修无果便更讨人嫌。那个刘峰爱了几年才敢触碰一下的掌上明珠因英语水平不行不能随丈夫出国,成了一个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可怜人,最终落得一个被豪门吃掉青春馅儿,剩下个半老徐娘的皮扔出来的下场。为了洗刷失败的婚姻经历,非海外华人不嫁的她再次盲目嫁到了海外。老公是个开快餐店的潮州人,让她吃边角料的鸡翅尖,包馄饨春卷包到手指皴裂。本以为可以获得幸福的婚姻也难逃精明的丈夫与小叔子的盘算,连青春的皮都让人吃了。“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既是人生的悲剧,也同时又是艺术的温床,因为它能激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和共鸣,具有悲剧心理学方面的意义”。[20]从众星捧月到最后的孑然一身,欲望驱使下的林丁丁最终丧失在欲望的海洋中,她不仅失去一切资本,也放弃了曾经的梦想。漂泊海外的她最后沦为保姆给人看房子,那个轻声细语的豌豆公主在现实面前变成一个笑声嘎嘎的泼辣妇人,那些曾经的美好在欲望中幻灭,到头来落得一地鸡毛。
男女两性于先天、后天的差异导致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被动性与不稳定性,因此众多女性将爱情、婚姻当成生活的全部。正如黑格尔所说:“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并推广成为爱情,他们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到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第一阵狂风吹熄掉。”[21]爱情之于女性就犹如赋予其重生的机会一般,所以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不长久的。那么对于放弃爱情追求欲望的林丁丁来说,当她眼前的欲望获得满足后,新的欲望又会接踵而至。欲望无穷但是满足却是有限,所以缺乏爱情支撑的失控欲望是导致其悲剧发生的根源。因此,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性冲突中读者体会着青春的狼狈与残酷,其背后暗含着严歌苓深切的反思意识与自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