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颗心
【英】斯蒂芬·韦斯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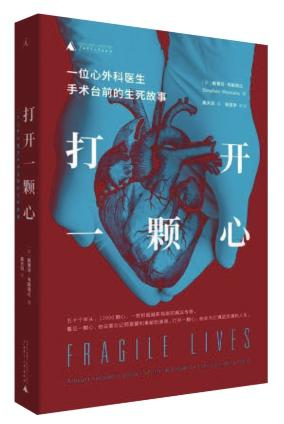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我经手过12000颗心脏。”
工薪家庭的穷小子,幼年时被医学纪录片鼓舞,也被亲人的离世刺痛,终于将自己历练成一名杰出的心外科医生。在展现心胸外科手术的神乎其技之余,作者也在书中借病症、病患和自己的业务游历,揭示了人世百态,展现了一名外科医生眼中所见的悲伤与爱,以及对医疗制度、伦理和医学教育的反思。
①
那是在1987年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我当时年轻无畏,自认为英勇无敌,自信得膨胀。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家富有声望的沙特心脏中心,服务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病人。他们的主刀医生请了三个月的病假,想找个临时代理,要求能同时做先天性和成人心脏病手术——这种人属于极端珍稀品种。我当时并不在意,但第二天就来了兴趣。三天之后我跳上了飞机。
当时正值主马达·阿色尼月,是中东的“第二个干燥月”。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炎热,猛烈的热气从不停歇,名为“夏马”的热风卷着沙子吹进城里。不过那家心脏中心还是很好的。我的医生同事汇集了各路人才,有的是在海外受训过的沙特男人,有的是为获得经验从大医学中心轮转过来的美国人,还有的是从欧洲和大洋洲组团来挣大钱的医生。
护理就很不同了。沙特妇女不做护士,因为沙特人对这门职业怀疑而不敬,沙特文化也禁止妇女从事护理,因为干这行需要与异性混在一起。因此这里的女护士都是外国人,她们大多只签一两年的合同,在这里享受免费食宿,不用缴税,等存够家乡的房贷就会离开。她们不能开车,乘公车时只能坐在后排,在公共场合要把身体完全遮起来。
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让我很感兴趣:宣礼塔上反复传来礼拜的号召,医院里总有一股檀木、焚香和琥珀混合的诱人气味,阿拉伯咖啡烘烤在平底锅上,或是和豆蔻一起煮沸。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告诫自己绝不要越过界限——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规矩,违反者会受到严厉惩罚。
这也给了我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接触任何你能想到的先天性心脏异常病例。大量的年轻病人因为风湿性心脏病从遥远的乡镇转到这里治疗,他们大多接触不到西方习以为常的抗凝疗法或药物。
这里的农村医疗还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我们在治疗中不得不有所创新和发挥,修补他们的心脏瓣膜,而不是用人工材料替换。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想法:每一个心臟外科医生都应该去那里历练历练。
一天早晨,一位年轻聪明的小儿心内科医生来手术室找我,他来自梅奥诊所,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座世界闻名的医学中心。他的开场白是:“我有个有趣的病例,你想看看吗?你以前肯定没见过这样。”紧接着又说:“可惜呀,你恐怕也做不了什么。”还没等看过病例,我就决心证明他想错了,因为对外科医生来说,罕见的病例永远是挑战。
他把X光片贴上灯箱。这是一张普通的胸腔X光片,上面的心脏呈现为灰色的阴影,但在受过专门教育的人看来,它仍能透露关键信息。很明显,这是一个幼童,他的心脏扩大,而且长到了胸腔错误的一边。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称为“右位心”——正常心脏都位于胸腔左侧,他的却相反。另外,肺部也有积液。不过单单右位心并不会造成心力衰竭。他肯定还有别的毛病。
②
这个热情的梅奥心内科医生是在考验我。他给这个十八个月大的男孩做过心导管检查,已经知道病因了。我提了一个富有洞见的猜想,卖弄说:“以这个地区来说,可能是鲁登巴赫综合征。”也就是说,这颗右位心的左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二尖瓣也因为风湿热而变得狭窄,这是一个罕见的组合,使大量血液灌入肺部,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处于缺血状态。我赢得了梅奥男的敬意,但我的猜测还差了一点。
他又提出带我去心导管室看血管造影片(在血流中注入显视剂,再用X光片动画揭示解剖结构)。这时我已经烦透了他的测试,但还是跟着去了。在病人的左心室里,主动脉瓣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团块,位置十分凶险,几乎截断了通向全身的血流。我看出这是一个肿瘤,不管它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婴儿都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能摘掉它吗?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右位心上动手术。做过这类手术的年轻外科医生很少,多数永远不会做。不过我很了解儿童心脏肿瘤。我甚至就这个课题在美国发表过论文,这位小儿心内科医生也读过。在这个领域,我算是沙特境内的专家。
婴儿身上最常见的肿瘤是反常的心肌和纤维组织构成的良性团块,称为“横纹肌瘤”。这往往会导致脑部异常,引发癫痫。没有人知道这可怜的孩子是否发作过癫痫,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颗梗阻的心脏正在要他的命。我问了男孩的年龄,还有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接着,他的悲惨故事展开了。
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着儿子穿越了也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找医学救助。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那里,他们发现她仍在设法为孩子哺乳。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她来自一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阿曼的医生看了男孩的胸腔X光片,诊断出右位心和心力衰竭,然后就把他转到了我所在的医院。梅奥男想看看我能不能施展魔法把他医好。我知道梅奥诊所有一位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这位同事丹尼尔森大夫会怎么做。
“应该会做手术吧。”他说,“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手术风险了,不做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料到他会这么说。
“好吧,我尽量试试看。”我说,“至少要弄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关于这个孩子,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不仅心脏长在胸腔里错误的一边,就连腹腔器官也全部调了个儿。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内脏反位”。他的肝脏位于腹腔的左上部分,胃和脾脏则位于右边。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因此从身体和肺静脉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这意味着通过动脉流向他身体的血液含氧量低于正常水平。要不是因为皮肤黝黑,他或许已经获诊为蓝婴综合征,也就是动脉中混入了静脉血。真是复杂的病情,就连医生都觉得头疼。
③
在这里钱不是问题。我们有最先进的超声心动图仪,这在当时还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设备使用的是侦测潜艇的那种超声波,一名熟练的操作员能用它绘出心脏内部的清晰图像,并测出梗阻区域的压力梯度。我在他那小小的左心室里看见了一幅清晰的肿瘤图像,它的样子光滑圆润,就像一枚矮脚鸡的蛋,我敢肯定它是良性的,只要摘除,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的计划是消除梗阻,关闭心脏上的孔,从而恢复它的正常生理机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理論上简单直接,但是对一颗前后颠倒、长在胸腔错误一侧的心脏来说却相当费力。我不想中间出什么岔子,于是做了每次境况艰难时都会做的事——我开始绘制详细的解剖图。
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就算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对他也依然有帮助;但如果开胸后发现那是一颗罕见的恶性肿瘤,那他的前景就很不妙了。不过我和梅奥男都确信这是一颗良性的横纹肌瘤。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很不喜欢。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她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美得令我震惊,像极了大卫·鲍伊的遗孀,那个叫伊曼的模特。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环抱在胸前。红十字会已经证实了她来自索马里,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她的头发并没有包起来。她手指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着乳白色的溶液,里面注满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好让他细小的骨骼上重新长出肉来。
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没说话,只是望着地板。带着卖弄的心情,我继续问道:“你懂阿拉伯语吗?”接着是:“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我走投无路了,终于问道:“你会说英语吗?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边上的梅奥男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我还有这项语言技能;他不知道的是,我几乎只会说这几句阿拉伯语。这位母亲似乎很感谢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了下来,心里松开了。我想对她表达善意,想抓起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在这个环境里,我做不到。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还抱在她手里就行。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他的肤色与母亲不同,我猜想他父亲是个阿拉伯人。他那深橄榄色的皮肤上盖了一层奇怪的皮疹,我似乎在他眼中看见了恐惧。
男孩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张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打开一颗心》)
链接:
【作者简介】斯蒂芬·韦斯塔比(1948— ),英国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主任医生,世界一流的心外科手术专家和人工心脏专家。参与过1万多台心外科手术,其中有很多极为精彩、惊险甚至开创性的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