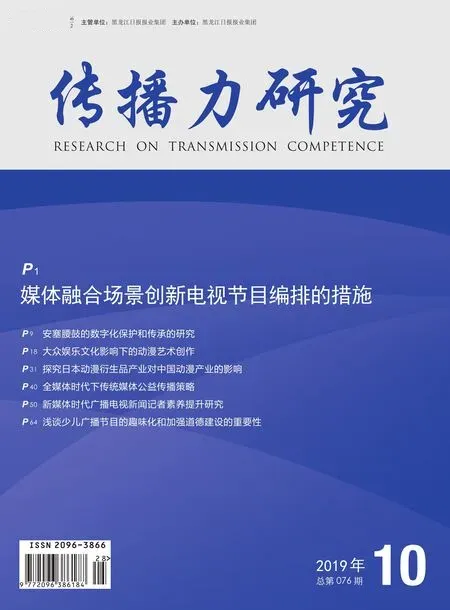电影创作中“戏剧单元”的运用探究
——以《兵临城下》为例
陈孜 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不断有学者针对电影创作方法做出研究,并且迄今为止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这些都成为各位艺术家在电影创作道路上的垫脚石,为推进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
“戏剧单元”本属于剧本创作中的戏剧性元素之一,“我们可以将戏剧单元看作是散文的段落:包括一个最重要的戏剧思想。让戏剧性思想相互分离将给予它们更大的力量,让他们在观众眼里变得更加清晰。就像在散文中,当我们转到另一种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另起一个段落,让读者指导思想的跃进。在故事片中,我们会让观众知道叙事或戏剧变化的发展。”[1]
而戏剧单元的划分方法并不仅局限使用于剧本创作中,如果导演在具体影片拍摄中恰当的使用这一方法,能够在银幕上充分发挥剧本最大戏剧潜力,使影片层次更加明确,从而帮助观众能够形成更加清晰的观影思路。例如在电影《兵临城下》中,对划分戏剧单元这一方法的使用就获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影片脉络的宏观把握
电影就像是在给观众叙述一个故事,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导演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更加需要明确故事讲述的逻辑顺序与叙述节奏,同时还要针对表达意图区分出故事的主次部分。这就需要导演在创作环节中能够首先从宏观角度把握影片脉络。
电影《兵临城下》是由让·雅克·阿诺导演执导的战争题材影片,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中的一位平民狙击手瓦西里·柴瑟夫与德军顶尖神枪手康尼少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生死较量。这部影片在整体创作诉求上有两点:一是完成对平民狙击手瓦西里·柴瑟夫的人物刻画,而这也是影片最主要的中心点,二是对战争环境的展现,增加影片的真实感。
这部影片从宏观角度上可划分为四个戏剧单元,而划分戏剧单元的主要依据需要围绕创作诉求展开,也就是瓦西里·柴瑟夫这一人物交代,他的存在是整部影片的中心点。第一个戏剧单元除了完成必要的开场任务之外,主要用于交代战况,但却并不是为了展现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苏联红军连连溃败的现状来凸显这位平民神枪手的重要意义;第二个戏剧单元在前面的铺垫下,正式开始塑造瓦西里的神枪手形象,这时人物的出现对于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人物的崇高形象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制高点;到了第三戏剧单元就开始为人物设置障碍,也就是德军少校康尼的出现给瓦西里带来了一连串的挫败感,所谓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由此开始;而后面瓦西里与康尼的对决就可以归结为第四个戏剧单元,直至影片走向结尾处。
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戏剧单元的划分,明确自己的创作逻辑,将符合段落要求的情节点进行归类划分,从而进一步对试图传递给观众的信息量进行聚拢强化,而这首先就需要从宏观角度对影片的整体层次进行把控。
二、影片情节的微观刻画
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需要逻辑严密清晰的故事脉络,还需要在刻画具体情节点时能够精准生动,而在这一部分,可以将戏剧单元的划分与剧作功能进行融合统一。首先剧作的三个功能依次是叙事、抒情与刻画人物,可以说电影中无论是大到场次,还是小到每一个对话节拍,导演都应该明确其剧作任务是什么,而其目的是能够更精准的把控影片结构,进而确保叙事节奏。
在《兵临城下》中,第一次正式塑造瓦西里的平民神枪手形象,是在帮助政委狙击敌方几名军官的情节点中完成的,而在这一情节点中同样可以从微观角度对其进行戏剧单元的划分。这一部分可以划分为两个戏剧单元。第一个戏剧单元的剧作任务是抒情,也就是展现出当下的紧张感和危机感,而在这一剧作任务下,相对应的选择了先交代政委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在当时状况下政委的慌乱和技能的生疏,通过环境和政委的双重铺垫,由此为第二戏剧单元打下坚实基础;因此第二戏剧单元的剧作任务显是塑造人物,顺理成章的完成了对瓦西里果敢、技艺高超的形象塑造。
在这两个戏剧单元中导演围绕创作诉求将主要篇幅落在了第二戏剧单元,明显在人物塑造上做了强化处理。正是通过对该情节点戏剧单元的划分,从而不仅保证了紧凑的叙事节奏,同时高效的完成了当下段落的剧作任务。
三、结语
电影创作中,导演在明确创作目的和诉求的前提下,需要把握如何让观众准确的获取影片传递出的关键信息,而最高效的方法就将信息集中化处理,把符合诉求的信息放置在一整段“地理位置”中,从而强化信息的传递力度与深度,这也就是将“戏剧单元”的概念运用进具体创作中的目的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