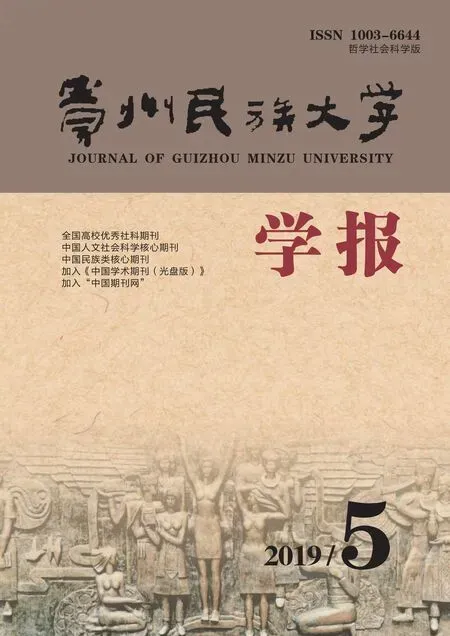大通老爷山花儿文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霍 福
自赵宗福先生发掘出明代诗人高弘《古鄯行吟》:“青柳垂丝夹野塘,农人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古诗以来,西北民歌花儿的形成历史便可靠地前推到明代万历年间。[1]64后来在河湟地区形成了若干个花儿会,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便是其中之一。老爷山花儿会与当地朝山会息息相关,这一观点被研究者不断提起[2],有人推测朝山会形成于明代中叶。[3]关于老爷山花儿会,有研究者推断其酝酿于18世纪中叶之后,形成于清末[4],这些推断尚待进一步研究。据张亚雄《花儿集》说,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爷山花儿会就已经是西宁附近规模与影响最大的花儿会,从六月初四至初六为期三天的花儿会期间,各地会唱花儿的男女青年不论远近,都赶来比赛花儿。[5]96
花儿以口头程式形式在民间传承。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文人学者开始搜集整理和研究花儿,在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出版相关成果,出现了文本传承。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花儿不断火爆,出现了视频、音频等新的传承形式,并且在花儿研究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下,文人创作花儿成为一种新潮,出版了大量作品。赵宗福先生指出,老爷山花儿会曾经是青海东部最大的花儿会[6],参加花儿会的歌手来自“各地会唱花儿的男女青年”(张亚雄语),所以文人们搜集出版的河湟花儿文本,也可以看作是老爷山花儿的传承文本。
一、花儿文本搜集
(一)书面文字搜集与整理
在口头程式阶段,民间歌手们创作了诸如“西宁”“老爷山”“郭莽寺”“石榴花”“杨六郎把守三关口”“尕马儿骑上枪背上”“青石头尕磨儿左转哩”等等若干个花儿大词,这些传统大词在后来搜集整理的文本中反复出现。爱情花儿和生活花儿为花儿传承的两大类型。爱情花儿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而生活花儿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别是抗日花儿、反封建压迫花儿、揭露马家军阀统治花儿、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花儿、歌颂新生活花儿、大炼钢铁、“大跃进”花儿等都深深印上了时代的烙印。爱情和时代两大主题也反复出现在文本之中。
早在明代时,花儿便已进入文人视野,出现在一些文人作品中时,但只是提到其名字而已。因为是“心上的话”,花儿演唱是一种“心声”的表达,歌唱者们又多为文盲,这些山歌野曲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形成文字。在民间或有手抄本流传,但其范围很小,基本没有公开出来。
自觉地进行花儿文本搜集整理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推动下,1925年,袁复礼在《歌谣周刊》第82号发表《甘肃的歌谣——“话儿”》,收录花儿30首,其时青海尚未建省,仍属甘肃省,其中《西宁的骡子下来了》和《西宁的大路我走过》两首花儿都属于老爷山花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亚雄对花儿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文本搜集和整理。自1928年张亚雄在北京大学新闻系学习时开始接触搜集花儿,后来利用在《甘肃民国日报》工作的机会搜集花儿,1931年起在《甘肃民国日报》登载,共收集到3000余首花儿。在此基础上,他于1940年出版《花儿集》,共收录歌词600多首,其中有大量河湟花儿文本,如“郭莽寺仔溜宝瓶。铁丝儿拉下的扯绳。出来个大门难打听,你是脑阿哥仔扯心。”并注“仔”是“的”,“溜”是“绿”,“脑”是“我”的西宁读法,作者注重在民俗语境中整理花儿文本。作者还注意搜集西宁一带流传的“西宁令”和“东峡令”,包括尕马儿令、尕阿姐令、尕寿令。[5]84张亚雄指出,“尕寿令”是“东峡令”中的翘楚,又名“才让曹”,“才让”藏语意为长寿,故称为“尕寿”,对该“令”的来源做了生动解析。张亚雄《花儿集》花儿文本搜集传承与范式对后来的文本搜集整理影响很大。
1941年,钟世隆《青海民歌的一斑》(1)钟世隆.青海民歌的一班[J].新西北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西北民歌专号”,1941年1月出版:15-20。将青海民歌分为小曲(俗名杂耍或小唱儿)、秧歌、山歌(俗名少年或花儿)、儿歌。文章说:“山歌的流行,无论在时间空间方面,都有很大的范围,尤以耘草时期为最盛。大半以恋爱为主。歌唱时常不以乐器配合,但也可以奏出来的。(也没有制就的曲谱)虽然同一山歌,可以拿三四种音调来唱。如尕马儿拉回来,水红花,花儿阿姐等。”作者引用20首花儿,并做了适当注解。
1941年,史仲《“花儿”一束》(2)史仲.“花儿”一束[J].新西北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西北民歌专号”,1941年1月出版:25-26。整理了12首花儿,并做了注解。作者说:“花儿一名少年,多言情之作,在西北流行之区域颇广;此处所录者,均为青海东部所常闻。”
除张亚雄外,其他搜集者多因文章介绍需要,引用一些花儿文本,但数量有限。1942年,曹默在《西北论衡》第十卷第四期“西北民俗专号”发表《三陇的花儿》,文章收录10首花儿,有一首为“西宁的作风”花儿。曹文还引《大华晚报》记者殷伯华在游记中记述的四首花儿,并且引用殷氏的原话说:“(1935年)到了临夏,承这位忠厚的老驴夫的好意,详细背诵了四只通俗的民歌,虽然句调是俚鄙的,但热情的暖流在字里行间奔放着。我舍不得割爱,把他抄过来”。《西北论衡》同一期还登载了江源《青海的民俗和民歌》,文中记录了13首花儿,江文在文末特别注明说:“上抄歌词中因需要写出原来语气及含义,故有的地方把原有的土语照录,差白字当所难免,尤其许多同音字,最容易以讹传讹,好在这是真正的民间文学,我们先保存其本来面目,然后再去仔细研究。”1947年,萌竹发表《青海的花儿》[7],记录数首花儿。
总体而言,上述花儿文本搜集整理行动是在当时全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些地方文化人所进行的个人搜集整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花儿搜集整理被纳入国家文化工作中,搜集者大多为国家公职人员,其工作与单位性质息息相关,出现了有单位、有组织、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花儿文本,花儿文本的传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50年11月,擎夫、寒荔出版《西北民歌集》[8],在第一册“第一辑陕甘宁旧民歌”中收录有一首“花儿”,有六段歌词,“兰州的木塔藏的经,阿哥的肉呀,拉卜寺上的宝瓶”等大词,这些词在青海传统爱情花儿中也常常出现。同书收录有10首对唱花儿《正是杏花二月天》,每首均注明“男唱”或“女唱”。
1954年3月,朱仲禄整理出版《花儿选》[9],朱仲禄当时在西安西北人民歌舞剧团工作。该书收录花儿歌词700多首,内容分为爱情“花儿”对唱,洮泯“花儿”对唱,一般“花儿”,反映劳动、斗争的“花儿”,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花儿”等六辑,绝大部分是河湟花儿。本书所整理的花儿分类细致科学,在“爱情花儿对唱”一辑中,作者就从追求、斗争、波折、别离、重逢、情遇、其他等七个对唱反映整个情节线索的发展过程,并对对唱作了说明。在“其他”类型部分还收录有《正是杏花儿二月天》《尕娃对唱》两组对唱花儿,《正是杏花儿二月天》出现在擎夫、寒荔所编的《西北民歌集》第一册陕甘宁之部中,朱仲禄将原来标注的“男唱”“女唱”简化为“男”“女”,比较简练。“一般花儿”收录228首歌词,除情歌外,还有大量反映农民、牧民、商人、小贩、工匠、脚户哥、黄河筏客、学生等的一般生活花儿。“反映劳动、斗争的花儿”收录歌词116首,反映了青海老百姓和士兵在马家军阀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情绪,以及老百姓对旧社会的痛恨与斗争精神,而“十二月忙”反映的是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儿”收录35首歌词,并特别说明其中后13首歌词在形式上与花儿有区别,是一种和小调很相似的花儿形式,只能用“花花尕妹”曲调来歌唱,其他花儿曲调不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花儿”歌词中,17首为歌唱解放军,18首为歌颂领袖,38首为劳动生产、抗美援朝及其他。朱仲禄《花儿选》可以看作是花儿文本搜集整理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文本搜集中往往还收录有曲谱,此后歌词与曲谱走向分化,出现了单纯的歌词本或曲谱本。
1957年12月,王歌行和刘文泰出版《花儿和少年》[10],内容分为“歌唱新社会”“爱情花儿”“历史花儿”“控诉”等四辑,其中《东海岸升起了红太阳》《合作化高潮到来了》《合作社好比大花园》《给祖国把绿袍罩上》《中朝人民心连心》《右派分子们错打算》等歌词,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1958年4月,达玉川出版《青海花儿选》[11],收录花儿歌词400多首,内容分为“歌颂新时代的花儿”“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花儿”“爱情花儿”等。1957年5月,兰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季成家、辛存文、富礼、进仓、呼晨等五人深入到青海民和、乐都、湟中、湟源、化隆、循化、大通县搜集整理民歌,他们历时38天,从8 500多首花儿和藏族民歌中筛选编辑,于1958年4月出版《青海山歌》[12],收录约800首山歌,绝大部分是花儿,内容分为“控诉旧社会”“赞美新生活”“情歌”。1958年5月,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青海花儿选》歌词本,内容分为“苦难的年月”“爱情花儿”和“为幸福歌唱”三辑,爱情花儿则由“开场”“热恋”“重逢”“波折”“相思”“盟誓”“结尾”“余音”等八章组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与朱仲禄《花儿选》收录的七章爱情花儿对唱本相比较,本书收集的花儿在情节安排上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与《花儿选》的歌词没有重复,是另一套完整的唱词。
1958年开始的新民歌运动,以及“文革”中推广的所谓村村举办“赛诗会”中(3)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社论,全国兴起新民歌运动,1959年3月由于毛主席的否定,新民歌运动偃旗息鼓。参见胡光曙.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J].世纪,2011,(3)。,花儿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内容,这些新花儿被不断搜集刊登在报刊杂志和各种花儿选集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也是花儿文本传承的一大特征。大通县在新民歌运动中据说涌现出了上千名诗歌作者,坚持经常写作的不下百人,他们的作品发表在《大通报》上,还被中共青海省委民族民歌收集整理办公室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大跃进歌谣选·大通专辑》。[13]5311959年9月,中共青海省委民族民歌收集整理办公室编辑出版《青海民歌选》歌词本[14],本书为插图歌词本,收录了一些花儿歌词,如《总路线光芒撒金线》《公社好比是天梯》《公社花儿万年开》《铁炉上映红了钢铁花》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而《蒋马匪帮吃人狼》属于传统民歌中揭批地主剥削、百姓生活困苦、军阀拔兵等内容,控诉斗争气息浓厚。
1960年1月31日《青海日报》登载专题《花儿怒放,歌儿飞扬——我省首届“花儿”现场会“花儿”选编》[15],选登了大通代表队的一首花儿:“鸡冠花开一树红,初升的太阳一盆金;公社好比旭日升,金光闪闪照前程。”1960年6月20日《青海日报》登载《歌声笑语不停点,千文万诗把党赞——西宁红光生产队诗歌“花儿”选登》[16],刊登了16首红光生产队业余创作组创作的“花儿”,可见当时新民歌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
1960年元月,中共青海省委民族民歌收集整理办公室和青海省文化局在民和县举办全省“花儿”现场会,来自大通互助村的62岁农民韩友鹿编唱了数首花儿,纪舜《“花儿”会巡礼》一文作了记录:“坐上火车往民和,“花儿会”上来观摩。我今年已六十多,也要高唱跃进歌。/下了火车过冰桥,千里歌手齐来到,万颗红心争上游,齐心合唱公社好。/千条河水万重山,现场大会找经验;万朵“花儿”齐争艳,著名花冠民和县。”据说这位不识字的农民编了千百首新花儿。[17]18-201960年《青海湖》第3期“东风得意百花艳”栏目发表《满园春风花儿红,首首花儿把党颂》花儿22首,《水利绿化保丰产,积肥深翻间春耕》花儿27首,《钢花铁水闪金光,车水马龙幸福长》花儿11首,《花儿装进炮膛里,大辩论中显威力》花儿6首,可见当时花儿在省级刊物的登载量比较大。1960年6月,中共青海省委民族民歌收集整理办公室编辑出版《青海歌谣》歌词本[18],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大跃进”和新民歌创作大背景下的歌谣词作,其中也收录了若干首传统花儿歌词。1961年7月3日《青海日报》以《各族人民齐声歌颂党和毛主席》为题,发表数首花儿,其中有一首回族花儿《幸福的“天堂”里到哩》:“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亮明星西山上照哩;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幸福的‘天堂’里到哩。”[19]1975年9月2日《青海日报》登载《土族人民唱新歌——记互助土话自治县大菜子沟大队开展新“花儿”创作活动的事迹》[20],文章说“1974年,大队党支部社员群众开展了新民歌创作活动。新‘花儿’宣传新思想,新思想带来新干劲。……不仅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推动着大队各项工作呈现出新面貌。”并用一首花儿形容:“社员们挥笔登文坛,新民歌,充满了革命的情感;干劲冲天歌满山,春意暖,新‘花儿’漫红了春天。”文章说大菜子沟大队党支部先发动两个青年民兵写了两首新“花儿”,拿给社员群众看,进一步启发了大家。1974年10月,卜锡文、强克杰出版《手搭凉篷望北京(新花儿选)》歌词本[21],本书前言说明在1973年秋季和1974年春季,甘肃师大艺术系革命民歌调查组赴甘青宁收集整理,内容分为“红花向阳”“战鼓雷鸣”“新歌满坡”“金色大道”“高原飞歌”等类型,每首新花儿只有歌名和演唱民族,没有注明收集地点和曲令名。因为作者搜集的目的是反击阶级敌人的复辟,将新“花儿”作为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得力工具,所以新花儿都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属于革命“花儿”,也是当时的时代花儿。
1978年,《青海文艺》刊登专题《华主席给我银铃嗓——青海省民歌会演选辑》[22],发表大通佛留花(土族)创作的两首花儿,表明花儿出现了回归民俗和田野的趋向。1979年10月,西宁市文化馆编印《西宁演唱》特刊之《花儿集》(内部资料),后记说明整理者坚持了忠实记录的原则,新编花儿以打倒“四人帮”后新创作的作品为界限,传统花儿选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各种选集中没有的作品。搜集的文本来源于花儿会上的现场记录,搜集者的原始记录,以及各州县的油印本。1982年7月,朱刚出版《传统爱情花儿百首》歌词本[23],搜集整理爱情花儿100首,只有题名和歌词。本书也标志着1976年之后,花儿搜集整理重新回归花儿的爱情主题。1986年,大通县文化馆编印《大通花儿集》(内部资料),本书是为编辑中国民间歌谣集成而先期编成的青海省大通县卷,共收集花儿1 500首,是第一本较为全面的老爷山花儿文本集。1987年8月,雪犁、柯扬出版《西北花儿精选》[24],内容编排上分为“上部洮岷花儿”和“下部河湟花儿”,河湟花儿又分为“开头歌”“对唱歌”“短歌”“叙事歌”等四个部分。在“对唱歌”部分,“抗日少年”“正是杏花二月天”都是传统花儿内容,“正是杏花二月天”对唱花儿则删除了朱仲禄《花儿选》歌词中的“男”“女”标注,虽然从唱词上可以区分出男女歌词,但也会有一定影响。“短歌”由《模样儿咋这么俊来》《维不下朋友没活头》《开心的钥匙就是我》《尕妹的心,就像钢刀刃子》《龙离了长江的水了》《想起尕妹的模样子》《心上的尕妹看走》《花枕头一对儿放来》《宁打官司不丢手》等爱情花儿组成,是本书份量最重的内容,而歌词文字更趋于书面化。2012年7月,本书由青海人民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第2版第3次印刷。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花儿文本传承经历了主题的演变,起初的文本以爱情花儿为主、兼有时代花儿;中期以爱情和时代花儿并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时代花儿为主,爱情花儿次之,甚至消失;1979年以后爱情花儿又重新引起重视。
(二)花儿曲谱搜集与整理
曲谱是花儿文本重要内容,但整理难度相当大。正如1941年《新西北月刊》弁言所云:“首先感到的是记谱,往往会唱的不会记,会记的不会唱,会唱会记并在一起,尚可解决,但是许多人不会唱,会唱的你又没有接触的机会,即有了,也不易接近,而让你慢慢记下来。何况记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在西北会记的更是稀罕得很!退而求其次,专记词吧,蒙藏语文懂者固少,就是翻译出来,歌谱极难适当配合,致失其原韵,有些歌词就是蒙藏同胞也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他们只是会唱罢了。况且许多故事如藏文三国演义,尽属口传,记录非易。例如花儿,有整套的‘本事花’,如花亭相会,岳爷,苟家滩,包公案,杨家将,三国,残唐等,又有零碎的‘草花儿’名目繁复,转相口授,差别特甚,局外人仿佛始入五里雾中。”(4)新西北月刊·弁言——关于西北的民间文艺[J].新西北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西北民歌专号”,1941年1月出版:1。所以早期的花儿曲谱大多作为说明性文本或附录出现的。1940年出版的《花儿集》中,张亚雄收录了4首曲谱,两首为河州民歌,两首为青海民歌。1947年第8期《西北通讯》发表萌竹《青海花儿新论》,文中插有一首《青海花儿(互助令儿)》简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花儿曲谱整理与歌词本一样受到重视,出版了大量的花儿曲谱本。1951年2月,紫辰整理出版《青海民歌》曲谱本[25],用简谱记谱,收录西野文工团陈毅通和一军文工团华思等在青海搜集的花儿共56首,命名为“野曲部分”,同时还有“社火曲部分”,这是迄今所见第一本专门的曲谱本。1954年的《花儿选》中,朱仲禄收录了60首花儿曲谱,甚至同一首令,在不同地区不同歌手演唱的,曲谱都不相同,突出体现了花儿演唱中的歌手个性特点。1957年10月,华恩出版《青海民间歌曲集》曲谱本[26],内容分为“山歌、野曲类”“秧歌、社火类”“酒令、家曲类”“藏民舞曲类”四大部分,整理花儿曲谱34首,其中《野曲》《绕三绕》《好花哟》《东峡令》《水红花》《回族令儿》《红花开》等曲谱采录于大通,从曲谱名称的命名上看,作者有时以歌词命名,有时以花儿令命名,不太统一,但这些曲谱都是作者在大量的田野采录基础上整理出来的。1959年12月,青海省群众艺术馆、青海省音乐工作者协会出版《青海民间歌曲百首》曲谱本[27],内容分为花儿、宴席曲和其他等三辑,收录花儿曲谱有汉族14首、回族9首、土族15首、撒拉族10首。1961年,黄荣恩在《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28]一文中引用了三首由他记谱的曲谱,分别是《什么人良心坏了(花花尕妹令)》《山里的松柏冬夏青(撒拉令)》和《处处是跃进的歌声(啦啦令)》。1967年,丑辉英《西北民歌集》曲谱本在台湾省出版(本书无版权页,仅在英文书名下写有1967字样),用五线谱记谱,收录有青海山歌《尕马儿拉回来》,另有7首“甘肃花儿”,有的有“阿哥的白牡丹”“阿哥的肉呀”等衬词,也是常见的青海花儿令。
1976年之后,花儿曲谱的整理又活跃起来。1979年7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花儿曲选》曲谱本(内部资料),收录“回族花儿”“土族花儿”“撒拉族花儿”“汉族花儿”“新编花儿”等五大类118首曲谱。1979年10月,西宁市文化馆编印了《西宁演唱》特刊之《花儿集》曲谱本(内部资料),收录水红花令、溜溜儿山令、尕马儿令、直令、依啊依令、河州令、大眼睛令、马营令、撒拉令、尕连手令、沙燕儿绕令、白牡丹令、尕妹子令等13首曲谱,并注明了歌名和流行地区,信息比较完整。1979年,王浩《“花儿”的格律与流派——与〈“花儿”的格律〉一文商榷》[29]引用了一首《尕马儿令》曲谱,为五线谱。1987年,屈文焜《“花儿”交错韵的美学意义》一文在分析花儿交错韵与音乐(曲调)关系时引用了五段花儿曲谱,没有标明名和令。[30]1987年8月,雪犁、柯扬出版《西北花儿精选》[24],附录了50首花儿曲谱,仅有歌名和曲令名。
1988年11月,周娟姑、张更有出版《青海传统民间歌曲精选》[31],本书采用曲谱加歌词的形式,入选花儿50首,流行于大通地区的有《尕妹是芍药打骨朵(乖嘴儿令)》《维人嫑说穷富的话(互助令一)》《阿哥们想的是乱心(东峡令)》《走了三步往后看(喜鹊儿令)》等,由于作品大多是编者亲自搜集记谱的,曲谱中不仅有歌名和花儿令,还注明了每首花儿的流行地区、演唱者和记谱者的信息,在以往的曲谱搜集整理中属最为规范。
2000年3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五线谱)出版,其中收录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花儿曲谱有《尕妹是山里的百灵鸟儿(绯红花儿令)》《心上的少年漫来(绿绿儿山令)》《身子回了心没回(绿绿儿山令)》《三天没见想死了(绿绿儿山令)》《阿哥和你十分好(绿绿儿山令)》《大眼睛看不上我了(绿绿儿山令)》《醒来时怀抱的枕头(阿哥的肉令)》《青冰上开一朵牡丹(啦啦令)》《阿门着没唱个少年(大眼睛令)》《越送时越难心了(老爷山令)》《六月六会上夸手段(古少年)》《一搭儿油锅里跳上(碾伯令)》《我为你三回去坐牢(东峡令)》《现代化道路宽广(北川令)》《再没有你心里亮的(北川令)》《尕妹妹不像从前了(好花儿令)》《东虹日头西虹雨(好花儿令)》《尕嘴儿抿下偷着笑(尕肉儿令)》《尕妹的模样儿画上(尕肉儿令)》《五岁上念了个三字经(尕肉儿令)》《年轻的阿哥抓走了(尕肉儿令)》《脚儿嫑响悄悄来(石山令)》《只要你尕妹妹心嫑变(土族令)》《阿哥们看个了去哩(土族令)》《这就是丰产的样儿(土族令)》《你把我冤枉错了(土族令)》等26首曲谱。[32]
2010年4月,颜宗成主编、郭兴智执行主编的《青海花儿·创作歌曲集》[33]曲谱本出版,搜集谱写218首青海花儿曲谱。
曲谱整理在文本传承和资料积累方面意义重大,它客观地记录了花儿的演唱面貌。然而,民间歌手中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认识曲谱者更少,他们是从口耳相传中学到花儿并进行自己创作的,因此个性化特色非常鲜艳。上述曲谱本显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花儿曲谱的记录始终也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大多数本子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诸如忽略流传地区、信息不完整等,这可能与记录者的个人素养和意识有关,也与搜集整理的难度有着直接关系。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旦一首花儿被记录成谱,便使某个个人的演唱风格被固化下来,成为这首花儿的标准模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花儿的地域特色,以及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演唱者的个人特色,有以共性取代个性之虞。因此科学规范的曲谱记录就显得更为重要,目前所见曲谱本中,当以周娟姑本最为规范,堪称范本。由于花儿地域、民族和演唱者都会对整理曲谱产生影响,只有将更多地域、更多民族、更多歌手的演唱记录下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出花儿的整体传承面貌。
二、花儿文本研究
赵宗福先生指出,20世纪花儿经历了三次研究热,第一次是30年代到40年代,第二次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第三次是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34]1我们大致沿着赵先生的观点,对花儿文本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早期花儿研究是从花儿的简单介绍和分类方面开始的,特别是从花儿名称辨析入手,着重研究花儿的类型、传承地理、文学价值、文化功能等。1936年,吴亿在《西北论衡》第四卷第八期发表《征集西北歌谣的重要性》长文,文章从文学鉴赏、方言研究、民俗学、新诗范本等诸多方面对搜集歌谣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1941年,宗周在《西北论衡》第九卷第十二期发表《西北文学的整理与创造》,就民歌的搜集与制谱、西北文学的新创造等进行探讨。
1940年出版的《花儿集》是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的一块丰碑,张亚雄比较宏观而全面地从花儿流传地的习俗、语言、传播、花儿名称、花儿个案(马五歌曲)、花儿的文学、音乐、花儿流派、花儿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出产‘花儿’的地带,多少带一点部落时代的古风,儒化的色彩甚淡。不出产‘花儿’的地带,已经是宗法社会的家族主义社会,深染儒化色彩。女子的缠脚与不缠脚,显然的代表了两种典型。”[5]76他将花儿的流传地划分为河州、西宁和洮泯三个区域,西宁区域包括了湟源、巴燕戎、贵德一带[5]75,并提出 “本子花”“草花”等概念。张亚雄《花儿集》对后来的花儿研究影响深远。1940年,寿昌在《西北的民歌》一文中提出花儿可分为河州派、洮州派,并划出了每派花儿的流传范围。(5)寿昌.西北的民歌[J].新西北月刊,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西北民歌专号”,1941年1月出版:3-4。
1942年,曹默在《西北论衡》第十卷第四期发表《三陇的“花儿”》(6)曹默.三陇的“花儿”[J].西北论衡,第十卷第四期“西北民俗专号”,1941年4月15日出版:14-19。,文章从风俗习惯说起,探讨了“花儿”名称、“花儿”的地理背景、“花儿”的文学价值、产生的地域民族关系等。
花儿分类是早期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1947年,萌竹在《青海的花儿》[35]一文中对花儿作了简单分类,分为表达别离情绪、表达想念情绪、表达爱慕赞美、表达光阴过得快人生短促、表达失恋的情绪、表达穷困而寒酸,以及骂人等类型花儿。1947年,萌竹发表《青海花儿新论》[35],文章讲述了花儿的禁忌、命名、形式(有四句、五句、六句、八句),花儿令,花儿的歌唱内容、演唱形式、演唱时间,并将青海花儿与苗歌进行曲谱对比,提出了如何花儿学习等学术见解。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4年,朱仲禄仍延续着早期花儿的研究路径,将花儿分为爱情、诉苦、反抗与讽刺、歌颂和其他等几大类型,并作了一定分析。[36]1-10
进入1960年代,花儿格律研究开启了花儿研究新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关注讨论花儿格律和表现手法等问题,并且形成学术争论局面。1960年,歌行发表《“花儿”漫谈》(7)歌行.“花儿”漫谈(一)[J].青海湖,1960,(4):75-76;歌行.“花儿”漫谈(二)[J].青海湖,1960,(5):58-60。,文章探讨了花儿的形式,指出四句式花儿中八个字三个顿,七个字两个顿,九个字-八个字为三个顿,八个字-七个字为三个顿,九个字-十一个字三个顿等特征。1961年,祁莲发表《从“花儿”的比兴谈到“花儿”的提高与发展》[37],对《青海湖》刊登的周朗等人文章关于否定传统花儿的比兴手法等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比兴是不同的表现手法,并引用了两首传统花儿,其一:“大豆花开虎张口,蔓头花好像个绣球;我们按着总路线走,美生活就在前头。”其二:“阴山里结下的红瓢儿,阳山里长的是杏儿;请哥哥住到我对门儿,给妹妹当一面镜儿。”汉元随即发表《说“兴”》[38],文章从“兴”的起源、意义和使用方面进行论述,对祁莲《从“花儿”的比兴谈到“花儿”的提高与发展》一文主张“用‘兴’的手法代替‘比’”等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赋比兴各有所长,应用其所长,发展特色。1961年,汉文发表《不能否定“花儿”中“兴”的表演手现》[39],文章驳祁莲文中“(兴)有这样两个作用:从韵脚上引起下文;借类似的事物来引起联想”的观点,认为第二个有理,第一个未必全面。并引用古人观点“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文有尽而义有余,兴也”(钟嵘),认为“兴”包含着景(事)和情(志)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联系。1961年,刘凯、任丽璋发表《谈谈“花儿”押韵问题》[40],文章提出花儿有三种押韵形式,一是一音到底;二是一、二、四句互押;三是采用随韵的方式两句一转韵,一、二句押一韵,三、四句押一韵;四是个别“花儿”,也有采取交韵方式押韵,即一、三两句,二、四两句交互押韵。1962年,刘凯发表《“花儿”格律试探》[41],探讨了花儿的句数、顿,用韵规律,花儿结尾的特殊要求等,认为固定的句数(类似诗行)、近似的字数和句中有规律的“顿”(或叫音组);押大致相近的自然口韵;每句“花儿”结尾都有特殊要求。文章分析了四句、六句、五句、三句式花儿的字数、顿的规律,四句式花儿每句三顿,六句式花儿的一、三、四、六各句与四句花儿一样,要求三顿,惟二、五两句是一顿。花儿押韵有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的,一、二、四句互押,交韵采用随韵的方式;两句一转韵,一、二句押一韵,三、四句押一韵。结尾时要求三字尾与二字尾相间,一三两句为三字尾,二四两句为二字尾。
这一时期,由于受新民歌运动影响,理论界关注如何学习发展提高花儿这一命题,出现了学术争鸣局面。如歌行《“花儿”漫谈》一文对“怎样学习写‘花儿’”进行了探讨。1961年,歌行《“花儿”的提高和发展》一文提出,花儿表现形式要适应当时的群众生活,鼓励在四句、六句外出现更多容量花儿。[42]周朗《“花儿”浅谈》一文提倡花儿朴素和明净的美,认为花儿风格“它很自然地反映了高原人那种朴质、单纯、热烈的性格。”他提倡在花儿的发展提高中要扩大容量,丰富体例,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43]荷菓《“花儿”初探》一文提出,花儿“加之它深深扎根于劳动生活的土壤,……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发生发展和变化,伴随着劳动,它是劳动人民的心血凝成的花。”他认为提高花儿创作,“和发展花儿内容与形式,就要认真踏实地进行研究。找出它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规律,不能就此否定鄙薄它的单纯、短小、简单的,废弃它的比兴。”[44]1961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青海分会和《青海湖》杂志社就如何学习花儿等问题联合举办了座谈会,西宁地区专业和业余作者、音乐工作者参与讨论。《青海湖》1961年6月号登载了这次座谈会上任清川、周书傅、布谷、任丽璋、尹克轩、马正元、朱健、黄荣恩、杨世伦等人观点摘要(第53—55页)。王浩《花丛习步》[45]、刘凯《读“花儿浅谈”有感》[46]、朱奇《也“浅谈花儿”》[47]等文章,关注的都是此类问题。
花儿的形式和起源是学界讨论的另一个话题。1961年,刘凯发表《花儿散论》[48],文章研究了花儿的“词”“令”“衬句”,这些正是民间传承花儿文本中的“大词”,该文还探讨了花儿的思想艺术、革命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花儿结尾等问题。黄荣恩《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28]一文,介绍并探讨了花儿的命名、内容、格调、押韵、演唱和创作语境等问题,提出“人们唱出的‘花儿’,实际是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1961年9月,启鸣发表《“花儿”拾零》[49],就周朗“‘花儿’的老传统形式:前两句一定是比兴,后两句才是描述本题”的观点进行反驳,引用花儿“有话可给谁带哩?活把人心想坏哩!山川绿的象菜哩。”说明前两句为题,后一句为比。第二首:“雪花儿下者满地了,望不见哥家的路了。云影儿低的遮盖了,看不见哥家的树了。”第一、三句是比,第二、四句是题。还就“‘花儿’叙事诗”与“本子花儿”的概念取代展开争论,认为“本子花儿”更名副其实。赵存禄在《“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一文中提出“‘花儿’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到三千年的光荣历史了。”“‘花儿’既然是劳动的产物,那么其作者无疑是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了”等观点,并提出了西宁派、河州派、洮岷派、宁夏派四种“花儿”派别。[50]孙殊青的《试谈“花儿”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一文分析了花儿的句数、顿数等节奏,韵律类别,以及因内容而灵活运用的比兴手法。[51]1962年,王浩、黄荣恩发表《“花儿”源流初探》[52],文章对当时“以花儿考花史”,“花儿”起源周代说、唐代说、北宋说等观点进行分析批驳,认为吴镇《我忆临洮好十首》诗作可靠地认定“花儿”在清朝康熙年间已经成熟,作者从历史传统“花儿”和“七言”诗歌史循名责实,将花儿形成年代划定在唐代至明代,并没有可信资料得出更确信的结论。1962年,黄荣恩发表《〈河州是“花儿”的正宗〉质疑——兼谈《“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53],文章对刘凯《可疑的和可信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读后”》[54]从民谚“西安的乱弹,河州的少年”的说法中认定河州是花儿正宗,河州是花儿起源地的观点进行讨论,他认为河州和青海花儿演唱上有着很多区别并各具风味,青海群众说河州人拉尖音、河州的令儿(曲调)硬得很,指的是河州花儿唱法和花儿音调高亢、刚劲之意。而青海一般擅长软音(也有与河州唱派相同者),即指青海的演唱风格和花儿音调贵在于软,这里的软不是绵软无力的软,包含着柔里透韧,稳中显烈的特点;令儿两地有许多共同之处;另从花儿文学方面看,青海花儿与河州花儿在句法、节奏、顿数、语言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黄荣恩的目的是要为青海争得“青海勤劳的先人创造了青海花儿”一席交椅。上述学术争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次花儿研究高潮。
(三)20世纪70-90年代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新创的革命花儿数量甚多,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但学术研究反而冷清,少量的理论文章,也仅侧重于探讨花儿的思想性,以及如何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1974年,臧志清发表《从民歌看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精神》[55]。1975年,刘凯《花儿创作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一文提出“花儿创作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是花儿发展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花儿创新要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6]。1975年,鸿雁在《让新“花儿”展姿怒放——读新“花儿”选〈手搭凉篷望北京〉》书评中认为《手搭凉篷望北京》一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创新,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57]。
自1977年以后,先从为花儿正名开始,花儿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1977年,力章发表《迎接“花儿”的春天》,欢呼粉碎“四人帮”后花儿获得新生,“雨过天晴(者)雾散了,红太阳普天下照了;‘四人帮’彻底完蛋了,神州舞,咱心里乐开了花了。”[58]1978年,工人、龙革锋发表《革命的民歌时代的强音——驳江青的“民歌下流”论》[59],对花儿进行正名。文章引用了数首花儿以证明民歌可以“表现革命”,如声讨地主阶级和蒋马军阀残酷统治花儿:“大肚子臭虫吃血哩,吃憋了满炕上滚哩;吃人咀牙缝带血哩,到时候,向你者讨血债哩。”“苦胆锅锅里熬黄连,马步芳当上了长官;抓了新兵又刮款,骨头里熬出了青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达人民喜悦和对毛主席爱戴的花儿:“天上有一颗北斗星,它本是指路的明星;中国有一个毛泽东,他本是穷人的救星。”“大跃进”花儿:“风停雨住天色兰,‘大跃进’,先进把先进追赶;昨天创造的新纪录,到今天,又落到别人后边。”“祖国好比锦丝缎,光灿灿,社会主义美景绣全;公社好比一枝花,红艳艳,全靠毛主席浇灌。”1966-1976年间的花儿:“俊不过高山的松柏树,枝叶儿四季(是)长青。”揭批“四人帮”花儿:“党中央决议真英明,心花儿开,大干的战歌(哈)嘹亮,深揭狠批(者)‘四人帮’,万炮响,彻底把‘害人虫’埋葬。”等。1978年,刘凯、任丽璋发表《“花儿”对形象思维的运用——浅谈“花儿”的比和兴》。[60]杨正荣在《“花儿”格律小议》文中简单讨论格律问题。[61]1979年,汪曾祺发表《“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文章对花儿句式、押韵进行研究,得出了“花儿”多用双音节句尾,即两字尾;“花儿”是严别四声的;“花儿”作者对于语言、格律、声韵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等结论。[62]随后王浩发表《“花儿”的格律与流派——与〈“花儿”的格律〉一文商榷》[29],作者根据三十年来在元朔山(大通老爷山)、瞿昙寺、莲花山实地考察和花儿研究,提出“青海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流派,并对花儿文辞句式、格律等进行分析,证明花儿不尽是六言,“花儿”中虚词不虚,有虚虚实实特点等观点。
除格律之外,花儿音乐研究也出现新作。1979年,张谷密《试谈“花儿”旋法艺术的规律》一文收录在《青海花儿曲选》(8)张谷密.试谈"花儿"旋法艺术的规律[J].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青海花儿曲选[Z].内部资料,1979.该文后经修改补充,以《论“花儿”的旋法特点及艺术规律》为题,发表在《音乐研究》1981年第2期。,文章认为花儿旋法中突出了“商”“徵”音的作用,“徴音”是花儿爱用的调式主音,“商音”是最重要的支持音,因此张谷密还起了个新称谓叫“商徵型花儿”。张文还说,这种旋法中常从商音直接进行到徵音,跳过了角音,即使出现角音也并不是重要的。此外,张文还研究了曲调构成音的自然音列朝相反方向运动,以单独构成旋律,可与自然倾向(上行)共同构成旋的逆行方式,丰富了花儿的艺术手段和曲调式样。
这一时期,“花儿王”朱仲禄关注花儿的创新问题。1978年,朱仲禄发表《编唱“花儿”的点滴体会》,就词曲结合、风格、情调进行讨论,提出“尕马令”等衬词在唱情歌可以,要唱新词,就成问题,要求在不伤害原有风格或对原有风格有所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破格,不然会阻碍“花儿”发展。[63]1981年,朱仲禄发表《“花儿”的破格与创新》[64],文中引用了两首传统花儿:“薛平贵回窑的十八年,武家坡挑菜的宝钏,尕光阴好像是打墙的板,上下翻,催老了英雄的少年。”“白云彩起来者端站下,绾疙瘩,好象是才开的棉花,纺成个线,织成个布,缝一件挨肉的汗褟。”以此提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要突破花儿四句六句的传统格式,可以有五句或七句式花儿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花儿要在文学、音乐、唱法上都要创新。朱仲禄也成为一些花儿研究的个案,研究者通过个案研究,探讨花儿演唱的准备及音域表达等问题,如刘尚仁在《“花儿”艺术家朱仲禄的演唱风格》[65]一文中引用朱仲禄的话说,“在演唱前呼吸的准备好象到了高山绝壁,不得不深深的屏住气息,开腔的时候,如以拳击人,须先收后放,才显得劲头十足,在旋律进行中,需要换气时,给人以声音毫不中断之感,如藕断丝连一样。”在演唱方法上,认为有尖音唱法(即比真声高八度)、有苍音唱法(即全用真声演唱),也有全用假声演唱的虚声唱法(即接近泛音的唱法)。在演唱中要真假声结合(即在中低音区用真声,高音区用假声),还要用颤音及滑音等特殊的音色。
1987年,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青海民歌音乐论文集》(内部资料),这是一部纯粹的音乐研究论文集,收录张谷密、周娟姑、黄荣恩、包恒智、马占山、马正元、朱仲禄、刘凯、赵志和等人在1981至1985年间发表的有关花儿音乐方面的研究文章和会议论文13篇,这些论文讨论花儿旋法特点、艺术规律、花儿音乐的民族和地区特点、曲令分类、艺术特征、花儿调式、花儿下滑音、花儿起音、演唱技巧等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花儿文本研究概貌。1987年,刘凯《关于西部民歌“花儿”的探索》一文介绍分析“花儿”演唱民族、独特格律,蕴涵多民族音调,多民族语言现象(风搅雪),提出“‘花儿’约产生于元末明初”。[66]1987年,屈文焜《“花儿”交错韵的美学意义》一文提出“(花儿)奇句尾单音音节为韵(或一音节或三音节),偶句尾双音音节为韵。整首花儿,韵韵交错,相押成篇。……可见,花儿原本是押双韵(即交错韵)的民歌”[30]等观点,不断出现新发现新观点。
正是在这一时期花儿研究热背景下,1989年4月,赵宗福先生出版《花儿通论》,这是继张亚雄《花儿集》之后,花儿研究史上的第二座丰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严谨规范的学术著作,作者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花儿的名称、源流、格律、内容、歌词艺术、音乐艺术、花儿会、花儿的演唱与歌手的关系、花儿的整理与研究、花儿的革新与发展等问题。赵先生在花儿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得出了许多改变当时研究方向的学术成果,如关于花儿的起源,在浩繁的史料中,赵先生发掘出明代高洪的《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人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继续长。”从而得出“花儿形成的时代最迟不超过明代中期”(9)赵宗福.花儿通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64.另据其他引文,本文将《花儿通论》中的“农夫村女锄田忙”改为“农人村女锄田忙。”见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11,(1):117-127。学术结论,至今被人反复引用,这也是迄今唯一可靠的科学论断。此外,赵先生关于“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的分类,花儿多民族属性的论述等观点都成为花儿研究中的共识。因其在范式、深度及创新程度等方面的原创性研究,本书迄今鲜有人超越,相反不断被人抄袭模仿。2014年以来,《花儿通论》被陆续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91年,张谷密出版专著《西海乐论》[67],其中对花儿与社会生活、土族花儿的曲调结构、花儿歌词的形式特点、旋法特点及艺术规律、花儿节奏、花儿曲式、撒拉族花儿调式等进行研究。1995年,刘凯出版《西部花儿散论》。[68]
(四)21世纪以来的花儿研究
进入21世纪,再一次迎来花儿研究热,但研究热点比较分散。
热点之一:花儿文本鉴赏与史话研究。2001年,罗耀南《花儿词话》出版[69],赵宗福先生指出这是第一本鉴赏花儿作品的书(见本书序言),作者就花儿文本中故事起兴、叠字、顶真、谐音相对、独木桥体及其他花儿词语进行典故考证,描述和解说民俗事象和民俗词语,进行简析和注释,发掘了若干新资料。2002年,滕晓天《青海花儿话青海》出版,作者挑选有关青海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的134首花儿进行讲解、注解,讲述故事及相关风俗民情。2005年,李泰年《走近花儿》出版[70],作者就历代文化对花儿的影响、花儿的国内外传播、花儿中的女性美、爱情花儿、花儿会、花儿格律、花儿的和谐性、民族花儿等内容进行梳理。
热点之二:关注花儿的社会适应与品牌打造。2007年7月,滕晓天等人发表《民族地域文化与花儿品牌》《哲理花儿的当代价值》《花儿走进城市的利弊》等文章(10)滕晓天.民族地域文化与花儿品牌[N],师守成.哲理花儿的当代价值[N],贾文清.花儿走进城市的利弊[N],青海日报,2007-07-13(8)。,可视为在“青海花儿已经从乡间走向城市,走进人们的生活中”(编者按语)的大背景下,对研究者关注如何打造花儿品牌等现实问题所做的一种引导。
热点之三:“非遗”保护、文化解读、文本规范。2010年,李言统等著的《河湟花儿与花儿会》[71]出版,本书是曹萍、赵宗福主编的“青海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丛书”之一,也是青海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瞿昙寺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和丹麻土族花儿会等四个花儿会,研究者从人文背景、文化展演个性、文化价值方面对老爷山花儿会进行梳理,并介绍了“非遗”传承人马德林。同年,滕晓天出版《花儿漫河湟》[72],以散文的笔调,挑选典型花儿进行鉴赏,讲述相关地理、历史、典故、民俗风情知识和修辞手法,并选录新花儿歌词。2011年,滕晓天等出版《花儿春秋》[73],本书梳理花儿起源流派、内容与形式、词曲和唱法、音乐、歌手、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花儿研究学者、花儿的社会涵义以及产业化等内容。2013年,滕晓天等主编《青海花儿词典》[74],这是花儿文本规范方面的第一本词典。2014年,《青海省花儿艺术志》出版。[75]
2010年,吉狄马加、赵宗福主编的《青海花儿大典》[76]出版发行,这部66万字的著作共分为综述、花儿词选、花儿曲令、花儿会、花儿演唱传承人、花儿创作、花儿研究等七编,在花儿词选大类中,又分为“传统爱情花儿”“大传花儿”“民国时期花儿”“新中国花儿”“新编花儿选”等类别,“爱情花儿”类别中再细分为“邂逅类”“倾慕类”等15个小类;“大传花儿”类别中又分为故事起兴、新编大传、其他历史故事等13个小类。本书视野宏观,不仅体量巨大,且篇目设计清晰,结构严谨,分类缜密,脉络贯通,在研究范式上有新的创新和突破,全景式反映了花儿文本传承的最新面貌。《青海花儿大典》是继《花儿通论》之后的又一部经典之作,堪称花儿研究史上的第三座丰碑。
花儿还成为硕博论文选题,有硕士生对老爷山花儿会进行个案调查与实证研究[77],还有博士生对花儿的文学与音乐关系传承进行研究。[78]2016年,曹强、荆兵沙出版《花儿语言民俗研究》[79],这是花儿文本研究方面的一部学术力作。
三、花儿的文人创作及其民间化
(一)花儿的文人创作
1.花儿歌词创作
在歌谣运动和《抗战歌谣》刊物(11)据张亚雄《花儿集》记载,该刊物为教育部民众读物组稿,老向所编。见张亚雄编著.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6:27。启发下,以民谣、民歌为载体的抗战新民歌新民谣成为当时的一个亮点。据张亚雄介绍,最早的文人花儿出现于1938年8月,罗伟兄曾在汉口广播甘肃民间歌谣中,就有谷苞等人编的花儿。[25]1940年,张亚雄在其《花儿集》中创作12首“抗日少年”,如第十二首:“八月四日者失北平,十二月十三的南京。收复失地哈灭东洋,不打日本者不太平。”这些文人花儿也反映出作者的爱国情怀,抗日少年成为当时的一个时代主题。在花儿的新创中张亚雄也注意到花儿的爱情主题传承问题,他说“我们利用花儿的形式,编制抗日歌曲,不可完全抛开男女求爱的口吻,假如完全抛开男女间情歌的方式,极易变作干枯的标语口号,减少歌词的作用。”他还注意花儿的创新,提出“我们编制抗战‘花儿’,何妨创造若干新的‘令’名,譬如‘尕日本’,‘杀东洋’,‘灭东洋’,‘打倒日本’等词句,用以代替上述‘阿哥的肉’,‘水红花’,‘嫩江白菜’等等字眼。或者创造新调子,新令名,都未尝不可。”[5]96这些意见,对当下的文人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1941年,宗周在《西北论衡》发表《西北文学的整理与创造》,提出所谓仿体花,即创作,还引用张亚雄的抗日少年:“老牛恶虎的兔儿军(军疑为年字),日本的鬼子反中原。阿哥是壮丁者上前线,小妹们唱一个抗日的少年。”(12)宗周.西北文学的整理与创造[J].西北论衡,第九卷第十二期,1941年12月15日出版:23。
20世纪60年代,花儿文本的形式体例不断创新,容量扩大,出现了花儿的“串子莲”(荷菓语)、联唱、对唱、长篇叙事诗(13)此名称成为当时争论焦点之一。周朗、荷菓等称为叙事诗或长篇叙事诗,但启鸣反对称为叙事诗,认为应该称为“本子花”。参见启鸣.“花儿”拾零[N].青海日报,1961-09-02(3)。、花儿剧、花儿小品等形式,花儿还被搬上舞台。(14)见周朗.“花儿”浅谈[J].青海湖,1961,(5月号):55-57.荷菓.“花儿”初探[J].青海湖,1961,(5月号):57-58。1960年,可国创作《花儿会小品》[80],作品背景是1960年在民和举办的全省花儿会,小品中有17首新花儿,时代气息浓郁。1960年,马德岳、海英创作《农村秋景》花儿六首,发表在《青海日报》上[81],其中“秋季里到了者遍地金,麦垛儿好象个森林;男女社员们忙驮运,花儿声飞满了农村。”表现了当时的生活劳动场景。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人花儿再次出现创作热。1978年7月6日,朱仲禄在西宁举办的青海首届民歌会演开幕式上演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花儿《华主席给了我们文艺的春天》:“清不过海水(者),兰不过天,俊不过新时代的‘花儿’与‘少年’。千万朵花儿开满川,华主席啊,您给了我们文艺的春天!”[82]1978年,大通县易放创作的花儿《镰把上攥的是丰年》发表在《青海日报》上:“大治的岁月(哈)收黄田,笑满脸,珍珠玛瑙(么)齐揽:龙口夺粮(者)泼上命干;顶烈日,撕片白云(么)揩汗。腰酸腿疼心里(么)甜,手不闲,镰把上攥的是丰年;串串‘花儿’向党献,华主席,把春光撒遍离原。”[83]
进入21世纪后,文人花儿再次出现创作热。2002年,“花儿王”朱仲禄出版《爱情花儿》[84],分“爱的新花”“河湟花儿”“洮泯花儿”“陇中花儿”“河湟传统花儿”等五个部分,收入爱情花儿43首,河湟花儿746首,河湟传统花儿67首。作者独辟蹊径,利用其自身深厚的花儿学实践,在传统花儿歌词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积数十年工夫汇集而成。因为朱仲禄在花儿界的崇高声誉和威望,他的作品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巨大的反响,《甘肃科技鑫报》专门开辟“每天一花”栏目,予以介绍宣传。[85]
受到花儿品牌化和“非遗”保护的鼓励促进,大通县也出现创作热,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2003年,马得林出版创作的《新编大传花儿》[86],2013年,他出版创作的《花儿千首漫青海》。[87]2011年,大通县文化部门出版《花儿大通》。[88]2013年,李成虎出版花儿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89],小说中插入若干花儿歌词。
2009年,西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西宁地区优秀文艺作品丛书·“花儿”卷(1949-2009》[90],收录有43位作者的创作花儿。2012年,李发君出版《荷月吟风新编花儿词集》[91],新编花儿歌词500首。2014年出版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92]是网络花儿创作的成果,收入花儿歌词近800首。据青海作家井石在该书序中说,2005年以前没有出现网络花儿。2010年8月,井石等人在QQ群聊天的花儿爱好者建了一个群。之后,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理事曹金泰(网名啸月苍狼)建起了“青海花儿研究与交流群”,是为QQ花儿群的开端。2010年12月,青海省花儿理事会理事一凡建立了 “花儿与少年交流群”。2011年初,六月荷花又建起了“青海花儿大家说群”,吸引大批的花儿爱好者入群,群里对花儿,有人出上阕,大家对下阕。甘肃、宁夏、新疆的花儿爱好者也效仿建群,不到4年便建起上百个QQ花儿群。井石估计人数达20 000人。(15)井石.《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序二《网络花儿结出的硕果》[A].祁海宏.花儿本是心上的话[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11-19。
2.花儿乐曲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人花儿创作过程中,花儿音乐创作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1961年,《青海日报》刊登省音协提供的《旱地里长出个金豆(尕马儿令)》五线曲谱。[93]1963年12月,张谷密出版五线谱《瓜果树移到山顶上(青海回族花儿保安令)》[94],该曲注明为“中国民歌独唱曲”“高音用”,除封面外,内容仅三页。1959年,张鸣剑编曲的小提琴独奏曲《山歌》(青海民歌萨拉大令)发表在《音乐创作》上。[95]1957年,朱仲禄编词、刘烽编曲的青海民歌《下四川》发表在《音乐创作》上。[96]
花儿乐曲的创作数量少于歌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才出现一轮高潮。1978年,刘凯发表他作词的青海花儿《柴达木盆地闪金光(河州令)》。[97]1979年,《歌曲》杂志同期登载左可国和朱健的青海花儿《湟海渠上漫花儿》[98],朱仲禄编曲的撒拉族花儿《旱地里结金豆哩》。[99]1979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花儿曲选》曲谱本,收录新编花儿曲谱6首(16)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青海花儿曲选[M].内部资料,1979-7。。1981年,丁善德发表他编曲的青海民歌《上高山望平川》。[100]2010年,大通县组织人员创作一首赞美花儿会的歌曲《花海放歌》,由歌唱家吕薇演唱。2011年12月和2013年6月,李少白、李养峰分别主编或编著五卷本《河湟花儿大全》,其中前三卷为歌词本,第四卷为曲谱本,第五卷以大事记形式对花儿的搜集历程进行回顾,并对各类型的典型花儿作了简要分析。
从花儿文本的搜集过程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文人创作的花儿数量较少,重心在于搜集整理传统花儿。自改革开放以来,花儿逐渐走向城市,大众化需要破除以往过分强调的爱情花儿主题,以适应不同环境和不同年龄层次的欣赏需求,在此背景下,时代要求的新花儿不断出现,并且转向文人创作,文人的创作讲求赋比兴的同时也趋向文雅,叙事花儿、赞美、提倡等内容成为主流。
(二)文人花儿民间化
中国文人对社会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因此文人花儿大多反映时代呼声,并将花儿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文人创作花儿,往往利用传统花儿的格律等程式,通过大词的组织重新灌入新内容,又与传统花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很容易被民间歌手们学唱。文人花儿民间化,对传统花儿影响深刻。
1.歌手学习文人歌词
赵宗福先生说,“随着教育的普及,书面传承的形式逐渐兴盛起来,花儿爱好者把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花儿记录下来,同时把公开出版的书刊中的花儿歌词加以摘录,然后反复唱诵记忆,变成自己歌唱的内容。改革开放后,随着录音录像手段的普及,花儿爱好者便把著名花儿演唱家的优秀歌手的演唱作录音甚至录像,然后反复播放,模拟学习。同时音像光盘等现代传播媒介也为花儿的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17)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1,(1):117-127。这正是民间花儿歌手学习文人花儿的主要途径和形式。笔者参加的一次花儿研讨会中,发言人罗耀南口述了一首他编写的花儿歌词,坐在笔者旁边的一位民间花儿歌手便请求我为她重复那首歌词,她反复记诵几遍,最后要求我写下歌词,说她虽然不识字,但可以让人念给她听,学会后就要演唱。
爱情与时代是传统花儿的两大主题,传统爱情花儿中不少是一种“悲音”,所求而不得的声音。但文人花儿更强调反映时代性,这是文人花儿的一大特色,从张亚雄的“抗日花儿”开始,文人花儿便有这样的属性。其次,文人花儿力求使花儿从表达个体的悲欢情愁向着承载集体情感的方向转变,凸显“正能量”,实现花儿从点到面的华丽转折。这一转折,使得花儿去“野”从雅,逐渐被城市接纳。据马得林《花儿千首漫青海》序二《花儿的有心人》中说,马得林《新编大传花儿》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花儿爱好者的好评,在民间颇有影响力。”[87]说明文人花儿对民间歌手们有着很强的引导力。朱仲禄被称为“花儿王”,在文人和民间都有着很高的认同度,他身兼民间歌手和文人双重身份,对文人花儿的民间化产生了很强的导向性,例如,他演唱的《雪白的鸽子(呛啷啷令)》是一首典型的文人花儿,雅俗共赏,在民间歌手中也常演不衰,成为经典。
2.从唱花儿到说花儿
在民俗语境中,如果想跟不熟悉的一方试探性地建立关系,或者在人群中想引起情人的注意时,常咏唱花儿来达到目的。花儿是高于语言的情感表达方式,其最初的格式是歌而非言。文人花儿使花儿的格式转向诗词化,可以像传统的诗词那样可唱可吟,改变了原来的演唱格式,从而出现了一种“说花儿”。说花儿与书面格式并无二致,说花儿时同样讲求节奏感。现代歌手在演唱时先说一遍花儿歌词,让观众能够听懂意思,而在演唱时往往并不按词演唱,除衬词外,甚至所唱的内容也会脱离原来的歌词,这便是文人花儿民间化后的一种结果。
据青海省文化馆老馆员石永给笔者回忆,(18)石永告诉笔者,他说那次经历使他知道除了唱花儿,还可以说花儿。石永,男,青海省文化馆退休职工。他们到乡村拜访一位有名的民间花儿唱家时,从敲门、进屋、上炕、吃饭、让客、离开的整个过程中,女歌手没有唱花儿,却改为说花儿,一首首精彩的花儿,有声有韵,琅琅上口。起初,“野曲儿”禁止在家中说唱,甚至连“少年”两个字都禁止出口。能在家中“说花儿”,且使其有韵律感,正是受到文人花儿精神的影响,也可以看作是文人花儿民间化的一个成果。
3.花儿语境实现转换
文人自搜集整理民间花儿之初,便进行有意识的语境转换,整理出来的文本通过精简,去掉演唱中的“冗余”,尽管很接近民间口语,但已经被文人化了,少了表演中的相互打趣、花儿曲令、衬词衬字,口头程式中更多的大词组织,因而脱离了此前的民间表演语境。
文人花儿凸显的是城市语境,追求现代性和表现手段的丰富性,不仅是形式上,甚至于花儿歌词也是一种新的语境表达。如柴玉槐作词,大通花儿歌手童守蓉演唱的《新广场修下的真漂亮》:“新广场修下的真漂亮,高空中把风筝放上,各民族舞蹈都跳上,休闲的人儿心情舒畅。老爷山顶尖上的尖,达坂山紧靠的门源,百姓的日子甜上甜,唱两声‘少年’了好梦圆。”
花儿语境的城市化是民间花儿进入城市,并受到文人花儿影响的结果,也是花儿从个体 “心上的话”经文人改造成为表达群体意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客观来看,城市与乡村是两种地理生态、发展历史和民俗文化语境,如果坚守民间语境中的“野”,与现代文化思潮相悖,花儿在城市中便无法生存,因此民间花儿文人化过程中的语境转换也是一种客观选择。
4.表现形式更为多样
文人花儿使花儿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还将舞台元素引入其中,可以谱曲配器、音乐伴奏,出现了对唱、说唱、舞台花儿剧等丰富的花儿表现形式,对民间花儿产生了深刻影响。舞台表演、歌手化妆、服装设计、音乐伴奏这些是民间原生态的花儿语境中所没有的元素,现在已被民间广泛接受,花儿歌手已经演化成了舞台化的表演。文人花儿的表现形式被民间广泛接受,传统花儿清唱对歌的表演传统反而非常少见。
四、现代语境下花儿创作与传播
(一)花儿会的演变
关于花儿会的成因,赵宗福先生指出:“花儿普及开来后,又不断与各地城镇村落以外的宗教活动黏合,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花儿会。这些宗教活动往往是围绕着名山胜水中的佛教寺院和道教庙观举行的,周边的各民族民众就在这难得的世外佳地,难得的聚会时刻,在草木幽静处相聚,放声歌唱花儿,尽情地宣泄一下情绪。更有一些有情男女在这里相互唱着爱慕的情歌,成就一段姻缘。这样的聚会歌唱也为花儿的进一步繁荣扩布和不同风格花儿的交流提供了土壤。于是,这种聚会歌唱就越来越兴盛,终于在适当的时期取代了宗教活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花儿会。”(19)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1,(1):117-127。赵宗福先生还指出,老爷山花儿会是在当地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交融基础上形成的。[6]
花儿会从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以后逐渐演变成 “赛歌会”。据张亚雄《花儿集》说,在每年的六月初四至初六的三天中,各地会唱花儿的男女青年不论远近,都赶来比赛花儿。[5]96说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老爷山花儿会已经演变成一种民间的赛歌会。此时所谓的比赛,完全是一种民间的自发形式,没有人组织,漫山遍野,密林花丛中,三人一伙,五人一簇,自由唱和。
据《大通县志》介绍,花儿演唱有分散和集中两种形式,既可以在田间地头,野外路途中无拘无束地独唱或对唱,也可以在花儿会上集中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在祁家寺和广惠寺的观经活动中有少数歌手自发前往演唱。1980年起,大通县文化馆开始组织“花儿”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通县花儿会主要有五月端阳娘娘山“花儿”会,六月六老爷山“花儿”会,六月十五后鹞子沟“花儿”会、祁家寺“花儿”会等,在清平乡清水沟四月八踩青会、窎沟乡四月十三踩青会、逊让乡和元朔乡五月十三踩青会上也会演唱花儿。[13]531进入21世纪以来,大通县较有名气的花儿会共有十三处,如东峡鹞子沟花儿会、娘娘山花儿会、城关城隍庙花儿会等。这一时期,花儿茶园应运而生,至2008年时大通县有13个“花儿”茶园,年赢利达10万元,优秀的花儿歌手在花儿会和花儿茶园演唱花儿,年收入可达15 000元。[101]
据有关资料,1986年以来,大通县文化馆共组织了17次大型花儿会,演出240多场,观众达300万人次。到2010年时,大通县涌现出的优秀花儿歌手多达300多人,他们参加全国、省、市、县级民歌大赛,获得78个奖项。[101]至2015年“中国·青海老爷山花儿会”系列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政府举办的花儿会,旨在打造花儿品牌,有一首花儿表达得更为直白:“老爷山上的百花儿开,放眼了看,它就像五色的云彩;把大通打造成花儿的海,锦绣的地,它就是旅游的品牌!”[102]为了森林防火等原因,有关部门对花儿会期间的民众活动进行限制,老爷山花儿会期间对游人有限定路线,有关部门搭台举办花儿演唱会,以往在山上自由对歌的情境难得一见。
(二)从对唱到表演
花儿是个人“心里话”的自然流露,对唱是花儿的本来面貌,老一代歌手们还基本以男女对唱为主,场景基本还是在农村山野,他们遵循着花儿的“原始血统”。随着民歌大赛、商演等形式的出现,改变了花儿歌手的原有演唱语境,花儿成为大众化的表演艺术,甚至成为获利的手段。现代语境影响下一大批新的花儿歌手成长起来,童守蓉、张国统、昝万亿、陈世忠、向国安、李国权、吴玉兰等人已经成为远近有名的花儿歌星,他们被邀请在各地举办的花儿会上做表演,有的加入某个民间花儿艺术团或花儿茶园中,成为签约演员,足迹遍及青海东部、海西、甘肃等地。市场化要求他们的表演要适应观众的现代审美需求,通过特色能吸引观众,赢得自己的声誉和可观的“出场费”,于是,原来的男女对唱、问答、表述等内容向着节目化、舞台化发展,这可以看作是现代语境下民间花儿对社会的自我适应。
新一代的花儿歌星们走上舞台,他们运用对唱、二人合唱、花儿联唱、花儿小品、花儿擂台赛等表现形式,丰富了表演效果。花儿艺术舞台化也出现了若干与花儿演唱无关的花儿人,他们或作为组织服务人员,或作为节目的导演编剧。如“腾讯网络视频”《青海花儿:青海花儿笑破肚擂台》[103]显示“出品:周海云、舍建英,策划:党海云、李发君、雨田,导演:雷有顺,编剧:雷有顺。伴奏:王贵英。”名为擂台赛,其实是一部导演出来的花儿戏谑剧,编导以花儿会为背景,组织华松兰、雷有顺、张国统、彭措卓玛、才仁卓玛、钟光来、汪英、蔡永梅等八位花儿歌手,以“参加花儿会”的形式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歌手们没有化妆,完全是一副参加花儿会的行状,他们在清唱戏谑时,也有普通观众或围观,或喝彩,营造了一个“自然”的花儿会对歌场景。但这种场景是被导演出来的,歌手们不自然的神态也说明这个问题,随着矛盾进展,剧情推向高潮,气氛紧张之时,再有其他花儿歌手走进来,以歌劝和解围,在此期间,歌手们不断换用不同的花儿曲令。虽然不是在舞台进行表演,但这样的擂台赛其实已经是一部情景剧,歌手们看似在对歌,其实是在规定的剧情中进行着表演,观众们不自觉地成为剧中人物。
(三)音乐程式固化
自由清歌形成的强烈个性化风格是传统花儿基本特点。由于花儿是多民族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同一首花儿的演唱风格会发生变异,出现了河州大令一、河州大令二、河州大令三等曲调。非但如此,就是同一民族中的两个人,其歌唱风格也有差异,如《马营令》,大通花儿歌手童守蓉的演唱风格(有网络视频)就不同于民和当地的歌手,她真假声结合,感情表达更为丰沛细腻,怆然凄切,更富有感染力。
音乐伴奏是城市化语境中花儿适应语境转换,紧跟大众审美,并走向舞台化的一个产物。现在的歌手在花儿会演唱中大都有音乐伴奏,或播放伴奏带,或有现场伴奏。这就需要提前拟定好演唱的曲令,而不能触景生情应情变调。音乐伴奏更讲求节奏,并有较长的调门过渡,歌手们在音乐过渡时只能在舞台上等待音乐。与民间清唱相比,音乐伴奏增强了歌唱的表现力,却限制了歌手形成个性化特色,演唱程式同质化和固化,出现了“有音而无声”“有歌无人”现象。总体而言,音乐伴奏表达的是学院派风格,讲求严格规范,自由创造受到一定限制。这些现象在网络视频花儿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音乐程式的固化,对民间花儿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四)网络花儿传播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视频、微博、微信成为花儿文本传播的新渠道,这些网络花儿的表演与原来的花儿会形式大不相同,但花儿文本却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为此,还出现了专门对歌手演唱进行录像出版的个人或公司,他们导演出花儿文本,并上传到网络上。大通花儿歌手中,童守蓉、昝万亿、陈世忠、向国安、张国统、李国权、吴玉兰等人的视频资料早已传到网上。
微博也成为花儿文本的传播方式。2012年7月21日,青海西宁作家贾文清在其微博中对第三届老爷山花儿会作了图文介绍,作者发了两首称据为最传统的大通花儿:“七手八脚的圆绝壁,绝壁上有神像哩;银铃声气金嗓子,我唱时你惆怅哩。/老爷山上的老虎洞,神秘得很,迷住了万人的眼睛;人伙里我唱的少年俊,赛百灵,阿一个唱家来竞争。”并作了注解“解释一下:七手八脚的圆绝壁,在老爷山的一处悬崖峭壁上,画有古老的岩画,岩画是一个长了七手八脚的神仙,但现在已没人注意它了。”随后引来很多点击量,“泉智潜”在评论中编发了两首花儿:“老爷山的花儿会,唱响了可爱的青海;人伙里的贾文清,诠释了游人的感慨/老爷山站来牦牛山睡,迎来了花儿的盛会;郭峰吼来殷秀梅唱,震撼了美丽的山水。”微博花儿传播量非常大,如“秋忆影的博客”上以《青海花儿歌词精选》为题,整理花儿歌词296首,其中有传统花儿,如“娘娘山(与大通老爷山相对)里云起了,四山的头儿里下了,想里想里的睡着了,睡梦里可梦了你了。”也有新编花儿:“桑塔纳跑开是一流的烟,尕手扶干响着里,阿哥们想你是看你里,你想了花儿哈唱里。”微博花儿中文字错误较多。
微信花儿多在微信群中传播。还有光盘、MP3、MP4等格式的众多花儿文本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近几年,快手视频花儿成为花儿歌手直播的新渠道,影响非常广泛。
五、小结
大通老爷山地处青海儒释道等三大民俗文化圈交汇之地,这里多元民族文化交流频繁,花儿语境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性。老爷山花儿有个性也有共性,个性体现在当地特有的花儿大词和花儿令,传承者多为本地歌手,老爷山花儿同时具备河湟花儿讲究赋比兴的一般共性。
作为一种民歌,花儿引起文人的关注史也久远,但花儿文本的搜集整理,即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歌谣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花儿还成为一种宣传工具,承载了宣传爱国、反抗侵略、唤醒民众斗志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文人们在搜集整理基础上有意识地创作花儿,对花儿的传承语境进行转换,从乡土语境转换为城市语境,在儒家传统中被视为“野”“俗”的民间花儿逐渐被市民大众接受,并进入大文化体系之中,向着城市化和舞台化方向发展。文人花儿从歌词内容、表现形式上对民间花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民间的唱家们逐渐“明星化”,以老爷山为背景的花儿会发展到现在,其背景已换成了舞台和布置的背景,演唱中出现了音乐伴奏,歌手们还穿着专门的舞台服装并进行化妆。如果说原生态的花儿会是大自然中个体意识的自由表达,现代花儿会则是策划出来的,表达的是集体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花儿茶园、网络花儿,深刻改变了花儿会和花儿文本的形态和传播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