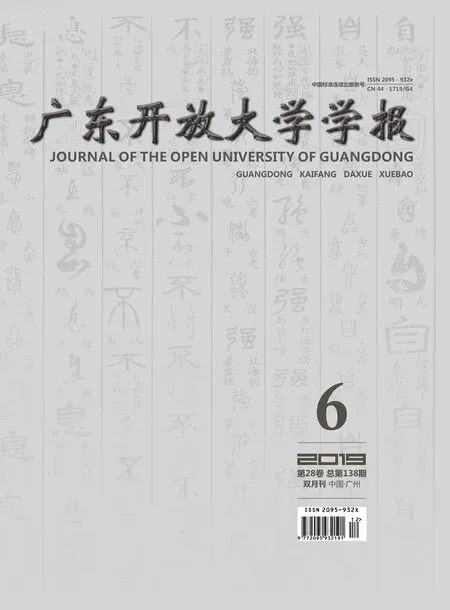论刘亮程散文中的儿童视角
严雪明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30)
从1998年出版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风中的院门》、《家园荒芜》,再到2012年的《在新疆》,刘亮程的散文曾红极一时,甚至一度形成研究其散文的热潮,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冷却反思之后,人们对刘亮程散文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无论是对其哲学思想、内容题材还是语言风格、创作方法的研究,都离不开他的乡土意识、故乡情怀,他也因此被誉为“乡村哲学家”。然而追溯刘亮程的生活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乡村体验多停留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成年之后则在城市里栖身,离故乡越来越远,此时对于乡村的书写更多的是追忆与怀念而非真实的感受与体验。纵观刘亮程的童年和少年,根据地理位置的变化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老黄渠时期、黄沙梁时期和元兴宫时期。老黄渠时期作者尚小,记忆尚不真切,元兴宫时期的时间较短,未给作者留下深刻记忆,唯有黄沙梁是作者的身体和心灵的成长成熟之地,也是刘亮程散文中反复出现的名词,与其说它是一个普通的村庄的名字,不如说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是刘亮程精神家园的象征。黄沙梁时期的刘亮程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他观察生活的视角和感受生活的方式也必定是孩子式的,本文便以此为切入点,对刘亮程散文中的儿童视角进行剖析。
一、断裂——“失乡者”与“寻父者”
儿时的经历对一个人的童年乃至一生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八岁时父亲的离世迫使刘亮程随母亲和四个兄妹从老黄渠迁到黄沙梁,刘亮程的童年也于此时产生了一种断裂,虽然身体上进入了“第二故乡”(即黄沙梁),但在精神上却成了永远的“失乡者”。在对黄沙梁看似诗意的描述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被抛弃被遗忘的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作家反复吟唱的故乡其实从未真正的接纳他。汪娟在《荒野的恐惧与忧伤的漂泊——对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非诗意的解读》中说“我们在细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后,就会明显地感觉到在乡村诗意的描写背后,笼罩着作家的种种非诗意的情感,而其中,恐惧、焦虑、忧伤、悲凉心态成为作者最为日常的情绪。刘亮程对于村庄的荒野恐惧、精神家园忧伤的漂泊都在这个人畜共居的黄沙梁中被自然的演绎出来。”[1]父亲是一个孩子精神上的根,年少丧父的作者跟随柔弱的母亲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面对陌生的人,其恐惧与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整个少年时期,我被什么东西压抑了,没有长高”。“我走路低着头,略弯着腰,像一个小老头一样,心事重重地走过我的少年岁月”[2]238。作者的童年停留在八岁之前,在黄沙梁的岁月呈现出断裂之后成长的空缺。
孩子永远渴望被关注,而这正是儿时的刘亮程所缺少的,可以说这是一种畸形的童年,一直处于被忽略、被遗忘、被抛弃的状态,“当我黑黑地回到家里,没人知道我已经回来,就像没人知道我曾经离开。”[2]175无人问津、自生自灭,这一切使得儿时的作家拥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我从什么时候离开了他们——那群比我大好几岁的孩子,开始一个人玩。好像有一只手把我从他们中间强拉了出来,从此再没有回去。”[2]112作家也曾幻想引起他人的注意,“我想让他们听见我的声音。我渴望他们发现我”。“我故意弄出些响声,还钻出来跳了几个蹦子,想引他们过来”[2]116。可结果依然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孤独中的反抗最终也不过是一个人的狂欢,一场大火没有唤醒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鸡鸣。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一个孩子在一片荒野中张牙舞爪、大喊大叫,然后沉默地垂下头,像一条忘记收回的裤子,在黑夜里被雨慢慢淋湿。
童年的创伤性经历对于作家的一生都将有不可泯灭的的影响,刘亮程这个被抛弃的“失乡者”像一个梦游的人在荒野和孤村中漂泊游荡。作家所失落和追寻的故乡实际上是父亲的象征,父亲的缺失造成刘亮程童年的缺失,“你死后我所有的童年之梦全破灭了,只剩下生存”[3]5。虽然有了后父,但“我”与后父之间始终是陌生的别扭的,“我们”总是挪动他的记忆,搅乱他的往事,而这些往事是“我们”未曾参与过的。“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他嫌我们赶不好车,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2]217。这种感情上的疏离和沟通上的不畅,使得“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父亲的男人有种难言的陌生”[2]218。实际上刘亮程的散文一直处于精神上的“寻父”状态,对于父亲的寻找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失落的童年,“你死去后我的一部分也在死去。你离开的那个早晨我也永远的离开了,留在世上的那个我究竟是谁?”[3]7这些经历在年幼的作家心里永远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以至于在刮风的夜晚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因为“许多年前,我的先父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独自从炕上坐起来,穿好衣裳出去,再没有回来。”[2]212黄沙梁被作家当做魂牵梦绕的故乡母亲,而在其潜意识里故乡是与先父连接在一起的,“我把黄沙梁和老黄渠当成了一个村子。在我多少年的梦境与回忆中,它们叠合在一起”[2]229。在老黄渠和父亲、母亲、四个兄弟姐妹一起度过的生活才是作家难以割舍的旧梦,无论是在黄沙梁的黄昏从西边田野上走来的影子,还是在元兴宫的房顶上俯身看到的一家人,抑或是在半夜里走进的那个在纯纯洁洁的月光下甜睡着的村庄,都寄托着作家对往昔生活的追忆。然而那夕阳下的影子已不知是谁的父亲,屋顶窟窿上的那张脸也成了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月光下甜睡的故乡已成了别人的村庄。没有父亲的引路,作家“将在黑暗中孤独地走下去”,并且身心的一部分永远地长不大了。
二、变形——孩子眼中的时空
对刘亮程散文中时空观的研究屡见不鲜,时间和空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在《一个人的村庄》中作者笔下的时空却是主观的,甚至是异化变形的,这种变形源自于儿童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参照物的不同。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体验: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生活的小村庄也仿佛大到无边无际,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时间也加快了脚步,生活的地方也好像变小了,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以自己为参照物观察世界,参照物变化的同时对世界的感受也必然发生变化。由此也不难理解刘亮程笔下时空的变形:小小的黄沙梁成了一个不知道有多大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村庄,真正多大,我住在它的一个角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村里,到底住着多少人”。“我全部的学识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认识”[2]51。村东头和村西头的人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时间被无限的拉长,人们可以在黑夜里做许多事,整个白天村庄都在生长,时间顺着土墙的墙根以看得见的速度流逝。
不光时间,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一切都是可感可知的,尤其是在一个孤独的“失乡者”那里,生命中一方面的丧失会使另一方面更加敏锐。在年少的作者看来,黄沙梁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不动的村子,更是一个巨大的怪物,它有自己的头和根,还有纵横交错的触角,它将根扎在天上,将触角伸到地底,它还有自己的头,“我一直觉得扔在我们家房后面那颗从来没人理识的榆木疙瘩,是这个村庄的头”[2]169。这个“怪物”在不停地生长,携裹着满村的人游荡在时间的汪洋大海里,“村庄就是一艘漂浮在时光中的大船,你一睡着,舵便握在了别人的手里,他们像运一根木头一麻袋麦子一样把你贩运到另一个日子。”[2]55甚至连村子里的一条路,一棵树,一堆草都被异化为他物,“我知道它们是一蓬一蓬的蒿草,也可能不是草,白天它们伪装成草,成片地站在荒野中,或一丛一丛蹲在村边路旁,装得跟草似的。一到夜晚便变得狰狞鬼怪,尤其有风的夜晚,那些黑影着了魔似的,嚎叫着,拼命朝村庄猛扑,无边无际都是它们的声音,村庄颤颤巍巍地置身其中”[2]120-121。
在儿童的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未形成定例,他们以自己的直观感受来理解身边的一切,从而产生异化和变形,这也是利用儿童视角进行叙述的巧妙之处,既可无拘无束的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不至于使读者觉得荒唐无稽,毕竟人们对于孩子总是宽容的。例如:在莫言的小说中就常常出现儿童视角,《枯河》中小男孩看到的太阳、原野,《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奇异的感受力和他对痛苦的体验,都经过了作者有意的变形和异化,刘亮程儿童视角下的村庄恰与莫言儿童眼中的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通灵——童年的神秘体验
刘亮程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到:“一个人小的时候,是有可能知道世界的某些秘密的,孩子可以钻到大人到不了的某些地方,那些隐蔽的连通世界的孔道有可能被孩子找见。其实,我们都是从童年的一个隐秘的小洞口探出头,看见整个世界。”[4]可见童年体验是作者窥探世界的通道,从刘亮程的散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又很难将其归为有神论者,刘亮程的“神”更接近于沈从文的“自然神”,即万物有灵。何英在《刘亮程论》中曾说过“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奠定了刘亮程成为一个万物有灵论者的情感基础。”[5]作者自己也说:“小孩能看见鬼。小孩啥都能看见。万物的灵在孩子的眼睛里飘。小孩看见的世界比大人多好多层。”[6]49在民间也不无类似的说法,认为孩子未经尘世污染,眼睛和心灵都是干净的,由此便可以看到许多成年人看不到的东西,即具有通灵的能力。这种“通灵”一方面表现在刘亮程散文中弥漫着的“神秘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刘亮程对于老庄哲学“齐物论”的继承。
作者说“神秘感是我在童年获得的最大财富”[7]49。我们在读刘亮程的散文时常常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来自于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无力感,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在控制着一切,我们看不到,却能真切的感觉到这种力量无处不在。于是,人变成荒野里无处躲藏的小丑,只有胡乱挣扎而后听从摆布,这力量令人恐惧无助同时又欲罢不能,这层神秘的外衣,也成为刘亮程散文最摄人心魄之处。作家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了一个孤独的少年,他像村子里的一个“异类”,他常常在夜晚悄悄摸下床,一个人在村子里游荡,看着“村庄带着一村沉睡的人在荒野中奔走,一步比一步更荒凉”[2]121。荒野里巨大无比的身影、独碑独墓一户一户排列着的别人的村庄、在梦里一直追着“我”跑的断腿男人……这些意象无不给村庄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气氛,在这种氛围里人如同困兽,只有听任摆布,普通人困于其中而不自知,自以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殊不知在自身之外一直有“另一只眼睛”在注视着你的一切。单守银在《另一只眼睛——试析刘亮程的文学世界》中说:“刘亮程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用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文明的视角来观照这个世界,描述事物,没有用人心的经纬编造有关事物,而是自觉地放下人心、人眼,打开他接近道心、道眼的另一只眼睛,于是他看到了被人心遮蔽久矣的世界的真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8]单守信将这“另一只眼睛”称为道心、道眼,而笔者则认为这是一双干净、透彻、满怀赤子之心的孩子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能够洞察万物,领略宇宙的神秘莫测,这种神秘感也是一种通灵——通宇宙之灵。
刘亮程散文中对于动物的描写不胜枚举,提到动物的次数甚至比写村中人物的次数还要多,有一篇文章直接以《人畜共居的村庄》命名,动物在刘亮程的村庄里俨然与人平起平坐了。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有人专门分析其散文中“动物书写”现象。其实不光是动物,在刘亮程的笔下一棵树、一根草、一朵花都是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和植物不是作为人类的附属品或者低人一等的生命而出现,它们和人类一样,甚至比人类更能懂得宇宙间的大智慧。前文说到童年的作家是一个被抛弃被遗忘的“失乡者”,是村子里的“异类”,与村中人的疏离,与同龄人的隔阂,使这个孤独的少年只好远离人群,与其他的生命做朋友。他将一棵长斜的胡杨树拉直、沿着一条野兔的路追赶、对着荒野里的一朵花微笑、帮一只蚂蚁搬运干虫、为一窝老鼠的收成担忧。他听到过一只鸟在半夜的叫声、听到树根在地下生长的声音,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多了一个人的呼吸、能知道一根檩子的秘密。在作家看来万物都是有灵的,“灵,能够不拘泥于事物的物质形态,直接到达事物的本质、精神、性情和气韵”[9]。在老黄渠村的地窝子里的生活经历和在黄沙梁的孤独体验,使刘亮程能够通晓万物之灵,从而能够达到老庄哲学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境界。
童年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利用儿童视角进行写作是不少作家的创作选择,但将独特的童年生活体验与儿童观察世界的视角结合起来,则使刘亮程的散文具有了与众不同的魅力。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曹文轩也曾说过:“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童年与故乡永远是人心灵的归宿,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以儿童视角书写浓浓乡愁也许是刘亮程散文大放异彩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