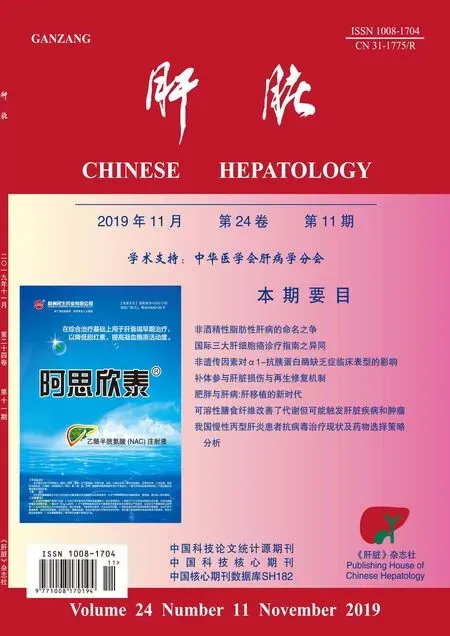非遗传因素对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临床表型的影响
张伟 贾继东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AATD)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其特征是血清α-1抗胰蛋白酶(AAT)蛋白水平降低及其等电聚焦电泳表型异常。AAT由SERPINA1基因编码,正常野生型等位基因为Pi*MM。据文献报道,该基因目前已有超过120个位点发生突变,但大多数和AATD的关系不明确;其中最常见的缺陷型变异为S、Z等位基因,尤其是纯合Pi*ZZ等位基因可导致AAT蛋白错误折叠以及多聚化,使之不能分泌入血从而蓄积在肝细胞内质网中[1]。因此,本病一方面表现为错误折叠的AAT蛋白蓄积所导致的肝细胞凋亡、自噬、再生及氧化应激,从而引起新生儿黄疸、新生儿肝炎以及慢性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血循环中AAT水平降低,不能有效对抗弹性蛋白酶对肺组织的破坏作用,从而导致肺气肿等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表现。 然而, 即使具有相同SERPINA1基因突变的AATD患者也可有不同的临床表型,其肝脏疾病或肺脏疾病的发病时间或严重程度差异可以很大。最近研究发现,除了SERPINA1基因突变决定临床表型以外,表观遗传学、其他修饰基因、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均可影响本病的发生和发展。
表观遗传对AATD的影响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常见的表观遗传改变包括DNA甲基化、非编码RNA、组蛋白修饰。
DNA甲基化是目前AATD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学改变。2019年Wang等[2]应用94例ZZ-AATD患者的肝脏活检组织,探索了DNA甲基化(5-胞嘧啶甲基化,5-methylcytosine)与肝脏疾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AATD患者普遍存在显著的基因低甲基化,这些基因是与肝癌、细胞周期、纤维化以及影响生长、迁移以及免疫功能的关键调节分子相关的基因;进一步分析显示,AATD患者之间存在甲基化差异,在全基因组低甲基化背景下发生局部高甲基化,这些改变可能影响疾病的进展。甲基化模式改变与临床资料关联分析提示,AATD差异性甲基化与临床特征相关,如肝细胞再生、异常AAT蓄积。研究还发现,AATD非肝硬化与肝硬化患者之间肝脏DNA甲基化模式也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其因果关系尚不明确,是肝脏疾病进展导致低甲基化还是不同甲基化状态导致肝脏疾病进展?只能通过长期随访AATD患者,并观察其甲基化状态才能得到结论。此外,AATD患者的DNA甲基化模式与肥胖相关脂肪肝患者相似。有学者在AATD肺病患者中也发现,SERPINA1基因位点cg02181506低甲基化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及肺功能下降相关[3]。以上研究均提示,DNA甲基化模式的改变与AATD的临床表型与严重程度存在相关性。
小RNAs(miRNAs)是一种短小、非编码、单链RNA分子,主要在基因转录后水平发挥作用,调节基因表达。Esquinas C等[4]分析了12例ZZ等位基因型AATD(6例为重度COPD、6例为轻度COPD)的基因及miRNAs表达,结果发现,与轻度COPD-AATD患者相比,重度COPD-AATD患者有205个差异表达基因(DEGs)(114个为上调、91个为下调)和28个miRNA(20个上调、8个下调),故认为has-miR-335-5p下调与AATD相关肺气肿的严重程度相关。另一项有关miRNAs与AATD相关COPD关系的研究发现,与Pi*MM相比,无症状Pi*ZZ人群miR-199a-5p的表达上调,有症状Pi*ZZ患者中miR-199a-5p表达下调[5]。而miRNAs表达在AATD肝脏疾病中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参与组蛋白修饰的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Cs)和去乙酰化酶(HDACs)负责调节乙酰化-去乙酰化之间的平衡,从而维持肝、肺的正常生理过程。一项研究报道,给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可以恢复Z-AAT的分泌,使AAT的活性恢复50%,因此有望作为治疗AATD的潜在药物[6]。
此外,近年已发现数个基因如编码基质金属蛋白酶1和3及肿瘤坏死因子的MMP1、MMP3及TNF基因变异,可能是影响AATD肺病进展的潜在修饰基因;但目前尚未发现影响AATD肝病进展的类似修饰基因[7]。
最后,环境因素,如饮食、饮酒、服药及共存肝脏疾病也可能会影响AATD疾病进展。目前已知吸烟会加快AATD相关肺病进展,吸烟对AATD相关肝病是否也有相同的作用尚不得而知。肥胖相关脂肪肝具有AATD相似的甲基化模式,这提示治疗肥胖相关脂肪肝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对治疗AATD也有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开展大样本、长期随访的临床研究及相关基础研究来明确。
综上所述,AATD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其发病主要与其致病基因突变有关,但其临床症状、结局变化多样,除致病基因突变之外,还需重视表观遗传、其他修饰基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等非遗传性因素对疾病临床表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