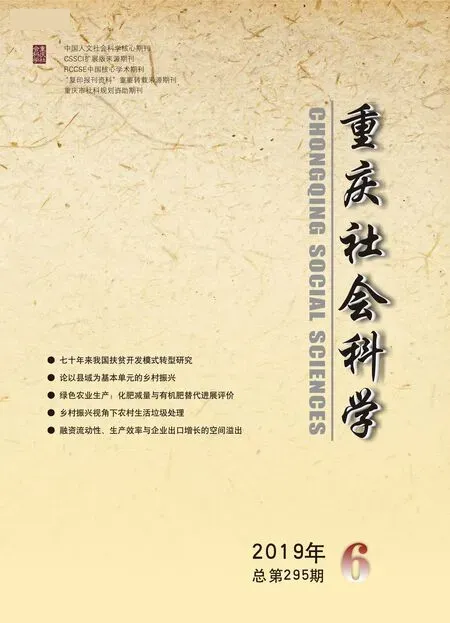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世界观及审美
马倩如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28)
当前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是近代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哲学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要走出生态危机,就需要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人类主体主义的视野,走入更广阔的生命视域之中。所以人类需要一种具有整体性视域的世界观,把人类自身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立场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紧密联结,这种关怀自然与人类命运的世界观就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生态的世界观。它意味着从原来主客对立的机械世界观走入一种人与自然合一的新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世界观的基本内涵就是一种生态的整体观,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个体、整体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动态关联,并且最终构成了整个大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生态世界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结构复杂性决定了生态实践必然会激发出丰富的、深刻的生态审美体验。生态审美体验又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关爱,发挥美与精神价值的作用,对人的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最终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目标,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生态背景
当今人类现实生存境遇正面临外部的生态危机与内部的精神危机的双重压制,人类进一步反思当今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样的反思其实是一种近代哲学的反思、文化的反思。近代工业化在作为一种文化成果时,其中混杂着文化的正价值和负价值。所谓正价值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是积极的,近代工业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时代进步并显著地改善了人们生活等等。而负价值同样也是无法回避的,生态危机的爆发,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精神的失落与心灵的匮乏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势必要对这种近代哲学与文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与反思,以减损、抵消它在运转过程中产生的弊端。
(一)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危机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的农业社会到近代的工业社会的变迁,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刻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在近代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繁荣。但在这种高度繁荣的背后,人类的精神却走入了“逐物”与“迷己”的困境之中。正因为物质资料的繁荣丰富刺激着人们内心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进而又不断地激发起大规模的物质生产,最后便是更大程度地向自然进军,不断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当人类的行为超越自然界自身的自我调节的能力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便遭到了破坏,逐步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当代生态危机,指的是伴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以环境的全面污染为主要内容,在二十世纪世界七八十年代开始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当代生态危机集中表现在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土地荒芜化、水质污染、海洋污染、森林等绿色屏障锐减、物种灭绝、工业废弃物猛增、人口爆炸这十大生态问题。它们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1]由此看出,是人类的行为导致了自身生存困境的出现,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生态危机的发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滞后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或者说在发达的技术与生产力面前,人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重要的因素。人类外在的行为在不断地“逐物”之中,内在的精神世界也走入了“迷己”的困境。所以生态危机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人与自然的核心关系出现了问题。
(二)生态危机背后的思想根源
近代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从十七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始,就把“我”(人类自身)安置为世界的中心和起点。实际上这就是把人类的理性(“思”)纳入到了本体的高度(“在”),让“我”成了世界的主体和自然的主人,人类走向了一种片面的、肯定性的维度当中。肯定了人及理性的优先地位,肯定了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十八世纪后期康德又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发展和完善了以“我”为主体的主体中心主义哲学。同时,加之近代技术理性的兴起,高扬了人自身主体性的价值,完善了主体中心主义。从传统哲学过渡到近代哲学,强调理性主义,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自然世界相对立,人运用理性与逻辑构筑了一个看似井然有序的世界。坚持主客二分、高扬理性主义的实体性思维影响到价值领域,便演化为人是目的,自然存在物是工具,人是认识的主体,人对自然是一种单向度的征服,这就意味着人是宇宙世界的中心。
这种主体主义前所未有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让人在面对自然时摆脱落后的观念,逐渐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意味着人走出了自然,不再拟人化地、神话般地对待自然,对人与自然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肯定了人的精神的独立,可以帮助主体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但把这种主体性的地位、理性的地位不断地肯定下去推向极端时就会贬低、忽略存在物的自立性。当存在物一旦被当作客体来看待时,就被迫放弃了自立性,变成了为了人而存在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人类自我生存的盲区,只能从片面的、静态的、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忽略了人类和自然、人类和他者之间的整体的、动态的、丰富而真实的联系。它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把人类自我抬高到了对自然单向的统治的地位。
因此,在主客二分的主体性主义眼中,自然界是可以被主体理性征服的对象,所以自然界在人眼中的位置也就越来越低。自然界被迫丧失了人类家园的诗意,沦为人类眼中的客体、手段、对象、资源,成了人类欲望的牺牲品。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都直接源于这种现代主体主义所支撑的生存逻辑,这种逻辑正在摧毁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命的共同体、生态的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生态世界观及实践方法
对生态危机发生的行为及思想根源的反思与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人类与自然环境、地球家园的共生共存的美好祈愿,进而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秩序和价值引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自然与人类共生共存的生态世界观能对当前的生态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生态世界观
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主体主义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要走出生态危机,需要重新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类主体主义视野中人对自然统治的机械的世界观已造成了当代生态危机的爆发。所以,当今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超越古代有机论世界观和近代机械论世界观,基于和平的、持续发展的、合作的世界观,携手共同面对全球的生态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应运而生。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做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球生态的这些论述,强调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类的行为会对自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人类与自然应处于一种天人合一、共同命运的关系之中,这才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契合了当代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思想。盖光提出了生态世界观是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一种有机性的世界观,是合理、有效地包容、整合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成果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生态存在理解为包含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的存在。将整个世界看作人—社会—自然相互关联、协调发展形成的复合有机系统整体[3]88-92。由生态世界观的内涵表述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基本观点就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生态的世界观,它从更广阔的生命领域、更宏大的自然背景、更深刻的因果联系中,将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紧密结合为一种系统的有机整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的基本特点是一种生态的整体观,是辩证统一、联系发展的世界观。在这种整体性的视域之下,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人类命运的整体关联和事物相互联系发展的本质规律。在系统的有机整体之中,宏观方面存在着个体和整体两大要素;微观方面存在着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它们最终共同构成整体系统的复杂多样性、稳定平衡性。人类是这个整体系统内部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其他无数的有机体、无机体之间存在至深的因缘联结,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和其他物种甚至是自然本身都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人类自身的行为都可以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产生或正或负的价值影响,人类和自然界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整体,共同从历史中走来,共同走向未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理想
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一种高智商的生命体,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产生了指向社会存在的“小我”,并且在这种“小我”主体意识的影响之下,人类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自然。而当自我意识指向自然环境,并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时,人的视野就超越了原来的“小我”,能对自然存在物产生一种“类”的认同感,站在自然存在物的立场上去感受该物的存在。此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产生一种“生态自我”,这是立足于人与自然整体命运关联的“大我”。这种“生态自我”“大我”不仅包括社会性的“小我”,还包括人类整体,包括所有的动植物,也包括山川、大地、河流、湖泊等等无机物的生命体。如雷毅在详述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时所说:“用‘生态自我’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4]
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社会性的“小我”,走向人类共同体、走向自然的“大我”的过程。也可以说人类主体意识的发展让人类曾经走出了自然,现在又回到自然,而这样的回归并非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人性提升之后,从更高的角度理解了自身与他者,理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至深命运相连。在这个走向自然、走向“大我”的过程中人缩小了与自然的疏离,缩小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疏离,并把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利益纳入自我意识当中,从而对其他自然存在物产生了认同。如气候变暖,可能引发冰川融化,给人类的生存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还可能引发森林大火,高温导致的动植物,甚至是人类的死亡。所以,当人类把视域提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对生命的理解放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维度,人类会对自身及对非人类世界产生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中,自然进入了人的本质,人进入了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体。本质就是那使“物”成为自己的规定性,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为一体就是指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人对自然产生了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同情的态度,基于这样的情感态度中,承认物(自然)的自立性,于是人与物、人和自然都能做到各是其是,各安其所,保持自身自立性(本质)的同时与他者和谐无碍。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理想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本质上的融合的思想根源,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中时,人类也就走出了生态危机,走向了共生共存的理想状态。
(三)“尊崇自然”的生态思维和实践
立足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必须有付诸现实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实践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中就包含了生态的思维方法与生态的实践原则。
首先,从生态思维的角度来说,命运共同体提倡要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理念。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向来主张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最典型的表述便是 “天人合一”。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各家各派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和指导思想。“天”在古代思想里除了具有神化与人格化的倾向之外,很大程度上古代哲人直接把“天”等同于自然。因此“天人合一”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表达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为一的状态。“道法自然”强调人应该遵循自然之道,顺应自然而生活。在这样朴素的自然观的影响之下,人与自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简单又和谐的关系;人是在自然之中,而不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今天当重新倡导“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样朴素的自然观念时,它所昭示的是一种人对自然世界的归属关系,人来自自然,人生活在自然当中,与自然世界是一体的,人的行为要约束在自然的规则之内。
其次,从生态实践的角度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实践行为的重要性。“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解决生态危机,关键在于行动”[2],这些思想都从实践的角度强调了行动的及时性、重要性。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的属性,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一样,“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这就是说人的自然属性要受其社会性的统帅,在人的社会性中完成了自然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社会性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实践,人的生命活动向外展开时就以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实践必然又受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当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出发时,必然会引发不同的实践行为。所以实践在自由意志(人的精神)的引导下有产生背离自然的可能,当这种背离自然的行为与自然发生严重偏差时就可能引发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最终产生生态危机,伤害自然,伤及人类自身。而当前生态问题的产生就是当下物质生产实践的负面现实,其产生的起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是人与世界的对立。人类只有重新确立了自己对自然、对生态共同体的归属关系,人的实践行为才不会逾越自然的范畴,人类才能自觉地将自身行为升华为一种对自然的尊重与回报的行为。在无数个个体实践的联合之中,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整体性的改造,即“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生态审美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将人与自然重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在这种整体性的视域之下的生态实践必然将人与自然万物融合在一起,同时生态实践又会相应地拓展了生态审美的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整体系统中包含了个体、整体、个体和整体的关系这三大基本要素,三大要素之间产生了静态相连、动态影响、彼此共生的丰富结构与层次。在生态美学的场域,这种丰富的关系与结构拓展了审美视野,生成了丰富的审美对象;并在个体的自立性中产生了真实的审美体验;在整体的共生性中产生了终极的审美感动,最终形成了一种系统整体性的和谐的审美意蕴。
(一)审美对象的丰富性
在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中,把“人—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系统的特点就是其中各要素具有自立性、彼此之间具有共生性、整个系统具有稳定性。而系统自身又包含着无数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最终呈现一种整体系统的复杂多样性。当人类以这种生态世界观为视域尺度时,自然而然人的视域的尺度也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尺度。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审美的视野从人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生态的视野,审美的对象自然也扩展到了人与自然合一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去。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有着无数不同种类的生命个体,它们有着自身的自立性;无数不同的自立个体和谐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了稳定完整的生态整体。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是一种“亲和共生”,“生物彼此之间处于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生命净化层次越高,生命的多样性就越发达,生命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生态环境也就越美。我们把生命物种公共生存的环境相互支持和协同进化的关系称之为‘亲和性’”[6]。由此看来,在生态系统内部的生命,彼此之间是处于一种亲和共生的关联之中,事物之间这种彼此亲近和谐的共生关联揭示出了事物与事物之间不是二元世界中简单的对立联结,而是平等互利的、相互激发交融,彼此渗透又不丧失个性的复杂的关联。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关联,让我们面对的自然和世界不可能是简单地符合某种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而成为美的世界,而是因为它的共生性、复杂性,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意味无穷的、精彩丰富的、变动不居的美的世界;并且关系越复杂,联系越深刻就越能显现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就越是美的。
正因为这种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拓展了我们的审美视域,使得审美对象呈现出精彩丰富的特质,展现了色彩斑斓的自然与社会生活,为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
(二)审美体验的复杂性
在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域当中,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有机整体。人类的审美对象可能是个体的生命,也可能是不同层面的整体系统,还可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动态的联结。丰富的审美对象也相应地生成了审美体验的复杂性。
首先,从个体的角度生命展现了独特的自立之美。个体是共同体中的自立体,不管这样的自立体是一朵小花,还是一湾清泉等等。“美在于事物的自立性。”[7]生命体自立的美,是当下的、具体的、真实的,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的、抽象的、可以理性认知的美。这样的美首先体现在生命体的自立性上,自立性就是上文提到的使物成其为物自身的那个本质,它不是能被决定与被限制的,而是自我决定的性质。生命的美恰恰就在于这样的自我决定的自立性中,审美观照的对象只能是自立的个体,无论这样的自立体是人自身还是其他的生命体,都需要保持自身自立性的品格。山中悄然绽放的一朵小花是美的,因为它们在作为纯粹的自立者被观照时才能是美的,美的前提在于事物的自立性。如果以现实的经验来观察这朵花时,人就回到了主客二分的实体性思维局限中,花儿的美被人类主客二分的眼光遮蔽了。而只有回到花儿本身,除去人类的“我思”之时,才能与存在者照面,也就看到了存在者(花儿)的自立性,就能真实地面对自然、万物与人生。此时,山中的那朵小花,已不再是生命的一般显现,而是生命的自我的挺立,真我的展现。像王维笔下所描述的那朵“木末芙蓉花”一样,在寂静无人的山涧中,自顾自地尽情地绽放生命。它无须迎合人的眼光,无须为人而表现什么,只是自在地存在着、开放着。
人类要欣赏到、体验到生命体的这种自立之美,是需要人具有从更广阔的生态视域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放下主体性的优越感时,物就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展现出各自生命自立的美。人不再是站在世界对岸看世界,而是回到世界之中;不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的方式进入世界。此时,人的眼光便是审美的眼光,花红柳绿、鸢飞鱼跃无不是真,无不是美。
其次,是整体共生性的终极之美。整个自然就是无数的自立者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自立体是相互联系着的,这种相互联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的关联,生命体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可以不断地、有序地前进,而是在各种因素、条件之中相互生成,在不同物体的联结、碰撞中存续与发展。这就意味着彼此创生、相互成就、共生共存应该成为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根本之道。在大自然自身的进化法则中,生命的存在不是各自的独白而是相互的对话,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之间有着至深的因缘联系。
在洞悉了这种因缘相连的整体性后,审美者超越理性的、对象性的思维,从存在的角度置身于共同体的生命背景之下,回到自然中,才能理解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体都禀赋着一种全面的、丰富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至深的因缘联结。正如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中讲述的一样:“于是就是四种声音的鸣响:天空、大地、人、神。在四种声音中命运把整个无限的关系聚集起来。但是,四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片面的、自以为特立和独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一方是有限的。若没有其他三方,任何一方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无限地保持着,成为它们之所是,根据无限的关系而成为这个整体本身……因此,大地和天空及其它们的关联,归属于四方的更为丰富的关系。”[8]海德格尔认为的天地神人的相互依存性也正是我们所探讨的整个自然生态的共生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性,成了宇宙人生的最终的根据,而美就是这种最终根据的真理的显现。
在整体的共生性中,涵容了宇宙人生的终极根据,所以海德格尔寄托了人类生存的最终理想“诗意的栖居”。洞悉了存在的真理,往往给人带来强大的心灵震颤和难以言说的终极美的感动,而这种终极的审美感动往往是人能领悟到的生命最辉煌的瞬间。
(三)审美意蕴的圆融和谐
当人类把视域投向这种宇宙万物的共生关联之中时,实际上就走出了人类“小我”的局限,走入一种生态的“大我”之中。人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与世界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人类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目标,正如《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天地各得其位,各有秩序,自成和谐之系统。天地中的各个生命体也能得到相应的育化,生生不息。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自然而然,有序有则。天地和谐了,万物生机勃勃。在天地中的人就要发挥“致中和”的“致”的作用,通过向外的社会实践建设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通过向内的功夫修养建设一种和谐的心灵境界,才能达到人真正的“和”。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生态关系的紧张就是在人的因素上,失去的“和”的能力,整体上便失去了天地自然中的和谐,只有复归于天地自身的和谐秩序,复归于人精神本体的真实和谐,才能天地人伦各得其位,自然宇宙间才充沛着生生不息的能量与活力。
天、地、人三才的和谐是宇宙根本的和谐,实现了这根本的和谐,生态问题和人内在的精神问题,都能随着根本问题的解决迎刃而解。这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终极问题,对于这个终极问题的探索和解决需要人类恒久的反思与实践,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被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解决。只有落实于实践中去反思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类的视域拓展到整个自然与人类共生共存的境遇中,才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精神前提。自然宇宙的生命就是人类自身的命运,对于自然宇宙和谐性的追求成了人生命中最宏大的目标。这种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自然价值的认同,最终产生了一种融聚生命情感的和谐圆融的审美意蕴。
当人类以自身和谐为起点,宇宙和谐为目标时,便会自觉地从个体出发,积极地调整和规范自我行为,能与己和,便能与人和,与人和便能与天地和,最终实现宇宙人生的大融合。同时,人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入了一种审美化的存在当中。人类关于整体和谐性的追求自然而然成就了一种和谐的审美意蕴。与己和,成就宁静顺性的自由意蕴;与人和,成就温柔敦厚的人生意蕴;与天和,成就自然无为的天地意蕴。在这种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中,生命齐同天地,万物圆融无碍,自然和光同尘,人类走向了至美至乐诗意性存在。
四、余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思想就是一种生态的世界观,它对于当下人类的生存现实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从命运共同体的终极性视角来体察当下的生态世界的裂隙,人类才能深刻察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今天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基于这种自然与人类命运共生共存的自觉,会在相应的生态实践的场域发生重要的影响,生成丰富而深刻的审美的体验,促使人们深度感受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和意义,并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那种生态审美的和谐意蕴,最终实现了人的生命价值的提升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