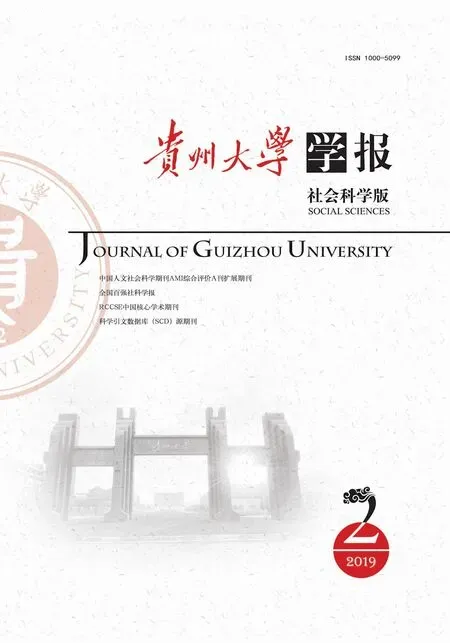德、礼和乐:传统君子人格的三个维度
何善蒙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22000)
一、君子:孔子对于儒家传统的标志性设定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儒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思想就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和行为准则。尤其是自汉武帝儒术独尊以来,儒学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着传统的教育和候补文官的培养和选拔,这使得儒家的教化通过现实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而得到强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行为的基础。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对于儒学和中国传统政治来说,是双方互惠的一种自然选择,由此,政治具有了儒家伦理规范的理论基础,而儒家则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掌控着思想文化的主导话语。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到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回避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当我们在讨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也决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环境这一基本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代表了中国传统。
当然,对于什么是“儒”,一直以来有着争论。如《淮南子·要略》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儒者以六艺为法”,而《汉书·艺文志》则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些解释侧重的角度不同,或者从起源,或者从含义,或者从功能。近代以来,学界对什么是“儒”的争论更是一度成为热点。不过,尽管人们对“儒”的解释存有歧异,但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儒家/儒学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思想形态,基本的概念指向都与孔子和仁义道德密切相关。其实,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去认识儒家/儒学,有一点不可以跨越,此即:孔子是任何一种诠释的中心;换言之,我们在讨论儒家/儒学的时候,无法跨越孔子。儒并非是孔子所创造的,因为按照既有的研究,在孔夫子之前即有作为职业而存在的儒,孔子自己也曾有君子儒、小人儒的说法,但是,作为儒家学派——即以某种核心的价值精神而形成一个思想流派——则是从孔夫子开始的。
那么,孔夫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最为基本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呢?从《论语》出发的种种既有的研究表明,人们或者试图把孔夫子的基本观念归结为仁,或者归结为礼,或者是仁礼并举。我们以为,虽然仁和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作为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来说,应当是以仁最为基本。仁在孔夫子这里代表着一种精神生命的价值和体验,表达的是建立在个体道德实践基础之上的生命境界,成为夫子对于人的日常行为的核心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仁才成为诸德之总称。由仁的生命境界出发,可以直接引导出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道德规范、要求。可以说,正是因为仁,人类的道德生活才具有了扎实的基础和切实的可行性。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一百余次,这也直观地表明了夫子本人对于“仁”的重视程度。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于“仁”的基本规定,并且以“恕”贯于整个体系之中。但是爱人是有原则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与恶的前提是仁者,亦即要符合礼的要求。“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知、勇、仁是孔子所认为君子应当具备的三种品格,也是孔子人格理想所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虽然把仁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但不忽视知识的学习,“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道德修养不能代替知识学习。勇是与道德意志相联系的,非匹夫之勇,盲目之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勇强调的是个人对于道德目标的强烈的渴望和坚忍的意志。仁是核心,“仁者必勇,勇者不必仁”,知是仁、勇的前提条件,知是为仁服务的,体现的是仁的要求,同时,勇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的。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仁?这也是孔夫子所极为重视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仁的实现取决于主体的自觉。读书为学均是为己之学,目的是要使自己实现仁知勇统一的境界,同时使主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实现心理上的愉悦。孔子认为,为仁不是个人能不能的问题,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境界是能够达到的,其方式就是能近取譬,将心比心。换而言之,道德之学没有外在的目的,是纯粹为己的,当物质利益与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体应当恪守义利之辨[注]追求财富,摆脱贫困必须有道德原则,承认这一点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排斥财富,而在于财富的获得是否是在道德的标准下进行的。的道德原则。
在孔子关于儒家传统的基本设定中,“君子”说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语》中,“君子”有107见,“小人”有24见,“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者有19见。何谓“君子”,何谓“小人”?杨伯峻先生指出:“《论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论语译注》)。作为一个观念,君子和小人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在孔夫子之前就存在,在《诗经》《尚书》以及《周礼》《仪礼》中,君子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汇,或者是以社会贵族的身份,或者以女子的丈夫的形象表达出来,大体上都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孔子对于君子的概念予以特殊的重视,是他论述的中心和重点。为了辨清“君子”的形象,孔子常把“君子”与“小人”比较而论,从道德修养、人格理想、义利观和行为观等方面区分了君子和小人,指出两者根本的区别。如果我们说儒家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话,那么,儒家的这种道德传统的承担者,就是君子。这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的一个最大改变,也是对后来的传统有着深远影响的设定。可以说,从孔子开始,君子就成为了儒家形象的现实代表。因此,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这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那里,当然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孔子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对于道的自觉承担,是君子的使命。君子之为君子,对于孔子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否自觉承担道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里仁第四》)。正是在道德担当的意义上,孔子完成了对于君子形象的重大变革,从身份君子变成了道德君子。将道德确立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这是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根本的影响,“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儒家思想的基本形式就是以仁义为根本的精神价值,道德成为了儒家最为重要的符号,而这个,恰恰是孔子所确立的,由此拉开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差异,真正地确立了儒家的精神世界。将道德赋予了君子,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这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的最为根本性的影响。这个影响与儒学的根本价值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密切相关,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调。
二、德:君子人格的内在规定性
如前所言,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主要是以道德作为最重要的精神价值,而道德的价值,不是一个空泛的说辞,它必须有着可靠的基础。为了能够使得儒家的道德理想具有更为扎实和可靠的现实基础,孔子将承担道德的重任赋予了君子。由此,君子也由一个社会地位的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从而现实地挺立出了儒家的道德理想。
在孔子对于君子的所有设定中,君子首要就是一个道德的承担者,是必须承担道义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对于道(道德),君子有义不容辞的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个体,君子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道德而不是个人的利益问题,必须要承担道德责任,是不可以选择的,必须一以贯之,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为什么必须由君子来承担道义?因为,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原本就是一个具有社会地位的人(贵族),有社会地位的人,自然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儒家道德理想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设定[注]所以,事实上儒家对于道德的设定,是基于非常平等的前提,这一点很多人往往会忽视。其实在先秦儒家的道德论述中,对等性原则是得到了非常重要的贯彻的,比如《论语》中对于“忠”的论述,“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很明显是对于道德行为的双方,都是有着明确的要求的,而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设定。。所以,孔夫子将道德的责任赋予君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君子和小人是不一样的,君子有社会地位,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而小人则没有社会地位,也就没有道德责任,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的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小人是被教化的对象,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可能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非常现实有效的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从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子的特殊意义也就十分明显了。由此,道德理想的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君子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其社会责任,这是君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其道德担当所在。这样设定,孟子论说得非常清楚: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很清楚,老百姓和士君子所关心的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解决,是利益问题的满足,所以,如果作为一个统治者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于欲望的追求,是不可能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的。所谓无恒产,无恒心。而士君子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就是道义,是以道作为判断的中心的,道义无关乎个体欲望的满足,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这样的设定,非常明显地延续着孔子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基本区分而强化君子的道德意义。
在孔子那里,君子和小人的价值取向截然有别:“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论语·里仁》)。君子必须承担道义,小人天然可以唯利是图,这就是传统中所说的义利之辨[注]当然,义利之辨并不是像通常理解的那样,君子是必须放弃对于利益的追求的,这实际上是对于义利问题的一种误解。在儒家这里,并没有要求君子放弃利益的倾向,孔夫子曾经明确的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为之。”义利之辨事实上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问题,而不是要求君子对于利益的放弃。所谓价值选择,是说在面临义利的冲突、选择关口,作为一个君子是必须以义为先的,这是君子承担道义的责任所在。所以孟子也很清楚说,“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不可得兼,就是意味着冲突的存在和选择的必要性,这只是一种冲突的情形,而不是一种常态。。而后来陆九渊对于这章意思的解释,非常能够表达出来儒家对于这样的一种道德意义的坚持: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陆九渊讲这段话是发生在淳熙八年(1181),当时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就在白鹿洞书院讲了《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据说当时听的人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陆九渊年谱》)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陆九渊主要讲的是立志的问题,按照陆九渊的看法,义利的差别就在于人之“志”如何,小人和君子之别由此而产生。
总之,在儒家的传统中,以道德为本,这是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基本立场。从一个社会地位的形象,转变为一个道德的形象,这是在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的确立。
三、礼:君子行为的外在限定性
如果说德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的最为重要(以道德作为君子的责任)的改变的话,那么对于礼的坚守,则是君子作为一个贵族形象所具有的行为规范,这是君子形象的历史遗留。德是一个精神价值意义的君子形象;而礼的坚守,则是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贵族所具有的外在行为的要求。
作为一个贵族,君子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礼就是对于君子生活的基本要求。《说文·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侍奉天地神明,以达到求福致福的目的,这可能就是礼的起源,所以,《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合于天地人神,就能够理顺万物,达到“致福”的目的。由此可见,礼最初的本质是和谐天地人神,也就是说,在事奉天地神灵的意义上,礼具有了其最初的意义,而在对于鬼神的祭祀仪式中,礼仪由此产生。而这种礼节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对于贵族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规范,从而要求君子的日常行为,而这种要求,根据《仪礼》的记载,实际上是涵盖在君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谓“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邵懿辰《礼经通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子的日常生活,就是被礼所规范出来的日常生活。礼成为了君子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最具有规范意义的和典范意义的象征。“君子无礼不动”“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礼记·仲尼燕居》),一言一行都合于礼的规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君子动则思礼。”《哀公十一年》又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渗透到君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礼记·仲尼燕居》)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左传》成公十三年)
《左传》的这段话,很明显地表达出了礼对于君子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标识性意义,“君子勤礼”这是作为君子的“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只有在对于礼的坚守中,君子才成为君子,君子的生活才成为君子的生活。
对于君子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合乎礼的要求,在孔子那里也是得到坚持的。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礼给予了非常重要的关注,比如在《乡党》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对于君子日常行为的意义。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礼甚至是有些繁琐,但是,正是在这些繁琐的仪文制度中,君子的人格形象才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一种基于礼的规范而来的贵族生活的形式。在《论语》乡党篇中,孔子的举手投足,对礼的遵循非常清晰: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寝不尸,居不容。
席不正,不坐。
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很形象地感受到一个对于礼的坚持的君子的人格形象,正是这些具体的礼的存在,才使得君子成为一个具有威严的、行为合乎规范的具体的人格形象。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并且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以礼来要求和规范自己,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化的要求,而是对于自我生命本身的认同和提升的要求。因此,在具体礼的规范同时,孔夫子更多要求的是对于自我内在的关照,使得礼可以超越纯粹形式的意义,而具有了和个体道德相关联的含义: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对于君子来说,礼是其生活本来就有的内容,也是不得不遵从的外在规范,这是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一种必须的行为方式。如果一个君子不遵守礼,那么很显然是对于其自身立场和身份的违背,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背离的结果,自然就是社会混乱的表现,所以在《八佾》中孔夫子对于乱礼的行为予以了非常严重的斥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但是,如果礼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那么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化,而礼一旦流于形式化,则其被背弃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要“文质彬彬”,即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形式就是作为外在规范的礼仪准则,这是对于一个阶层的身份认同。而内容则是道德价值,这是对于一个阶层的精神价值的认可。两者的结合,成为了后世儒家对于君子形象的一个总体认同。
四、乐:君子人格的精神境界
儒家强调德和礼,作为对于君子人格形象的基本要求来说,两者有着不同的内涵。德更多是对于君子的精神价值的确认,而礼则更多是对于君子人格的外在形象的塑造。当然,无论是礼,还是德,都是一种规范,差别在于一则是外在的、他律的,一则是内在的、自律的。既然是君子,其生活必然是需要有规范的,无论是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的价值追求。但是,在儒家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君子行为的规范,并不是让君子表达出非常受局促、限制的那种感觉,换而言之,这些规范对于君子来说,实际上是需要通过自身的修炼以内化为自我品性的一部分,从而达到对于外在的限制性的超越,而呈现出一种快乐的境界。快乐的境界,则是儒家的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儒家的传统一直如此,在孔子那里开始,儒家从其开端处就十分强调这种乐的精神,这在儒家的经典系统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表达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作为《论语》的第一章,本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我们忽视[注]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观念,《论语》的编撰是随意的,没有一定的倾向性的。但是,无论从《论语》的历史影响来说,还是从我们今天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似乎都应该忽视本章在整个《论语》文本中的特殊地位。。我认为这一章实际上传递出了《论语》(或者说儒家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信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学和乐。两者有什么差别?简单地说,“学”是孔子儒学的真精神,在《论语》中,孔子对于自己特点的概括,就是“好学”[注]比如,在《论语·公治长》中孔子就很确定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如果我们从后来儒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广泛的好学传统来说,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换而言之,如果离开“学”这个基础,儒学将无以存在。“乐”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儒家倡导的是“学”的精神,通过对于诗书礼乐的学习,最终想要达到的境界是什么呢?那就是乐,一种快乐的精神。这在儒家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无论去读《论语》,还是去读《孔子世家》,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孔子所传递出来的这种精神的境界,快乐的境界,对于儒家来说,是一种精神生命完善的表现。本章的内容,实际上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句话,是从个体的学习的行为来说,是快乐的;第二句是从跟朋友交往而增进学习的事实来说,是快乐的;第三句是从人对于自我认识的意义上来说(从学习作为自我完善来说),也是是快乐的。如果从一个人的经验生活来看,这里既有经验知识的学习,又有人际互动,又有自我感知,可以说覆盖到人的整个生活世界,这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快乐的精神是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最为根本的特质。而作为一个君子,在孔子看来,必得以学习和快乐作为自己生命中的两大要件。
如果我们从孔夫子的一生遭遇来看,虽然他的一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是,他发自于内心深处的那种快乐,是从来没有消失的,这其实就构成了孔子形象的最大意义。孔子对于其最为重视的学生颜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予了肯定,孔子对于颜回推崇,实际上也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好学,一个就是快乐。关于颜回的好学,在《论语》中,孔子给予了非常明确的确定,而且,按照孔子的说法,他的弟子唯有颜回好学,无论是在《雍也》中回答鲁哀公时,抑或是在《先进》中回答季康子的问题时,孔子都是很明确地确认颜回是唯一好学的特质,“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而对于快乐这一境界,在颜回那里,同样是得到了极为直观地表达,“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我们都认可,颜回作为孔子弟子的特殊地位,即,颜回是孔子最为赏识的弟子,也是孔门最为重要的精神象征。而颜回的特点,恰好就是孔子在《论语》开篇中所揭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不能把《学而第一》的第一章简单地忽视过去,它实际上是对儒学真精神的一种直接描述。尤其是在孔子和颜回身上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快乐的精神,更是受到了后来儒家的普遍推崇,“孔颜之乐”的提出[注]理学对于孔颜之乐的推崇是非常明显的,周敦颐就曾经说,“颜子‘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 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 而乐乎贫者, 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 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 心泰则无无不足;无不足, 则富贵贫贱, 处之一也。处之一, 则能化而齐, 故颜子亚圣。”(周敦颐:《周子通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第38页)这样的说法,在理学的传统中是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对于孔颜之乐的推崇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昔受学于周茂叔 (周敦颐) , 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 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从后来理学的历史脉络来看,包括朱熹或者王阳明,虽然在立论上有着差异,但是,对于孔颜之乐的推崇确是一贯的。,非常直接地表明,快乐作为一种精神境界在孔子那里,具有着特殊的意义。由此,在孔子和颜回那里,恰恰都是非常准确地传递出了儒家对于生活世界的这种快乐的精神的坚持。这种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家的最为重要的传统。这一点,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孟子也十分强调君子的快乐,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尽心上》)
孟子依旧强调着快乐作为一种精神境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为君子必然是有快乐的境界的,当然,君子的快乐跟世俗的那种基于欲望享受而来的快乐是根本不同的。在孟子看来,君子有三大快乐,称王天下不在其中。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没有怨恨,这是第一大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大快乐。对此,朱子曾经做过解释,“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四书集注》),不愧不怍,就是对于个体道德的要求和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唯有道德之完善,才是君子个人的努力可以达致的,并非是受制于他者的,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所以,毫无疑问,快乐自然就是个体完善的道德境界所彰显出来的,或者说,就是因为个人的道德努力,最终表达在精神境界上的状态。君子是要做道德的努力的,而且,君子的这种努力,也是快乐的!因此,对于一个君子来说,道德完善、礼仪完备所带来的是自我的最终确立,这种自我是以一种快乐的形象而呈现在生活世界之中的,这一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由孔孟而来,得到了非常有效的坚持。
如果儒家的传统只有礼义的坚守,只有道德的要求,可能在历史上很难实现出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而正是在快乐的境界上,儒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口,这是基于人类的生活特性而来的,反映的是生命的本真特点,由此,儒家的生命力以及儒学的精神价值,才是真正永恒的。由于快乐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经验事实,它和经验生活之间的关系原本就非常密切,或者说,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生活的本来特征。生活世界本来就是活泼泼的、快乐的,这样就把对于现实生命、感性生活的关注,切切实实地落到了具体的生活世界、生命感受之中。由此,作为一个君子,他不仅是有道德承担的义务的、有礼仪规范的要求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君子的生活是一种快乐的生活,这对于君子形象的完善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