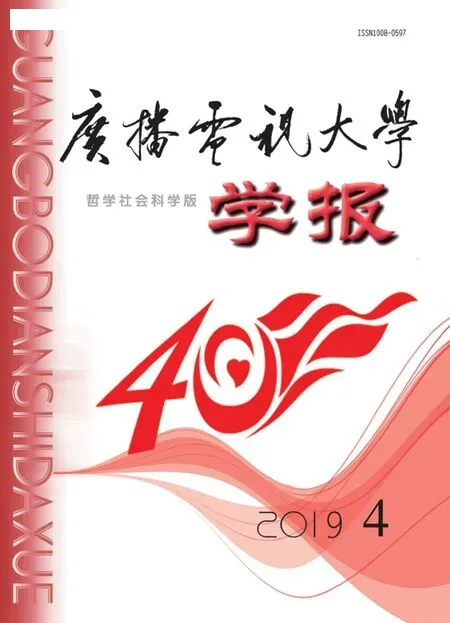一次穿越麦田的精神之旅
——论何敬君《谛听:阳光走过大地》
关海潮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1100)
《谛听:阳光走过大地》[1]是何敬君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诗集,也是诗人的第四本散文诗集。青岛作为散文诗的创作重镇历来备受关注,何敬君承袭诗歌写作传统创作出了“很值得推荐的优异杰作”[2],获得散文诗前辈耿林莽先生的称赞。栾纪曾也惊叹于老同事:“时下世事虚华炫嚷,何敬君身处纷杂烦乱且全社会聚焦的广播、电视等新闻漩涡多年,对散文诗写作如此执着和坚守,不仅是一种文学与精神定力的显现,更是一种可贵的生命情态。”[3]王幅明在“21世纪的散文诗丛书”中收录有何敬君的散文诗集[4]。学者徐妍对诗人创作也有持续关注[5]。
在这本新出版的散文诗集中,何敬君带我们一起走过他的穿越麦田的精神之旅。也许一提到“麦”“麦子”“麦地”,我们脑海里便会闪现出80年代的抒情诗人“海子”,他的“养我性命的麦子”(《麦地》)、“在麦地里拥抱”(《五月的麦地》)、“熟了麦子”等等都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如果说身为南方人的海子的“麦”作为“词根”具有“文化原型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符号,一种巨大象征性的符号”[6],那么在何敬君——这位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笔下,“麦”作为意象因更多的渗透着个人的日常经验和生命历程而呈现出了别样的精神情怀。也正因为此,题目里的“麦田”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具象的以其为代表的一类古典自然意象,以及与此有关的民间风俗和传统文化(在此诗集中表现为对二十四节气和古代传统节日的描述),更浸润着诗人对“安宁朴素和生命的秩序”(《冬至:往北去》)的守望和追寻。
一、 “乡愁”:“麦田”的记忆
散文诗集《谛听:阳光走过大地》是“中国有诗以来,第一部在二十四节气中探寻散文诗境的作品。”[7]从其诗歌内容所涉及的题材来看,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集聚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它自身时序特征已经根植为中华民族的特有记忆,不论是因循农业文明的自然规律,还是对家族血脉绵延的“寻根”之旅,都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这一维度,柏桦称之为‘尚古’”[8]。何敬君的这部诗集前后历时十年,无一例外都酝酿于“城市”之中,由于在海滨道散步的机缘,对立春的感受促使“我的某种深层的意识似乎在那几分钟觉醒了”[9],遂而有了对二十四节气的整体性思索。我想诗人所言的“某种深层的意识”,是“尚古”,尤其表现为“乡愁”。
诗人的这串“乡愁”交织着二十四节气和其一一对应的气候、物候变化,其间来自对自然大地的细致观察凸显了乡土中国作为将要“逝去”的立体记忆在诗人这里的独特价值。通观这些诗歌,“麦”这一意象成为感知二十四节气脉搏跳动变化的不可缺少的存在。春天里,“我”“在干旱的大地上穿过‘雨水’”“为麦子”祈雨;在“蛰伏者和甦醒者的节日”(惊蛰)中,“越冬的小麦”也加入这场即将拉开帷幕的“最辉煌的演出”中;夏天里,“老家麦子的爱情已经成熟,期待临近的婚期”,“麦浪是田野的音韵”,在小满里“低低地歌唱”,“麦芒”在“芒种”时节疯长着,叶子变黄,籽粒饱满,回归粮仓;而在秋季,沉睡的“田野依然疲惫地伸着懒腰,等待我的父亲去慢慢敲醒……”;冬小麦在“小寒”时节“在大地上独自热闹着”“往地下扎伸根须”,共同“等待着雪的消息”。由“麦子”绵延的记忆将诗人与我们一同带回到纯粹的乡间自然,体味由植物生长变化以及与人的互动关系构成的寒来暑往,夜短昼长。西班牙诗人马查多有诗云:“记忆有益于一件事/令人惊奇地:它把梦带回。”而在何敬君笔下,记忆带回的是如梦般的童年记忆和简朴的农耕生活,波德莱尔式的感官综合就如“阳光走过大地”的通感般明亮澄净,清澈透明。我想这其中必然有何敬君身居都市“围城”的一份浓浓的“乡愁”。
如果将这份“乡愁”仅仅定位于对表层“物象”的“现实主义”描述,无异于忽略诗人最重要的精神内核:“诗歌的实质并不在于词语的声音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色彩,也不在于他的音步,也不在于感官的复合,而在深层的精神冲动。”[10]而这与前述诗人“某种深层意识”相关,或者是它组成的一部分,也是构成“乡愁”的驱动力量——生命意识中的历史感,这一方面很明显地表现在对传统节日的描述中。我惊讶于在这12首散文诗当中,作者提到父亲/祖先/古人的次数。或是祭拜,或是迎接,或是敬畏,情感至深,而也由此洞察出西式公历的时间秩序给我们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剥夺了古人留下的生命仪式。
正因为此,何敬君的散文诗将节日习俗重申为与“古”的对话的诗学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典型地体现在《谁是大地的主人?》中:
我想对你说,在今天,在往后的日子里,要对那些不曾见过也不曾梦到过的人,对那些遥不可及久久仰望过天空、俯瞰过大地的人,对他们俯首敬仰。
他们曾经沉缓而有力地说过:五月是一个“恶月”……
他们曾经无数次叮咛过:人们啊,你们要懂得大地上的生命,要让他们自由生长……
我们知道,他们未曾尝试主宰大地,他们未曾有过这样的异念。
他们说了一些话,安排了一些事情之后,便去了更加遥不可及的地方,或成佛,或得道,或化为鬼魂,风影一样游弋。
这几句引文中的你在诗文中有“YM兄”作指涉,但我想把它当成对阅读者的言说应不为过。我们都知道端午日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而设立的。诗中的“不曾见过也不曾梦到过的人”“遥不可及久久仰望过天空、俯瞰过大地的人”的“他们”是以屈原为代表的真正的“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者,这里诗人指出了“他们”除具备上述情怀之外,还提出:尊重生命生长的独特性、强调自由意志而非作意见领袖、留下精神遗产追求独立人格这几点特质。结合中国当代历史,文化政治式的对应解读虽然在这里留下些许痕迹,但诗人对他们的“俯首敬仰”有如宗教信仰般的靠拢呈现出价值的倾向性才更值得重视。“大地在天空下飘荡了一千年又三千年……它慢慢变成了不只是谁的奴隶”的批判性大概达到了整部散文诗集的最大强度,而同样伴随着对现代化带来的习俗的消失“端午日已是举家郊游或演绎情爱的假日、艾蒿、五色索、粽子都使往日的情愫消散,诗人逐步将古典传统文化被解构的宿命推至顶峰。然而,诗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思,“而我自己在四季恒温的书房里四处游走,腆摸着肚腹。”这一句诗,看似轻描淡写,却将诗人以“我自己”的主人公身份和盘托出,不隐瞒自己与“人们”的“共谋”立场。随即,自然而然有了接下来的发问:“到哪里找一条溪流濯面洗心?到哪里看几缕炊烟摇曳土地的恩赐?”对“你”的“拷问”(《中元节,敞开院门》)也可当作一种扪心自问,精神于何处栖息?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批评家,应该具备与其雄心或欲望或使命感相称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深度,他应该对世界文化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11]我想何敬君以“乡愁”之名完成了这次“尚古”的精神之旅,这构成了何敬君散文诗的母题。
二、 局外人:“省略号”的叙事
何敬君曾在“后记”中自言,“读大学之后就生活在城市,自以为离开甚或主动疏离了许多人眼里的‘乡土’文化。”句中的“自以为”颇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味,这也是本文中“局外人”的内涵指向:身在都市,心归自然,所以有了深处自然之外的陷入都市的“局外人”身份,很显然文本依然是把“自然”和“乡土”当作诗集的中心范畴。
如果说“局外人”身份的获得在某种意义上是地理位置的迁移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也正因为这种“区隔”的划分使得诗人在“内”与“外”的感知差异凸显,从而获得更深的体悟。《谷雨:我听不懂玉兰花在说些什么》是这种感觉最直观的表达。诗文中,作者看着“花瓣儿与花瓣儿悉悉簌簌地热烈交谈着”“她们像幼儿园里下了课的孩子,又像广场或草地上散漫扎堆的女子/她们揽腰搭背,厮鬓磨耳,面带羞涩而眉飞色舞/她们交谈着,议论着”,一遍又一遍在重复“而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我想这时的作者,隔离在玉兰热闹世界之外,不免有几分孤独落寞,尚未有更深一层的认知。到了2014年的诗歌当中,这种认知逐渐被清晰化:“无花果悄然而神秘地成熟了/它的果肉让我品尝春风和夏雨和秋天阳光融会的玄妙/它的籽核像在讥笑我的愚钝和麻木:我不曾在任何世界想象到一棵树的身体深处……”“愚钝和麻木”大概是诗人的天敌,“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挽留和拯救的正是一种感受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是对世界的诗化的领悟。”[12]而这种感受力的下降,源自于都市生活的相对而言的理性与规训,《秋分:我又错过了一场典礼》中诗人从形象与内容两个方面都使我们在“城与乡”之间有明显的分辨。
“普照的阳光开始拾掇行李……
我如往日一样,在摄氏24度的房间里,喝着机器净化过的像水一样的液体
目光在湖蓝色的窗玻璃上撞成一地又一地碎屑,被清洁工归为不可再生的垃圾
花盆里三种植物疯长着同夏季里一样的春意
我已不再需要短袖衫和绒衣裤,只需保持玻璃缸里金鱼的微笑以及轻言慢语,脸上盖一张不挂些许怅惘抑或踟蹰的绿萝的叶子”
首先从这段文字的“物质性”层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句子开始变长,这是与之前描述自然之物轻快的短句(“隐隐的雷声召唤,蛰虫从深梦中苏醒,舒展慵懒的腰身,抖落冬蛰的积尘,以滑步蜿蜒而出,来到季节的舞台上,唱起无声的交响诗/微微南风伴奏,阳光均匀照洒,温暖深入躯体”以及之前例举的关于玉兰花的内容)具有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如果说句子的长短并不能成为两者对比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可以从听觉上来考察句子内部短语的音调,不难发现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短语——摄氏24度、机器净化、像水一样的液体、碎屑、清洁工、不可再生的垃圾——阅读起来起伏不明显且音调单薄冷漠,并没有自然描写所运用的词语跳荡、丰盈,节奏感弱,这也构成了诗歌语言的客观性例证之一。而这样的一种文本机制被柯雷称为文本的“形象性”:“形式直接确定内容”,“在这种机制下,文本形式成为内容的形象或图像(icon),而不再仅作容纳内容之用的可有可无的文体。”[13]这是何敬君诗歌形式的潜在层面。
再从内容观察,“诗歌作为‘经验’(里尔克语)”[14],其对日常生活事物的描述更多带有偏离和漠视,相对而言,散文的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更接近(“大雾漫漶,尘霾浮嚣,驿道塌陷,Wifi断路”),这也构成了何敬君写的是具有散文意涵的诗歌的特质之一。其次,由以上描写这些都市生活的短语的生硬之感也可以让我们明显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变化:“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肚量取代了身份、从而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利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15]作为“局外人”的何敬君想必对此深有体会:夏暑之日“在响亮的阳光下翻晒仅有的衣服”到“我已拥有多种面料和款式的衣服;但很久没有在阳光下曝晒”,而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温情也被假笑、轻言慢语、和类似静态的面具表情所替代。由此,形式与内容的一致性让我们能更深地了悟何敬君传达出的情感密码。
城乡之间的鲜明对比在何敬君诗歌中鲜明地存在着,《小暑:漂浮于时浓时淡的往事》《小雪:山里的消息》《寒露:在时速300公里的列车上》《上元夜:我仍旧仰望天空冥思》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一条潜在的分隔符——省略号,被鲜明地放置在作者将要回顾旧时、或是作为“梦”的场景中乡土记忆影像的开端。我想这是何敬君的特殊发明,也是给读者阅读时的一个启发。譬如上文的“普照的阳光开始拾掇行李……”的省略号其实意味着语意里物象描写区域的转换,结合前两句“迁徙鸟听到了天街上调集车马的消息,它一大早就伸展翅膀梳理羽毛/他要跟随太阳的脚步”,与之后的内容相对比便一目了然。
在何敬君这里,省略号所代表的省略之意固然仍有遗迹,但更大程度上展现了诗人对散文诗叙事形式与内容的调节,从而也能感受到诗人在“省略号”前后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自由转换,这样的方式在展现了诗人酝酿语言的过程的同时,也使读者在阅读时形成没有隔行空隙那么大的稍稍停顿的由视觉引发的思维习惯,相伴随的是读者也做好了进入另一时空的情绪准备,读者被邀约和诗人一道进入新的“叙事”,散文诗中的“散文”性质再次被确认和激活。
三、 摆渡:“道在人伦日用之间”
“溱与洧,方涣涣兮……”
我们来一场最初的沐浴,以歌声和蜂蝶的翅膀擦拭经过的天空与河岸
然后,漫步青草之间,我赠你芍药,你馈我幽兰
手指花林深处:杏雨幽幽,桑云淡淡……
这是节选自《上巳节,去趟上古》中的一小节,开头选自《诗经·溱洧》,学者赵园曾评说:“这一句总能使我在目光触到的瞬间心醉神迷。我看到了一片深而清澈的水,水波荡荡,在阳光下闪闪灼灼。”[16]随后,诗人所描述的动态画面让我们同样心醉神怡,似幻如梦,淡远宁静又不失浪漫欣喜的雅致,这样的乌托邦憧憬表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了和谐与质朴的感动。这样植根于古典诗性的农耕记忆在救赎着都市被现代的命运的同时,也启迪了我们“传统中国人的人情物理以及生命哲学”[17]。
何敬君是1957年生人,经历过八十年代诗人作为“文化英雄”的神话和九十年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18],以及其中诗歌代际潮流的更替,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何敬君的散文诗并不似《今天》的宏大叙事承载的“意识形态”、先知般的视野、正义、美、真、苦难的灵魂等重大命题,但也并不只是“诗到语言为止”的仅为“他们”的写作[19],在“崇高”与“世俗”之外,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何敬君安然地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游走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的交叉地带,似乎是文化人不得不面临的宿命,何敬君一方面,曾深入新闻工作的前沿,对时事(大历史事迹)的敏感体察和对现实小事(现实往往比小说、电影更残酷)的捕捉、对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社会的变化的率先感知、对“新媒体”等等时尚化、大众化的流媒体方式的兴起以及纸媒的衰微所带来的算法的运用对整体阅读取向的把控都有“在场”的体会,现代人无根的漂泊加之后现代碎片化的价值取向,人们越发难以找寻精神的栖所和皈依,也就越发适应个体作为社会运转的机械化生产的手段,所以另一方面作为诗人的身份认同尤为重要,“在芜杂的现实生活中保留自己的一小块领地,用心耕种着,适度地挥洒一下情感,散发一下思索,开放自由之花,收获思想之果。”[20]
偏安“琴岛”一隅,与北上广的众声喧哗不同,小城的“自然地理环境好,适宜人生存;跟大城市比较,多了很多朴实和舒缓,给人的压力小,满足感大。”[21]我想这也是与何敬君本人的性格以及诗歌精神相互依托、相互生成的。“随遇而安”的诗人写出的诗歌给人整体感觉:平和、朴素、真诚,没有佶屈聱牙亦没有汹涌恣肆的情感波动,就像海岸边时不时涌过来的浪,就像麦田在风的吹拂下缓缓地摆,不温不火。也正因为此,个体的修养不是凌空地化鹤与成圣,而是朝向了人伦日用间。“人活着”的命题在何敬君这里更为踏实和细密。
“活着的标志就是渺小是安身立命”[22],选取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这一题材首先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所谓“安身立命”,时间的分割和循环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绵绵不息和源源不断,成为我们生存的规律性依托,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华民族更如俗语所言“靠天吃饭”,所以,二十四节气对我国来说更具有生存本体的重要意义。所谓“渺小”,何敬君在散文诗里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理念:以古人为师,以自然为法。不论是祭拜古人的虔诚(“整洁堂屋,拾掇院子,供奉新鲜的玉米谷子和扁豆/祭飨回家的亲人/也招待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我以目光一遍遍抚弄,以呼吸以鼻息拥抱/我看到灰朦中更多色彩泛出,阵阵敬畏直抵心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何敬君在谦和、低调中耕耘自己的生活,并努力感受它。而这样的生活状态即如作者所言“对一步一步走着路的人而言,能够活得有滋味,充分领略活着的全部意义,既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追求,本身又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那种对生活的爱,来自对现实生活中一切现象的始终如一的关注,来自了解一切、看见一切和理解一切的热情(库普林语)’”。[23]
李泽厚“人类历史本体论”从“人是什么”开始,提出“人活着”(出发点)、“如何活”(人类总体)、“为什么活”(人的个体),而将归结于“活得怎样”,他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儒道传统思想,提出“如何活”、“为什么活”是理性的内化或凝聚,是理性对个体、感性的偶然的规划、管辖、控制和支配;而“活得怎样”的审美境界,是理性渗透、融合、化解(却又未消失)在人的感情欲中,叫理性的积淀或融化。而前两者致力于人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后者给予人生存状态——个体的审美之境,他往往超出知性语言,它只是诗。[24]我想何敬君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慵懒地前行与李泽厚的哲学不谋而合。以儒家的“仁”(情)为入世本根,又有道家的洒脱开阔,所以遇事“不愿勉强自己更不苛求别人,认真做事但不考虑事情之外还有什么目的”。[25]更为可贵之处,何敬君在六十一甲子的轮回里仍在“审美”之境中修行——一场追寻自我的旅程。
“一宗纸钱、两杯老酒、三柱新香——归于烟火/向一个个坟头跪下去,我似乎触摸到了我”,祭祖跪拜时,向祖先行礼,与大地连心,“我”发现了“我”,那个纯粹的不带任何修饰的“我”,那个孤独静思的“我”,那个皈依天性澄澈清明的“我”,那个真实的“我”。我想这样的“顿悟”只有在偶然、意外之间在诗人思想中闪现,这是“审美”的力量、“诗”的力量,更是“精神”的力量。
在此意义上,我解读《重阳日,想起形只影单的你》中的“你”是另一个“我”,带有“父亲”血脉的、大地滋养的那个“我”,那个“真实的我”。“邀不到你我便不会去哪里登高/我就背着这囊酒,酒囊上插几支菊花和茱萸/寻找一爿儿看不到暗流的水域继续泅渡,从冬到夏,再到秋季”,这里的“泅渡”与全部诗集最后《乙酉年除夕夜,大雾》中的“渡口”“彼岸”“摆渡”等词相呼应。除夕夜的“大雾”是即将要开启新一轮“摆渡”的暮景,而这次的“摆渡”与通往“彼岸”“渡口”无关,他仍在“此在”、在“现实”、在“人伦日用之间”。虽然结尾“摆渡是我们的宿命。”里有“将人们引向人生路上更多的遭遇,无可解脱时,也只有‘徒叹无奈’而已”[26],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忙碌与虚无中,获得“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妙悟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