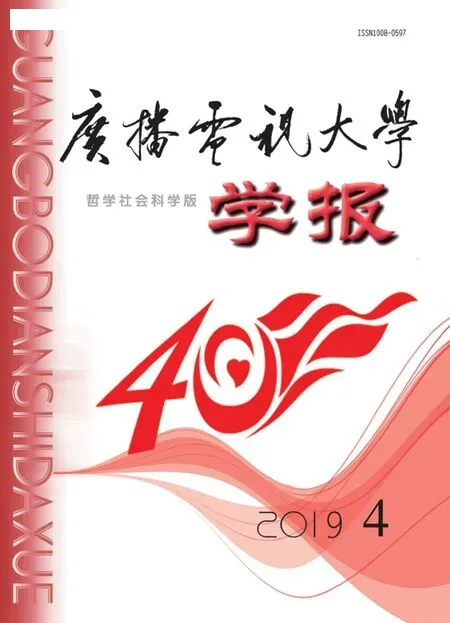论“思想改造”主题对知识分子叙事的规训
——以1950年代小说为例
张 勐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始于建国伊始的“思想改造”运动,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界自上而下的规训,凸显了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处境。缘于此,五十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诸如“我们夫妇之间”的情感龃龉与磨合[1],知识者林道静的“青春之歌”[2],以及一个上海姑娘在大时代洪流中的“浮沉”史[3],大都被整合进“思想改造”的主题中,借此换取新政权下知识分子叙事合法化的话语权力。
一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多有将家庭伦理与政治道德互喻的良苦用心。如其自况,本意试图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后”“逐渐得到改造的过程”;尽管后来因着过多地渲染了“家务事、儿女情”,而被视为:“曲解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4]P67-68,庸俗化了思想改造。
毛泽东有言:“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5]P851“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6]P815领袖好将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扬此抑彼的观念方法,不仅每每促成肖也牧小说的主题先行,时而亦化作了作品设置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的结构方式。
《我们夫妇之间》开门见山,“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1]P15,这一叙述句式本身就暗含了某种历史时间与阶级比照的维度,可见作者意在放弃文学形象的身份模糊,先在地将两位主人公归入特定的阶级类型加以塑造。
在小说修辞学层面,李克因兼有叙述功能,似乎充当了小说的主角,作品更多地通过他的视角品评妻子,与知识分子创作主体交互移情;然而,在政治修辞学层面,正如作者自况的,妻子才是主角,是作品着力表现的“一个新的人物”“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尽管作者意中的妻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如“狭隘、保守、固执”,但这些缺点一经知识分子视点揭示,却陡然招来自命无产阶级代言人的批判,无视作品极力讴歌妻的“革命历史”:自幼苦大仇深,抗日战争年代造过枪弹、杀过鬼子,解放战争时期曾当选“劳动英雄”;赞美进城后妻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憎爱分明。一旦作者不无生硬地取下知识分子“我”的“有色眼镜”后,身边的那个家常琐碎的个体顿时超拔为一个工农革命群体的符号。
值得注意是,小说除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题旨外;还兼及藉“我们夫妇”这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表现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彼此取长补短”关系。作品因此交织着两种叙述话语,一是将工农身份的妻子的“人物等级”不断提升,与之匹配的叙述话语充满了主流意识形态定式化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与规训;二是保留了知识分子“我”的叙述者功能,内中渗有流于本心的所谓创作主体的“感觉结构”,尽管不时地敏感知识分子话语已不合时宜:“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1]P21
此外,作者似不满足于对人物作为阶级“符号的单一表述”,农村与城市的地缘文化学互动也一度被作者援以隐喻工农与知识分子间的双向“改造”。然而,缘于对阶级论与地缘文化学两套编码的交替使用力不从心,加之对农村/农民、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传统道德伦理、城市/知识分子、城市/现代性、城市/物质文明之间的对应错综关系似乎也未能厘清,于是,文本中既有妻的都市怀乡,进了城犹不“忘本”,毋忘“这十年来谁养活”了革命军队,毋忘受灾的广大农民一类的传统教育;也有“我们进了北京。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一类的现代化进行曲[1]P17。——尽管作者有意无意地让城市抒怀出自未改造好的“我”之口,使之在一种不无轻浮的语调中变味。既有她来到城市后“不妥协,不迁就”,“立志要改造这城市”,连同改造像李克这样的知识分子一类顺应时势的话语;又有 “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以致“我”逗她说“小心让城市把你改造了啊!”[1]P27如是的反拨琵琶。究其原因,恰是过度的寓言化写作,造成了编码逻辑间的抵牾、分裂,多次修改更使内蕴剪不断、理还乱。
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的同时,还希图亦反映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取长补短”、双向“改造”关系,为此还笔涉工农形象的缺陷,如此多重题旨及裂隙,遂招来“为工农兵文学”之“保卫者”的见缝插针,横加挞伐。
反观文本之外亦紧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的这一社会大背景,想来并非多此一举:1952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毛泽东携女出游颐和园,听说丁玲在此度假,便来看她。此刻丁玲正在写那篇批判肖也牧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她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7]P119。而因小说株连,肖也牧不得不学着笔下人物李克写起检查来:“我知道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像我那种有着极浓重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观点的人,如果不立刻加以切实的改造,是决不会有出路的。我必须加以切实的改造,不论路途是多么遥远,也不论为了改造自己,而所需承担的巨大的痛苦,我是有决心一切从头来过,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4]P73短短一段话中,竟接连出现四次“改造”一词!文本内外,终成互文。
在肖也牧笔下,知识分子形象始终伴有一种自我否定的身份焦虑,叙述者的情感倾向亦不时摇摆于工农阶级意识与知识分子立场之两极,生成了诸多叙述缝隙。《爱情》就文本逻辑而言意在由革命知识分子李吉以自身为爱人复仇心切而导致革命队伍遭受损失的故事为“我”上课;却不时让“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反观李吉,见出改造好了的他的种种“不懂人情”。[8]P185文末李吉“想想我们整个阶级的事业比起个人的爱情来,何轻?何重?”的棒喝显得过于突兀生硬;而“我”言及听了李吉的话,“心里腾然一亮,也因而使我了解到什么是幸福。我应该有所改变”云云[8]P194,也直如小学生作文表决心、抒理想般简单空洞;相形之下,由李吉叙述的爱情故事(包括转述房东老太太讲述的其妻石婴被日本鬼子逮走后牺牲的情景)——“正当冰雪消溶的时候,在这村的南坡跟前,在那冰雪堆里,露出了一个血窟窿。里面有一个光身露体的尸首,那是石婴。她没有走!”[8]P188——却是那么的含情带血、撼人心魂!让人陡生出作者何以非将个人感情与阶级伦理置于这样不共戴天、非此即彼的选择的疑虑。
如此人为纠结,自然百思不得其解。《爱情》中,“我”曾经反省自己:以“无产阶级的道德观”衡量,“没有把爱情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8]P194;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八年过去,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犹在思索:“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
二
与《我们夫妇之间》将一对知识分子出身与工农出身的夫妻的“家务事、儿女情”纳入“思想改造”时潮相类,杨沫的《青春之歌》也重蹈覆辙。恰如识者指出的:《青春之歌》“并非一部关于女性命运、或曰妇女解放的作品,不是故事层面上呈现的少女林道静的青春之旅”“真正的被述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或曰思想改造历程。”“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充当着“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9]P195-196。
尽管小说中作者依然未能摆脱甚至仍不时纠结于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情感方式、精神气质及话语形式,尽管作品毕竟在表现思想改造的名义下正面展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艰难求索、步步见血的心路历程;但就作者创作的主观愿望而言,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显然是其“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
因着作者的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多有抵牾之处,虽勉力缝合亦难免见出裂隙,遂引出论者众说纷纭,或于裂隙处一分为二,揭示文本的“‘双主题’现象:一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找革命,二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女人寻找英雄般的生活”[10]P252,(又说一是革命主题,二是爱情主题);或合而为一,着眼于作者(或改编者)如何“缝合起一个少女的青春之旅与关于知识分子道路的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9]P197。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每每以革命与爱情的融通关系及至引路者与恋人的重合叠影(最典型的莫过于作品中的“卢……革命”之抒怀)[2]P564,来缝合小说的先在矛盾。
如果说,前述《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夫妇俩,一度政治化了家庭情感的纠葛,又家常化了政治思想的斗争,适可谓情爱政治的“现实版”;那么,《青春之歌》中的男女情爱关系,则已升格为情爱政治的“寓言版”。林道静追求——弃绝——献身恋人的一波三折过程,业已表征着其革命抑或不革命的曲折选择。爱情小说与政治大话适成互阐互喻。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的三角关系跨越并兼容了“才子佳人”与“英雄美人”两种叙事范型。确切地说,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才子佳人”姻缘终为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的“英雄美人”结合形式取代。
毛泽东有言:“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1]P559“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指示,遂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由之途。不仅《我们夫妇之间》开宗明义直接以“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一语为首节之标题;《青春之歌》也极尽婉转地图解这一方针。于是,曾经在林道静眼中“有才学的青年”余永泽,只能被冠以“上了胡博士的圈套,钻到‘读书救国’的牛角尖里”等罪名遭到唾弃;即便是青春洋溢、才华过人的卢嘉川的功能也仅止是“唤醒了林道静”,尽管在作者及至笔下人物的潜意识中他本是她的“最爱”[12]P629;林道静仍最终献身江华。原因无他,作为革命者的一体之两面,卢嘉川可谓革命者+“文学青年”的组合(他竟能在警笛呼啸、枪声骤响情景中昂然发出“诗人雪莱说过:‘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呼声)[2]P539,江华形象才是革命者与工农的叠影。作品中,对二人的肖像描写略已透出端倪──卢嘉川“那挺秀的中等身材”“聪明的大眼睛”;江华“身躯魁伟面色黧黑”,“神情淳厚而质朴” ——皆非无意为之,应可视为身体政治。在对江华“沉稳”“踏实”等性格的刻意强调中,有意无意间已含有对卢嘉川诗意浪漫气质违心的针砭。
相形之下,《青春之歌》结尾对“一二九”及“一二一六”游行中的知识分子群像的倾力塑造则在彼一时期显得极为难得!“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们。”老教授被“众星捧月般拥戴着”,人们的心中对他“充满了崇高的敬意”。他“挥着拳,探着受了伤的庄严的头,向工人群众高声喊道:‘工人兄弟们!欢迎你们呵!’”工人群众亦陆续涌到游行队伍里面来了[2]P900-901。排山倒海的人群,涌流着的鲜血,激昂的高歌……作者的亲身经历与血肉体验于不自觉间冲破了历史的讳言,恰可谓“现实主义的胜利”。
尽管小说后来几经删改,但正如识者所称:“作品的‘潜文本’却没有完全被删除。因为修改本删除的可能是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它其实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删除得掉作者内心世界中的知识分子意识。”[13]P68诚哉斯言!
三
无独有偶,较《青春之歌》稍早面世的艾明之的长篇小说《浮沉》亦内蕴了“才子佳人”与“英雄美人”两种叙事范型的交响论辩。医学院高才生沈浩如大学毕业后原有其医学攻关与小家庭建设的精明计划,然而“身上虽然还带着某些孩子气”的未婚妻简素华,却拒绝了他的指教、开导。彼一时代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号召呼唤着简素华弃家出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工地在吸引着她:“这里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片沸腾的海洋,每天有许多新的事物在涌现,在喧嚷”[3]P66……令人不由地联想起《青春之歌》中那引路人的呼唤:“在这狂风暴雨的时代,你应当赶快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出来” ;联想起革命年代“人群迅急汇合成了昂奋的队伍”“突然一面红色的大旗灿烂地招展在空中,好像阴霾中升起了鲜红的太阳”的炽热场面[2]P559。识者曾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14]。值得注意的是,《浮沉》中不仅有“才子” 戴着“黑色玳瑁的宽边眼镜, 皮肤特别白皙”;“英雄” ——工农干部高昌平则“皮肤红得发黑,闪着健康的光泽”一类理念化、公式化了的肖像描写;且不乏深入感性层面乃至审美层面的工农英雄形象塑造。作者每每借青年知识者简素华的内视角见“英雄”。
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崇高与优美的思辨,曾被王斑移用于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崇高美学”的诠解(王德威将其译作“雄浑美学”)。如果说,《浮沉》藉高昌平献身社会主义建设,哪里艰苦哪安家,不断斗争,驱除自身的“生物与自然特性”,牺牲常人的幸福,“对生活抱着崇高的理想”等叙述,已“把主体召回到更高的一个法则”,即所谓“崇高”的境界[16]P189-190;那么,当作者别具匠心,将对工农英雄的崇拜审美化,如刻划“情人眼里”高昌平那络腮胡子的脸、那雄阔豪迈的气势,尤其是反复渲染他那“朗声大笑”,像雷,听着,不仅简素华“心里就涌出一种特异的微妙的颤动”,而且令彼时的读者也不禁为他的魅力感染时,借用王斑的表述,此刻,审美“就给了意识形态一张有人情味的脸”[15]P189。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简素华的内视角中饱含着“自己的幻想和色彩”,如同小说称林道静的内视角亦充满了“年轻人的狂热的幻想”,如是知识分子视角“仰视”中的工农英雄形象,不免失之浪漫,或者美其名曰:“革命浪漫主义”。后者正是“崇高美学”的题中之义。
除上述小说外,白刃的《战斗到明天》、扎拉嘎胡的《红路》等长篇亦都凸显“思想改造”主题。
《战斗到明天》描述大学教授女儿林侠、东北流亡学生沙非、小有产者家庭出身的辛为群、以及大学讲师焦思宁等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战火中锻造的故事[16]。茅盾鉴于“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而慨然作序推荐,并高度评价小说翻开了“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未料小说出版不久即遭到多家报刊的集束抨击。从发表系列批判文章的《解放军文艺》上所谓小说“打着小资产阶级改造思想的招牌,却散发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的编者按语[17],以及作者“起先想写一个连队在敌后英勇作战,入关以后,看到大批新知识份子涌入部队,又想到全国解放了,长篇小说的读者主要还是知识份子,就是在为自己争取小资产阶级读者的坏思想的支持下,把‘第一为工农兵’扔到脑后,把‘第二为小资产阶级’摆在前面,改变了主题”的检讨中,不难悟出小说触犯了知识分子叙事已不合时宜这一禁忌。然而茅盾在其检讨中,除反省小说作者与自己均“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外,却以此印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因而,“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值得改的[18]。
联系到茅盾后来在为《青春之歌》辩护时,又一次以小说“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作者既然要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不着力地描写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人的行动中的表现及其顽强性”为由这一史实[19],禁不住百感交集:在喟叹茅盾始终难以逸出“思想改造”主流意识形态羁束的同时,亦依稀悟得内中未尝不隐含其藉此主题守护“五四”以来一度蔚为主流的知识分子叙事那一脉遗泽之苦心。
——以林道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