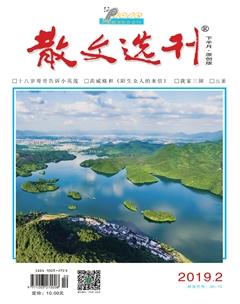二十年了,那里的人们依旧记得我
廖献红
整整二十年了,离开那之后,我一直没有再去过,那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驿站——洛清江上游的一个村小学,我在那待了三个学期。
“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应当年的同事之邀,回到那吃其儿子的婚酒。走进村子,犹如轻轻开启了青春时光的日记本,十八九岁那段苦涩而美好的记忆夹杂着一丝青草的气息再次扑面而来。
依旧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只是沧桑了许多;依旧是那样的笑声,只是更加爽朗;依旧是那些老故事,只是多了新内容;依旧是那几间教室,只是撤点并校后改成了民房和小卖部;依旧是那条村道,只是新农村建设开始后铺成了水泥路……眼前一切的一切近乎遥远而又那么熟悉。
见到了他。我的一名学生家长。这是我进村迫切要看望的人。尽管村里多了许多楼房,村道有了改变,但凭着记忆我还能准确找到他家门口。他正与邻居烤火聊天。我轻声呼唤着出现在门口时,大家都怔了怔,但很快便认出了我这个小廖老师。而我眼前这位昔日生龙活虎干活不知累、天还没亮就挑满两大缸水的庄稼汉子,如今已年满六十,因脑血栓而手脚颤抖、走路颤巍巍的了。当年我在他家搭伙吃饭,是他家帮我解决了一日三餐无处生火煮饭的大问题。每天傍晚摆桌吃饭时,他都不忘唠叨孩子他妈做一个不拌葱的盐碟放在我面前(我不爱吃葱,他记得很清楚)。乡下的日子很是拮据,一个月能吃上肉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就像他的家庭成员一样,加菜要等我,宰杀自家养的鸡鸭更是要等我。每天我和他全家吃饭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学期,让我没有一点远离父母兄姐的孤独。学校周围治安环境不是很好,我一人住校害怕,他十二岁的女儿每天到学校陪我住校。
我还见到了他。他是这次酒席的总调度。登记礼簿、协调厨房,切菜、洗碗、摆桌、上菜都由他统一指挥。他是本村的,原是一名优秀的代课教师,后因每月170元工资难以应付家庭的日常开支,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年,他便辞职了。他比以前胖了点,还是那么精明干练。这些年他的家庭建设搞得红红火火,是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
我還见到了老阿婆。她当年住在学校附近,常常给我送来青菜、粽子、野果的阿婆,现在已八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她拉着我的手端详了一阵便喊出了我的名字,她还提起当年我为她织的那件深蓝色元宝针的毛衣,她仍穿着。
我还见到了他们。一个在课堂上把书扔向我擦伤我眼睛而嬉皮笑脸的男生;一个老是缺交作业迟到的男生;一个常带我上山摘桃金娘找三月笋的男生……他们现在个个都成家了。
农村请酒几乎全村人都到场。吃饭时,村里的许多群众家长都能认出我来,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学生、家长、老师,我们通过各种细节回忆交流传递以往的信息,他们还记得我那场还没有实质开始便夭折了的所谓初恋。
二十年间,我的单位几经变换,同事也换了一拨又一拨,而这山村里的人们始终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
责任编辑: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