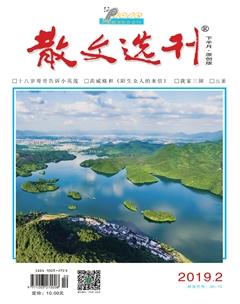唱歌的小麦
蒋建伟
泥土是一件陶罐,万物生灵装进去,倒出来,再装进去,一年就过去了。它什么秘密都可以装的,很多腐烂在里面,也有很多,接着生长出新的秘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小东西被打开,不再是什么秘密,呀,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世界可以那么小,一粒粮食那么小,“啪”,打开了。
你轻轻地躺在一道沟堰上,满脸贪婪,眼儿微闭,呼吸着绿泼泼的空气,鸟雀“啦啦啦”唱着三五首童谣,忽然就飞起来,忽然就落下去,藏进那个小东西里。你不知道的,小麦这时候偷偷钻出地面,一个又一个婷婷娉娉的少女走过来,一个又一个头顶散着热气的小伙子走过来,“咝咝,咝咝”,他们穿着绿油油的衣裳,芝麻粒儿大小。墨绿中,笑声会传染,能嗅出一缕一缕的清香来,空气甘洌芬芳,麦苗婉转飞翔,小麦们开口唱歌,浑身就不那么冷了,后来,开始热汗淋漓,像极了地平线上跳舞的那么多、那么多快乐的霜花。
歌声好像白云一样飘,落下来,好一场大雪啊。白墩墩的大雪,急慌慌地走着,像棉花做成的被子,盖在麦苗身上,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垄垄麦苗中间,屎壳郎美滋滋地大睡,梦着自己的好事,天塌地陷似乎与它无关,像是死了,又像是还活着。脚尖一划拉,一坨坨牛粪露出来,许是太阳晒久了,臭味没了,不再那么热烈,扁扁的,膨化得好像俄罗斯大列巴面包,掰开一块,许多没有消化掉的麦秸儿团了一处,麦秸上,残留着一道道咀嚼的牙齿印,可惜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远的地方,那些掺杂了牛马粪、驴粪、骡子粪、猪粪以及多种腐烂物的熟土,也被太阳晒着,酥酥的,软软的,滑滑的,酸溜溜的,风一刮,没了魂,一下瘫了。指不定哪一粒上,你会扯出三五根头发丝儿,不知道是不是它们自己的或者大人小孩的,长长短短,纠缠一处。它还在“呼呼呼”地睡觉,动也不敢动,无论你怎么叫,也叫不醒。脚底下,又一划拉,“噌”的一声,踢出来一堆死去的小东西,也踢翻了它,它挥舞开六个爪子,一抱拳,一曲腿,身子团作一个小黑球,竟然连骨碌带爬,没命似的跑啊跑啊,咦,哈哈,小鼻子小眼,细腰肥臀,女的,哎呀,一眨眼,不知道又钻去了哪里。雪花飘在土粒子上,一朵托举着一朵,最下面的那朵融化了,土粒子湿了,缓慢地冻上了,随着雪花的不断增加,不断融化、冰冻,一骨碌,骨碌出老远。土粒子在不断发胖,小小的,圆圆的,冰丝丝的,玲珑通透,好像装了满满一副跳棋盘里的玻璃球,一踢,蹦蹦跳跳着你追我赶地乱跑,也不知道它们要跑到哪里?雪继续下,一直下,把所有的所有所有都覆盖了,看不见别的色彩,只剩下了白。天地我一白。小风一刮,弥漫了雪雾的白色旋起,倾斜着向上飘,几番盘旋,那冒着甜兮兮的冰气,炊烟一般散了,在半空中停顿了几秒,末了,消逝得无影无踪。
二三月间,一位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站在麦田边,她要唱歌,她,如果能唱一首蒋寨村的民歌就好了!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暖乎乎地照耀着大地、村庄、河流,“噗”,被凝固了的冰挂化了,坠落在枝枝丫丫里。她的歌词,只有一个“啊”字,可是,调儿唱出来了,味儿却散发着土腥气。小风,似乎停了,似乎又没有停,不过没有先前那样冷,到后半夜,风真的停了,满屋子的热气一下子圈住了。麦苗们横出了被窝,长长伸了一个懒腰,“憋死了!”就势做了个驴打滚。这田野,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一道白,一道绿,横横竖竖,深深浅浅,发展到后来,白皑皑的变成了绿油油的。
小麦们进入了变声期。它们,脸蛋上开满了一朵花,挺胸,收起气,脚尖翘起,小手伸展开来,随着3/4拍子、4/4拍子放声歌唱,婉转悠扬,两脚不动,但其余的部位都在唱歌,都在跳舞,天籁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麦地。你恍惚看见,一开始,天地间,空气中,好像有一根头发丝儿,从它们的口腔、鼻腔、胸腔和腹腔出发,越来越长,几米,几十米,几百米,几万公里,甚至无限的长,越来越粗,上接白云深处,闪电般击中了你。有的唱啊,“一万个爹来,一万个娘,喊熟了大片大片的好麦浪”,你肯定是躺在麦田里了。有的唱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你呢,也就打开了一幅工笔画:夜色中,你的数学老师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有的唱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还有“捧一把黑土,我亲爹亲娘的土”,不用猜,你已睡在孟春时节的木床上,雨,不紧不慢地下,其实它们呀,好像小磨香油一样金贵哩。有的呢,记不住一句歌词,只好在每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上,找出那个字的韵母,比如“土”的“u”,“天”的韵母“an”,“娘”的韵母“ang”,打开小嘴巴,随声附和,只唱一个音,外边的观众谁也听不出来。从童声合唱,到少年合唱、无伴奏小合唱、六声部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清晨的原野里,歌声也由整体齐鸣,变成了这一片、那一片地演唱,无伴奏,无指挥,哈,浑然天成。为什么是演唱呢?小麦们长高,开始拔节了,抽穗了,开花了,授粉了,小麦的歌声里,可以听出男人的爽朗、女人的婀娜,也可以听出花开的波涛声、灌浆的大潮声,南风北上,“哗——哗哗”,“哗——哗哗”,如此反复,连续。
麦子是被布谷鸟叫黄的,是被麦黄风刮黄的,是被毒太阳看黄的,是被平原上的男女老少喊黄的,对,一夜一夜,一天一天,一眼一眼,一声一声。黄,是金黄色,黄金一样的金属色,哪怕看上一眼,你就是贵族了。这麦浪,大海一样起伏,歌声从天而降,似遥远,似圣洁,那,是男中音、女中音?是男低音、女低音?太低了,低得不能再低,“哗哗”,“哗”,“哗哗哗”,“啦啦,啦啦——啦”……天门打开,春夏秋冬都进来了,红红火火都进来了,爱情都进来了,酸甜苦辣都进来了,听啊,这是麦子在唱歌!
把所有的镰刀举起来,把大型的收割机开进来,拼尽你浑身的劲儿,把所有的血水汗水泪水扔到天上吧!在收获的节骨眼儿上,忙,没日没夜,一天吃两顿饭,不吃饭都可以,只要能把一袋袋麦子拉进打麦场,一粒粒麦子能够全部装进茓子,只要能咬上一口新麦子做的馒头,即使累死,一头歪倒在木板子床上,也值!开进吧,装得满满当当的吧,摊麦子晒场吧,不就是二十来天嘛。无边无际的麦田里,镰刀一挥,天地一晃,机器轰鸣,割麦搶场,它们的歌声,和着小麦的歌声、田野里沸腾的人欢马叫声、打麦场上香气弥漫的晒麦子声,一年一年歌唱着中国农民的丰收,分分秒秒都在累积着一个个数字。麦子装茓子那一天,我看见你解开一个麻袋口,抓了一把麦子,你蹲在一边,轻咬麦子,“嗑嘣,嗑嘣”几声,嘴角,挂着一股一股奶白色的汁液,真香啊!
餐桌上,多少年多少天了,我陶醉每一顿饭的面食:一碗面条,一碗饺子,一碗糊涂,一个白面馍,一盆稀饭,几根油条。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麦香啊,总让我闻到流口水,想象到香气弥漫的那片田野、那块麦地。这一碗面那一个馍,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垄麦子吧?何止是闻哪,我还会去听。听小东西里这么多氤氲升腾的麦香,到底是哪一缕,隐藏了小麦奔放的歌声?
把所有的太阳都打碎,把一首完完整整的歌打碎,你,可以唱得“哼哼唧唧”的,可以格外的舒坦,走心。这一首首歌,不那么连贯,全都装进小东西里,碎碎的,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用一双双大手轻轻捧起。
它们,就是遍地金子,就是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