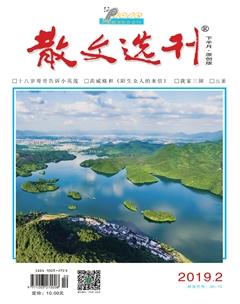那些年有座桥
徐玉向
鲍家沟像一条捻不断的细线,一头连着千里长淮,一头穿过我们小小村落,最终向西南方向流去。鲍家沟上的那座碾盘桥,对我而言,却不仅仅是个传说。
我所知道的碾盘就是那圆圆的磨盘,恰如奶奶平日切菜用的案板,只不过一个是石雕的躯壳,一个是木做的身体。假使这两件东西中的任何一样压在心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是无比沉重。
我见到碾盘桥其实早已不是桥了。有桥便有河,便有路。桥没了,河还在。路被河隔成了两块相向的、半圆形的土墩。路西头成了奶奶的菜园,而河的对岸,却是一片寂寂庄稼地和萋萋野草。
奶奶自18岁嫁给爷爷,便与这个家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一起熬过旧社会,一起跑过鬼子返,一起抚养四五个孩子,一起打理幾亩薄田,又一起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奶奶说早年村子里的唯一大路就是碾盘桥这里,从朱庄南面一直通向村子的北面。在牛马拉大车行走的年代,爷爷经常从这条路往市里、集上运油运粮,下地、收工也是在这条路上来往。自从桥被洪水冲断之后,公社在原路址南面约500米处重新修了一座水闸和一条用水泥、石头砌成的新桥,一条新的乡路便成了。爷爷和其他几位村民便在荒废了的碾盘桥西侧的路面上开荒种粮。
三十多年前爷爷病逝,碾盘桥头的开荒地便成了奶奶的心头肉。
这里有爷爷留给她的念想。她不但把原先种庄稼的地方全部种上了菜,还把河边多余的空地也填上土、搭上架子,就连坡上也挖坑埋上菜种。每逢周六、周日或是暑假,奶奶便安排我们堂兄弟几个往碾盘桥运农家肥。一个架子车,上面两三个大筐,我们三个大孩子拉着车子在前面走,奶奶踮着小脚,一手搀着弟弟一手扶着粪箕紧跟在后面。
到了新桥头,车子就得停下来,河边通往碾盘桥的路只容得下两个人并排走,空车子过去都很麻烦,何况还是装了肥料的笨重家伙。于是,再把筐分几趟抬进去,一筐放在菜地的最上头,一筐放在菜地的中间,最后一筐匀做几处,那是留给坡地和河沿菜苗的。
我们在奶奶的指挥下分头给菜分肥,二哥负责已开花的辣椒和茄子,大哥负责坡地刚刚上架子的豆角和黄瓜,我和奶奶负责河沿和边角上的冬瓜、南瓜、西红柿,有时也有扁豆,弟弟坐在粪箕边上唱歌给我们鼓劲,兼看着东西。收工前,每个人可以得到一块或大或小的冰糖作为奖励。
在众多蔬菜中,蚕豆和毛豆是我们的老相识。在撒了肥料的土里刨个坑,丢两粒蚕豆种,浇半瓢鲍家沟的水,掩了土便可回去等消息了。约莫半个多月,或是一场雨后,再来看时,土里便会钻出两片胖胖的叶芽,新的希望便诞生了。
蚕豆收获的季节便是奶奶少有的开心时候。叫齐我们四个,带够篮子和蛇皮袋,每人分一小块,把头茬蚕豆全部摘下。第二天一早,由父亲骑脚踏车把装好的蚕豆送到山南头的东站菜市场,奶奶自己则是鸡一叫就起床,带着秤和零钱从村西翻过黄泥山赶过去。吃中饭前准能看到奶奶轻快的身影,中饭过后再到地里转转,直到傍晚才回来。
接下来隔个三五日,奶奶便去卖一次蚕豆。等蚕豆都下来的季节,奶奶便会分一些蚕豆给我们炒菜吃。再过一段时间,蚕豆老了,我们就可分到更多,或煮或炸,便有更多的美味了。
另一个老相识便是毛豆,它带给奶奶的收获和我们的欢乐大抵与蚕豆相仿。
从清明前后直到中秋,碾盘桥上一直可以看到奶奶忙碌的身影。
10年前,94岁的奶奶无疾而终,想那碾盘桥,如今变成了荒地,怕是再没人去打理了吧。
责任编辑: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