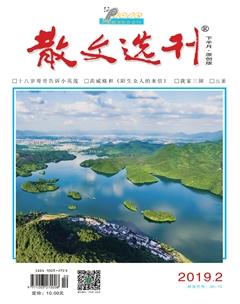永远的痛
刘丰歌
我从来没有像那夜那样清晰地梦见母亲,母亲对我说,她很冷,她说我二哥三哥都不管她。我从梦中醒来,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心像被猫抓似的慌乱,难受。
后来从老家三哥的来信中得知,母亲去世的日子和我梦见她的日子完全吻合,时光已整整轮换了二十多个春秋。
母亲的生命之路如家乡的山道般狭窄陡峭,她从花季年华到垂暮之年一生都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重复着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轨迹从未延伸至县城之外的任何繁华之地。在她生命之弦突然断裂的那天,还自己步行了七八里山路到乡卫生院看病。而上天竟有意捉弄这位善良的老人,在她跨出卫生院大门那一刻,被一块该死的石头绊了一跤。母亲摔倒在地再也无力爬起来。一位好心的小伙子发现母亲后,便依母亲口嘱,将她送到镇上一位关系很好的熟人家。当熟人家那位热心的大嫂熬好大米粥端到母亲床前时,我苦命的母亲已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就这样客死在熟人家中,临终前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为她送行。我不知道母亲临終前想了些什么,是思念儿孙却无一人在身边而失落痛楚,还是为即将脱离凡俗间无边的苦海而快慰?——我的心如针扎一般。
今夜,我坐在离家乡千里之遥的这盏孤灯下,默默追寻母亲一生走过的路,我的笔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数次难以成书。母亲在她有生之年以柔弱之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却以博大的胸怀哺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记忆中,母亲要么昏睡在床,要么被人用滑竿抬出家门,过几天又被人抬回家。母亲在我一岁大一点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肚子却胀得老大。每次母亲被人从医院抬回家放在床上,我都要跑过去叫姆妈,姆妈,我要吃奶。这时父亲就会走过来搂着我的头说,乖,到外面玩去,别打搅姆妈睡觉。我知道母亲在睡觉,因为我使劲叫她时,她要么根本就不答应,要么只是声音极细小地“嗯”一声。但本能的饥饿和对母乳的渴望仍使我不愿离开母亲的病床,以致有次我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偷偷揭开母亲的被子,撩开她的衣襟将乳头塞进嘴里便狠命吸,因吸不出一点奶水,我心中所有的委屈便化作“哇”的一声大哭。那段时间全家人忙着给母亲治病的事,没时间照顾我,我便被大伯领去带着。大伯想尽办法给我弄来一些面粉搅成糊糊喂我,我仍因营养不良瘦得像根缺肥少雨的瓜秧,蔫不拉唧,毫无生气,见啥东西都想往嘴里塞,晚上睡觉时朦胧中还噙住大伯的乳头吸个不停。每当此时,大伯都会披衣起床,给我再冲一点面糊糊填充我的辘辘饥肠。
就在母亲的病一天天恶化,乡卫生院已束手无策,让父亲着手料理后事时,一位从西安医科大学毕业的徐大夫不知什么原因从西安某医院下放到了我们那个偏僻的乡卫生院,他看了母亲的症状后对父亲说母亲得的是结核性腹膜炎,如果立即做手术还有生还的希望,但乡卫生院条件简陋,且病人已奄奄一息,手术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他害怕手术出现问题,他承担不起责任,有些犹豫不决。父亲说人已成这样了,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如果人死了那是她命该如此,我决不会怪你。徐大夫仍下不了决心,父亲再三恳求,他才主刀为母亲做了手术。听父亲说手术那天徐大夫从母亲腹中抽出了两大盆血水。母亲终于被徐大夫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在以后母亲住院治疗的日子里,我最多的玩具就是父亲从医院给我拿回的母亲输液、打针后用完的空药瓶。我和比我大几岁的三哥便用空药瓶摆房子、垒宝塔……我们家也就时刻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药水味。在我的印象中,药瓶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玩具。那段时间,母亲的胳膊和臀部全是输液、打针留下的针眼。到后来每次输液、打针时,护士们都会为找一个恰当的位置而大费脑筋,以致有的年轻护士见要给母亲输液、打针,便以各种借口把这苦差事推给别人。大约过了半年多时间,母亲身体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便回家进行保守治疗。徐大夫给母亲开了“雷米封”“钙糖片”“鱼肝油”三种药,让她一直服用。这三味药已牢牢记在我的心里,因为我经常给母亲拿药。我对鱼肝油最感兴趣,那是一种褐色半透明的圆颗粒,很好看。母亲说这是补药,偶尔还给我吃一粒。
母亲不能到生产队干活,便在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那时家中有一个独凳,是父亲为母亲特制的,因凳子只有一条腿而得名。其实就是在一块木板下钉了一根木棍,木棍的下端被削成了尖形。这是那年采茶季节,母亲看人们忙着采生产队的茶,家中自留地的几株茶树叶长得老长却没人采,心里急,而她因身体虚弱,只能坐着干活,平常用的凳子在山坡上又放不稳,便想出这么个办法,让父亲做了那个特制的凳子,采茶时将下面尖的一头插在地里,她便坐在上面采茶,一株茶树采完了,凳子挪一个地方,插稳,坐上再继续采,一刻也闲不着,谁劝她都不听。
母亲结核性腹膜炎治好后,又得了低血压病,有时蹲着一起身便头昏眼花,晕倒过去。家里人要让她到医院检查,她却说前面得病已经借了生产队许多钱了,还有一屁股账没还,哪有钱再看病呢!她只按一位江湖郎中说的偏方自己采了些草药吃吃,没见多少好转,她也就一直拖着。一次母亲出门去打猪草,我在家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母亲回来,就在我正准备出门去找时,同村一位堂哥急匆匆跑来说,母亲打猪草从山上滚到几十米的山下一个乱石滩里,现正在村子我姑父家躺着,准备往医院送。我忙告诉正在屋后放牛的二哥,二哥听说后背上我就往姑父家跑。到了姑父家,看到父亲和几个人在院子里扎滑竿,我姑正在给母亲擦洗伤口,地上的一盆水早已变成了红色。这时,大哥、三哥、姐姐得知消息都赶到母亲身边,兄弟姊妹几个围着母亲号啕大哭。
我小时候爱尿床,每当我尿床后母亲就把我放到她睡的那边,她自己找块布片垫在我尿过的地方继续睡下。当我进入梦乡时,母亲是如何安眠的我却不得而知。大哥结婚那年,我们家为办喜事借了生产队几百斤粮食。后来为了还账,每月家中只分到二十多斤粗粮,母亲就经常上山挖野菜和着这点可怜的粮食想方设法为我们调剂伙食。因家里人口多,她每天把饭做熟后便用碗分均匀,每人一碗。我那时年纪虽小,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每次分饭时给我的那一份和其他人一样多。我几个哥有意见,嫌母亲偏心,说我年龄小应该少吃些,不能和干活的人一个标准。母亲说我小时吃奶少,身体本身就瘦弱,长身体的时候吃不好,怎么上好学呢?他们才无话可说。其实,我知道这是母亲偏袒我,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在家中年龄最小,又从小受苦,母亲就对我特别疼爱。上中学时,我每天得往返七八里山路,一次我起床迟了,没来得及吃早饭就赶到了学校。下午放学后我正饿得头昏眼花,无精打采地往家走时,忽然发现母亲用布兜提着一碗饭到半路上接我来了。我高兴得几步跑到母亲身边,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碗,狼吞虎咽把饭菜填进了肚里。在我的记忆中,那顿饭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尽管只是一碗米饭和炒土豆丝,却比大鱼大肉还香。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爱情可言。母亲嫁给父亲后,为家庭生活日夜操劳,无怨无悔。父亲担任过多年村支书,多次被评为劳模,还到北京参加过劳模会。应该说父亲当村干部是称职的,但在家中他却不是一位好丈夫,父亲脾气特别暴躁,在家中他的话就是圣旨,母亲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常常为一些家庭琐事对母亲看不顺眼,便非打即骂。母亲像许多中国传统女性一样,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每天参加完生产队的劳动后,回家还要为全家人做好一日三餐,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偶尔单独为父亲煮几个鸡蛋为他滋补身体。父亲对母亲所做的一切熟视无睹,见惯不惊,好像母亲为家庭付出的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事。母亲经常向我诉说内心的酸楚,说父亲的诸多不好,说着说着就会流下泪来。我那时还小,不懂大人之间的事,便问母亲为什么不和父亲离婚。母亲说,傻孩子,我和你爸离婚了,谁心疼你,谁带你。我说我跟你过,我才不跟爸过呢,他老打我屁股。母亲说,离婚了我能到哪里去呢!我说大舅对我最好,我们去跟大舅过。母亲说离婚的女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回娘家也不会受欢迎。我说那以后要是爸再打你,我长大了打他。母亲这时变得严肃起来,说,小孩子家不要胡说,他是你爸,你咋能打你爸呢,打父母的人是要遭五雷轰的。我无话可说,便拿来毛巾给母亲擦眼泪。每次母亲向我诉说了心中的苦楚后就有一种满足感,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好像我能医治她心灵的伤痛。
我参军第三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生活。她的负担却一点也没减轻,几个孙子、孙女成天围着她转,她背这一个,抱那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直到最后病倒在床。而一生奔波劳碌的母亲在生命之舟即将驶向尽头时,仍然在不停地与命运抗争着,自己到乡卫生院去看病,我实在难以想象病中的母亲是以怎样的羸弱之躯步行七八里山路走向卫生院的。我问过二哥、三哥,因为他们和母亲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都说自己忙农活去了,根本不知道也没想到母亲会自己去看病。我想母亲一定有啥心愿未了,她才会如此毅然决然地迈向医院,希望现代医疗技术能再次创造奇迹。然而命运之神这次却没给母亲一丝宽容与怜悯,残酷地夺去了她73岁的生命。
我苦命的母亲,你可曾知道,那个酸楚的梦,变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