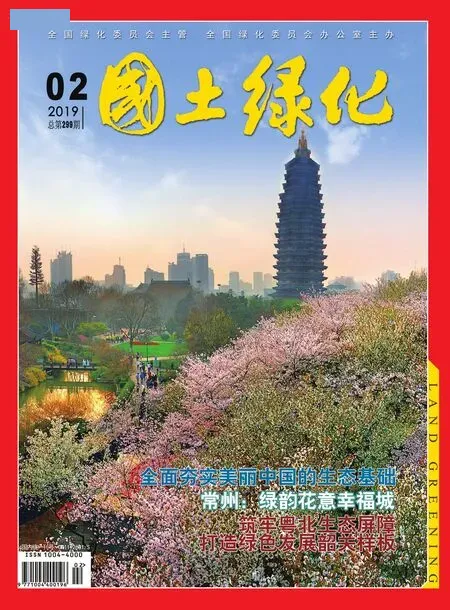桃仙
■王丕立
一场大雪之后,桃树的枝干上长出了黑色的疙瘩,我知道那是桃花打苞的前奏。不由自主地,儿时关于桃树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此刻的我正寻访桃仙的踪迹。
小时候,我家后山的两棵脱骨桃树枝桠婆娑,结出的桃子缀满枝头,又甜又脆。桃子表皮上靠近蒂把处有着密密匝匝的黑斑点,果尖处渗出红色的斑痕。用手掰开,桃核光溜溜地跌出来,干净得如剔出来一样。蒂部肉色鲜红艳丽,尖部赭红水润,果肉吃起来味道醇厚如醴。

打我有记忆起,那两棵树就并排掩映在屋后岩山上。奇怪的是,从没喷洒药物杀虫,那两株桃树结出来的桃子,却没有一个虫眼。村里的人都说,那两株树是得到桃仙照拂的。我信以为真,也曾悄悄地问母亲,桃仙什么时候来照看桃树?母亲告诉我,从打骨朵开始桃仙就开始忙碌了。
整整一个春天,我都在桃树间穿梭,我从来没看到什么桃仙,只看到花骨朵绽开成了一朵朵娇艳的桃花,在桃花凋谢的时候,蒂部挽结出一个个指头大小的青色桃子。早晨一睁开眼,我就跑去后山,晚上家里点上了煤油灯,我还在桃树枝叶间找寻,总是想象着桃仙会在什么地方以一种什么姿势出现。
那年夏天,二姐染上了漆树毒,身上长满了白亮的水泡,背部水泡更为密集,一俟磕破就溃烂。全身涂满草药的二姐恹恹地趴伏在床上,父母和大姐、三姐都下地劳作去了。守候在床边的我,用头脑中那少得可怜的见识编笑话讲给二姐听,她没有任何反应。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忧虑从心底冒上来:二姐那么瘦,不会有什么好歹吧?正出神间,二姐喊我给她翻身,侧躺着的她轻声说:想吃桃子。
急急忙忙地,我马上从踏板上跳下来,跑到后山,爬上右边较大的那棵树顶端,给二姐摘最红最甜的桃子,然后站在树杈上默默祈祷,希望不露面的桃仙能保佑我姐姐好起来。当我揣着几个又红又大的桃子从树上跳下来时,正好踩在一个竹桩上,尖利的竹桩刺穿了我的脚趾间,血一点点滴落在我回家的小路上。我将桃子放在脸盆里,强忍着疼站在凳子上揭下板壁上一个又一个的蜘蛛窝,迅速盖在伤口两端止血。我削好桃子,掰成小块送到二姐嘴里。吃过桃子后,二姐精神好多了。
康复后的二姐不敢再上山。我却仍然绕树爬上爬下,心里对桃仙救治我姐姐充满了感激。一次,我去后山时,发现桃树干上结满了一团团透着丝质光泽的黄色桃油。母亲说,桃树都老了,它们生命短暂,活不了多少日子了,言语中透出无限的怜惜。我对此无动于衷,心想桃仙定会让它们渡过困厄。
第二年开春后,已长出鲜嫩绿叶的两棵桃树竟然毫无征兆地枯萎了。桃树每年奉献几箩筐无痂无疤的脱骨桃给周围村民解馋,享用过美味的村民一同前来查找原因,却都没找到症结所在。母亲说,它们长得委实张扬,月满则亏啊!我固执地认为,是桃仙的离去才导致了这一结果。慢慢地,我喜欢一个人独自呆着,用耳朵倾听那些似有却无的声音,察看那些若隐若现的痕迹,期冀桃仙再次驾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熟稔于世间万物的生长与寂灭,也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但我仍习惯于留意那些细若纤毫的改变。德国音乐家、作家古斯塔夫·雅努施在《卡夫卡对我说》书中,曾借用他父亲的话说,这是与胆怯的纤细弱小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对这种力量来说,一切细小的就正是最重的。常常,那些不起眼的疏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深以为然,像窥探到了自然世界的隐形密码,每当遇到快乐的事,我不再忘形;遇到艰难的事,我不再绝望,只是用尽心力让那些细小的改变朝好的那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