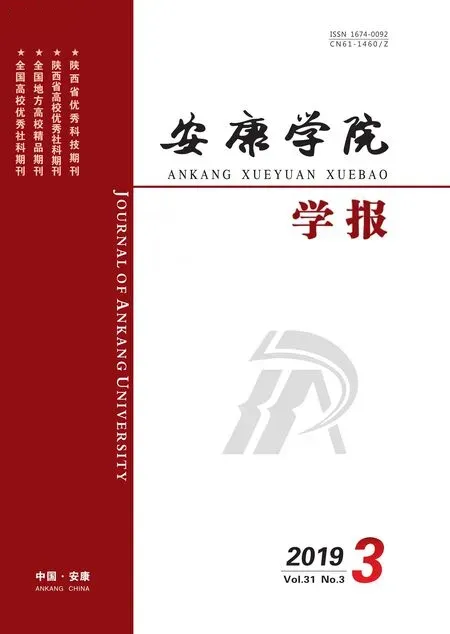论严歌苓《穗子》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牛浩宇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严歌苓是当代华人创作中较为活跃的作家,风雨飘摇的岁月已经成为她回忆那段隐秘经历的窗口。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她的作品淡化了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荒诞年岁的一味控诉和指责,也摒弃了先锋文学对历史的个人化经验的犀利想象和新历史小说对宏大历史的先验构想,而是更多的表现荒原景象之下人们的主观印象[1]。严歌苓的《穗子》系列是自传色彩很浓厚的自成系统的短篇小说集,穗子由稚嫩到成熟的蜕变,似乎是自传式的叙述,渗透着严歌苓自我的人生反观。正如严歌苓在《自序》中所说的:“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以往对严歌苓《穗子》系列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个人化的历史遭遇与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即忠于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并不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负责,或者探讨小说的叙事空间,分析以穗子这一少女为中心的个性的人物形象塑造,等等。然而针对其女性视野的独立研究还较少,本文主要在以往严歌苓《穗子》系列的研究基础之上,试图分析《穗子》系列当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觉醒。小说的自传性色彩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情感和鲜明的女性视角,是对有着明显男性话语叙事特征的“文革”叙事小说的超越。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女作家都苦于作家前面的“女”字,她们认为加了“女”这一定语会让读者产生偏见,从而对她们的身份和学识产生怀疑,认为没有明显“性差别”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然而,作为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关照了女性所独有的体验和情感。因此笔者以为,女性作家无需对“女”作家的身份产生苦恼,独特的女性意识有利于打破男权主义中心话语权的叙事模式,从而丰富文学的叙事话语和空间。
一、女性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
孤独,是什么?孤独是孤芳自赏,好像自己存在于和其他人不同的空间里,孤身一人欣赏人生沿途的美景,无人陪伴,无人诉说。孤独是有苦难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茫然和无知,独自克服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好与不好。孤独也是人云亦云,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变成被遗弃的那一个,群体活动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害怕孤独,只能选择背叛自己。
那荒诞,又是什么?荒诞是放纵欲望,重复罪恶,丢失人性,开始动物的狂欢。荒诞是蔑视常规,高扬偏执,消解善意,崇尚邪恶。荒诞也是一本正经地发展事业,在群体活动中走向地狱。
二战中的集中营是象征群体活动的场所,普里莫·莱维说过,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等等,最好的人都死去了。莱维在《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一书中,对纳粹大屠杀性的群体暴力活动做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只有那些被淹没者、待在监狱没有回来的人才是证人,活着出来的人都是罪恶的守护者,并没有完全控诉法西斯的罪恶和大屠杀的真相。”[2]“文革”同样是群体活动盛行的年代,人们栖居于一片枯萎的荒原之上,幻灭和绝望是主旋律,人们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令人窒息的荒诞现实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特别是女性群体,在她们强烈的感觉世界里,天生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渴望他人的陪伴和温暖,是适合群居的物种。
在《老人鱼》中,小穗子骨子里带着娘胎里就有的孤独感,她依稀记得在半周岁时挨过的两脚,母亲的不耐烦,使得她出生后便被爸爸妈妈遗弃给了外公外婆,缺少父母疼爱的小穗子,她的童年注定是孤独的。幸运的是,小穗子是在外祖父的怀抱里找到了些许的温暖和关怀。她故作姿态的顽皮和傲娇,只有在外祖父这里才能找到合理性,他包容小穗子所有的蛮不讲理。然而,小穗子终究还是服从了父母的意愿,背弃了疼爱她的外祖父,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女性的体验感本身就比男性强,童年时代的孤独是穗子始终不想碰触的地带,所以后来她才不假思索地加入了“拖鞋大队”。
“拖鞋大队”(《拖鞋大队》)是女孩们组成的一个“团体”,之所以称为“团体”,是因为团体成员必须保持一致的看法和观点,个人必须服从于团体,否则就是背叛集体,搞个人主义是不被允许的。在政治紧张、人心惶惶的年头,“群体”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人行为不再代表自己的主观意志,不可忽视地打上了集体的烙印[3]。女孩们结伴一起到农场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爸爸们,把辛辛苦苦带来的夏天的衣服和礼品交给了自己的父亲。然而,女孩们为父亲带来的“高级物品”[4]169成了他们生活作风糜烂的标志物,别出心裁的礼物却惹得父亲们当众受到羞辱,蔻蔻爸为了表示自己的悔意,主动将女儿带来的“高级物品”上交给了领导。此后,蔻蔻因为爸爸的不当行为被“拖鞋大队”开除在外。穗子对蔻蔻充满了怜悯之情,但作为“拖鞋大队”的一员,就不能违背集体的意志。她已经背叛了疼爱自己的外公,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如果因为同情蔻蔻,也被“拖鞋大队”排除在外的话,她就成了孤身一人,孤独感让她“绝不背叛拖鞋大队”[4]168。孤独感在特殊时期无疑是可怕的,它病态的发作会淹没人性中的所有美好。人在本质上都是渴望群体生活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常见的群体心理现象,这一心理默默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为了避免孤独,而融入集体,却换来了荒诞。蔻蔻又何尝不想再次融入那个可爱的小集体,她背叛耿狄,诬陷耿狄欺负自己,无疑是想让“拖鞋大队”重新接纳她。
历史的残酷激发了人性中的魔鬼,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的女孩们就沉睡在地狱中,她们甘愿自暴自弃、自我放逐,过度的放纵反倒是一种罪恶的自由,这就是不堪回首的荒诞年代留给每一位后人的思索,愿吸取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二、女性的身体认知和性欲发泄
中国向来是一个含蓄的国度,性欲本是天赋人权也,却长期以来遭到中国人的回避,致使大多数人无法正确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正面描写性爱的小说寥寥无几,性爱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拘禁在卧房,不得张扬。事实上,性爱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不需要偷偷摸摸,而应是顺其自然。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阐述了性对人的生存体验的重大意义:“我敢肯定有一天我们会不再把它当成笑料,而是认真对待并教导儿童,说正像音乐、卓见、美丽的草坪、逗人的婴儿等等许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样,性也是其中之一,正如音乐是其中之一那样。”[5]124马斯洛公开表现了性爱的甜美,而不是罪恶。
当然,压制性欲是正统文化的主流观念,但并不代表着每一个人都恪守规则,历史上大量禁书的出现,间接地反映出人们隐秘的心理,即对性欲的渴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金瓶梅》是经典的“淫书”,大量荒淫无度的性行为描写,无疑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大胆抨击和斥责,具有进步意义。然而,潘金莲、李瓶儿更多充当的是西门庆的性奴角色,在封建男权制社会,没有获得独立经济权的女性,只能凭借秀色可餐的姿色,将自己供奉给男性,女性是被动卑微的。而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笔下的莎菲则不然,她摆脱了传统的缠绕,表现出对情欲的冲动与浮躁,为女性在性爱关系中赢得了主动的席位。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总趋势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由于紧张的政治环境,女性意识已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所取代,高扬同志关系、战友关系、阶级关系、军民关系,排斥儿女情长、男女之爱。在文化荒芜的岁月,性爱成了禁忌。
严歌苓追忆的正是封闭的“文革”年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活成为常态,性欲只能在想象中得到满足,高压的政治环境致使人们隐藏着真实的自己,以反人性的生活方式度日如年。然而,过度的性压抑会导致变态的性心理和畸形的性文化。
在萧穗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懵懂地上了性教育课。十几岁的柳腊姐(《柳腊姐》)“有些要迷住了她的意思”[4]3。柳腊姐有着戏子名角才有的长辫子,穿着戏服,那胸那腹那臀刚好中规中矩,“该凸便凸该凹便凹”[4]7。小小年纪的穗子有着一肚子的坏心眼,事事欺负腊姐,腊姐很快成了小穗子的贴身丫鬟,小穗子从未对她客气过,完全满足了她的主人梦。当腊姐向城里女人学习穿着时,小穗子总是用主人的权威百般阻挠,骂她不要脸,再去揪她“胸口两坨中的一坨”[4]7来解恨。面对腊姐充满诱惑力的身体,小穗子是嫉妒的,同时又难以抵抗。她喜欢腊姐凉滋滋的手臂搂着自己,甚至迷恋上了给腊姐“抓痒痒”[4]11。从头一次触摸“桑葚似的圆圆的乳头”[4]10,到后来的随处看、随处摸。腊姐无疑是禁欲时代里的牺牲品,她无法享用自己热辣的身材带来的欢愉,身体火一样的渴望,只能通过小孩子的触摸得到发泄和满足。她给小穗子普及身体认知的常识,“这里几岁会开始凸出来,这里几岁会长毛毛,这里哪年会流血”[4]11,无疑表现了腊姐对女性身体的迷恋和隐秘欲望的倾泻,突破了女性所固有的保守和被动的形象。
在凹字形的艺术家协会大院楼里(《小顾艳传》),特殊的楼层设计导致了每家的私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一群无聊透顶、整日需要恶作剧来调味的女孩们(后来的“拖鞋大队”),时时监视着小顾和黄代表的地下恋情。她们朦胧的性欲意识,对小顾“很破鞋很破鞋的声音”[4]105上了瘾,爬到了玻璃窗向里看,从门下的门缝往里听,还参加了“表哥抱表妹,表妹抱表哥”[4]105的绕口令大赛,甚至行使侦探这一神圣职业的特权,将小顾和黄代表的丑事捉奸在床,她们终于看到“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连内裤都没来得及穿”[4]108。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论述过性的自然属性:“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5]129那个有意规避男女之爱的年代,使众多的女性饱受性压抑、性苦闷、性饥渴,无论是懵懂年纪的女孩们,抑或是丈夫被捕后孑然一身的小顾,她们都渴望被压抑的性能量的释放。女孩们窥淫癖的非正常的心理的产生,在那样的年代是不足为怪的,当正常的性心理和性行为被视作“异端”时,人们就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性心理来满足自我。
在黑暗无声的世界中,无瑕的洁白能否像莲花开在其中,莲的无声告白可否赢得黑暗的尊重,还是“近墨者黑”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高度的性压抑必然使人正常的自然属性得不到发挥,荒凉的现实催生着女孩们快速长大,快速接受成人世界的疯狂和丑恶,耳濡目染地吸食着畸形性文化的毒品。
三、女性的爱情至上观和异性崇拜
爱情是女性作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感性动物,女性能够强烈地体悟到自我的感情向往和微妙的爱欲冲动,往往追求情与性相统一的爱情。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数不胜数,浪漫的爱情让人心驰神往。然而,在男权主义盛行的文化下,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物,这里的根源来自于《圣经》。夏娃是上帝取了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6],从肉身的源头上来看,女性似乎没有所谓的“主动权”,居于卑微的地位,她们像玩偶一样任人摆布和践踏。
在爱情和婚姻里,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追求。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说过:“爱情只是男人生命中的一小部分,它是女人的整个生命。”男性的社会属性要求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出众,他们由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也是变为“社会人”的过程,故情爱只是他们人生的调味品,不是生活的全部。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男权秩序的维护者,公开将女性看作是男性人生的帮扶工具,女人是为男人而活的。而在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国度,传统的女性将婚姻看作是人生中的全部,追求孤注一掷、全身心的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心爱的男子。对爱情的追求,远比男性要痴情得多,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女性遭受很大程度的不公平待遇。即使是现代社会,在追求自我与保持婚姻二者中,顾此失彼是常有之事,又迫使很多女性重新回归到最原始的角色,将男性看成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上帝,顺从他,依赖他。
严歌苓笔下的爱情则是欲罢不能的,欲望荡漾又克制,正是在昏暗无日的年代里,情爱应该保有的形态。穗子最美好的生命力是活跃在文工团里的,她是天生的舞者,整段青春岁月里的青涩、执着、纯真都在这里悄悄殆尽,生活的真实面目也促使她快速成熟。童年的孤独,使得她处于情感饥饿的状态里无法自拔,恋人成为自己多情的寄托对象。初恋是人爱情萌动的端点,长了会讲情话的眼睛,抑或是自己婀娜多姿的舞影,都足以衬托出美丽年华的纯粹和无暇。初恋固然是美的,而对美的渴望与追求,女性往往又比男性要敏感得多。她对排长邵东俊救自己的事件耿耿于怀,她的浮想联翩,注意到了冬俊的眼睛总是跟着她,认为那其实就是在表白。整整一年,常常在一大群人里面,“眼睛就这样跟眼睛对答”[4]203,此处无声胜有声。冬俊眼睛的火焰早已吞噬了小穗子的心,她暗暗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然而,冬俊却早已想好和穗子停止眼神交流。“他有过女朋友,也跟一些女孩暧昧过,十四岁的穗子使他产生过罪过的柔情,他从未那样心疼过谁”[4]203,但很快又后悔。他意识到“和高爱渝恋爱,才算是个男人”[4]206。邵冬俊并没有阻止新女友的不怀好意的举报,将一百六十封情书交至文工团党委,很快,小穗子成了大家饭后茶余的笑话,所有人都躲着她,她瞬间身败名裂。
小穗子和邵冬俊的男女纠纷是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她被押送到了党委办公室,被审讯,写检查,检查又退回来,以及曾指导员深层次的逼问细节,还参加了盛大的批斗会。然而,穗子仍然守口如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被外人扭曲和讹传得与真实南辕北辙,她呕心沥血写出的文字裸露在外,像是裸露着自己的身体任人宰割。她的声誉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是有谁知道穗子仍然傻乎乎地爱着冬俊,想找他谈话,想他靠近,渴望着他的怀抱,却被拒在千里之外。穗子并没有放弃,她是个死心眼,她认为自己得到的是和高爱渝不一样的冬俊。穗子为爱的人做尽了傻事,吃了安眠药自杀未遂,想通过电缆电击自己而被冬俊救下。她相信相爱时的缠绵柔情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受了处分也没关系,她确定了自己在冬俊哥心中的位置。穗子虽是现代女性,但她尚未完全获得女性独立与自由的意识。在恋爱关系中,女性处于被玩弄的状态,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和爱情的结果。穗子就像男性手中的一件物品,想抛弃的时候可以随意抛弃,毫不留恋。幸运的是,穗子并没有走上子君式的旧路,将自己完全供奉给男性当陪伴的物件,她只是一时地沉浸在美好的初恋中无法自拔而已。在她以后的人生里,她也勇敢反抗像王鲁生科长这样的权势,认识到她和刘越之间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刘越太单纯了。在那次巨大的背叛和伤害后,十五岁的小穗子无力承担“我爱你”那三个字的重量,“她早就不是十五岁的恋人和情书作者了,她现在懂得,真实情感正是在那三个字以外。”[4]263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凭借自己对男性的痴情经历诉说了大多数女性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她们总是任由男性主宰和统治,似乎很难逃脱自身的命运。在女性的定义中,爱情的意义远大于自己的生命,但是,爱情的体验会伴随着成长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终有一日女性会读懂爱情的真正内涵。
婴儿状态的人是无意识的,人是从照镜子那一刻开始,才萌发了自我存在的意识。男权文化盛行下的女性就像婴儿,尚未认识到镜子里的像就是自己。待到童年和青春期,镜子里的自己像迷雾般的表象,女性意识会逐渐深入,向内探索自己不可知的一面。成年后,迷雾的面纱并未完全揭开,仍在继续探索自己,但已失去了最初表象里的稚嫩和单纯。萧穗子的成长,从懵懂到成熟,从依附到独立,从单纯到复杂,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