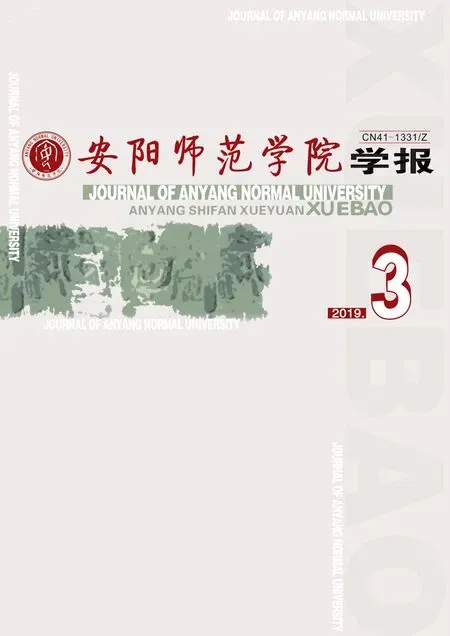当代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革命历史叙事研究
何城禁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对于“历史”一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将这一名词理解为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包括发生的事情本身也同样包括对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康德、彼特·盖伊、杰弗里·埃尔顿、克罗齐等理论家在不同的话语经验中都认为历史总是和叙事联系起来使用。当代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比喻实在论》前言中指出历史叙事与其说是呈现的,不如说是表达的,也就是说,不是生产的而是再生产或模仿的。[1](p46)他的历史叙事理论是对历史进行成功“虚构”和“想象”之后的产物。当代藏族文学自1951年西藏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日趋繁荣。仔细研读当代藏族文学史,不难发现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创作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总结这40多年的长篇文学创作成果,不难发现广泛的革命历史叙事共性,而学界尚没有对此进行过多关注。结合西方历史叙事理论成果和藏族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实际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国家认同和主流话语表达、民族民间记忆和地方性书写、革命历史的建构和想象性重述。可以纳入“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有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1980)、《十三世达赖喇嘛——1904年江孜之战》(1985)、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1981)、《迷茫的大地》(1985)、央珍的《无性别的神》(1994)、阿来《尘埃落定》(1998)、梅卓《太阳部落》(1998)、《月亮营地》(2000)、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2005)、达真的《康巴》(2009)等。
一、国家认同和主流话语表达
1980年降边嘉措的汉语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藏族当代文学上的第一本汉语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艰苦历程,以及广大藏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尔后有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1981)、《迷茫的大地》(1985)、《菩萨的圣地》(1988)、降边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1985)等作品纷纷出版,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藏族文坛上集中出现的一系列表现革命历史的小说题材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因素。
早期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展现出一幅西藏解放的历史画卷,在战争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叙事中展现出国家认同意识和主流话语表达。最早开始进行汉语长篇小说创作的当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益希单增都是军旅出身的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惯常采用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即非聚焦或零聚焦叙事。作家将自身的亲历性革命历史加以回顾和艺术加工,用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赋予小说浓烈的时代气息。
降边嘉措在小说《格桑梅朵》献辞中讲道:“此书献给为解放西藏、巩固国防而斗争的进藏部队全体指导员!为维护祖国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这为小说定调,突出国家认同和主流话语的言说立场。小说分别以解放军和藏族同胞为叙事主体,从战争革命和思想革命两个层面展开对革命历史的叙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叙事主体中,对其进军西藏的历程进行叙事聚焦。“1950年11月初,昌都战役刚结束,中央发布《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1951年夏,郭志诚和李刚带领二支队的战士,分别完成了追击逃窜的残匪和在帮锦庄园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后,接到命令到扎青宗建立兵站,筹办大军渡江事宜”……“李队长在《进藏手册》上写‘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十六个字。”[2](p42-509)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党和国家的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沿途经历了与帮锦庄园的农奴主兼大堪布益西、管家次仁多吉、噶朵代本、旺扎宗本、穷达活佛等分裂势力的正面或侧面周旋的斗争,最终在1951年10月26日成功解放了古城拉萨。
同时小说又以受压迫的底层藏族同胞为叙事主体,从藏族个体的民族身份角度对西藏解放的历史进行阐释。藏族青年男女边巴、娜真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藏族农奴子女,他们被统治青藏高原一千多年的封建农奴制残害,在一边痛述“领主的税多如牛毛”、领主“吃人的手段多”之外,看到了解放军解放西藏给底层百姓带来的光明,并选择加入解放军,成为金珠玛米。藏族青年边巴自白“我是一个穷苦农奴的孩子,旧社会逼得我没有法活下去,是党和毛主席,是亲人解放军,把我从死亡的道路上搭救出来。我总是想,没有共产党、解放军,就没有我边巴”……“藏族同胞们,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些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金珠玛米。一定要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2](p510-596)在藏族个体的叙事主体的聚焦中,展现出西藏解放的伟大事业给西藏旧社会中的生命个体带来了生存的空间和幸福的可能,更加丰富了革命历史叙事的话语视角。小说《格桑梅朵》将解放军和藏族人民作为叙事主体对西藏解放的历史进行双声部的全景式鸟瞰,将规模庞大、线索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采用非聚焦的视角,在两种类型的各个人物身上进行展现,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主流话语立场。
同期的藏族作家益希单增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等多部长篇力作,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坚持书写“我的西藏人和西藏人的故事”,还原了历史转折时期西藏的社会面貌和藏族人民曲折的心路历程。《幸存的人》讲述1936年-1950年间,西藏的底层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血泪史。噶厦政府血洗藏北德吉村,少女德吉桑姆和两岁的侄儿桑节普珠成为“幸存的人”。少女孤儿四处漂泊、沿路乞讨,在农奴主的残害下艰难地寻找生存出路。在共产党解放西藏的前夕,德吉桑姆被农奴主仁青晋美迫害于雅鲁藏布江中。而西藏农奴的反抗斗争没有结束,桑杰普珠、金棕、白朵等人将继续加入反抗旧社会的队伍,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懈斗争。
姐妹篇《迷茫的大地》从《幸存的人》的落笔处起笔,将开麦庄园作为藏族社会缩影进行叙事空间的聚焦,讲述了1949年10月-1952年秋季解放军进驻西藏过程中西藏旧贵族才旺曲珍、农奴之子丹达、姆弟巴桑、解放军等不同阶层的人物在同一时空场景中的矛盾和较量。主人公丹达被贵夫人才旺曲珍所救并被收为义子,进而落入上层贵族的圈套中,成为其统治下层百姓和抵抗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帮手。丹达内心有着牧民的淳朴善良,他一方面同情受苦受难的差民和仆人,另一方由于认知的局限,饱受贵妇人的愚弄和规训。才旺曲珍企图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政治野心也移植到丹达的头脑中,以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有意曲解来误导丹达,期望丹达在思想上能够与她保持一致,并利用丹达来捍卫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丹达在昌都之行中首次接触到解放军,陈营长和郎吉等人让他看到与贵妇人口中截然相反的解放军形象,在真相和谎言的较量中慢慢觉醒。在地方顽固势力和解放军的斗争中,农奴主贵族的残忍自私暴露无遗,丹达的妻子姆弟巴桑也沦为庄园主才旺曲珍泄愤的牺牲品,广大藏族百姓也彻底看清了真相,丹达在认清才旺曲珍的真面目后投入了解放军的队伍中。益希单增在20世纪80年代写就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是作为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礼物,让解放后处于建设和发展新时期的藏族人民能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美好未来。
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等最早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以西藏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讲述这段漫长而沧桑的藏民族血泪史,将西藏解放、农奴解放的抗争史和心灵史再现在世人面前,让生活在解放后幸福的藏族人民铭记这段历史记忆。早期小说家以作家的敏锐、战士的执着、学者的深沉,讲述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革命历史,弘扬“老西藏精神”[3](p987),体现出国家主流话语的体认以及深厚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
二、民族民间记忆与地方性书写
20世纪90年代藏族作家的汉语长篇小说历史题材开始从宏大的时空场景转向对特定藏族民间族群做地方化书写,例如阿来的《尘埃落定》(1998)、梅卓的《太阳部落》(1998)和《月亮营地》(2000)等。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以特定的藏族部落族群为描写对象,以国内革命环境为时代背景,对处于西部边缘地区的藏民族历史画卷进行了叙事深描,展现出在革命战争时代藏族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时代变革的特征。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并荣获第五届矛盾文学奖。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以康巴藏族土司制度为背景,讲述了封建农奴制度的覆灭和民族统一的历史风云。麦其土司的傻子儿子具有超前的神性预感和言行,是一个凝聚了跨越时代局限的圆整人物。傻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他由一个懵懂的小孩成长为独立于北方边境市场的“机智”人物,后又经历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这个贯穿了小说文本的人物身上承载了国家统一、民族进步、文化冲突、血亲复仇等多重主题意蕴。《尘埃落定》将藏族旧封建农奴制度中的土司制度的末世悲剧在革命历史背景做出地方化的呈现,将血腥暴力、两性情爱、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军阀势力的周旋较量、土司官寨的毁灭都表现得惊心动魄,此外鸦片、梅毒、武器、粮食贸易等富有现代性特征的事物的涌现,也让小说呈现出多元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必然性的发展趋势。阿来的《尘埃落定》凝聚着嘉绒藏族部落的集体记忆,是在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历史必然中的地方化的具象呈现。
梅卓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是对青海藏族部落的历史记忆的现代重述,在幽邃的历史建构中,流露出藏民族历史的隐痛。《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的思想意蕴和叙事策略大体一致,叙述者将青海马氏军阀对几大藏族部落的虎视眈眈放在暗处,在藏族部落自相戕伐后企图坐收渔翁之利。梅卓重点审视了民族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劣根性和痼疾,她以一个女性知识精英的高度理性重新痛述男性精神几近阉割的委顿。在人物塑造中,本该具有民族英雄气质的索白、嘉措、阿·格旺、甲桑、阿·文布巴、章代·云丹嘉措等人沉迷于情爱私欲和酒精的麻醉中,对近在咫尺的民族生存危机视若罔闻,将唇亡齿寒的民族大义置之不理,陷入藏民族传统的血腥复仇漩涡中。梅卓的长篇处女作《太阳部落》中的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月亮营地》中的月亮营地和章代部落为了草场、土地等眼前利益互相征伐,常年不睦。嗜酒贪杯的民族习俗也成为磨灭英雄斗志的原因之一,此外男女情爱纠葛更是彰显出人物的委顿和消沉。《太阳部落》中伊扎部落千户索白玩弄万玛措的感情,迎娶了美丽的妻子耶喜后又苦苦追求桑丹卓玛。《月亮营地》中阿·格旺与尼罗相爱,并有一子甲桑,但他贪慕阿家财产入赘阿府,妻子死后,他又迎娶了年轻貌美的娜波,致使心灰意冷的尼罗郁郁而终,从此阿·格旺陷入悔恨中难以自拔。甲桑深爱阿·格旺的继女阿·吉,在阿·吉嫁给章代部落头人后甲桑陷入失恋的伤痛中。当章代部落被马家军团吞并,阿·吉带着儿子重新回到了月亮营地,寻求年轻一代团结起来抵御外敌入侵时,甲桑一味地沉浸在个人爱恨情仇中对迫在眉睫的民族生存危机不予理会。在草原部落蒙受巨大损失和灾难之后,安多藏族部落开始团结起来抵御马家军团的侵略,并将其赶出了草原。在叙事文本中本该是民族有为之辈的人物呈现出的卑琐、委顿、无聊,成为安多地方的民间记忆,叙述者通过文学的方式对民族历史进行理性反思,对整个民族痼疾做了深刻而沉痛的展露。
阿来和梅卓对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都饱含着地方化民间记忆的特征,是藏民族民间族群对革命年代民族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民间化了的集体记忆。这些地方性的革命历史书写是在以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的宏大背景中的局部深描,是将藏族民间历史在时代镜像中的叙事聚焦,其中凝聚了藏族作家对民族史的理性审视,具有强烈的反思色彩。
三、革命历史的建构和想象性重述
“后革命”这一概念来源于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 认为后革命有反思革命、解构革命、消费革命等含义。后革命的“后”,一方面是革命之后,在革命历史及革命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表明革命及其话语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是对革命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甚或批判,革命已经不再作为严肃的政治性事件而是夹杂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后革命时代’,则主要是指这种反思抑或批判革命的话语及革命叙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4](p41-42)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达真的《康巴》是藏族文坛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凸显了新的时代语境下革命历史文学写作的新动态。在当下商业化时代浪潮中,“革命”已经与时代生活相去甚远,不再作为国家的核心话语,同时也在不断退出民间的集体记忆,成为了充分历史化和商业资源化的事件。大众对革命的解构和调侃已经成为时尚,作家也将革命历史作为一种可供改造的素材,在市场经济逻辑中重新建构和想象革命历史。
格央的《让爱慢慢永恒》以姬姆措和玉拉两位女性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采用双线叙事的方式,以1916年-1923年间西藏的复杂局势为时代背景,对这一历史时期内西藏底层人民的人生遭际进行了跨时空想象。姬姆措从安多老家来到拉萨投奔开茶馆的哥哥平措,并与贵族嘎乌家族的三公子索南平杰相恋,但平杰在家族的要求下出家为僧,已经怀孕的姬姆措只好黯然离开拉萨,跟着商队来到遥远的锡金大吉岭。嫂嫂玉拉也在同一天跟随初恋情人噶朵私奔离开茶馆,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作者格央没有放大当时英国入侵西藏的历史,而是对这段历史中具体人物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描。锡金人莱顿纳少校的表弟苏吉亚与姬姆措相恋,但是横亘在二人中间的国家立场和民族立场让他们之间的感情饱受危机,最终二人抛下对峙与分歧,去英国定居生活,做“快乐而辛苦的农夫”。玉拉跟着噶朵来到波密,但是并没有过上美好的生活。二人在嘎乌府下帕多村庄园服役过程中,噶朵一方面靠着一定的勇武狡诈得到了索南旺堆宗本的信任,一方面又反复引诱索南旺堆的三太太与他私奔,置即将生产的玉拉于不顾。玉拉对自己的不幸始终保持着逆来顺受,并在噶朵做了假账后和他一起逃亡至江孜。在江孜士兵和警察的械斗中,噶朵死去,玉拉失去了丈夫,独自承受不幸的命运。两个女人在时代波动中或被动或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在历史和男性的裹挟中始终对人生际遇保持一种坚韧不屈的态度。格央笔下的历史是充满人性温度的,在革命历史背景呈现女性的人生困顿中,两位女性主人公一步步成长和成熟,并试图以独立的姿态留下一抹英姿。
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讲述了几十年间希薇庄园三代人的人生轨迹,其中琼芨白姆在历史风云变幻和政治运动中跌宕起伏的一生充分展现出作者对于革命和政治的当代想象。白玛娜珍作为一个70后藏族女作家,以女性细腻的感知笔触将饱受历史创痛和伤痕的女性内心世界以及生存处境呈现出来,极具哀婉和感伤色彩。16岁之前的琼芨是希薇庄园的二小姐,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贵族小姐生活,在西藏解放的民主革命中,琼芨生父参与阴谋策反革命叛乱等组织活动而逃往印度,希薇庄园受到牵连,昔日的贵族耕地平分给广大贫苦农奴,万贯家产也被查封。“拉萨传来消息:中共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执行平息西藏叛乱任务的部队,宣告平息西藏叛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村民的房屋都升起了五星红旗”,[5](p29)面对扑面而来的政治运动,琼芨试图逃离希薇家族惨烈的命运,她连夜骑马到拉萨请求解放军刘军的帮助,刘军将去内地上学的名额给了琼芨。在内地的西藏预科班中,琼芨与巴桑顿珠相爱,巴顿提前毕业后,琼芨又和语文老师雷相恋并怀孕。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琼芨与雷的孩子被扼杀,雷被下放边远地区劳动改造,琼芨也被退学遣送回拉萨。回到故土的琼芨与巴顿破镜重圆结婚生子,这时席卷全国的十年浩劫在西藏拉开了帷幕,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属于“保守派”据点的巴顿的单位和属于“造反指挥部”的琼芨单位互相对峙,这对年轻夫妻的婚姻也被迫走向解体。琼芨在红卫兵串联动员大会中遇到了曾经在解放军农场中爱慕她的战友、如今的市委领导巴桑,在对时代局势的妥协中,琼芨有了巴桑的孩子,并再次结婚。十年浩劫的政治运动中,琼芨家希薇家族在解放前的庄园主身份被查出,巴桑被解除党内职务并发配去地方改造,琼芨也被定为反革命子女,沦为清洁工。在无法与之抗衡的命运中,琼芨再次失去了婚姻,在苦恋的丹竹活佛决定去印度修行后琼芨失去了拥有正常的家庭温暖的机会。琼芨的一生在政治运动中像浮萍一般被吹打磨砺,命运的伤痕和人生变故让她成为“曹七巧式”的女人,她对儿子旺杰畸形乃至变态的感情成为一个时代在琼芨身上留下的毒瘤。“白玛娜珍将动荡历史中的人性做了充分的展示,并用饱含温情的笔触去感受她们的遭际,抚摸她们的灵魂,探查女性的困境,期望着救赎与温暖。”[6](p87)
达真的《康巴》是一部具有康巴藏人史诗气质的长篇巨著,其叙事空间主要集中在多元文化交汇地康定。小说文本以降央土司家族、尔金呷家族、回族郑云龙家族为叙事主体,充分想象了20世纪50年间的历史洪流中康定地区降央土司家族的秘史、与尔金呷家族的恩怨仇杀,以及回族青年郑云龙为情杀人逃亡康巴藏地后在行伍中发迹并进入主流社会的历程。在达真的革命历史想象中,郑云龙从士兵到军官的传奇经历以及其子郑显康在军校毕业归来参加远征军赴缅甸抗日前线,并在内战中被白崇禧部队裹挟逃亡台湾的经历都极具革命历史的传奇性。郑云龙从汉地成都富商的保镖,到康藏行伍间杀伐决断的战神,他也走私鸦片、倒卖枪支,为避开红军前往青海会见军阀马步芳。郑云龙见证了西康省的成立,也经历过儿女爱恨情仇,他被塑造为一个刚性人物,没有扭捏缠绵之气。面对不服从婚姻安排的儿子郑永康,目睹其在眼前开枪自杀,他不是不悲痛而是将更多的情绪内化,呈现出男性刚性隐忍的气质。在小说文本的尾声,郑显康孙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台湾回到康定祭祖这一故事情节显得韵味悠长,在温情感伤的唏嘘中又折射出作者呼唤全人类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达真将中国记忆死角的大西南康藏地区的传奇历史面纱揭露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具有文化“混血”特征的康定的历史生命力和强大包容性,将康巴的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民风、民俗做了全面的呈现,极具穿透性和感染力。
格央、白玛娜珍、达真将革命历史作为可供改造的文学素材进行编码,在后革命语境中不同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这一时期的作家们顺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建构历史,铺陈历史想象,是对历史的再创造。
四、结语
当代藏族作家汉语长篇小说的革命历史叙事在不同的创作语境中又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早期的作家在国家话语下倾向于主流话语的言说,随后逐渐转向民族内部的理性反思话语,在当下的后革命氛围中将革命历史神圣祛魅并重新想象、建构和阐发革命历史故事。革命历史不再作为僵死的事件而是可以供改造的文学素材,作者将革命历史素材组织起来成为符合当下时代语境的新的话语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