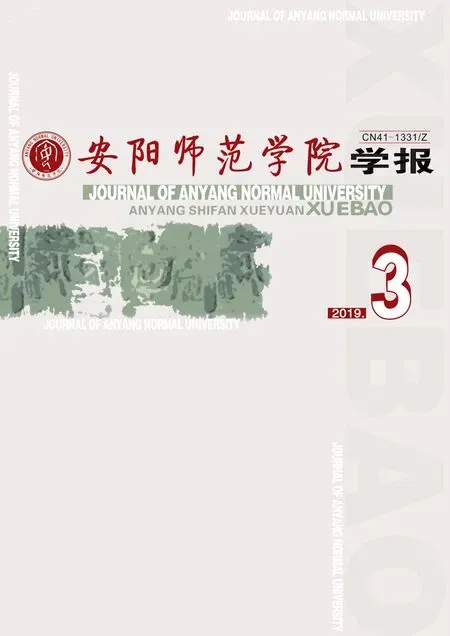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与恽代英的救国探索比较研究
葛星辰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与湖北两地相继产生了两个由青年学生创办的进步社团——新民学会与互助社,两个社团从发起人、创社宗旨、发展轨迹、历史作用上来看,都有相似之处。对这两个学生社团展开相关研究,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考察维度,可以对建党之前各地青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付出的各种努力有更加深入认识。本文将视角聚焦于新民学会与互助社的发起人——毛泽东与恽代英,并以二人创办的进步社团为对象展开比较研究,以二人的互动与二社团的发展走向为范本,分析两湖地区青年学生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尝试与探索,以期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对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有所启发。
一、年少有为,立志图强
在求学期间,毛泽东、恽代英两位青年关注和思考着个人和社会问题,且在内容上有异曲同工之处:重视自身的修养,广交朋友,对哲学的学习颇有心得,关心时局,心怀天下,以救民济世为己任。两人均少年有为,立志图强。
1914年,国际上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辛亥革命刚刚葬送了中国的千年封建帝制,但新生的民国却没有为大众带来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国家正处于一片沉闷的氛围中。此时,毛泽东开始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恽代英正在武汉中华大学读预科。
1915年,毛泽东撰写过一篇《自讼》并寄给好友萧子升。在文章中,毛泽东用冷静的文笔对自己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将自我反省的全程毫无遮掩地摆给自己的朋友看,既是反思自身,又是规劝朋友戒骄戒躁。毛泽东深受杨昌济、徐特立两位老师的影响,对哲学、史学、文学等课程具有浓厚的兴趣。初入校门即修学储能,在1916年以前阅读大量的典籍,并经常与好友通过书信交流心得体会。从这些书信中时常能见到他对学习方法的思考,对最近所学经典抒发一些解读观点,也不乏对时局发表的一些看法和主张。毛泽东已经开始与同学若干,“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1](17)随着9月新文化运动勃兴,文化界受到“民主”、“科学”之风的吹拂,毛泽东为了寻觅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在长沙各校张贴征友启示。不久,毛泽东通过竞选,谋得了学友会文牍的差事,在处理学友会各项差事中,锻炼了能力。以任职学友会为开端,毛泽东走上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与恽代英“利他主义”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17年写下的《伦理学原理》万字批注中提出了“唯我论”的哲学思想,强调个性解放:“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1](P40)这些批语显露出毛泽东已初步具备一些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自我意识已经觉醒。
恽代英正在武汉中华大学读预科时期,已经笔耕砚田。在1916年,为了督促自己进步向上,恽代英发表一篇自我解剖的《自讼语》,对自己的缺点弱项进行无情的批判。1916年10月,恽代英就在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义务论》,将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描述为一场争夺权利的祸乱,将法律政治家的“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亦应知其权利”[2](P1)的利己派界定为权利论者,将宗教道德家的“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不必知其权利”[2](P1)的利他派界定为义务论者,对帝国主义的虚伪和残酷进行无情批判,并发出了“天下之人,……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2](P5)的呼喊,从而标志着恽代英“利他主义”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随着对哲学的学习逐渐深入,1917年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怀疑论》,其唯物主义思想已经乍现,并展露出批判精神。同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恽代英在武昌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3](P14)恽代英为了在与全班同学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免费上学的名额以减轻家中负担,他把班上几个实力强劲的同学、朋友都列在自己的清单里,对他们的优点长处进行了深入剖析,下决心超过他们;为了经济上进一步实现独立,他向各大报刊广发文章,赚取稿费,他的思想与主张,能力与见地,均随着其写作实践得到了长足进步。恽代英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两件事上,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练习演讲。他的文章涉及领域广泛,从社会问题到妇女问题,他也翻译文章,涵盖体育、医学、世界大战等方面;他为了把嘴练成宣传的武器,常常昼夜不知疲倦地练习演讲。
毛泽东与恽代英具有十分相似的经历,二人自我要求严格,勇于锤炼自己,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许多同龄人不曾具备的优良品质。这两个富有魅力的青年学生的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不乏真知灼见,掌握了真才实学,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储备着澎湃的能量。
二、创办学生社团
毛泽东与恽代英的品行与个性有相像之处,从自身性格而言,毛、恽皆有务实向上的风格,不尚空谈。毛泽东饱受湘学经世致用学风的浸润,并且曾写信规劝喜欢夸夸其谈的朋友萧子升;恽代英为了达到学校减免学费的条件而十分努力,在一年内拿到了两次本班冠军成绩。二人对待交友问题也有共通之处。恽代英自言:“每谓天下难得一益友,不得益友,则不如其无友。”[2](P21)这种宁缺毋滥的择友标准常常使恽代英心生人至察则无友的困惑。毛泽东在《征友启事》中写道:“上下而欲觅同道者。”毛泽东与所交往的朋友经常谈论的内容,大多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4](P39)。
恽代英的结社实践要早于毛泽东。1917年9月,受基督教活动的启发,恽代英将酝酿多时的建立一个学生社团组织的想法提上日程,目的是联络好友、互相鼓励督促、为献身社会搭建一个平台。他在日记中写下了结社初衷:“此会重自治,不重他治,重利人,不重利己”[5](P146-147)。由此以“自助助人”为宗旨的好学生社由此成立了。没过一个月,恽代英发表了一篇题为《理想儿童俱乐部》的文章,文中犀利地指出全国一片散沙的现状,即是由“吾国人之无互助的精神”[6](P61)所造成的,文章体现出恽代英当时对社会的关切。为了进一步实现互助的愿景,恽代英又创立“互助社”,通过“自助”,遵循社团的戒条,摒弃自身的不良习惯,达到“修身”的目的;各社员联手起来,为需要扶助者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恽代英在他实现个人理想的初步探索中,将个人与社会的纽带维系于社团,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途经统一于社团。
毛泽东在1918年成立新民学会的前一年,有过一次组织湘潭校友会的实践,还当选了校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校友会以“有社团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为目的。筹办校友会的时间与恽代英建立好学生社的时间相差不多,虽不能视作毛泽东创办进步社团的起点,却为新民学会的成立扩展了人脉,积累了组织经验,启发着毛泽东的结社思想。毛泽东经过用心经营,在他身边已经聚集了约十五人,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就“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类问题展开讨论。1917年底,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提议组织一个学会,立即得到很多人响应。毛泽东等人发起学会的动因急迫而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
毛泽东与恽代英结社的背景与目的有诸多一致,两人都是在对孤立的学生生活产生厌倦后积极投入集体生活,与其他群体积极展开联络;对个人发展有着向上进取的期待,同时又高度关切时局的变化,努力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平衡,热心改造社会的实践,对救国救民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围绕在二人身边有数量可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生活与学习上皆能互相帮助,重视青年时期个人优良品性的培养与积累知识、掌握技能;组建学生组织的宗旨、性质更达到了高度相似:不仅强调戒除自身陋习弊病,更强调互相帮扶,互助互利。两个组织起初都是较纯粹的“修身、互助”性质的集体,并没有将功能更多地延伸到政治领域,但成立不久,即纷纷突破创立宗旨,接触政治,并开展了一定的政治实践。两人成立的组织逐渐成为一批有志青年进行政治思维、政治活动的训练场和投身实践、奔走救国的候场室。
三、在组织中独立探索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的学生进步组织开展了无畏探索、积极尝试,依靠自身力量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这里提出的“独立探索”,是相对于当下存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依靠俄国人输入,没有俄共、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而言的,以毛泽东、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种种实践,有力驳斥了中国人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从而证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主要是中国社会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必然结果。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嗅觉敏锐、思维活跃,对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保持一定的好奇心与尝试欲。在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时至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起举国震动,离开北京回到长沙探望病重母亲的毛泽东重新主持长沙新民学会的工作。他利用在小学教历史课的便利,“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1](P41)
5月4日一场以学生为主力军的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震动余波传递到湖南,毛泽东与新民学会联系更加紧密了。毛泽东领导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改组活动,并在学联的发起下,湖南各界成立了联合会。毛泽东担任学联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与撰稿人,发表多篇文章传播新思潮,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他对陈独秀推崇备至,曾作文《民众的大联合》,将民众大联合视作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此时的毛泽东主张“平民主义”,即反对强权,进行“无血革命”,“暴力革命”的思想尚未觉醒。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在文章中大谈其“新村主义”的畅想:“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7](P841)1919年,恽代英与林育南商谈,准备尝试新村主义,“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我们的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6](P153)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对“新村主义”产生了兴趣,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的思想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以和平手段改造社会的“新村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只能流于空想,国家、民族尚不能独立,将改造社会的重任寄希望于不流血的革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人的思想尚不完全成熟,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毛泽东、恽代英的探索并未止步于对社会主义的空想,在五四运动爆发至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主要的实践活动是:在湖南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在斗争过程中受到启发,积极推进湖南“自决自治”;期间还前往上海与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谈话,交流自己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一些感悟;在返湘时,途经武汉,与恽代英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的问题。恽代英与毛泽东“畅谈革命理想,纵论天下事,将筹办利群书社事相告毛泽东”。[6](P164)1920年刚入2月,利群书社在武汉创建,这个倾注恽代英与互助会其他成员大量心血的书社,成为他们联系社会的纽带与追求独立自给生活的平台,书社同样秉承着互助社“自助助人”的宗旨,也吸纳了其他社团的部分成员,成为武昌地区进步社团的代表。书社在强调社会价值的同时也注重营利,“是武汉地区进步青年对外的联络点,也是《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在武汉的代表处”。[6](P165)毛泽东对恽代英创办书社的办法十分认同,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也专心经营起自己的“文化书社”,与恽代英的“利群书社”展开密切合作,“经由……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8](P69),并将书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专卖新出版物。
随着与社会接触程度的逐渐加深,恽代英的注意力从青年学生转移到工农大众身上,并发起“工学互助团”。毛泽东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在长沙各学校寻觅进步青年作为发展对象。在1920年5月间,恽代英与刘仁静曾有过一次关于“用‘暴力革命’还是‘工读互助’改造社会”的激烈讨论。6月,在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提议将恽代英的利群书店作为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后的一个核心枢纽,这说明利群书店的发展已经引起俄共(布)代表的关注,恽代英进行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得到了认可,为他及他身边的一群人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同年,毛泽东与他的新民学会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7月间,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会议,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学会方针。会员也分成两派,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俄式的激进革命道路,有成立共产党的意向。与蔡和森交往甚密的毛泽东,在通过书信交换思想后,决定接受俄式革命这个“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9](P6)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投身到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去了。而到了1921年春,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给恽代英造成极大思想冲击,同时也彻底动摇了他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开始接受“暴力革命”,逐渐公开地宣布自己“很信唯物史观”。
四、结语
在将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设时期,一批为了革命事业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的青年们主动接受时代的洗礼,既深受历史潮流的影响,又成为历史潮流的推动者,他们的思想、意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呱呱坠地而展现出全新面貌。我们继续往前追溯便能发现,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在于“新民”,给当时一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带去了新的思想,他们勇敢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空想,将希望寄托于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毛泽东与恽代英只是他们之中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代表,在中国大地上,这些青年从少到多,其思想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诚然,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最主要、最关键的内部因素是这些勇敢肩负起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的进步青年,正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