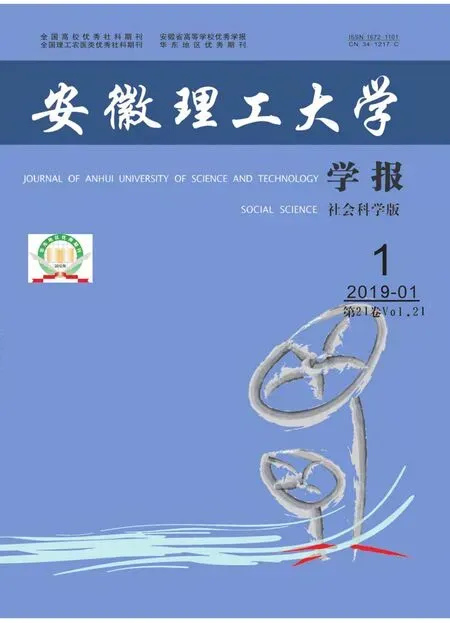《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与接受研究
孙宏新
(淮南师范学院 科技处,安徽 淮南 232038)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美国小说,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部名著早在1901年即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方式,经历了由小说翻译到戏剧改编的转变,在中国接受的视角则经历了由政治对话、文化对话到文学对话的嬗变。这种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诸多方面的嬗变轨迹,可以对我们考察中外文化交流过程规律性的东西,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文学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达到高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南部康斯坦茨的五位教授,即姚斯、伊瑟尔、福尔曼、普莱斯丹茨和斯特里德,他们被称为“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理论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中。”[1]就其接受方式而言,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之分,垂直接受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及其变化;水平接受则是指与作者同时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情况。接受理论同时指出,接受也是一种再创造,“读者通过接受活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作品中蕴藏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但是,读者在改造作品的同时,也在改造他自己;当他将作品中潜藏的可能性现实化时,也在扩大自己作为主体的可能性,这就是作品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接受活动是使这两种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2]读者通过接受活动与想象力对作品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不是对文学作品的简单“复原”,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读者在使文学作品的潜能为自己服务的过程中,唤醒的不仅仅是审美潜能,同时也为自己的审美潜能增添了新能量。接受提高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接受美学理论不仅为人们艺术审美活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成为我们考察中外文学传播、接受的内在规律,考察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内在规律的理论依据。本文以美国斯托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与接受史为例,探讨中外文学交流过程中的规律性因素。
二、《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历程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南部的奴隶制与北部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对峙。黑人在南方身为奴隶,他们过着屈辱、悲惨的生活。许多有识之士非常同情黑奴的命运,他们拿起笔来,为黑人的不公遭遇大声疾呼。斯托夫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斯托夫人曾经居住的辛辛那提与保留蓄奴制度的南部村镇一水之隔,南部逃亡的黑奴使得她有机会与之接触。斯托夫人深深同情黑奴们的悲惨遭遇,她要“让全国都认识奴隶制是最可诅咒的东西”[3]269。 1851年,《汤姆叔叔的小屋》开始在华盛顿一家杂志上连载,作品以感人的形象和真实的描写揭露了黑暗的蓄奴制。作品甫一问世,立即在国内外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年内多次印刷出版,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戏谑地称赞斯托夫人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句看似戏谑之语却从另一方面表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价值。
《汤姆叔叔的小屋》主要讲述老黑奴汤姆的悲剧命运和其他黑奴的悲惨遭遇,揭露和控诉了美国南方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罪恶。小说围绕汤姆几次易主的遭遇和伊莱扎争取自由的斗争展开。汤姆原本是肯塔基州奴隶主谢尔贝先生家里的“家生”奴隶,从小侍奉主人,成年后当总管,忠心维护主子的利益。谢尔贝投资失利,决定把家里的老黑奴汤姆和其他几个黑奴卖掉抵债,其中包括女黑奴伊莱扎的儿子小哈利。汤姆俯首帖耳,任主子摆布,伊莱扎却带着儿子连夜逃跑。汤姆被卖出后一度在城里给一个资本家当马车夫,主人暴死后,又被送到奴隶市场拍卖,后被转手卖给了新奥尔良的一个叫李格利的庄园主。李格利生性残暴,对黑奴毫无同情之心,汤姆最终惨死在他的皮鞭之下。与此同时,伊莱扎带着孩子,经过千辛万苦,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废奴派白人的援助,终于到达了自由的加拿大。《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其对美国南方黑奴非人生活的真切描绘,对平等、自由的热切呼唤,以及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震撼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的变化轨迹是显而易见的。从外在形式上,它经历了由小说译介到戏剧改编的过程;对于作品内涵的解读,也经历了从理解其思想政治与文化意义到欣赏其作品艺术特色的演变过程。
(一)《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就其方式而言,主要有两种:小说译介和戏剧改编。
1.小说译介。陈惇在其主编的《比较文学》中指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更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4]《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研究首先是从作品的翻译开始,而其在国内的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林纾版的《黑奴吁天录》和黄继忠版的《汤姆大伯的小屋》。
(1)林纾版《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最早的翻译者是林纾和魏易,早在1901年,他俩以文言文形式合作翻译出版此书,译版取名《黑奴吁天录》。这是第一部中国人译介过来的美国文学作品,也是林纾翻译的第二部外国小说(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是1899年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一生译作一百八十余种,对中国翻译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林纾本是晚清举人,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古文功底。他不懂外文,一般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先由精通外文的人口述,他用古文笔录。林纾版《黑奴吁天录》与其他“林译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原著存在诸多的“误读”。林纾与当时其他翻译家的“误读”,实际上是在译述过程中对原作描写的域外社会生活及某些文化现象进行有意无意的“本土化”理解,并对之进行有意无意的“本土化”改造。正是在这极其复杂的误读与改造过程中,实现着中外文学的对话。在译述过程中,林纾对原作的“误读”与改造,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淡化了原著中的宗教主题。斯托夫人在其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极力宣传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希望用宗教来拯救泯灭的人性,改良物欲横流的社会。林纾在翻译时,删除了宗教信息较浓的内容,如《圣经》的引文、赞美诗、宗教对恶人的感化等。例如原文第二十二章,伊娃在临终前召集所有黑奴,劝他们以耶稣为信仰,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并要学习《圣经》。林纾在这部分的翻译中,却改成女主人公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训导黑奴,她不是让黑奴们去读《圣经》,而是去“读书”。林纾希望用儒家的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与其自身的儒家文化的教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次,淡化原著中所体现的女性力量。斯托夫人在作品中宣扬了女性拯救社会的力量,这也是作品所突出的主题之一。作品中很多女性信仰耶稣、心地善良,善待黑奴。最突出的就是小伊娃,她是书中最完美的形象,她用基督似的爱来感化人,并用基督似的方式来教导人。还有不甘逆来顺受的伊莱扎,通过自己的抗争,最终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幸福。林纾在译本中要么对这些内容视而不见,要么大量删除描写女性影响力的内容。在林纾的骨子里,女性的形象必须符合中国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三从四德”。林纾的儒家文化背景奉行的是“男尊女卑”价值观,原作的描写与林纾的儒家思想意识发生严重冲突。而且面对中国读者,林纾是不会允许依靠诸多女性来拯救世道的。但原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奉行的“仁”又是内在相通的,于是,林纾以淡化女性身份的“误读”方式,实现了中西文化基本价值观念的对话与沟通。
(2)黄继忠版《汤姆大伯的小屋》。黄继忠是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早在1956年即接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请翻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本已于1958年译毕,但未能如期出版,后其译稿在“文革”中被焚。1982年重新翻译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译本甫一推出即大受欢迎,第一版印了59 000册,很快又再印刷了30 000册,都销售一罄。黄继忠版《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一大特点是忠实于原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于“Uncle”一词的考证。小说的原名是Uncle Tom’s Cabin,庄园主谢尔贝的儿子乔治称汤姆为“Uncle”,而汤姆比谢尔贝大8岁,乔治应该称汤姆为“大伯”,所以黄继忠建议把书名改为《汤姆大伯的小屋》,由此,除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黑奴吁天录》译名之外,又多了个译名。该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由此可见一斑。黄继忠版《汤姆大伯的小屋》的另一特点在于异化翻译法的运用。“异化”是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创造的用来描写翻译策略的术语。异化(Alienation),又被称为“Foreignization”,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迁就外来文化的特点,吸纳外来文化的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表述原文的内容。”“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5]Lawrence Venuti把异化翻译法归因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Schleiermacher的翻译理论说“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黄继忠的译本充分采取异化翻译法,这里试举一例略为佐证。
原文:Evil rolls off Eva’s mind like dew off a cabbage-leaf,——not a drop sinks in.[6]
黄继忠的译文:坏事落在伊娃的心灵上,就像水滴落在白菜叶子上,一下子就滑掉了,一滴都渗不进去[7]179。
cabbage-leaf是指白菜叶,斯托夫人把伊娃纯洁美好的心灵比作白菜叶。而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物美好心灵的比喻往往用荷花做比,如果把它译为荷花,虽则优美,但不能保持原生态的生活画面。黄继忠采用直译的方式,也比喻成白菜叶,使得译文原汁原味。而林译版恰恰就把它译成了荷花:“如吾夜娃,尘污何得入侵!此女盖出水新荷。骤雨密点,不能由一星之驻。”[8]这是翻译过程中照顾本土读者文化心理的“归化”手法。黄继忠的译本体现了对原文的忠实,使读者能够真实感受作者表达的意图。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之后,对原作文化内涵的尊重。
2.戏剧改编。戏剧是一种侧重以人物台词为手段,集中反映矛盾冲突的文学体裁,它以浓缩的反映生活、集中地表现矛盾冲突、以人物台词推进戏剧动作为基本特征。就其文学上的概念而言,戏剧主要指的是戏剧表演所创作的剧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经历了两次改编并上演,分别是春柳社改编的《黑奴吁天录》和欧阳予倩改编的《黑奴恨》。
(1)春柳社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被介绍到中国后很快就被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演出。1907年6月,春柳社组织的由曾孝谷根据林译版同名小说改编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在东京大戏院公演。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认为这“可以看做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因为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自己写的这样整整齐齐几幕的话剧本。”[9]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包括《早稻田文学》等刊物在内的日本舆论界的高度赞扬。剧本以全新的逼真于生活的演出形式,直面黑奴的悲惨命运,表现黑奴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勇于抗争的精神。春柳社改编《黑奴吁天录》,时值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之际,因此,该剧的改编和演出,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色彩。
(2)欧阳予倩改编的《黑奴恨》。欧阳予倩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早年参加春柳社,并参与了《黑奴吁天录》在日本的第一次演出。1957年纪念话剧运动50周年之际,欧阳予倩就有把《黑奴吁天录》重新整理改编出来的欲望。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正值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欧阳予倩认为“《黑奴吁天录》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应该好好搞它一下。”[10]他花了10天时间,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十幕话剧,并改名为《黑奴恨》,发表于1959年《剧本》月刊上,1962年又出单行本。《黑奴恨》可以说是欧阳予倩的压卷之作。
话剧《黑奴恨》较之于原著《汤姆叔叔的小屋》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其一,内容的剪裁。原著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伊娃这个小女孩,本意是希望用伊娃的善举去感化没有受过教育、冥顽不灵的黑奴。斯托夫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以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去拯救处在悲惨境地的黑奴。欧阳予倩在改编时,把有关伊娃的内容全部舍去。他认为,黑奴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要自己去争取。所以花了较多的笔墨写汤姆因逆来顺受而惨遭不幸;而伊莱扎、哲而治及凯西等不甘受压迫,经过千难万苦逃到了自由的加拿大。从改编者潜在的文化心理看,这样处理应该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革命文化背景下,坚决反抗,自主求解放价值观念的表现。这也应该是一种积极的“误读”吧!
其二,谢尔贝形象的处理。原著中谢尔贝是个心地善良、仁慈的奴隶主,生意失败被迫卖出自己的黑奴,有钱后又想及时赎回他们。但欧阳予倩在《黑奴恨》中撕去了谢尔贝伪善的面具,他在外边欠了债无法偿还,就拿汤姆等黑奴去还债,根本不顾黑奴妻离子散的痛苦。在他的骨子里,就是个流氓,他的凶狠与残暴丝毫不比李格利逊色。在剧本的《后记》中,欧阳予倩指出,“我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凡属美国绅士老板们虐待黑人的情形,都根据斯托夫人小说所描写,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夸大。至于书中认为善良的绅士如地主谢尔贝、工厂主威尔逊等,我不能不撕碎他们的面纱,揭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11]这实际上是通过简化人性的复杂内涵,简化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来彰显阶级的对立。
其三,结局的安排。原著的结局是汤姆遭奴隶主李格利虐待惨死,伊莱扎和丈夫及孩子等在废奴派白人的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加拿大团聚,获得自由。《黑奴恨》剧本初稿有十场,其中在第九场中安排哲而治的妹妹凯西逃跑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回来刺死了奴隶主李格利。第十场安排一群逃到加拿大的汤姆的好友,讨论和评价汤姆的愚忠和他死亡的价值,进而展望黑人的命运及黑人运动的前途。后来刊发的单行本和戏剧的演出中,第九、十场全部删除,重新增加汤姆临死前壮烈的场面为第九场并作结局。欧阳予倩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杀死一个李格利,还有许许多多的李格利存在,黑奴实在是无处可逃的。与其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作为结尾,不如直接删除。以汤姆之死作结,更能激起黑奴们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欲望。欧阳予倩改编《黑奴恨》呼应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力。
(二)《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就其接受视角而言,经历了由政治对话到文化对话再到文学对话的嬗变。
1.政治对话。20世纪80年代之前,《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视角主要是以政治对话为主。在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目的性比较强。《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和控诉了蓄奴制,其政治内容在斯托夫人的叙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作者心目中的读者不是某些人,而是所有美国公民。例如她在文中说:“南方那些思想高尚、胸襟宽广的男女同胞”,“马萨诸塞、新罕布尔什、佛蒙特和康涅狄格各州的农民……纽约勇敢而慷慨的人们……还有你们,美国的母亲们。”[7]85斯托夫人以先知者的方式直接对读者讲话,或规劝、或赞扬、或谴责、或警告。她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借助小说对美国社会宣扬她的政治理想,以期影响美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斯托夫人在原作中表达的废除奴隶制、要求种族平等政治理想,与林纾渴望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形成强烈的共鸣,以致达到他在译述过程中“且译且泣”状态。林纾在《黑奴吁天录》“序”中说:“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迩又寖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譬喻;而倾心彼疾者,又误信西人待其藩属,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12]2在“例言”中,林纾又说:“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秘鲁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证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视之,幸甚!”[12]6林纾在“跋”中再次表明:“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12]45由此可见,出于爱国的拳拳之心,林纾希望通过翻译斯托夫人的这部小说,敲响国人亡国的警钟,唤醒民众沉寂的心灵。恰逢其时,旅美华工在美受到迫害,小说的出版很快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
《黑奴恨》的改编同样也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高潮。而在黑人的解放运动中,一方面,美国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变本加厉,充分暴露其反动嘴脸;另一方面,美国对黑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唤醒了广大黑人的觉醒,激起了他们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黑奴恨》的改编,是对黑人解放运动的有力支持,作者希望用艺术的形式传达政治的思想。
2.文化对话。政治对话的基础是文化心理。有什么样文化心理,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对话。但文化对话比政治对话的领域远为广阔与隐蔽。在文化对话领域,文学翻译表现出翻译界通常所说的“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所谓“归化”,就是原作所描写的异域社会生活与翻译者本土社会生活在文化基本价值观念大致一致、基本切合的情况下,让原作中的生活尽量向译者本土社会文化背景靠拢,从而达到中外艺术生活世界在文化观念上的相接近,为本土读者顺利接受。所谓“异化”,就是原作所描写的生活,其价值观念与本土生活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或相冲突,而原作中的文化观念可以对本土社会生活起到“移风易俗”的进化作用。这时,翻译者则尽量让域外文化精神切入作品,实现对读者思想意识与审美趣味潜移默化式的改变。上述林纾在译述《黑奴吁天录》时,有意淡化小说中女性启人救世情节而把原作中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尽力“儒家化”,就是成功的例子。当然,“归化”与“异化”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超出社会读者当前的文化心理承受能力。林纾曾经在翻译《迦茵小传》时,把女主人公迦茵未婚先孕的故事忠实译出,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事例。因此,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对话”,从翻译角度看,就是“归化”与“异化”在读者文化心理承受范围内的巧妙处理。
3.文学对话。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接受视角开始由政治对话逐渐转移到文学对话上来。董衡巽主编的《美国文学简史》就对这部小说作了较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指出“它的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所以在创作方法上也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突破了在小说方面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传统……不失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内战后现实主义小说运动的前驱。”[3]272黄继忠在《汤姆大伯的小屋》译文的前言中对小说的文学价值做了特别的论证。黄继忠肯定了爱德华·威尔逊的观点:“《汤姆大伯的小屋》尽管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另外,在前言中,黄继忠还对全书的结构布局和人物形象塑造进行点评,指出作品的布局“颇具匠心”,汤姆的形象“读来有血有肉,感人至深”。黄继忠既有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有对小说缺陷的批评,比如作品宗教色彩“太浓,对小说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有损”;作品中两条主线轻重不一,“汤姆这条线索比较充实、真切,而乔治、伊莱扎夫妇这条线索相对比较简略,显得单薄”[7]36。学术界通常把黄继忠的《前言》看做是国内第一篇从思想特征到艺术手法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对于该小说的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后,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文学价值进行分析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文章分别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的艺术特色以及小说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文学评价,详细阐释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文学性。
三、结束语
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百年间的传播与接受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文学传播——接受的基本规律: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信息的传递规律大致由外而内、由内涵而形式,即从外在功利性的政治——社会内涵,深化到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文化层面,最后再扩展到艺术欣赏与借鉴范围。“对话”中的“误读”,“误读”中的接受,源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取决于接受方当下的社会与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于是,具体译述过程中巧妙处理“归化”与“异化”的辩证关系,是文学交流的关键。《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总结其传播与接受的规律,对于当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