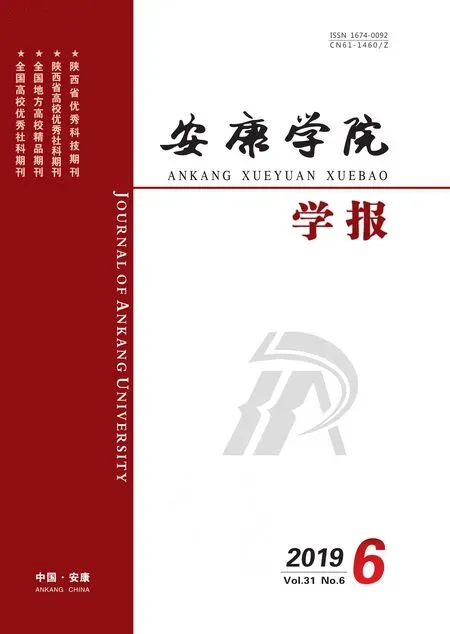人存在的精神困境与出路
——对《一句顶一万句》的再解读
秦佩佩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在《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里,刘震云从最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出发,洞察着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危机。小说中,每个人无一不是些“小人物”,他们的生活无比琐碎,但就是这些每日在琐碎中过着日子的人,也都有着无法逃离的精神负重。小说围绕着“说”和“话”来组织着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让每个人都被“说”死死地纠缠。而一系列密切关乎人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叙述环境中,被一一有条不紊地铺展开来。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倾注了刘震云对人本身存在的极大关怀。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该小说中展现的人的存在困境及其出路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真相
(一)难以消解的“交流冲突”
《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反复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他道出了人存在的必然,那便是对交流的倚靠,即希望在交流中,通过他人看我之所是,来认识自我的存在,证明我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不在渴求着遇到那个“说得着”的人。然而,“说不着”才是人与人之间最为普遍的交流状态,所以小说中的众人都在经受着没有“说得着”的人而带来的精神苦痛。
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说不着”,而这种“说不着”的背后,展现出来的最大冲突点,便是“把一个人说成了另外一个人”。小说中的剃头匠老裴,因为老婆老蔡信口胡说他与他姐一块下流而光了火,动手打了老蔡,在这事上,老裴本也是占着理的,但老蔡的娘家哥绕来绕去,把老裴扯成了他娘,硬是顺理成章地把老裴说成了“不讲理”的。老蔡娘家哥还不肯罢休,把老裴他姐年轻时的事、老裴在内蒙古的事扯一块,硬是把老裴说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老裴“怒从心头起,拿起砍刀,就要杀人,但不是要杀老蔡,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也不是要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的这些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1]21。从这里可以看出,被说成了“另外一个人”,成了人与人交流冲突的爆发点,也形成了人在交流过程中最大的精神负重。
萨特说:“我对他人的认识,是他人在我的经验中的显现,通过手势、表情、活动和行为等有组织的形式的在场表露出来。他人的情感是出现在他的内感觉中的,我根本察觉不到,而这就造成了意义:它需要我在我的经验中以表情或手势等概念把握一系列的现象”[2]。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冲突的。而《一句顶一万》就展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冲突性的本质状态。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隔”在生活的各处都普遍存在着。教书先生老汪,读孔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潸然泪下,他感慨孔子也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而伤了心,但学生没一个懂他。而县长小韩去学堂演讲,本是为了救国救民,但省长老费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五十年固守一句话就不错了;他半年讲了六十二场话,能是做县长的材料”[1]51。如此种种的交流冲突无不显示着与他人交际的困难以及人际关系的险恶。所以,当人要从与他人的交际中收获存在的意义时,孤独和痛苦只会如影相随,而这正是小说中众人难以逃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二)难以排解的“认知冲突”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除了不断论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冲突外,还深刻地刻画了人与人关系中的认知冲突。像小说中的杨百顺和银匠老高,杨百顺认为老高能把乱七八糟的事码放整齐,能帮自己排解,是个能说窝心事的人,所以把老高当作了好朋友。可曾想,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好碰上了自己老婆吴香香和老高的幽会,杨百顺才终于知道,自己心里念着的好朋友却处处想致自己于死地。如此的情节安排,固然能看出人本身是个复杂的存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人根本无法通过日常的现象捕捉就形成对他人的最确切的认知,从而真正地进入他人的内部。人和人之间总是有那么一道“墙”,让人无法跨越。
小说中,杨百业的爹老杨本想捡个便宜,乘机傍上大户人家才去老秦家提的亲,可当他见着了大户人家的贵气,又失了胆,急急忙忙地想道出自家的实情以求赶紧脱身。可老秦的女儿秦曼卿却认为:“如果换个人家来提亲,肯定句句说的是自家的好;杨大爷自打进门,处处说自家的不是。这样的人家,世上也算是难寻了”[1]83。此处歪打正着,老杨是为自己的小算盘心虚,秦曼卿却认定了这是贫苦人家的实诚。再加之秦曼卿还曾遇见过杨百业卖豆腐,别人买三斤豆腐,杨百业却给人称了三斤三两,所以她就更加断定这是户好人家了。可是,杨百业之所以多给人豆腐,只是为了借豆腐发泄对老杨的不满罢了。而秦曼卿之所以坚持要嫁去杨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秦曼卿明清小说看得多,看到许多富贵家女子,因种种事由婚姻发生变故,困顿之时,遂立志下嫁,有嫁给卖油郎的,有嫁给砍柴人的,甚至有嫁给乞丐者,后来皆有好的结局”[1]80。秦曼卿对杨家的认知不过是建立在自己捕获到的二三现象之上,而她对自己婚姻下的判断,也不过是从明清小说中获得的经验认知罢了。于是,小说中写道,结婚那日,当秦曼卿真正来到了杨家,见到了杨家的贫穷脏乱,以及跑起来像个笨拙的猴子一样的杨百业,才终于明白自己原有的那些认知是大错特错了。
秦曼卿的故事,在小说中看起来戏谑,但细想之却惊心动魄。毕竟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又有谁能跳出现象的制约,直达他人的真实存在呢?秦曼卿仅捕获二三现象便将自己的一生草草托付,可即使对他人的认知足够多,就敢说对他人全然的了解吗?秦曼卿是被明清小说里的爱情传奇耽误了终身,但所有的人不都是如秦曼卿一样,是在用自己所固有的经验认知来对眼下的生活做着决定吗?人总难跳出与他人关系的困局,也难以摆脱印象式经验的控制。这样的书写不禁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人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二、安放精神苦痛的生存选择
当“说不着”成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最普遍状态,并且认知的冲突总是无处不在时,如此的生存困境就意味着自我存在意义的缺失,它所造就的是人内心最大的孤独与痛苦。为了逃离生活中自我存在得不到他人确认而致的精神苦痛,小说中的人物们出现了几类相似的生存选择。
(一)喜虚不喜实——自我“存在”确认的“隐遁”
小说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总是不断强调自己喜虚不喜实。杨百顺就说自己喜虚,所以他喜欢罗长礼喊丧以及舞社火。当杨百顺想去舞社火时,小说就曾说道:“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1]165。杨百顺一生都钟情于罗长礼喊丧,甚至最后还将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罗长礼。而小说中除了杨百顺以外,杨百利、县长老史、破竹子的老鲁无一不有着喜虚不喜实的内心剖白。
总的来说,小说中的人物所喜欢的“虚”都有一个特点,那便是把自己放置在了另一种身份之中。比如杨百顺所喜欢的喊丧,对于其所具有的特征,就有人曾经论述到:“一方面是借用死者的权威和恐惧,利用鬼魂的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规划和构建亲属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喊丧的人却有一种他者的地位,他几乎灵魂出窍,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指使别人来到死者面前,而他超然于死者的权威之外”[3]。也就是说,喊丧者在喊丧的过程中扮演的根本不是他自己,他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隐藏,将自己完全置于一个与他本身无关的他者身份之中。
小说中的县长老史也是如此。老史喜欢听戏,喜欢舞台上的人连说带唱,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人扮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老史在和男旦苏小宝手谈之时,定会要求苏小宝不能卸了戏装和脸上的油彩。老史无论是在听戏还是手谈,最享受的就是把自己扮成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戏中之人,与老史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破竹子的老鲁更是如此,他喜欢在自己脑子里走戏,会随着戏在那里摇头晃脑、挤眉弄眼,在旁人看来还以为他犯了癫痫病。走戏时,老鲁自个儿沉迷于脑中的锣鼓喧天之中,也是把自己扮成了那戏中之人了。
而杨百利的喷空,更是虚之又虚。小说中解释道:“所谓的喷空,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1]53说白了,喷空就是任意天马行空地编故事,它意味着人不受任何观念、常识、道德评判等的限制,无限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就是由于喷空的自由,才把人从本身的不自由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在喷空的过程中,喷空的人享受着的也是对自我不自由身份的逃离。
如此看来,这些厌倦于与他人交流但仍经受着精神苦痛折磨的人,在虚中搁浅了孤独,获得了安慰。而这“虚”的生存要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呢?胡塞尔所提出的“悬搁”的概念,或许对此有些启发,因为它意味着将存在置于虚无之中,即当存在被“悬搁”,只要不产生意向性活动,用自我意识将虚无填充,存在就会面临意义的缺失,实现它自己的隐藏。小说中的虚便是如此。虚带给了他们另外一种身份,无论是喊丧者,还是戏中人,都与他们自我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牵连。这种身份的置换,使其从自我的真实存在中逃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他者身份的空间。当人们处在他者身份时,所有的意识都指向这个身份,又由于他者身份与自我存在的毫无相关性,所以这些意识都无法到达真实的自我存在,于是“我”被“悬搁”了,置于一片虚无之中,实现了自我存在的隐藏。也是因为如此,“我”把自己推入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再没有人会对“我”的真实存在进行意义的判定,“我”从交流的冲突中超脱了出来,孤独感便也被冲刷了干净。所以小说中的杨百顺,在真实的生活中唯唯诺诺,但舞起社火扮起阎罗来,“有些憨厚,又有些调皮;有些羞涩,又有些开朗;提肩掀胯,一颦一笑,他不像阎罗,倒像潘安呀”[1]123。
(二)与动物为伴——自我“存在”确认的“转移”
为了排解交流及认知冲突所带来的精神苦痛,小说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生存选择——与动物为伴。如开染坊的老蒋,不喜欢跟人交往,却喜欢养猴子。而他就是因为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才喜欢猴子的。蒋家院里有棵枣树,那猴子经常窜到枣树上晃,晃下一地的青枣。这青枣要是被人晃下来的,老蒋马上会急,但是是猴子,他只是摇头笑笑。老蒋对人苛刻,但对猴宠溺,生活中更是不能缺了猴的陪伴。在小说的下部,牛爱国遇见的汽修厂的老马,也是不招惹人,只玩猴。对于老蒋和老马的描写,小说除了写他们以猴为伴之外,还交代了另外的细节。如老蒋,年轻时爱说话,五十岁之后突然不爱说话了,然后就养了只猴伴在左右;而老马,也是因为在与人交往中伤了心,才离开了家,每日与猴戏耍。
从老蒋和老马的经历来看,两人都是因为不想再与人交际后,才选择与猴为伴。交际是人的必须,是人自身存在和意义的需要,当与人交际只会不断招致交流和认知冲突并最终造成难以承受的精神重负时,动物的陪伴便成了人寻求意义的替代品。人转至与动物的交流来重获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安抚了人因为缺少“说得着”的人而带来的心灵躁动。
三、直面生存的精神困境,把路指向远方
小说中那些经受过“说不着”而内心无比孤独和痛苦的人,往往终其一生,要么独自一人小心地舔舐着“不杀人,就放火”的精神苦痛,要么干脆把自己放逐在人际交往之外,或沉溺于“虚空”之下,或终日只与动物为伴。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存在选择,他们都永远地将自己禁锢在了生存的精神苦痛所铸就的牢笼之中,只不过前者是终日备受煎熬,后者则是“闭耳塞听”暂时寻得了精神苦痛的安放,他们都不敢在寻找的路上再迈出一步了。这些人是整部小说中的众生相,他们鲜活且不乏深刻,然而,却绝非作者理想的生存出路,因为到了小说的下部,在对牛爱国的刻画上,刘震云进行了突破性的书写。
牛爱国的前半辈子,无疑就是对其“姥爷”杨百顺的重复,一样地经历过和朋友、家人、妻子的“说不着”,甚至也同样地经历过妻子的背叛。他也深深地体会过“说不着”带来的“不杀人,我就放火”的狠绝心境。然而,与老汪、杨百顺一类的终生放弃追寻那个“说得着”的人不同,牛爱国在小说的结尾,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自己的选择:“不,得找”。而对于牛爱国最终做出的不一样选择,小说中出现过两处铺垫,刘震云让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牵连的人,却对着同一个人(牛爱国),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警语——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当牛爱国深陷妻子与人私奔的往事而不能自拔时,他就从母亲曹青娥的劝慰中听到了这句话。而后,牛爱国为了寻得罗长礼(杨百顺)生前想对巧玲说的那句话,来到了罗长礼的家。当罗长礼的孙儿媳妇何玉芬听完牛爱国的心事后,也是把这句话送给了牛爱国。可以说,对于小说中“以后”和“从前”两个关键词的分析与思考,将成为勘破牛爱国人生分界点的关键所在,同时也能探及作者在面对难以逃离的生存困境时,对突破此困境进而找寻到出路所做的沉思。
小说中的老汪、杨百顺等一系列人物,都因为曾经在“说”上伤过心,便永远地沉浸在这样的过去之中,也就终其一生,不再寻求任何的可能性了。然而牛爱国不同,虽说他也有着解不开的烦闷,也苦恼着“说不着”,但当他决定一定要去找章楚红,把自己的那句话告诉她时,牛爱国就已经跳出了小说中众人的生命常态。牛爱国其实已经想到了自己伤了章楚红的心,即使找到了章楚红要对他说的那句话也已经变了味,但他仍旧选择要摆脱以前那个胆小的自己,大胆地去追寻,去过自己的“将来”。小说用牛爱国的选择把生存的出路指向了将来。
有了以上的分析和理解,再回过头来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整体结构进行思考,我们就能发现,其结构原来也暗含深意,而且深意之处正是通向那条作者精心铺设的生存之路。小说分成了上下两部,无论从标题“出延津记”“回延津记”,还是从小说上下两部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来看,都似乎只意味着命运的重复,从而使人看到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困境。然而,从作品中“以后”和“从前”这两个关键词对我们的提醒来看,上部的“出延津记”是在过“从前”,它更像是一部“过去史”,因为它记录的是杨百顺等一类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精神苦痛,而这种苦痛就是过去给他们造成的。但到了下部,当小说在牛爱国“得找”中戛然而止时,“以后”这一关键词便于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牛爱国的选择,并把小说下部的时间向标指向了将来。牛爱国去找章楚红,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可能找到了发现也“说不着”了,但是牛爱国的确为自己寻求了变化,做出了选择。牛爱国毫不犹豫地走向了自己的将来和不确定的可能性。如此一分析,便知晓小说最后通过牛爱国的寻找,使其整体结构突破了一种死气沉沉的重复和循环,它意味着的是新的超越,是人生存的新出路。
总的来说,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对人的存在的确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小说中,每个人都渴求着交流,可人与人之间交流及认知的冲突本质,导致了交流的必然失败,而这交流的失败,加重了人的精神负重,让人不断地在人际网中辗转奔逃。人存在的本质意味着获取自我意义确认的难寻,然而刘震云依旧倚靠着小说下部的主人公,道出了他对人存在出路的希冀,那便是直面精神的苦痛,不断并且勇敢地追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