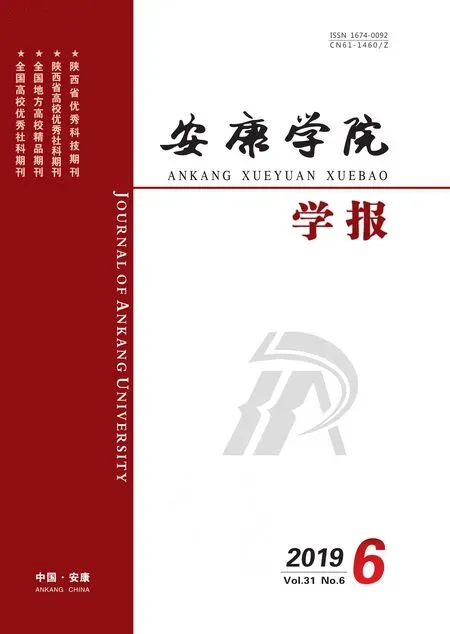冯延巳词的江南地理空间建构
何 慧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冯延巳(903—960),字中正,五代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人,南唐词人,有词集《阳春集》传世,陈世修在《阳春集序》中评道:“观其思深辞丽,均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1]。其词多描写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或借春闺思情表达愁苦之绪。在词作风格上,超越了花间词的奢靡之音,表现出深美闳约、含蓄深厚的艺术特征,并且影响着后世欧阳修、晏殊等人的创作,为宋初词坛树立了典范。本文以文学地理学为研究方法,分析冯延巳词中所反映的江南地理风物的特征,以及冯词所建构的江南地理空间对于江南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文学地理学概述
文学地理学旨在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主要的研究任务是“通过文学家(以及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景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2]。
文学与地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世界,创作者创作风格的形成受到其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作品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镜”和表现主观世界的“灯”,是外在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与创作者的审美理想与情感倾向的融合共生。“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3]
二、江南地理文化对冯延巳创作的影响
冯延巳生于扬州、长于扬州,其一生生活的区域集中于扬州和金陵一带,即具有典型南方地域风格的江南地区。南方气候温和、湿润多雨,形成了温柔静雅、清秀婉约的地域风格。江南,作为南方地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山水胜地和人文精神中心,其本身所具有的深厚文化思想和人文精神内涵,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政治—伦理型话语不同,它最突出、最重要的维度是审美。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与江南之山水形胜有着天然的联系。”[4]江南的秀丽风光形成了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而江南文化的审美精神又为江南的风景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光辉和色彩。江南的山川河流,不仅是单纯的自然风景,更是中国审美和抒情传统的符号性象征。
江南的自然风景和人文精神影响着冯延巳的创作,与花间词的浓妆艳抹不同,冯延巳的词是精美婉约的,其词描绘的江南景物,透露出一种江南士人的清丽隽永和南唐贵族的文雅深厚。对于江南景物的描绘方式和在其中所倾注的哲理思想,形成了其“堂庑特大”的词作风格。“堂庑特大”者,是指冯延巳词在意蕴上表达了一种深广的人生哲理和忧患意识。冯延巳在词中书写的景物或情感,实则是其对于人生无常和世事难料的感叹,在对江南景物的描绘过程中,融入了词人的人生感慨和思想情怀,具有深刻的哲理思考,表现了南唐五代士大夫普遍的忧患意识。王国维称其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5]5。正是因其词表面上是对于景物、事件和情感的描绘,实质上是表达了深层的思想意蕴,为宋代词坛树立了典范,给后代读者以无穷的思考和阐释的空间。
三、冯延巳对江南地理空间的建构
冯延巳在受到江南浓厚的地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影响。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发展,而是一个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冯延巳在词中所描写的江南风光与景物,不仅是对当时江南地理环境的反映,更是表达了词人主观情感倾向和审美趣味的艺术想象空间;不仅是江南地理空间的体现,更是南唐五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感情在江南地理上的特殊反映。冯延巳书写的是士大夫阶层独特的心灵感受,构建的是南唐五代时期的江南地理环境,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双重意义。
(一)月影下重帘,轻风花满檐——浓丽易逝的江南繁花
冯延巳笔下的江南繁花笼罩着词人的忧生之叹,不仅是词人个人的离愁别绪,更代表了南唐五代时期士大夫普遍的悲哀情怀,对生命无常的悲哀。如《鹊踏枝》: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6]85
陈秋帆先生评论此词“愁苦哀伤之致动于中”[7];陈廷焯评价此词“貌不深而意深”[8];王鹏运评价此词“郁伊侊倘”[9]。冯延巳在此词中借江南落花发端起兴,寄托词人幽深的情怀。落花飞舞,犹自多情,一个“犹”字将“落花”与“多情”联系了起来,落花带上了人的感情与思想。落花为何多情、如何多情,是对于生命的不舍与眷恋,亦是对于自己一生短促、好景不长的感慨。“学雪随风转”,随风飞舞,随风飘散,是落花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但落花即使是走到生命的尽头,仍然以最美丽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或是保持生命最后的尊严,或是享受最后的欢乐。叶嘉莹先生在评价此词时,点出发端三句“写出了所有有情之生命面临无常之际的缱绻哀伤,这正是人世千古共同的悲哀”[10],有情生命面临无常之际,这是落花的写照,更是南唐五代时期江南无数文人墨客,抑或是所有有情之人的真实写照。时局动荡,士大夫所依附的政权实力弱小,所仰仗的君主整日只懂花前月下、吟诗作对,个人在动荡的时局面前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随时都有可能随风飘逝,那这时候能做的也只有“学雪随风转”,保持生命的庄重与尊严,或是秉烛夜游,放荡不羁地享受生命最后的时光。这是南唐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在五代十国动荡的时局面前,保住尊严和享有生命,做不了平定动乱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就做一个真性情的文人。
此时的江南落花已经点染上了词人的愁情。落英缤纷,美好的生命随风消逝,越是美艳动人就越是脆弱,词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和世事的无常,此为第一愁也。“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繁花散落之时,词人想到的是昨夜的高朋宴饮、美酒佳肴、欢声笑语,然而相聚的欢乐如同美丽的繁花一般都不会长久。酒醉醒来之时,欢乐已然散去,只剩下孤独与惆怅。由繁花想到宴饮,想到相聚必定与分离相连,南唐宫廷贵族的欢声笑语不过是一时的迷梦而已,梦醒之后,面临的仍然是南唐五代战火纷飞的现实。宴饮时的欢乐与酒醒后的惆怅相连,巨大的反差形成一种强烈的艺术张力,人们无法留住欢乐,对于往昔留恋不舍,对于未来担忧恐惧,此为第二愁也。“楼上春山寒四面”,寒山四面,形成的是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仿佛冻结住了所有的欢乐,寒冷的天气,寒冷的心情,如黑云一般步步逼近。同时,此句也直接使用了中书舍人潘佑曾讽刺后主李煜的诗句,“楼上春山寒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春风一半”[11],批评后主在丧失南唐江淮大片领土之后仍旧沉醉于纸醉金迷的奢侈腐败的享乐生活当中。“寒山四面”不仅是词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惋叹,更是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南唐五代的“无常之际”更多的来自军阀混战,国家尚且朝不保夕,更何况是个人的生死命运。词人的命运如同繁花,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时代之风而飘散,此为第三愁也。
全词以“落花”起兴发端,由“落花”想到的悲哀愁苦之情统摄全篇,“落花”这一意象不仅是江南地理景物的再现,更倾注了词人对于生命无常、人生难测的悲哀和恐惧之情,融入了南唐五代时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忧世情怀,具有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双重意义。
冯延巳所建构的江南落花是浓丽美艳的,但也是易逝易老的,折射了词人身处南唐弱国的悲哀。这种美丽易逝的落花正象征着南唐朝廷,南唐坐拥江南经济文化繁荣地带,物资富饶,文化深厚,但是却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可以抗衡外敌入侵的军事实力,国家随时面临灭亡的命运,似繁花一般,由始至终都逃脱不了被东风摧残的结局。词人是敏感的,他看到了南唐的奢侈腐败,也看到了其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因此,冯延巳词中的江南繁花这一地理空间物象的建构,表达的是其对于自身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于存在与消亡的深切思考。
(二)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悲啭缠绵的江南烟雨
江南湿润多雨,形成了温柔婉约的审美风尚,不同于北方豪迈阳刚的自然环境,江南的一切在烟雨的笼罩中显得柔美细腻,在水中浸润的文化,如水一般灵动自然,柔顺缠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雨色空濛,江南的文化温柔如水。冯延巳在词中的建构的江南地理空间也少不了江南的烟雨。江南柔媚细腻的自然景观为冯词增添了美感的特质,冯延巳笔下风情万种的江南地理空间成就了南唐时期独具一格的江南文化。
江南的烟雨是朦胧的,冯延巳借江南迷濛的烟雨表达一种悲哀之情,使这份朦胧之中有了哀伤情调的点染,江南烟雨不仅是景,更加是情。如《南乡子》: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6]125
此词为闺思怀人之作,“芳草年年与恨长”,点明了全词的感情基调,“恨”既在“细雨”的环境中孕育,又在“细雨”的氛围下愈来愈深。王国维称此词,“人知和靖《点绛唇》、梅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由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也”[5]6,而“春草之魂”便是“恨”的惆怅之情。“烟锁凤楼无限事”,“凤楼”是古都的美称,这里指代金陵,烟雨笼罩着金陵古城,少女心事重重。“茫茫”,既是对烟雨迷濛的环境的书写,也是对女子心思茫然,不知所措的细致刻画,烟雨笼罩的不仅是金陵古城,更是女子愁重难解的内心。魂梦悠扬,杨花满床,都在烟雨的环境中,渲染上了一层惆怅的情绪。全词以“细雨”开端,以“细雨”关联全篇,无处不在。“摄春草之魂”,女子的悲愁被细雨打湿,在烟雨中如春草一般滋生蔓长,烟雨象征了其愁绪的纷繁错乱与凝重难解。
冯延巳笔下的烟雨是朦胧的,在细雨中的人事物也带上了迷离的色彩。冯延巳的闺怨词不同于花间词派的闺怨词,冯词侧重于描写闺中女子思妇的情感,而很少有容貌服饰的描写。“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只着一“泪”字,便将词中女子惆怅的神态与寂寞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斜阳”“残春”渲染出衰残破败的景象,在这样的烟雨中,女子的形象是模糊的,情感是真实显现的,冯词侧重描写情感,不刻意于累赘的外貌描写,清丽真实的风格,引起世人的共鸣,这种感情融注着江南的烟雨,在景色的衬托下,愈加细腻缠绵。
(三)夜深寒不彻,凝恨何曾歇——凄寒彻骨的江南气温
冯延巳词中有大量寒冷的意象,虽说江南四季不都是寒冷的,但词人敏感的心灵容易感受到气温的变化,即使是温暖的春天,词人的内心依旧乍暖还寒。这种寒冷,似乎与现实当中温暖明媚的江南地理气候不相符,但考虑到南唐朝廷飘摇动荡的命运和冯延巳忧生伤时之心,于是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了。如《临江仙》: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画楼帘幕卷轻寒。酒余人散后,独自凭栏杆。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裴回飞尽碧天云。凤笙何处,明月照黄昏。[6]109
桃花片片飞舞,说明已经是暮春时节,词中春末夏初的时节,气温依旧寒冷,“冷红”一词不仅描绘出自然的温度,更反映了词人内心的温度,冷得让人心痛,因桃花飞逝而冷,因自身漂泊在外而冷。飞花轻寒,青春衰落,桃花越是红得艳丽,越能衬托出词人内心的悲哀,“画楼帘幕卷轻寒”,画楼上的帘幕似乎也带着寒气,一片凄凉之境、悲愁之态。酒余人散,本已心生寒意,独自凭栏,寒意倍增,这种寒冷是晚风带来的,也是因孤独无人依傍的寂寞愁苦带来的。夕阳西下,萋萋芳草,残败与衰落之时想起王孙,想起故国,倍感凄凉。“徘徊飞尽”,正是词人孤独一人,无依无靠的写照。
全词以“冷红”一词起兴,不仅有温度上的表达,更有颜色上的冲击,“冷”与“红”的相互组合,使人印象深刻。虽然花是明艳美丽的,但是周围的环境和词人的心情却是寒冷彻骨的,“红”代表热情和温暖,象征春天的美好,但“冷”字却彻底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给人强烈的反差,而正是这两个反差极大的词语的组合搭配,才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和冲击。寒冷笼罩全篇,无论是帘幕的轻寒、独自凭栏的孤寒、夕阳西下的残寒、想念王孙的哀寒,都由“冷红”而起,由“冷红”而生,处处透露着寒冷与衰败的无尽忧伤。
四、江南诗性文化的书写与回归
在中国诗学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话语体系,即现实叙事的话语体系和浪漫抒情的话语体系。前者以《诗经》为代表,《诗经》的出现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后者以南方楚辞《离骚》为代表,《离骚》开启了我国浪漫主义书写个人情怀的先河。江南具有典型的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其在文学上的成就,继承了《离骚》开启的南方浪漫抒情的传统。
江南文化底蕴深厚,但在北方政权强大之时一直沉沦,直到魏晋士人的出现,江南清新秀丽的气质才再次得以展现。至安史之乱,唐王朝中央集权遭到破坏,政权混乱,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征战不断,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与文化的南移。江南成为文人向往的净土,成为文人心灵栖息的家园,以江南为文化中心、以《离骚》为代表的南方抒情文学传统得到回归与彰显。江南人杰地灵,南唐中后二主和冯延巳都有高超的文采诗性,艺术才情飞扬,都代表着一种自由的审美精神。同时,江南气候温暖、山明水秀、意蕴深厚,这样的诗性江南影响着冯延巳的创作,而冯延巳的词所建构的江南地理空间,成为南唐时期的江南所特有的地理空间,因时因地而制。南唐五代时期的江南,落花是浓丽易逝的,烟雨是惆怅深重的,四季是寒冷彻骨的,这是现实的江南风物和词人心灵共同建构的地理空间,成为江南文化与中国古典诗词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冯延巳词中的江南地理空间,在景物的书写中融注着个人的感情,并且这种感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其所表达的情感并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融入了时代的特征,抒发的是动荡时局中世人哀伤愁苦的情怀,是中国古典诗词“诗言志”传统的回归。
冯延巳所建构的江南地理空间,不仅向着中国审美抒情传统回归,更影响着宋初词人的创作。王国维肯定了冯延巳的词史地位,称其“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清代刘熙载在其《艺概》中评曰:“温飞卿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已、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12]。冯词中的“俊”与“深”影响着晏殊与欧阳修,“俊”来自江南水乡温柔秀丽的气质,是明丽俊朗的山水塑造了冯词流丽明快的创作风貌;“深”来自南唐的动乱,整个时代的不安与忧患,塑造了词人幽深的哲理思想和忧时伤世的情怀。二者的结合正是冯延巳笔下所建构的南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地理空间。
总之,冯延巳以其独抒性灵的词作风格构建了江南地理空间,是江南风物的诗意再现,实现了对江南真实地理空间的超越。冯延巳所建构的江南地理空间,是现实景物和词人审美理想、审美品格的融合,实现了江南诗性文化传统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