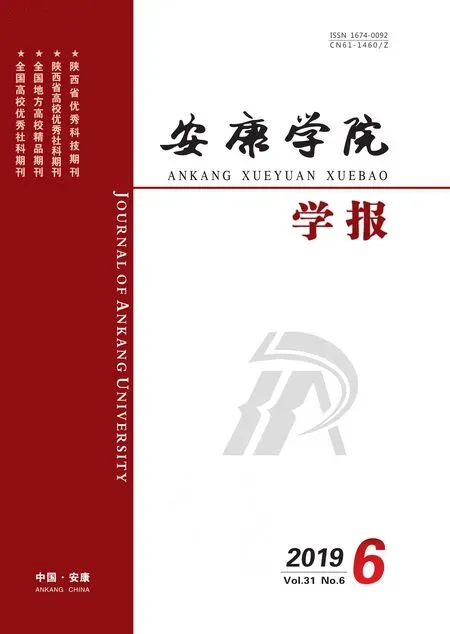潘岳《西征赋》创作心态探究
赵莹莹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1]700,“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1]135-136,对《西征赋》很是推赏。潘岳按照传统纪行赋“因地怀古”的写作模式有条不紊地展开篇章,勾连时间和空间、历史与现实,将所经地域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典故融注于笔端,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所思所感,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全赋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情感深沉、结构精巧,被视为潘岳才情的集中体现,也被认为是将纪行赋推向高峰的优秀之作。
《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2]张伯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认为:“如果我们对作品的产生背景以及作者的心理状态缺乏深切的认识和体会,甚至拒绝加以认识和体会的话,那么,在对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就往往会导致随心所欲、自说自话,其对作品所评定的价值也就会因为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而失去意义。”[3]他指出了结合历史史实对作家创作心态、作品产生背景进行探析的必要性。《西征赋》洋洋洒洒四千余字,从夏朝直写到西晋,涉及的人事历史众多,头绪纷繁复杂。通过对潘岳创作心态进行探析,可以深入了解赋的写作背景、作者的写作意图,以便更好地理解赋的行文安排和作者引经据典的深层用意。同时,潘岳作为西晋时期的典型文人,他坎坷的仕途经历很具有代表性,同时代很多文人也有类似的体验,所以对《西征赋》创作心态进行探析也为解读西晋文人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角度。本文拟从潘岳的仕宦经历入手,结合西晋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赋作具体内容来探讨潘岳的创作心态,以期更深入地解读这篇纪行大赋,进而对潘岳其人有更精准的把握,对于了解西晋同时文人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心理感受与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飘萍浮而蓬转”——仕宦有感
《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4]1500潘岳少有才名,又有魏晋人偏爱的俊秀姿容,具备一定的出身条件,这种环境很容易激发潘岳从政的自信与热情。潘岳于晋武帝泰始二年弱冠之时入仕,春风得意,高步一时,泰始四年一篇《籍田赋》更是令其声名鹊起,一鸣惊人。《晋书》本传在注引《籍田赋》之后说:“岳才名冠世,为众所嫉,遂栖迟十年。”[4]1502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露才扬己招来众人的嫉妒,不得已栖迟十年,虽然潘岳仕途起步顺畅,但是过程坎坷。晋武帝咸宁二年,潘岳为贾充太尉掾,逐渐为贾充所赏识,贾充在当时属于党争的一方,另一方有山涛、庾纯、任恺等人。西晋政权取之不义,便立身不稳,于是统治者在一些矛盾的处理上就面临尴尬境地,这些矛盾中最为突出、与文士命运联系最密切的一种就是党争。从西晋建立之初,两派势力相争的问题就十分严峻,司马氏既需要作为心腹的贾充一党,又需要山涛等名士们的声望维护其统治,于是西晋初期的政局就一直维持着两党相互倾轧的局面。朝中党争会对士人心态造成影响,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指出:“政局中耻尚失所,政失准的的局面,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失去士人心中用以行事立身的凝聚力”[5]。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西晋士人对于皇权的疏离感,从西晋的官吏选拔制度来看,大族家长或是地方长官对士人的出仕有相当重要的决定权,皇权对于士人的统治也需要通过这些大族家长或地方长官实现。所以当时的士人们只有投靠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大族权贵,来实现个人政治理想。潘岳既投靠了贾充一党,那么他的仕途命运也就跟随着贾氏浮沉兴衰。潘岳曾因贾充举荐,举秀才为郎,后来受党争牵连被外调出任河阳县令,虽自负其才郁郁不平,但除题谣阁道发泄不平之外也无能为力。四年后潘岳又被调至离京更远的怀县担任县令,虽勤于政绩,仍沉沦下僚,内心的抑郁压抑可想而知。后调回京城补尚书度支郎,又迁廷尉平,不久又因公事被免,闲居洛阳,但“公事”为何,史书无载。闲居洛阳期间,潘岳作有《狭室赋》来表示自己因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而造成的极度郁闷。
对《西征赋》创作影响最大的一次仕宦体验就是潘岳在杨骏府中任职时,从潘岳任河阳令、怀县令到回京的一段时间里贾充病逝、名士派势力削弱,朝政逐渐为杨骏一族控制。杨骏是晋武帝皇后杨芷的父亲,在晋惠帝元年矫诏辅政,高选佐吏,将潘岳引为主簿,“纳旌弓于铉台,赞庶绩于帝室”[6]1。于是潘岳的命运又和杨骏绑在了一起,后来杨骏被贾后一党诛杀,潘岳身为其党羽也受到牵连,尽管侥幸得免,还是心有余悸,战战兢兢。西晋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场,依附的文人确实如同飘萍转蓬,很容易沦为党争的牺牲品。《西征赋》中有潘岳对以往仕途经历的总结,尤其是直接造成潘岳此次西去长安的“杨骏之祸”,将官场的血腥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他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仕途体验,这次经历对潘岳造成的心理打击在赋中有直接体现。
二、“心战惧以兢悚”——庆幸后怕
晋武帝时期,外戚杨骏被越封为临晋侯,在武帝晚年时期杨骏和两个弟弟独揽大权,史称“三杨”,后于永熙元年五月辅政,权势气焰如日中天。但好景不长,永熙二年便被贾后党所杀。《晋书·杨骏传》中记载杨骏被诛时的情况,“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4]1179。牵连人数之众,情形十分惨烈。《晋书·潘岳传》中记载潘岳侥幸得免的原因为“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玮,谓之假吏,故得免”[4]1504,所以“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心战惧以兢悚,如临深而履薄。夕获归于都外,宵未中而难作。匪择木以棲集,鲜林焚而鸟存”[6]2。这就是潘岳因牵连党争险些丧命的心理体验,既庆幸又后怕。这次经历带给潘岳的冲击远非青壮年时期怀才不遇的情绪可比,关乎生死,更为深沉复杂。尽管潘岳出任长安令时距杨骏被杀已一年有余,但战惧兢悚、临深履薄的恐惧心理在赋中仍清晰明显,可见杨骏事对潘岳的刺激之深。
潘岳在赋的开篇便感叹道:“唯生与位,谓之大宝。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圣智弗能豫。”[6]1“唯生与位,谓之大宝”语出《周易·系辞》,原句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位曰宝。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7]。潘岳化用此句,表示只有生命和禄位是最重要的,全赋也是在此句的统摄下展开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围绕“生”和“位”的问题进行理性思索,探讨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因何得位、如何守位、为何失位。其实“生”和“位”在一定程度上是挂钩的,一着不慎失位也即失命,潘岳在杨骏事件中失了位,但侥幸并未失命,后因“皇恩眷顾”复又得位,经过这一番得失体验,潘岳对“生”和“位”的体验和感悟更加深刻,也把这种自身的感悟和体验贯穿到了赋的行文中。
三、“皇鉴揆余之忠诚”——渴望有为
李善注《文选》引臧荣绪《晋书》曰:“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8]潘岳此次西征是为了出任长安令,在此之前潘岳也任过县令之职。《晋书》本传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4]1502除《晋书》记载的“郁郁不得志”,潘岳本人所作的《河阳县作》《在怀县作》也显示出自己因任小官而郁郁不平的心理状态。《河阳县作》中说:“徒恨良时泰,小人道遂消。”[6]244《在怀县作》中言:“虚薄乏时用,位微名日卑。驱役宰两邑,政绩竟无施。”[6]249潘岳在河阳任上勤于政事,有“河阳一县花”的美誉,但之后不仅没有升官,反被迁到离京更远的怀县出任县令,于是《在怀县作》二首的情绪明显更为低沉郁闷。对比来看,潘岳此次任长安令的心态和前两次完全不同,在杨骏之祸中捡一条命已是万幸,不想竟又被任为长安令,得到了这样的“恩赐”和“施舍”,潘岳此次西任长安令不仅没有表现出外任小官的郁郁不平,还流露出“遭千载之嘉会,皇合德于乾坤。迟秋霜之严威,流春泽之渥恩”[6]2的感激之情。潘岳一方面为仕途不畅险些沦为党争牺牲品感到后怕,一方面又因劫后余生感到庆幸,并且还为得到一次施展才干的机会而踌躇满志,这三种复杂心理体验的交织构成了潘岳西征前的心理基础,在赋的开端就有明确地表示,字字句句都吐露着“命运难卜的焦躁不安,既往反思的忧惧惶恐,托身匪人的懊悔,劫后余生的庆幸”[9]160。
潘岳前两次出任县令有《河阳县作》二首和《在怀县作》二首。在《河阳县作》其一中,潘岳首先对其任河阳令之前的仕宦经历作了简单回顾,虽然中间发了些牢骚,但最后还是落脚到自勉上,“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6]244。《在怀县作》二首也是如此,“对过去仕宦生涯进行总结,然后表示不嫌官职卑微,鼓励自己要勤政爱民,留下美名”[10]。潘岳在人生的转折时期,总结反省过往经历,展望未来,抒发情志,以便更好地看清仕途方向。《西征赋》中也采用了这样的模式,潘岳在“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6]1到“甄大义以明责,反初服于私门”[6]2一部分中回顾了作为此次西行背景的为官经历和心理体验,赋的结尾部分从“尔乃端策拂茵,弹冠振衣”[6]10至“如其礼乐,以俟来哲”[6]11是潘岳对于未来的展望。新沐者弹冠,新浴者振衣,潘岳此时正如新沐新浴者,整装待发、踌躇满志地想要治理好长安这一方土地。同时,这一部分还集中体现了潘岳的施政愿景,表现出潘岳对圣贤仁政的敬佩与向往。虽然长安这个地方情况不太理想,“五方杂会,风流溷淆。惰农好利,不昏作劳。密迩猃狁,戎马生郊”[6]11,有内忧又有外患,但潘岳还是希望通过教化的力量,以上化下,改善民风,并且潘岳有改善当前不良状况的信心,“制者必割,实存操刀”[6]11。他认为只要采用有效的手段,治理得法,就一定能够获得良效。潘岳在赋中一面回顾过去,一面展望未来,对仕途充满了信心。这种踌躇满志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另一方面也是对“皇鉴揆余之忠诚,俄命余以末班”[6]2的感恩报答。
《西征赋》体制规模庞大,记录了潘岳从洛阳出发至长安一路上的所思所感,在赋中他感怀历史,凭吊古今,歌颂明主英才、贤臣良将,批判昏庸暴君、奸臣佞子,对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君臣关系等都进行了理性思考,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分析《西征赋》的怀古内容,归纳《西征赋》的怀古意图,大约也不外于美刺两端。所谓刺,即揭露、抨击历代统治者的昏庸、残暴、荒淫与腐朽,这是其怀古内容中最具进步性的地方,也是作者笔墨用力最多之所在。”[9]161潘岳批判“坐积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6]2的夏桀、“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6]3的项羽、“贪诱赂以卖邻,不及腊而就拘”[6]3的虞公、“加显戮于储贰,绝肌肤而不顾”[6]4的汉武帝、“举伪烽以沮众,淫嬖褒以纵慝”[6]5的周幽王、“倾天下以厚葬”[6]5“俾生埋以报勤”[6]5的秦始皇、“扞矢言而不纳,反推怨以归咎”[6]8的秦昭王……正如潘岳在赋中说“若循环之无赐。”[6]7诚然,历史上许多场景和当时的西晋王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对汉成帝宠信外戚的批判:“张舅氏之奸渐,贻汉宗之倾覆”[6]9,不免使人联想到晋朝贾氏、杨氏两个外戚集团的专权;赵高对秦二世“假谗逆以天权,钳众口而寄坐”[6]8,也和西晋晋惠帝受外戚势力控制的处境类似。所以,潘岳在赋中所感的人事很大程度上带有“以史为鉴”的意味,他是在思考西晋王朝的前途走向,意在提醒统治者避免重蹈覆辙。
创作心态属于作家创作的主观因素,难以揣测完全。本文仅是根据潘岳在赋中的自述、赋作内容、西晋社会政治环境和作者仕途经历等因素,综合推测分析其创作心态。总而言之,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使潘岳在战兢后怕之余又感激涕零,渴望任期内能成就一番作为,这种复杂的感情在《西征赋》行文中确有体现。对潘岳的其他作品如《秋兴赋》 《闲居赋》,或是同时代西晋文人如陆机、左思的作品,也可以采用从创作心态入手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