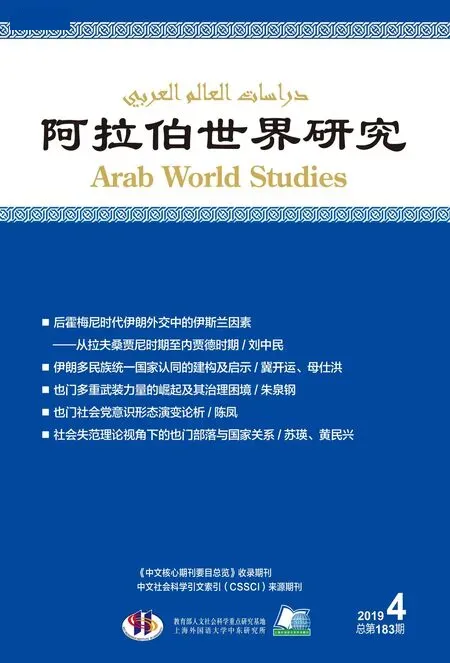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流变*
吕耀军 张红娟
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现代国家建立、伊斯兰复兴、全球化冲击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多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女权主义理论从概念界定到理论渊源经历了各种争论。在对女权主义的界定上,一些学者强调伊斯兰世界不存在女权主义,认为穆斯林妇女为提高权利而开展的活动充其量只能称为“女性主义”[注]Mulki Al-Sharmani, “Islamic Feminism: Transnational and National Reflections,” Approaching Religion, Vol. 4, No. 2, 2014, pp. 83-85.,强调女权主义这一术语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在西方国家对中东实行干预时,经由法国和后来的英国输入到阿拉伯地区的,因而不适用于伊斯兰文化。有的学者则指出,这种对女权主义的否认“忽略了反映当地社会意识形态已然发生变化的事实,如果考虑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化的背景,阿拉伯女权主义可以看作是本土的”[注]Nawar Al-Hassan Golley, “Is Feminism Relevant to Arab Wome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5, No. 3, 2004, p. 529.。尽管学界围绕女权主义的话语存在争议,但穆斯林女性之中确实存在为提高权利而展开的各种行动,女权理论在宗教或世俗的框架中已经被构建,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
本文通过梳理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形成的不同阶段,探讨女权理论历史流变的理论路径与逻辑叙事。鉴于英文著作在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学者或以英文来著述,或其著作和观点被译介成英文;也有一些身处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学者使用英语表达观点,为女性权利而呐喊,以期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本文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英文成果。
一、 19世纪自由主义女权理论的缘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妇女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社会生活,女性权利意识逐渐浮现。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的发展注重女性现实问题的解决,呈现偶发性和松散性特征。在理论上首先关注女性权利的是持改革观点的男性穆斯林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将伊斯兰世界在近代的衰落以及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地区的殖民统治,归因于统治者或宗教保守势力对伊斯兰教的误读。他们将穆斯林女性地位的提高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质疑宗教律法和习俗对穆斯林妇女的约束。当时,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穆斯林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包括妇女的受教育权、性别隔离制度、蒙面纱、一夫多妻制及其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等。持改革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黎巴嫩学者兼作家艾哈迈德·法里斯·希迪亚克(Ahmad Faris al-Shidyaq, 1805~1887)、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里发阿·塔哈塔维(Rifa’ah Rafi’ al-Tahtawī, 1801~1873)、埃及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 Abduh, 1849~1905)等。近代穆斯林改革家只是将女权作为民众参与社会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重以“以道德救赎的语言表达国家复兴计划”[注]Deniz Kandiyoti, “Identity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and the Nation,”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t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79.。通过将早期伊斯兰教描绘为一种理想模式,伊斯兰世界的女权主义由此可溯源至更遥远、更可信的起源,而不是脱离过去,与传统割裂。也有学者试图超越宗教语境,从新的角度探讨女权。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学生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 1865~1908)在《解放妇女》(1899)和《新女性》(1901)两本著作中表达的观点,更多是基于自然权利和社会进步。他认为,如果妇女地位得不到提高,国家就不会发展,因此主张增加女性工作权利,提高女性的法律地位。当时在伊斯兰世界持类似主张的,还包括埃及作家卢特菲·赛义德(Lutfi al-Sayyid, 1872~1963)、伊拉克诗人兼政治家贾米勒·绥德齐·扎哈维(Jameel Sidqi al-Zahawi, 1863~1936)、土耳其作家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 1840~1888)和阿赫梅特·米塔哈特(Ahmet Mithat, 1844~1912)等。
进入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部分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穆斯林妇女首先对深闺制度和蒙面纱表达不满。她们主张女性应识字和受教育,以此摆脱传统陋习的束缚。这种态度的表达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女性已从教育或与欧洲女性的不断接触中获益,本身也受益于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进口车厢、新铁路和轮船在内的现代交通工具,为她们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她们可以去歌剧院,到处旅行,在海边游玩,甚至去欧洲;可以碰到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了解其他文化,有时也有机会参加有关女性的研讨会。”[注]Nawar Al-Hassan Golley, “Is Feminism Relevant to Arab Women?,” p. 533.这种经历激发了部分女性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公开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一些女性尝试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女性权利意识的兴起。城市中生活富足的女性开始走出乏味、受限制的家庭生活,通过成立俱乐部或松散组织来结交志同道合的女性。这种“非正式交往”模式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穆斯林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早期穆斯林女权意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第一,通过诗歌、小说、自传、散文等文学作品以及报刊文章和学术著作,呈现和传播女性意识。如黎巴嫩散文家宰乃卜·法瓦兹(Zainab Fawwaz, 1850~1914)、瓦尔达·雅兹吉(Warda al-Yazigi, 1838~1924)和瓦尔达·特柯(Wardah al-Turk, 1797~?)、埃及社会活动家兼诗人阿依莎·泰穆瑞娅(Aisha al-Taimuriya, 1840~1902)、马莱克·希夫尼·纳西夫(Malak Hifini Nasif, 1886~1918)、巴希特塔特·巴蒂雅(Bahithat al-Badiyah, 1886~1918)等发表了大量探讨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文章,倡导妇女应获得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印度人鲁凯耶·赛赫瓦特·候赛因(Rokeya Sakhawat Hossain, 1880~1932)和纳扎尔·赛贾德·海达尔(Nazar Sajjad Haydar, 1894~1967)则以短故事、小说等形式,批评伊斯兰世界盛行的性别隔离制度。一些穆斯林妇女还通过撰写回忆录,记录自己性别意识的产生,包括爪哇的拉丁·阿詹·卡尔提尼(Raden Adjeng Kartini, 1879 ~1904)、桑给巴尔的埃米莉·鲁艾特(Emilie Ruete, 1844~1924)、伊朗的塔吉·萨尔塔纳(Taj al-Saltanah, 1884~1936)、埃及的胡达·夏拉维(Huda Sharawi, 1879~1947)和纳巴维耶·穆萨(Nabawiyah Musa, 1886~1951)等,都积极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女权意识,主张妇女参与工作。
这一时期,以女性为主题的报纸和刊物纷纷出现。从黎巴嫩南部提卜宁(Tibnin)移民到埃及亚历山大的法瓦兹,于1891年创办了《尼罗河报》(Al-Nil)。1892年辛德·纳法尔(Hind Nawfal, 1860~1920)在埃及亚历山大创办《青涩女孩》(Al-Fatat),该杂志除报道有关女性的新闻外,还刊登著名人物传记、书评、诗歌和文章,鼓励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和辩论,倡导现代女性理想。至1910年,埃及国内已有8本女性刊物。这些刊物大多关注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家庭问题,偶尔也会刊载呼吁提高女性地位的文章,并与西方社会的女性地位进行比较。某些杂志有时甚至会将国家自由与女性自由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并不是铁板一块,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朗国内出现的一些刊物更加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1906年伊朗实行宪法改革和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后,两国国内刊物审查制度有所松动,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以女性为主题的报刊杂志。土耳其的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Halide Edib Adivar, 1884~1964)创办了一本以女性为读者的杂志《百花香》(Demet)。学者巴兹(Jurji N. Baz)在黎巴嫩杂志《美人》(Al-Hasna’)撰文,高度评价和推崇这些倡导提高女性意识的刊物,赞扬创办刊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女性的勇气:“受过教育的叙利亚女性很快了解到,让东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权利与义务并拓宽其视野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媒体。这是女性除接受学校教育外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所有女性都熟知的方式。基于此目标,也是为了大众权益,我们看到这些女性正着手于这些努力中。然而,只是在埃及,她们的梦想最终实现了。”[注]Toufoul Abou-Hodeib, A Taste for Home: The Modern Middle Class in Ottoman Beiru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5-56.所有这些刊物,代表了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女性对现代女性的看法,吸纳了“如何看待自己”与“如何经营自己一生”等新观念。
第二,女性直接参与提高女性地位的“日常活动”,包括创办女校、建立慈善机构和参与社会运动等。印度尼西亚教育家卡尔蒂妮(Raden Adjeng Kartini, 1879~1904)积极倡导女性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为爪哇官员子女创办了一所女校。她去世之后,该校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学校。除创办女校外,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部分伊斯兰国家妇女协会的雏形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第三,女性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女权主义表达方式。在伊朗,一些妇女在19世纪中叶参加了巴布教徒起义(1848年至1952年),该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一夫多妻制和妇女佩戴面纱。后来,一些伊朗妇女先后参加了1890年的“烟草抗议”(Tabacco Rebellion)和1906年的“宪政革命”。
在上述这三种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女性虽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却尽量避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以免被公众认为她们是女权主义者。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在参与社会运动中,公开宣布女权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此过程中,并非所有的穆斯林改革者或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都支持女性实现解放。例如,埃及抗英民族斗争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1874~1908)和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工业家塔拉特·哈尔卜(Talaat Harb, 1867~1941)就反对女性摘下面纱。在印度,伊斯兰教改革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也主张维持深闺制度,延迟对女性的教育。
二、 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女权理论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一时期的女权理论深受各国民族主义发展态势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妇女在民族国家独立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埃及,各阶层女性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政治局势的变化。埃及妇女通过参与示威、罢工甚至暗杀活动,支持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和本国的独立运动。瓦伦丁·查若(Valentine Chirol)曾在《伦敦时报》(LondonTimes)撰文提到:“在1919年暴风雨的一天,女性聚在街头。这些人中既有受人尊敬但头戴面纱、身着宽松黑色罩袍的高阶层的女性,也有从城市最底层街区涌现出来的街头妓女,她们抓住政治动荡的机会,希望摘下面纱、脱掉罩袍,快乐地生活。在每一场混乱的示威游行中,妇女总是走在最前列。她们列队行进,有的步行,有的在车厢中高喊‘独立’口号,挥舞着国旗。”[注]Eileen Philipps, “Casting Off the Veil,” Marxism Today, August 1986, 转引自Nawar Al-Hassan Golley, Reading Arab Women’s Autobiographies: Shahrazad Tells Her 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3, pp. 31-32。在1905年至1911年伊朗爆发的反抗沙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期间,伊朗妇女建立了许多小型女权主义团体,其中比较典型的有1910年于德黑兰成立的“爱国妇女联盟”(Patriotic Women’s League)、1918年由赛迪盖·杜夫莱泰巴迪(Sediqeh Dovlatabady)创立的“伊斯法罕妇女协会”(Isfahan Women’s Association)和1927年由赞杜赫特·希拉齐(Zandukht Shirazi)在设拉子建立的“革命妇女协会”(Association of Revolutionary Women)。这些松散的组织支持妇女接受教育,关注妇女健康,有时也会致力于倡导争取妇女政治权利。
20世纪30年代末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来自于西亚地区、曾致力于慈善事业或文学创作的女性,逐渐成为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将民族主义的内容纳入女权主义运动中,使穆斯林女权理论被打上了泛阿拉伯主义的烙印。1938年和1944年在埃及先后召开的女权问题会议上,来自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女性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殖民主义女权理论不同的阿拉伯女性意识。此类泛阿拉伯的妇女组织,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妇女权利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泛阿拉伯女权组织的建立,最早可追溯至1923年埃及的胡达·舍厄赖维建立的“埃及女权协会”。舍厄赖维是阿拉伯地区早期的女权运动领袖,她领导的女权运动与华夫脱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结成了“一种复杂的亲缘关系”,成为埃及女权主义发展的一大特色。“埃及女权协会”赞助学校、工作坊、女子俱乐部,注重对妇女进行培训,其目标是使女性接受教育,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提高至16岁,确保女性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废除卖淫,并建立孤儿院、妇女中心以及失业妇女可以谋生的工厂。“埃及女权协会”以法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出版杂志《埃及妇女》(Al-Misriyya),并与国际妇女组织“女性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建立联系,后者的目标是实现妇女的普选权。然而,“埃及女权协会”最终因“女性国际联盟”沿袭“英帝国主义的政策,拒绝支持巴勒斯坦的妇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注]Wolfgang Benedek, The Human Rights of Woma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and African Experiences, London: Zed Books, 2002, p. 243.而与其分道扬镳。
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时期以及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妇女运动将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巴勒斯坦妇女民族主义者因此呼吁“埃及女权协会”帮助她们开展民族斗争。1944年,“埃及女权协会”成员前往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讨论阿拉伯女权联合会的成立事项。1945年,为实现阿拉伯妇女的斗争目标,“埃及女权协会”促成了带有泛阿拉伯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妇女联合会”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中叶,北非国家妇女积极投身民族独立斗争,并结成组织发挥作用。在阿尔及利亚,大多数年轻女性积极投身革命,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本国女性权利的倡导者。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成立后,便发起了抗击法国的武装斗争,该国妇女加入到反抗法国统治的起义中,成为战士、情报人员、联络员或救死扶伤的护士。女性戴面纱为参与战事提供了便利,她们可以暗地运送武器,但一些人因此受到监禁或酷刑。然而,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革命政府在登记这些女性的社会活动时,许多人并未得到应有的荣誉,理由是这些人或是文盲,或是其行为被看作是“平民的行为”,而非“军事参与”。否认女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所作贡献的现象,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比较普遍。女性在国家实现独立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国家独立后,“男性通常宁肯选择恢复‘正常’,他们重新强调女性传统的角色模式和双重标准”,这揭示了“在自由平等原则与传统女性附属地位之间一种令人痛苦的对比”。[注]Mineke Schipper, Unheard Word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Africa,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84, p. 10.可以说,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受困于双重斗争所带来的窘境,即内部反对以宗教之名而实行的传统习俗、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外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在社会内部,穆斯林妇女对传统的父权观念也发起了挑战,她们试图将具有父权特征的民族主义重构成一种更具性别平等意义的民族主义。然而,伊斯兰国家法律体系和世俗化程度、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都存在差异,这使得各国妇女运动呈现出不同特点。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以宗教为导向的伊斯兰女权主义和以世俗为导向的世俗女权主义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女权主义理论对权利来源持有不同观点,即权利的理论基础是否应该来自于宗教。世俗女权主义者挑战伊斯兰框架的特殊性,强调任何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女性获得权利只能是有害无益,并倡导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妇女适用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人权规则。相比之下,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旨在通过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神圣来源,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妇女的权利。但即便如此,两种女权主义思想的行动目标仍具有一致性,即构建现代女性地位,推动家庭法改革,使女性获得行动自由和着装自由。女权主义者采取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试图建构现代女性观念。埃及著名女权主义者、诗人兼编辑杜里亚·沙菲克(Durriyah Shafiq, 1908~1975)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该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沙菲克于1945年创办阿拉伯文杂志《尼罗河之女》(Bintal-Nil),并于1948年成立“尼罗河之女联盟”(Bintal-NilUnion)。“尼罗河之女联盟”在埃及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家扫盲中心,与“埃及女权协会”一道,在埃及形成了一股组织完备、独立的女权运动。“尼罗河之女联盟”呼吁为妇女提供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为所有女性公民提供医疗保障,改革家庭法;“埃及女权协会”则发起妇女参政运动和努力提高埃及女性识字率。
在伊斯兰世界,有的国家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女性地位,无形中影响着周边国家对女性权利的看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具有民族主义者身份,他们努力提高妇女的地位,削弱宗教人士的权力基础。1936年,随着伊朗礼萨·汗政权的巩固,伊朗政府宣布妇女佩戴面纱为非法,颁布涉及穆斯林结婚、离婚、继承等方面的《家庭法》,推进伊朗实现现代化和遏制宗教势力。在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改革运动,“取消宗教法庭,代之以世俗法庭;实行一夫一妻制,允许妇女进入医校和艺术学校,允许出版有关妇女解放的书籍,以及建立世俗学校等”[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The Role of Islam, New York: Praeger, 1984, p. 3.。随着土耳其新政权的巩固,该国于1926年颁布《民法》,成为世俗化的家庭法规范。土耳其还颁布新法,废除歧视妇女的法律,在妇女“取下面纱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尽管妇女在婚姻和离婚方面获得了某些权利,但由男性主导的父权制仍普遍存在。
三、 威权国家体制对女权理论发展的消解
二战前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由国家主导的、以提高妇女地位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女权主义”,“政府通过重新构筑一种公共的而非个人的关注,通过在公共部门雇用更多妇女,努力消除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注]Mervat F. Hate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in Egypt and the Demise of State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4, No. 2, 1992, p. 231.。国家层面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个人家庭法》或《个人身份法》。在中东地区,约旦(1951年)、突尼斯(1956年)、摩洛哥(1958年)、伊拉克(1959年)、阿尔及利亚(1961年)、叙利亚(1953年)、黎巴嫩(1963年)与伊朗(1967年)等国实现独立后,政府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制定了内容涉及结婚、离婚、儿童监护权、妇女的家庭权利和赡养等诸多领域的《家庭法》或《身份法》。在《家庭法》中,穆斯林女性的某些权利受到保护。巴基斯坦实行的《穆斯林家庭法条令》(1961年)则对妇女结婚和离婚作出了有利于女性的规定。这使得当时伊斯兰世界女性所关注的权利要求得到基本实现,女性的各种诉求趋于平缓。二是国家通过政策制定,使一些妇女得以进入以前只有男性才能涉足的政治领域,从事之前对妇女不曾开放的职业,部分女性因此在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中谋得了好的职位。其中,许多遵从宗教传统的有权势的女性,往往借助强大的亲属关系或影响而步入政坛。少数有权势的年长妇女还主导着带有官方性质的协会,如担任伊朗“妇女组织高级理事会”(Higher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zations)主席的阿什拉夫·巴列维(Asharaf Pahlavi, 1919~2016)等。然而,在政治生活中,一些妇女常因其精英出身,对待下属妇女颐指气使。但是,这些精英妇女本身因无力改变男性对政治的绝对主导地位,也无力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影响而备受诟病。例如,在巴基斯坦,“妇女行动论坛”(Women’s Action Forum)这类小型组织试图扭转这种局势,但没有成功。[注]Ayesha Jalal. “The Convenience of Subservience: Women and the State of Pakistan,” in Deniz Kandiyoti, ed., Women, Islam, and the Stat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5.
国家女权主义客观上制约了女权理论与运动的自由发展模式,并进一步限制了伊斯兰世界妇女运动的独立发展。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女性团体先后建立,逐渐形成了官方的国家女权主义与民间女权主义两种发展模式。在伊朗,莎赫拉·舍尔坎(Shahla Sherkat)和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等独立人士与国家权力机关保持距离,并与女权律师梅朗吉丝·卡尔(Mehrangiz Kar)、评论家和性别平权倡导者莎赫拉·拉希基(Shahla Lahiji)、社会学家娜希德·莫提伊(Nahid Motiee)等世俗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及海外伊朗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开展密切合作。而玛苏梅·艾伯特卡尔(Massoumeh Ebtekar)、玛尔亚姆·贝赫鲁齐(Maryam Behrouzi)、帕尔温·玛茹菲(Parvin Ma’arufi)、贾利赫·杰洛达尔扎德(Jaleh Jelodarzadeh)等在政府或议会担任职务的国家女权主义者,则与政府或议会保持密切联系。在对待文化和性别问题的立场方面,国家女权主义者较独立女权主义者保守。例如,部分国家女权主义者仅强调家庭凝聚力的重要性,认为母性和家庭生活可使家庭在道德上树立典范。独立女权主义者和国家女权主义者在倡导重新解读《古兰经》、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改革穆斯林家庭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但两者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建设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立场。[注]Valentine M. Moghadam, “Islamic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Signs, Vol. 27, No. 4, 2002, p. 1137.
随着妇女获得进入公共生活和融入社会的机会增多,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角色问题,讨论妇女的身心健康、家庭暴力、性侵犯、恋童癖以及妇女受到的阶级压迫等相关话题。20世纪70年代,埃及女权主义者纳瓦尔·萨达维(Nawal al-Sadawi)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经济、两性和心理问题的文章。她对女性心理创伤的研究涉及女性贞操观念、女性割礼对心理和身体的危害,并对乱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作为一名小说家,萨达维擅于以日常生活为背景描述女性生活,广受埃及读者喜爱。阿尔及利亚小说家、散文家艾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在其文学作品中深刻揭露了受压迫的妇女和在父权制民族主义下发展受限的女性主义。伊朗女诗人芙茹厄·法洛赫扎德(Furugh Farrukhazd)则通过诗歌传达女性的复杂情感。拉蒂法·宰亚特(Latifa al-Zayyat, 1923~1996)和因吉·阿芙拉敦(Inji Aflatun, 1924~1989)等埃及作家通过著述个人回忆录,揭露家庭、社会和国家对妇女的压迫。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著述或文学作品言辞含蓄,意蕴深长,但并没有就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达成一致,甚至彼此之间常出现论争。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穆斯林妇女运动几乎陷于停滞,大量伊朗妇女被解雇,女性的社会地位跌落至低谷,女权理论逐渐进入低潮期。受伊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在部分伊斯兰国家保护妇女的《家庭法》或《个人身份法》遭到破坏。1981年,阿尔及利亚提出修订《家庭法》的议案,该国保守派强烈主张将一夫多妻制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写入《家庭法》,但最终“因各行各业妇女的游行示威,以及一些退伍军人的抗议,该议案没有被制定成法律”[注]Boutheina Cheriet, “Gender,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hip in Algeria,” Middle East Report, No. 198, January, 1996, p. 24.。同年9月,巴基斯坦“妇女行动论坛”成立,其初衷便是为了抗议1979年“胡都法令”(Hudood Ordinance)即执行伊斯兰刑罚的法令的通过。由巴基斯坦右翼军事政权制定的“胡都法令”,以伊斯兰教法的“重罪”之名,模糊了通奸与强奸之间的界限,不仅不采用妇女的证据,反而对遭到强奸的妇女处以重罚。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妇女争取权利的行动,主要针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女性职业者受到骚扰、女性因政治信仰遭受折磨、女性职业活动受限、女性公共雇员服饰等歧视妇女的问题,开展有组织的斗争[注]Sara Suleri, “Woman Skin Deep: Femin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18, No. 4, Summer, 1992, p. 766.。巴基斯坦各阶层的妇女都积极加入“妇女行动论坛”,把为所有巴基斯坦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育、就业、人身安全、婚姻身份选择、消除社会歧视等基本人权[注]Abida Samiuddin, Muslim Feminism and Feminist Movement: South Asia, Delhi: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p. 66.作为共同目标。1985年,埃及议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未加入任何社团组织的妇女,对政府欲废除1979年《家庭法》草案反应强烈,保护妇女权利和家庭的委员会与女权组织迅速产生,以捍卫1979年《家庭法》改革成果。[注]Mervat F. Hate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iberation in Egypt and the Demise of State Feminism,” p. 245.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妇女组织相继建立。1987年,土耳其妇女在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举行游行,抗议家庭暴力。为反对性骚扰、家庭暴力和其他侵害妇女权利的行为,“反歧视妇女协会”和“妇女团结协会”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成立。1990年,土耳其女权活动家又建立了“紫屋顶妇女瓦克夫庇护所”。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女权活动家也成立了“妇女社会和文化协会”与“青年妇女俱乐部”。为反对社会对妇女的结构性、制度性压迫,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还同信仰其他宗教的妇女开展合作,于1985年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建立“全体妇女行动协会”,发行刊物《浪潮》,为妇女发声。
在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一些穆斯林女权主义者曾试图借用伊斯兰教法中的创制(ijtihad),通过解经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她们以早期伊斯兰历史上妇女受教育的先例,证实这些权利曾经确实存在过,试图唤醒伊斯兰教赋予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巴基斯坦学者瑞伏坦·哈桑(Riffat Hassan)和摩洛哥社会历史学家法蒂玛·梅尼西(Fatima Mernissi)以宗教学解释为基础,对《古兰经》和“圣训”展开研究,进入传统上只有男性宗教学者才能解释宗教经典的领域,探讨女性问题。瑞伏坦·哈桑通过审慎解读《古兰经》经文,证明穆斯林男女之间存在绝对平等,认为男性对宗教经典解读的主导权,导致一种“父权制伊斯兰教”的产生。梅尼西则运用历史方法研究“圣训”,揭示了伊斯兰社会父权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瑞伏坦·哈桑曾发行过一本宣传手册,阐释《古兰经》中的男女平等思想。
女权组织的发展和宣介女性权利思想网络的形成,逐渐成为女权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新平台。成立于1984年成立的“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团结会”(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组织最初是为回应发生在伊斯兰国家的三起紧急事件而成立的,三起事件皆是以“伊斯兰教法”之名剥夺妇女应享有的权利。当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伊朗、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9名妇女,为支持伊斯兰国家妇女的抗争,共同发起成立了“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团结会”。该组织旨在为“那些在被称作穆斯林律法和习俗下被限制和规训的妇女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及集体抗争的空间和讨论平台”[注]参见Women Living Under Muslim Laws, http://www.wluml.org/,登录时间:2019年6月10日。。
四、 21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反思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式微和全球化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世俗化进程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渐增多,穆斯林妇女的视野日益开阔。随着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研究和行动主义引入阿拉伯世界,大量阿拉伯女学者的作品被译介成英文并传播至西方社会,阿拉伯穆斯林妇女逐渐从受隔离的境况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更广泛的女权主义的圈子中。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话语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兴起并时常被用于阐释阿拉伯妇女运动和女权理论。“在新千年,阿拉伯女权主义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扩大了女权主义分析的方法,打破了各种限制类别——无论是东方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多元文化,甚至是女权主义,这些类别的殖民主义倾向往往束缚了阿拉伯妇女。”[注]Therese Saliba, “Arab Feminism at the Millennium,” Signs, Vol. 25, No. 4, 2000, p. 1091.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是穆斯林女性权利发展的恒定话题,即穆斯林妇女权利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发展模式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是伊斯兰模式,抑或是西方模式?一些学者和女权活动家对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反思,分析了民族主义对妇女权利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女权主义理论家聚焦穆斯林女性经历的历史多样性,从性别、社会、经济、殖民主义以及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反应等视角,分析不同时空环境对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影响。哈佛大学从事伊斯兰文化研究的玛丽莲·布思(Marilyn Booth)教授认为,20世纪早期埃及著名女性活动家的谱系是以“国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构建出“一种资产阶级的身份”[注]Marilyn Booth, “May Her Likes Be Multiplied: Famous Women Biography and Gendered Prescription in Egypt, 1892-1935,”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2, No. 4, 1997, p. 837.。参与公共生活使得埃及妇女有可能“逾越男性民族主义思想家为女性设定明晰的边界”。同样,在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和为国家主权斗争的运动使得地区冲突、民族主义成为当地女权运动讨论的核心话题。研究巴勒斯坦难民和中东人权的学者朱莉·彼泰特(Julie Peteet)基于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女性难民的研究,指出“母性牺牲”的民族主义话语虽然有限,但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受到认可的地位,从中她们可以发起一种批判性的运动和发挥领导作用”[注]Peteet Julie, “Icons and Militants: Mothering in the Danger Zone,” Signs, Vol. 23, No. 1, 1997, p. 104.。
有学者同时观察到了将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认为,尽管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提供了一种平台,挑战了本地的国家制度和文化实践。但中东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与文化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纠缠于一起,常常使得人们对“本地制度和文化生成”的观察和研究受挫。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后,来自草根阶层的暴力主义逐渐让位于国家和社会建设,女权行动者遂开始将自身的角色定位置于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寻求“妇女生活的积极改变”。然而,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妇女运动在政策制定上仍扮演着一种边缘化的角色。巴勒斯坦妇女活动家也开始注意到这种“民族主义的贫乏”[注]Said Edward. “The Poverty of Nationalism,” Progressive, Vol. 62, No. 3, March,1998, p. 27.,并重新聚焦于批评传统女性角色,目的是在当时逐渐兴起的民主话语中提出特定的妇女议题。巴勒斯坦比尔泽特大学社会学家丽莎·塔拉琪(Lisa Taraki)认为,巴勒斯坦社会是“革命性的”代表,但它仍是“传统的”,宗教保守力量仍是巴勒斯坦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此外,也有一些女权活动家对世俗的或自由主义的女权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些女权活动家认为,脱离宗教文化、直接的、世俗性的女性理论在穆斯林草根阶层中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权利是具体的、现实的。只有复归宗教文化自身,通过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现代性解读,强调一种平等主义的伊斯兰文化,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这理应成为新时代穆斯林女权理论来源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摩洛哥女权思想家法蒂玛·梅尼西本人,也完成了从“世俗女权主义”到“伊斯兰女权主义”的态度转变。梅尼西在1975年出版的《超越面纱:现代穆斯林社会中的男女动态变化》一书中提出,穆斯林的女权发展的目标应该按照一种全球范围内所主张的性别模式的措辞进行表达,这意味着整个穆斯林社会需要进行“革命性的重组”[注]Fatima Mernissi, Beyond the Veil: Male-Female Dynamics in Modern Muslim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6.,即一种基于世俗主义的女性权利。然而,梅尼西在1991年出版的《面纱与男性精英:对伊斯兰教中妇女权利的女性主义解读》一书中却又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她主张应重新评估伊斯兰传统,认为妇女在穆斯林社会的地位问题是“男性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误读或错误解释的结果,而不应归于伊斯兰教本身”[注]Fatima Mernissi, The Veil and the Male Elite: A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Islam, Cambridge: Perseus Books, 1991, p. 12.。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穆斯林女权思想家的矛盾心理。
巴基斯坦著名的女权理论家瑞伏坦·哈桑出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个富裕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1974年开始长期从伊斯兰教传统的视角研究妇女问题。她主张从宗教自身来解决女性的权利平等问题,强调要更好地运用“宗教讨论”,认为《古兰经》是一部“人权大宪章”,规定了人权和人人享有的平等,但许多穆斯林妇女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是由社会和文化影响造成的。瑞伏坦·哈桑支持对《古兰经》进行灵活解读,认为《古兰经》虽然是真主的语言,但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因此,《古兰经》的意义应该通过经注学来赋予,即通过研究经文降示时的时空背景加以阐释。她强调,要正确理解《古兰经》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就必须从整体上看待《古兰经》中有关妇女权利的所有章节,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如果这些经文被孤立地、脱离特定时空背景加以解释,《古兰经》阐释的妇女地位将受到误解,这也是对《古兰经》的普遍目标即在人类平等基础上建立公正社会的误读。这种误读助长了关于女性身体和智力低下的理论,最终导致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瑞伏坦·哈桑认为,这是保守的伊斯兰学者所设的陷阱:“他们断章取义地阅读《古兰经》经文,忽视《古兰经》经常使用象征语言来描绘深刻的真理。”[注]Niaz A. Shah, “Women’s Human Rights in the Kora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8, No. 4, November, 2006, p. 883.
瑞伏坦·哈桑同时批评穆斯林世界某些人权组织的立场,这些组织认为人权与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强调放弃伊斯兰教是妇女从压迫和发展中解放出来的先决条件。她将普通穆斯林妇女的三大特点归纳为贫穷、文盲和在农村生活。“我作为一名人权活动家,如果想要‘解放’从安卡拉到雅加达任何地方生活的普通穆斯林妇女,不能通过与她谈论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方式来实现,因为这对她们来说毫无意义。我可能会通过触及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来实现,即提醒我所遇到的穆斯林女性,真主是公正和仁慈的,女性作为至仁至慈的真主创造物,她有权得到公正和保护,免受压迫和不公平。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许多生活在绝望和无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当她们意识到在界定她们身份的信仰体系框架内,她们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可能性时,她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注]Riffat Hassan, “Challenging the Stereotypes of Fundamentalism: An Islamic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Muslim World, Vol. 91, No. 1-2, Spring, 2001, p. 66.
法蒂玛·梅尼西和瑞伏坦·哈桑两位女权理论家思想中呈现的“伊斯兰觉醒”意识,在穆斯林女权主义理论中逐渐成为主流。这主要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穆斯林女权主义理论家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本能反应;二是对不断低迷的经济环境的适应。在这种环境中,伊斯兰传统在弥合渐趋衰微的一些中东福利国家面临的社会窘境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戴面纱成为一种对男性与女性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竞争的功能性反应”[注]Macleod Arlene Elowe, Accommodating Protest: Working Women, the New Veiling, and Change in Cair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6.。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家萨巴·马哈穆德(Saba Mahmood)教授通过对开罗妇女清真寺运动的研究指出,有些理论分析常常“忽略妇女自身的宗教需求”,穆斯林妇女所寻求的宗教虔诚和谦卑,在女权主义那里常被解释为“错误的主观性”。与此同时,这种人权理论中的“伊斯兰觉醒”意识也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这些运动推翻了自由—人道主义传统及其女权主义变体的假设,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带来了进一步挑战,对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构成了更严重的对抗”[注]Therese Saliba, “Arab Feminism at the Millennium,” p. 1090.。
2010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进一步验证了穆斯林女权主义者这种摇摆的矛盾心理。在这场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初期,阿拉伯国家的妇女一方面亲身参与示威抗议活动,一方面动员他人加入,其中不仅有妇女活动家,也有先前未曾涉足政治活动的家庭主妇。女性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照片在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甚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女性成为了革命的象征,如也门记者兼人权活动家、2011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塔瓦库尔·卡尔曼(Tawakkol Karman),巴林女权运动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宰乃卜·哈瓦贾(Zainab al-Khawaja)等。
然而,“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丝毫改善,反而出现了“倒退”和“令人担忧”的状况。在这场波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抗议浪潮中,宗教力量一度上升,对女权运动的发展造成冲击。根据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公布的一项调查,“阿拉伯之春”对阿拉伯社会带来的动荡与不安,反而使女性成为这场运动的“最大输家”。2012年6月埃及议会解散前夕,立法委员会接到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降到14岁。这项提案一旦通过,不仅女孩受教育的时间会被缩短,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最终,该提案遭到议会中大部分议员的反对,特别是女议员的反对而未获通过。女性在“阿拉伯之春”期间遭受到的境遇,引发了阿拉伯女权主义者的新一轮争论。埃及专栏作家艾塔薇提指出,埃及女性需要“双重革命”,一场是“对抗毁了我们国家的独裁者”的革命,另一场是“对抗毁了我们身为女性的文化与宗教的荼毒”的革命。[注]江静玲:《阿拉伯之春掀动荡 女权遭践踏》,中时电子报,2013年11月1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cn/amp/newspapers/20131113000515-260108,登录时间:2019年6月11日。
埃及伊本·赫勒敦发展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和人权活动家达利娅·齐亚达(Dalia Ziada)曾指出,社会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来改变女性的状况,包括制定新的宪法和法律,提升妇女的经济独立性,改变草根阶层男性和女性的成见。
五、 结 语
通过对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发展的历史性梳理,可以勾勒出女权理论发展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伊斯兰世界各时期女权理论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易受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一种迭进反复、波浪式前行的特点;二是伊斯兰世界的女权理论并非铁板一块,伊斯兰女权主义与世俗女权主义两种理论路径,是我们认识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类型的基本线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斯兰世界社会内部变革的两种态度;三是女权理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语之一,并逐渐渗入至公共生活、法律和政策制定中,促使穆斯林开始反思传统,推动新的宗教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这种宗教知识在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和教义中产生,令人信服地使女性获得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权利。
可以说,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只有是系统的、一致的、持续的,并且与宣传工作和社会实践相联系时,才是有效的。否则,伊斯兰女权主义,无论是以知识探究的形式呈现,还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呈现,往往都是昙花一现。从运动自身来看,被称为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尚缺乏严格的分析方法。涉及到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各类著作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尚未被充分考察、分析和研究。同时还应看到,学者学术思想的学究化和缺乏宗教权威性,也往往会牵制其观点深入草根阶层。不过,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思想上的学术动员仍有其重要性,这也是当代伊斯兰女权主义理论存在的真正意义。
从整个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来看,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东方的宗教文化,而是如何解决妇女对男性和宗族的经济以及人身依附问题,如何在伊斯兰国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和培育公民意识,如何在法律中确立男女平等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关系的问题。盲目地把宗教与女权结合到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穆斯林女性权利的发展。2016年7月阿尔及利亚妇女部前部长、女权主义者瓦西莱·塔姆扎利(Wassila Tamzali)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伊斯兰女权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成为一个穆斯林或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你不能把伊斯兰硬拉到女权主义中去。宗教的角色不是女权主义,也不是民主。不能想着让宗教去做与其不匹配的事情。宗教指引我们走向精神或道德,你可能赞成或反对。而女权主义是别的东西。女权主义不谈伦理,它只谈自由。”[注]Barbara Slavin, “No Arab Spring Without ‘Flower’ of Women’s Rights,” Al-Monitor, October 3, 2012,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2/al-monitor/arab-women-fight-for-rights-at-feminist-conference-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html#ixzz5qVO9mcdO,登录时间:2019年6月11日。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那就是努力尝试在理论上把女权置于世俗性的语境中,在公民权的范围内发展女性权利,或许是唯一选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