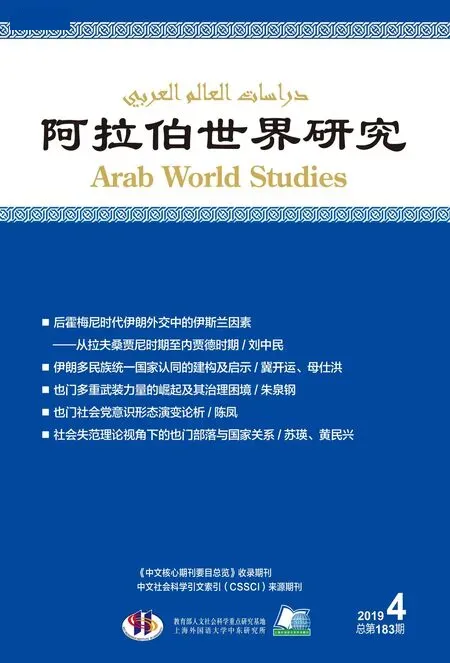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建构及启示*
冀开运 母仕洪
国家认同[注]从政治学视角界定,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从民族文化视角界定,国家认同是个人承认和接受民族文化与政治身份后的归属感,是个人对所在国家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的承认和接受。参见李瑞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认同”研究概述》,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第93页。的概念因视角差异而不尽相同,具体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意识、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注]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第37页。国家认同是国家维系自身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的基础。如果国民对国家缺乏强烈认同,国家就可能因缺乏稳固的心理基础而解体。[注]吴玉军:《国家认同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第69页。历史上不乏大国因国家认同脆弱而走向分裂的案例,当前世界上诸多国家亦饱受国家认同危机的困扰。例如,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有效整合而一直非常脆弱,而国家认同感的丧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印度尼西亚亦因国家认同危机致使国家统一面临巨大威胁;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的国家认同困境,是各国国内矛盾和冲突频仍的重要诱因,比如多元认同并存、国家认同脆弱成为阻碍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所在。[注]参见郭艳:《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4期;郭艳:《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载《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8期;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冯燚:《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上述案例诠释了国家认同对民族国家构建以及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意义。相较而言,伊朗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现代伊朗[注]伊朗古称波斯,1935年更名为伊朗,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伊朗。本文中的“伊朗”是国家概念,“波斯”则是指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以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由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同部分后发国家一样,多元身份认同对伊朗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政治挑战,但伊朗成功打造了具有强烈认同的伊朗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
国外学者对伊朗民族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卡维赫·巴亚特 (Kaveh Bayat)的《伊朗族群问题》[注]Kaveh Baya, “The Ethnic Question in Ira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37, 2005.概述了伊斯兰共和国宣扬伊斯兰主义对国家认同的消极影响,分析了外部因素对伊朗民族分离主义的刺激作用。阿克巴·阿格哈加里安(Akbar Aghajanian)的《伊朗民族不平等概述》[注]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5, No. 2, 1983.一文对波斯人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失衡及其原因作了精辟析论。图拉吉·阿塔巴克(Touraj Atabaki)的《伊朗的民族多元与领土完整:国内和谐与地区挑战》[注]Touraj Atabaki, “Ethnic Divers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ran: Domestic Harmony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Iranian Studies, Vol. 38, No. 1, 2005.从中央与边疆、领土依附与政治边界、民族认同与社会流动三方面解析了伊朗领土完整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马拉特·格雷本尼科夫(Marat Grebennikov)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忠诚之谜:阿塞拜疆人缘何支持伊朗国家?》[注]Marat Grebennikov, “The Puzzle of a Loyal Minority: Why Do Azeris Support the Iranian Stat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7, No. 1, 2013.从人口、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多维视角分析了阿塞拜疆人对伊朗的国家认同。卡维赫·巴亚特的《伊朗与“库尔德问题”》[注]Kaveh Bayat, “Iran and the ‘Kurdish Questio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7, 2008.梳理了伊朗库尔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历程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理查德·卡塔姆(Richard W.Cottam)的《伊朗民族主义》[注]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4.分析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基础、类型和作用。斯蒂芬妮·克罗宁(Stephanie Cronin)的《现代伊朗的构建:礼萨·汗时期(1921~1941)的国家与社会》[注]Stephanie Cron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Riza Shah, 1921-194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探究了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途径。
国内学界对伊朗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伊朗民族分布、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格局的概述;[注]王菊如:《伊朗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第32-36页;冀开运:《伊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载《世界民族》2008年第1期,第65-72页;李鹏涛:《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81-87页。二是考察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路径选择;[注]詹晋洁:《礼萨·汗时期(1921-1941)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2期,第1-12页。三是对伊朗国内的阿拉伯人、俾路支人、阿塞拜疆人等少数民族进行个案研究,剖析这些少数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历史演变和解决路径,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对伊朗的国家认同感。[注]赵克仁:《伊朗胡齐斯坦问题透析》,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4期,第38-45页;冀开运:《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4期,第23-28页;苏欣:《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第34-47页;祖力甫哈儿·哈力克、黄民兴:《当代伊朗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探讨》,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3期,第25-30页。总体来看,国外学界对伊朗民族问题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伊朗民族分布格局、伊朗民族主义以及伊朗部分少数民族有重要价值,但对伊朗政府因应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路径缺乏深入探讨。整合国族意识、打造国家认同是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大多数后发民族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的共同困惑和难题。因此,本文拟在梳理伊朗民族问题的基础之上,力图厘清伊朗应对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主要路径,希冀对后发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提供些许借鉴。
一、 伊朗的民族问题
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波斯人早在2,500年前就建立了国家[注]即举世闻名的第一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又称阿契美尼德王朝。,但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伊朗屡遭外族入侵,希腊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蒙古人以及阿富汗人先后入主伊朗,在伊朗大地上建立政权。阿拉伯帝国覆灭后,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先后如潮水般涌入伊朗高原,改变了伊朗原有的民族结构,促进了伊朗多元民族格局的形成。伊朗高原数千年的民族迁徙史、八百余年遭受外族统治的辛酸史、近代英俄操控伊朗疆域划定的屈辱史以及巴列维王朝民族政策的负面影响,使伊朗面临诸多民族问题,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民族构成复杂,跨界民族众多
伊朗是一个民族多元的国家,和周边邻国相比,其民族多样性远超伊拉克[注]阿拉伯人是伊拉克的主体民族,约占伊拉克总人口的78%,库尔德人约占18%,其余还有少量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参见张维秋:《中国驻中东大使话中东:伊拉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和土耳其[注]土耳其的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85%,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少数民族,约占15%。参见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惟有巴基斯坦[注]旁遮普人是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63%,信德人占18%,帕坦人占11%,俾路支人占4%,此外,巴基斯坦还有众多少数民族。参见杨翠柏、刘成琼:《列国志·巴基斯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7页。可与之相提并论。据统计,2017年9月伊朗人口为8,135.25万,位居世界第18位。[注]陆瑾、王建:《中国和伊朗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与风险评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由于伊朗政府拒绝实行民族识别政策,因而伊朗国内究竟存在多少个民族,目前尚不得而知。据学者统计,伊朗国内有40多个民族,按照各民族的语言可划分为三类:伊朗语系的波斯人、库尔德人、卢尔人、巴赫蒂亚尔人和俾路支人等民族;突厥语系的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卡什凯人等民族;闪语系的阿拉伯人等。[注]王菊如:《伊朗的民族与民族问题》,第32页。
除语言差异之外,伊朗各民族在人口比例和宗教信仰上也迥然有别。波斯人是伊朗的主体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66%;阿塞拜疆人是伊朗的第二大民族,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库尔德人约占5%,其他民族一共约占4%。[注]杨涛、张立明:《伊朗概论》,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15页。在宗教信仰上,伊朗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全国9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的比例高达90%。[注]Donald N. Wilber, Iran: Past and Pres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62.伊朗穆斯林大多为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徒,其中包括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吉拉吉人和马赞达兰人等,而伊朗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则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此外,伊朗还有部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
伊朗存在众多跨界民族。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主体民族同属一族;伊朗的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民族特征上别无二致;伊朗西南部地区居住着300多万阿拉伯人,他们与邻国的阿拉伯人同宗同源;[注]Hussein D. Hassan, “Iran: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Congressional Reserch Service, November 25, 2008, p. 9,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L34021.pdf,登录时间:2019年6月15日。俾路支人散居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交界处。伊朗东西南北皆有跨界民族,每当伊朗处于历史动荡期,这些边疆民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分离主义倾向。
(二) 各民族发展失衡,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差距极大
自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以来,各民族发展失衡一直是困扰伊朗的民族问题,尤其是波斯人与其他民族的差距极大,并有继续扩大之势。伊朗各民族发展失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地理分布。从伊朗各民族的分布格局来看,波斯人主要聚居于中央高原和北部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是伊朗的核心地带,属于先进文明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伊朗其他民族则主要聚居在伊朗的边疆地区,除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较为富庶外,大部分民族聚居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属于国家的边缘地带。
第二,职业结构和城市化。1976年,伊朗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36.1%,这一数字在波斯人居住的中部省区仅为13.8%,表明波斯人在农业部门的参与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1996年,中部省区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为25.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2%,除克尔曼沙赫库尔德人(37.7%)和胡齐斯坦阿拉伯人(36.5%)略低于全国水平外,伊朗其它少数民族均高于全国水平。[注]Statical Center of Iran, “Iran Statical Yearbook,” Statical Center of Iran, https://www.amar.org.ir/english/Iran-Statistical-Yearbook,登录时间:2019年6月15日。伊朗的城市化水平因族而异,非波斯人的城市化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6年,伊朗的城市化水平达46.8%,俾路支人和库尔德人的城市化比例尚不足25%,而中部地区波斯人的城市化比例则高达80%。[注]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pp. 214-215.到2006年,伊朗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仍极不平衡。据统计,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波斯人居住的中部地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少数民族地区仅有1个,其余都分布在波斯人聚居区。[注]“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ity Population, https://www.citypopulation.de/Iran.html,登录时间:2019年6月15日。
第三,受教育程度。伊朗各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极不平衡。1976年伊朗六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47.5%,而中部地区人口的识字率达到66.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相比之下,其他各民族的识字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远低于波斯人的识字率,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极低,如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女性的受教育率不足20%,而中部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率达56.5%。中部省区男性的受教育率高达74.8%,而在俾路支斯坦和库尔德斯坦,这一数字分别为39.1%和43.8%,东阿塞拜疆和克尔曼沙赫男性的受教育率状况相对较好,但也无法同中部省区相提并论。[注]Akbar Aghajanian, “Ethnic Inequality in Iran: An Overview,” pp. 215-216.
第四,公共设施的使用。1976年,伊朗50%的家庭能够使用电力,而中部省区使用电力的家庭比例高达80%。相较之下,库尔德人使用电力的家庭比例不足20%,俾路支人仅有12.4%。自来水的饮用与居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直接相关。1976年,在波斯人聚居的伊朗中央各省,约75%的家庭安装有自来水,而俾路支人则不到25%,库尔德人仅有12%,土库曼人约为25%。总而言之,公共设施在伊朗各民族当中的分布极不平均。[注]Ibid., pp. 216-217.
通过对地理分布、职业结构和城市化、受教育程度以及公共设施使用等指标的分析,伊朗各民族发展失衡的状况已十分清晰,波斯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差距明显。
(三) 国家认同与少数民族认同和部落忠诚的抵牾
纵观伊朗历史,游牧部落一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伊朗地域广袤,高原与山脉纵横相间,地势崎岖不平。内陆地区气候干旱,降水匮乏。卡维尔沙漠和卢特沙漠位于伊朗高原的腹地,盐泽广布,人迹罕至。[注]哈全安:《伊朗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高原、荒漠和山脉镶嵌的地形使伊朗高度碎片化,伊朗国内基本没有内河航运,各地区相互孤立,人口流动性较差。碎片化的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部落的形成和发展极为有利,中央政府大多数时候难以将统治延伸至国家的边远地带,这使得伊朗的边陲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部落的控制当中,中央政府的管控更多是名义上的,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政治统一、中央集权和文化认同,自古以来就很难维持。[注][美]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7页。地方分权与地方自治成为一种常态,只有少数王朝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在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税收、贡赋、臣服和安定,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和信仰的关注度有限,只要各民族效忠王朝并缴纳贡赋,其生存就不会面临威胁。有学者指出,“在伊朗古代社会中,波斯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政府倾向于鼓励而非消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注]李鹏涛:《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伊朗民族矛盾的产生与演变》,第82-83页。。因此,在近代之前,伊朗各民族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民族差异性极大,缺乏国家认同,这是伊朗古代社会遗留的沉重历史负担。即便在当今社会,伊朗境内的40多个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族名,具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特色,多元化特征明显。
波斯人虽然是伊朗的主体民族,但自萨珊王朝覆灭以来,伊朗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皆是异族,直到巴列维王朝时波斯人才重新执掌政权。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认为,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4页。而伊朗由于长期缺乏主体民族的有效整合,各民族和部落形成了服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异的多元局面。血缘、地域、族群和宗教信仰是民族和部落认同的重要依据。如何使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认同纳入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一直是伊朗统治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正如有学者所言:“长期的分离主义倾向、区域自治状态以及地域亚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伊朗境内各族群的身份认同危机,部落认同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民族与国家认同观念比较淡漠。在‘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少数族群有着首先归属于部落、本民族和宗教的天然自觉性,部落与什叶派伊斯兰信仰始终是少数族群忠诚和义务的中心……其次才是政治认同意义上的伊朗国家。”[注]詹晋洁:《礼萨·汗时期(1921-1941)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第10-11页。
二、 当代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简单来说,国家认同是指“人们对其所在国家的认可和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国家认同决定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进而决定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注]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22页。。国家认同建构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发展至关重要,对伊朗统治者而言,如何培育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枢纽。国家认同建构指统治者运用手中的资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使公民对国家产生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注]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第74页。礼萨·汗从部落、行政区划、交通通信、教育和文化整合[注]推行文化整合是礼萨·汗构建国族认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方面,其内容广泛,包括文字改革,更改国名、姓氏和历法,宗教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民族服饰改革等。鉴于国内学者对此已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具体内容可参见詹晋洁:《礼萨·汗时期(1921-1941)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第10-11页。等多维路径入手,整合民族意识,打造伊朗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完成了伊朗从传统部落型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
(一) 部落政策: 镇压叛乱与游牧部落定居化
历史上,游牧部落是伊朗重要的社会力量,也是伊朗国家统一的破坏性因素。巴列维王朝建立前,伊朗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一些重要的部落酋长和氏族首领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统治权。部落林立使伊朗国家缺乏内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凸显了中央政府的脆弱性。礼萨·汗掌权后,决心肃清地方部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礼萨·汗的部落政策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坚决镇压部落叛乱,削弱和挤压部落势力的生存空间。自执掌权柄起,礼萨·汗先后平定库尔德人、卢尔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等地方部落势力的叛乱。至20世纪30年代,礼萨·汗通过监禁、处决、流放部落首领,削爵夺位、没收地产以及异地流徙等方式,基本扫除了部落势力的威胁,伊朗中央政府的权力触角得以延伸至部落政治结构的最底层。[注]Stephanie Cron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Riza Shah, 1921-1941, p. 225.为摧毁部落政治的经济和军事基础,礼萨·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包括在部落聚居区驻军、解除部落战士的武装、征召部落青年入伍、挑唆内部矛盾、没收地产、打击部落首领、限制迁徙以及强迫定居等。[注]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1.礼萨·汗对游牧部落的镇压和瓦解行动十分成功,游牧部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伊朗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强制游牧部落定居。为打破游牧部落对部落首领的忠诚与追随,加强中央政府对部落的驾驭和管控,从20世纪30年代伊始,伊朗政府强制游牧部落定居,部落民必须放弃游牧、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转向农耕和定居生活。该政策效果显著,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前,伊朗部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5%,30年代骤降至8%,60年代下降到3%;1976年伊朗人口约为3,370万,部落人口仅有35万,比例约为1%,伊朗的部落民几乎消失殆尽。[注]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9, 251.
礼萨·汗实施的游牧部落定居化政策解构了部落属民对氏族首领的从属关系,部落民依赖国家赐予的土地为生存之本,由牧民转化为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提供兵源。受此影响,新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建立,部落首领的绝对权威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和服从,从而培育了新农民的国家认同。
(二) 行政区划政策: 加强中央集权与完善地方行政机构
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主要被皇室成员、高级官僚和地方部落首领垄断。国王在理论上可以自由任命地方各省的行政官员,但实际上,国王受到严重掣肘。在部落族群聚居的地方行省,国王必须从具有声望的部落家族中挑选省长,或任命为部落家族认可的官员。纳赛尔丁国王(Nasir al-Din Shah)被认为对地方行省的掌控超过了该王朝的历任统治者,但他也被迫从部落家族中选择省长,并对官职世袭继承的惯例束手无策。即便是对地方法官等行政官员的任命也必须得到地方部落的认可。[注]Shaul Bakhash,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an,” Iranian Studies, Vol. 14, No. 2, 1981, p. 33.礼萨·汗掌权后,旋即着手改革地方行政区划,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6月先后两次颁布《行政区划法》,以法国和普鲁士的单一制行政区划为蓝本,建立新的合理的地方管理体系。新颁布的《行政区划法》规定,伊朗实行省、县、区、市(镇)四级行政管理体制,全国分为10个省,省下设县,县下设区,区下设市(镇),市(镇)管理若干乡村地区。[注]H. E. Chehabi, “Ardabil Becomes a Provinc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9, No. 2, 1997, p. 237.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省长、县长、警官以及其他地方官员一律由中央内政部任命。
在巴列维王朝之前,同中东多数国家一样,伊朗国家政权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城市之中,无法对部落社会实行直接统治和有效管辖,只能进行间接控制。国家只能接触到部落首领,通过他们对部落属民实行间接统治。这些首领成为地方统治者和军事首领,扮演国家与部落民之间的掮客。[注]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111页。中央政府既无地方官吏任免之权,也无部落事务裁决之责。国王意志和政府法令难以传达至社会基层,部落属民尤其是边缘地区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自然淡漠。改革后,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立以及官员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担任,使国家政令畅通全国,社会大众知晓国家意志。有学者认为这是伊朗现代史上,中央政府的权力触角第一次迈出首都,深入地方行省、县乃至乡村。[注]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137.此举消除了中央政府与社会底层的鸿沟,对于宣扬君主权威、塑造国家认同以及强化国家凝聚力意义重大。
(三) 交通通信政策: 兴建全国交通网络
伊朗辽阔的疆域和地理碎片化是地方分离主义势力频繁滋生的重要因素。闭塞的地理环境使游牧部落形成封闭型社会,游牧群体依靠游牧产品基本实现自给,内部服膺于氏族族长的绝对权威,等级森严,结构稳定。国家实际上分裂为众多相互独立、互不统属的松散社会实体。1900年伊朗的铁路里程尚不足800英里,相对于广袤的疆域可谓微不足道。礼萨·汗认识到,不打破各地区相互隔绝的闭塞状态,伊朗的国家认同建构无从谈起,因而致力于建造全国交通网络。1923年至1938年,伊朗修建了1.4万英里的新道路,其中一级道路(高速公路)的长度超过3,000英里。1920年至1933年,伊朗商品的运输费用降低了3倍,耗时节省了10倍。[注]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p. 67.修建贯穿伊朗的铁路大动脉是礼萨·汗在道路建设上的最大成就,他将这条铁路称为“伊朗发展进步、繁荣富强的最有力保障”。到礼萨·汗逊位前,伊朗新建的道路总里程达1.5万英里,伊朗的乘客、货物和邮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不再需要漫长的数月,数日即可到达。[注]George Lenczowski, Iran under the Pahlavis,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p. 30.同恺加王朝相比,礼萨·汗时期从德黑兰或各省省会调派军队前往边远地区的速度提升了数倍。
穆罕默德·礼萨继承其父的未竟事业,继续修建贯穿伊朗的道路系统。1957年4月,德黑兰—马什哈德铁路开通,1960年10月,从班达尔沙至戈尔甘的支路开通。1958年4月,德黑兰—大不里士铁路开通,1971年9月,从谢拉夫·卡勒赫至土耳其边境的支路开通。在东南部,伊朗修建了库姆至伊斯法罕的铁路,并继续延伸经克尔曼,最终直抵扎黑丹。[注]Ibid., pp. 155-157.新建的铁路直抵伊朗的东北、西北和东南边疆,这些地区分别是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等民族的聚居区。
交通通信的迅猛发展对伊朗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控,使边缘地区不再孤悬于国家统治之外,并服膺于中央权威。其次,打破了各地区的封闭状态,侵蚀和削弱了游牧部落原有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地区或全国性的经济融通,有利于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注]美国学者戈尔德施密特将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视为伊朗民族凝聚力强烈的重要原因。参见[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05页。最后,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消除各民族语言、服饰、传统和习俗多元各异的局面,有利于构建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国家认同。
(四) 教育政策: 强化文化认同和爱国主义
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是伊朗培育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符合礼萨·汗时期的基本国情。1921年政变前,库尔德斯坦、胡泽斯坦和法尔斯等地相继爆发分裂运动,众多部落建立了半自治的统治区域,伊朗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尽管礼萨·汗顺利戡定内乱,但他意识到使用武力只能在短期内维持统治,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克服伊朗人根深蒂固的两种认同:次国家的地方和部落认同以及超国家的伊斯兰认同。礼萨·汗认为,惟有教育才能使伊朗各民族紧密团结,为伊朗人构建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将教育视为伊朗构建民族凝聚力、削弱伊斯兰教认同和地方部落认同的最有效方式。[注]David Menashri,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4.
从20世纪20年代伊始,伊朗着手实施教育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全体学校一律使用波斯语为教学语言,向全国中小学推行用波斯语统一编写的教材,教师在课堂上必须使用唯一正确的标准发音,禁止使用地方方言。第二,挖掘和弘扬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第三,在地理教学上努力培养学生的国家统一意识,强调伊朗各地区的联系。第四,清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借用词汇,寻找“纯粹”的波斯语词汇替代。第五,宣扬爱国主义,培育学生对祖国的热爱是教育的核心主题。礼萨·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爱国主义,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他教导学生要将“服务祖国视为最高理想”,并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注]Ibid., pp. 92-97.
通过推行波斯语、弘扬古代波斯文化以及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礼萨·汗缩小了伊朗各民族及社会各阶层的差异,促进了伊朗国民的同质化,强化了伊朗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卫·梅纳斯赫利(David Menashri)认为,塑造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是礼萨·汗教育改革的首要贡献,“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缩小了伊朗中央与边疆地区的鸿沟,培育了伊朗国民的国家认同,促进了伊朗的现代化”[注]David Menashri,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3.。
三、 当代伊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近代以来,伊朗先后经历英俄(苏)入侵、巴列维王朝覆灭和两伊战争等剧变,仍维持了国家统一,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分崩离析的命运,这同少数民族对伊朗国家的强烈认同密切相关。在此期间,伊朗虽曾出现个别少数民族的分裂运动,但并未形成各少数民族对抗中央政府的合力。两伊战争中,伊朗各民族同仇敌忾,抵御外敌,捍卫伊朗的领土完整,便是伊朗国家认同超越少数民族认同的最好例证。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以下几大基础之上。
(一) 共同的历史认知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共同的历史认知或记忆对于培育国家认同和凝聚人心十分重要。伊朗拥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早在2,500年前,波斯人就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帝国。阿契美尼德、安息和萨珊波斯构成了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辉煌历史,伊朗人对此久久不能忘怀。2003年,伊朗阿塞拜疆人希琳·艾巴迪(Shirin Ebadi)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还自豪地宣称:“我是伊朗人,是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子孙。”[注]祖力甫哈儿·哈力克、黄民兴:《当代伊朗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探讨》,第29页。苏联学者伊凡诺夫认为,礼萨·汗采用古老的巴列维作为姓氏,其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王朝同古代的安息王朝结合起来,实际是对古代波斯帝国荣耀的一种记忆。[注][苏]米·谢·伊凡诺夫:《伊朗史纲》,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上海: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45页。正是基于对古代辉煌历史的共同认知,伊朗人具有强大的历史认同感。有美国学者认为,在历史认同感方面,中东国家没有一个能与伊朗相提并论。[注][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205页。
伊朗的国家认同还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灿烂的文化是伊朗各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伊朗学者扎比胡拉·萨法指出,从11世纪末开始,波斯语不仅成为伊朗高原普遍使用的文学语言,也成为整个伊朗民众日常交际的通用语。[注][伊朗]扎比胡拉·萨法:《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张鸿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7页。有英国学者认为,从那时起,波斯语就成了打造和保持波斯认同感的重要一环。[注][英]杰佛瑞·帕克、[英]布兰达·帕克:《波斯人》,苑默文、刘宜青译,新北:广场出版2017年版,第145页。在中世纪,波斯语是伊朗各民族文化名人创作和交流的媒介,波斯诗歌和波斯文学成为各民族传诵的对象,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王朝也深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伊朗各民族对国家的忠诚不再基于土地,而是基于波斯语言和文化。伊朗史专家阿尔玛贾尼(Yahya Armajiani)将波斯文化的凝聚作用称为“文化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波斯人和其他各民族在“文化主义”中找到了认同。[注]Yahya Armajiani, Ira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2, p. 86.
(二) 伊斯兰教和什叶派的凝聚作用
伊朗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朗总人口的90%左右。尽管伊朗多种宗教并存,但从信徒比例来看,穆斯林和什叶派信徒占据绝对优势。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伊朗是宗教信仰相对纯粹的国家。伊朗以什叶派立国始于萨法维王朝,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之前,伊朗高原四分五裂,各民族相互攻伐,一盘散沙。萨法维统治者以什叶派为纽带,将伊朗各民族打造成为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伊斯兰教史学家认为,以什叶派为国教,使伊朗有力量抵御邻国的扩张势头而获得生存,这是自7世纪以来第一次以波斯民族占主体的国家独立于世,它以什叶派的形式保留了波斯文明和波斯民族的独特性格。[注]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此后,什叶派深深扎根于伊朗人的心中。兹举一例,伊朗众多男性都以什叶派伊玛目阿里、侯赛因、哈桑和礼萨之名为名。据统计,伊朗男性人名最多的是阿里、侯赛因和礼萨,其中名字叫阿里的男性占伊朗男性总数的十分之一。[注]杨涛、张立明:《伊朗概论》,第115页。什叶派教义作为伊朗大多数民众的共同信仰,是联结伊朗大多数人民的纽带,同时也是伊朗国族认同的重要来源。
(三) 伊朗政府应对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措施
伊朗各民族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还得益于伊朗历届政府灵活务实的因应民族分离主义、打造国家认同的措施。
第一,对分离主义思想和运动保持高压态势。面对少数民族分裂运动,伊朗历届政府皆主张使用强硬手段,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库尔德人是20世纪伊朗民族分裂运动的最大祸源,先后三次掀起叛乱高潮,皆遭中央政府镇压。
第二,拆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减少地域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各省面积辽阔,人口众多,且多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难以管控。巴列维王朝采取大而化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拆分地方行省,分割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为了消除一些省份的地方主义和民族内涵,各省只设数字代码,不授予具体的省名。[注]H. E. Chehabi, “Ardabil Becomes a Provinc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 in Iran,” p. 238.阿塞拜疆省是阿塞拜疆人的聚居区,礼萨·汗将阿塞拜疆拆分为第三省和第四省。二战后,两省被短暂合二为一。1958年,伊朗政府再次将阿塞拜疆省一分为二。此次阿塞拜疆省的再分被广泛视为伊朗政府将阿塞拜疆人“分而治之”的一次尝试。继阿塞拜疆省之后,其他民族聚居区也被陆续拆分。第八省的东部地区从克尔曼分离,建立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第七省(法尔斯)被拆分为法尔斯、布什尔和博耶尔·艾哈迈迪。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地方行省的数量已经增至24个。[注]H. E. Chehabi, “Ardabil Becomes a Provinc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 in Iran,” p. 238.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沿袭前王朝拆分民族聚居区的政策。1990年科吉卢耶博耶尔—艾哈迈迪从胡泽斯坦分离建省,1993年阿尔德比勒从东阿塞拜疆分离建省,2004年伊朗政府将呼罗珊省拆分为南呼罗珊、北呼罗珊和拉扎维呼罗珊。[注]分治少数民族并非推动伊朗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的唯一因素,尤其在当今社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信息互动和文化交流等或许显得更为重要,但拆分民族聚居区的确起到了将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效果。
第三,身份证和户籍管理不设民族身份识别。民族身份只是伊朗民间交往的个人习惯,出生证明[注]伊朗人的户籍证明,类似于中国的户口本。、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不显示个人的民族信息,以此淡化民族身份认同。
第四,利用伊斯兰认同削弱少数民族认同。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霍梅尼曾就伊朗少数民族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库尔德人、卢尔人、突厥人和俾路支人等民族不应该被称为少数民族,因为这个词本身意味着这些兄弟之间存在差别,然而伊斯兰教完全不存在这种差别。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穆斯林是没有差别的,譬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就没有差别。少数民族问题是由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刻意制造的,他们不希望穆斯林国家获得统一……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问题,可这些问题违背了伊斯兰的教义”[注][伊朗]霍马·卡图简、[英]侯赛因·沙希迪:《21世纪的伊朗:政治、经济与冲突》,李凤、袁敬娜、何克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76页。。霍梅尼强调穆斯林皆兄弟,企图利用宗教的同化作用抵消各民族的差异,削弱少数民族认同,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强化伊朗国家认同。
第五,伊朗各民族通婚基本没有障碍。不论在伊朗上流社会、还是寻常百姓之家,民族身份不成为彼此通婚的鸿沟。巴列维国王的第二任妻子苏拉娅来自巴赫蒂亚尔族。[注][法]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张许苹、潘庆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父亲是阿塞拜疆人,其母则是波斯人。不论在前王朝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伊朗民族通婚不存在政策层面的禁忌或限制,婚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第六,选拔官员不论民族出身,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官员在伊朗政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官政要屡见不鲜。其中,阿塞拜疆人尤为出色,涌现众多开国元勋和知名人士。譬如,共和国首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前总理穆萨维(Hossein Mousavi)、前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帕尔维兹·达沃迪(Parviz Davoudi)、伊朗能源部长帕尔维兹·法塔赫(Parviz Fattah)、伊斯兰革命卫队前司令叶海亚·萨法维(Yahya Safavi)和原子能组织前主席吴拉姆·礼萨·阿加扎德(Gholam Reza Aghazadeh)等。[注]Marat Grebennikov, “The Puzzle of a Loyal Minority: Why Do Azeris Support the Iranian State?,” p. 72.现任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Bijan Namdar Zangeneh)是库尔德人,他政治生涯履历颇丰,在伊朗历届内阁中9次担任部长,时间长达32年。
正是在上述措施基础上,伊朗成功构建了以波斯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但伊朗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也为国家认同的弱化埋下了隐患。
第一,波斯人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加深了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鸿沟。巴列维王朝的民族政策带有明显的波斯霸权主义特征,忽视或压制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权利。礼萨·汗主张建构波斯民族的历史,宣扬古代波斯文化,波斯语作为国语通行全国,学校、政府、报刊和出版书籍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公共场合不允许穿少数民族服饰。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经济发展差距尤为显著。巴列维王朝重视对波斯人聚居区的建设,少数民族世居的边陲地区则被忽视。礼萨·汗统治后期,伊朗政府在波斯人居住的中北部地区建设了20座工厂,而在阿塞拜疆地区仅有2座。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的边疆地区继续遭到边缘化。至伊斯兰革命前夕,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居住的省份在医疗、教育和收入水平上远低于波斯人居住的省份。在波斯人聚居的中部地区,贫穷人口有20%,而在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超过30%,俾路支斯坦则高达70%。进入共和国时代,波斯人与非波斯人的差距仍未改善。1999年的联合国报告指出,库尔德斯坦是伊朗婴儿死亡率最高的省份,俾路支斯坦则是伊朗成人识字率最低的省份。[注]Keith Crane, Rollie Lal and Jeffrey Martini, Iran’s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ies, 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 2008, pp. 46-47.长期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使伊朗少数民族积怨甚深。2005年伊朗伊斯兰议会所属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当前伊朗在民族问题上面临两大挑战——少数民族地区青年人失业问题和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并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能审慎处理少数民族提出的要求,伊朗将面临严重的内部稳定问题。[注]杨涛、张立明:《伊朗概论》,第72页。长期以来,伊朗少数民族与波斯人政治权力失衡,经济发展差距显著,易滋生不满情绪,从而弱化国家认同。
第二,伊斯兰政府以什叶派为纽带打造国家认同,压制宗教少数派,使非什叶派民族与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伊斯兰政府试图利用宗教的同质化作用培育国家认同,弱化少数民族认同。该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在强化什叶派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引起了非什叶派民族的不满。自革命以来,非什叶派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迫害和歧视。例如,伊斯兰政府将巴哈伊教徒视为异教徒,肆意戕害。20世纪80年代政府曾处决200余名巴哈伊教徒,监禁600余人。逊尼派民族遭受宗教和民族双重歧视。[注]Keith Crane, Rollie Lal and Jeffrey Martini, Iran’s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ies, pp. 42-43.伊斯兰政府强调什叶派认同,歧视和迫害宗教少数派,伤害了非什叶派民族的情感,对伊朗的国家认同不利。
尽管存在国家认同弱化的诸多隐患,但总体而言,伊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阿塞拜疆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阿塞拜疆民众对伊朗国家具有高度认同感。[注]Marat Grebennikov, “The Puzzle of a Loyal Minority: Why Do Azeris Support the Iranian State?”.两伊战争中,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青年自愿走上战场,肩负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阿尔德比勒的阿塞拜疆商人自发向士兵和革命卫队输送给养,只需要一句祝福作为回报,后来被全国各地的商人效仿。[注]H. E. Chehabi, “Ardabil Becomes a Provinc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 in Iran,” pp. 240-241.伊朗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也表现出高于本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感。在两伊战争期间,尽管萨达姆一再号召阿拉伯人反抗伊朗中央政府,但收效甚微,大多数阿拉伯民众首先认同自己是伊朗人,其次才是阿拉伯人,并未倒戈相向。俾路支人对伊朗的国家认同也较为强烈。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政府采取压制和安抚并用之策,既加强对俾路支人的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俾路支人的经济文化要求。俾路支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对良好,没有出现大范围分离主义的迹象。从俾路支人内部来看,逊尼派宗教领袖、各政治团体以及反对派军事组织,大都不支持分离主义,而是主张在伊朗国内追求有限的政治自治和权力共享。[注]苏欣:《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第45页。库尔德人是伊朗最棘手的民族问题。相较伊朗国内其他民族而言,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最为严重。二战结束后,库尔德人一度裂土建国。两伊战争期间,部分库尔德人接受伊拉克的军事援助,反抗伊朗中央政府,趁机谋求自治或独立。但从历史上看,伊朗库尔德人的叛乱多是外国势力与库尔德高层相勾结的产物,大部分库尔德人并不主张谋求独立。正如伊朗民族问题专家卡维赫·巴亚特所言:“对于大多数库尔德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逃避税收、兵役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控制政策,只有一小撮库尔德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谋求自治或独立。”[注]Kaveh Bayat, “Iran and the ‘Kurdish Question’,” p. 29.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领袖亦反对分裂,如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谢赫·伊兹丁·胡塞尼曾公开宣称:“我们是伊朗人,我们不会从伊朗分离。库尔德人和波斯人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雅利安人。”[注]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从现实来看,伊朗库尔德人势单力薄,内部矛盾丛生,不具备凭一己之力挑战中央政府的实力。可以预见,未来库尔德人仍将是伊朗国内少数民族生乱的主要隐患,但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库尔德人难以对伊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构成实质性挑战。
四、 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建构的启示
有学者提出,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还是新近建立的国家,国家认同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举足轻重且随时代不断变化的问题。[注]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第8页。由此可见,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具有普遍性的难题。通过对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建构的分析,可以从中得出对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治理的几点有益启示。
第一,树立国家政治认同高于少数民族认同的理念,少数民族应首先认同国族的集体概念和国家精神,其次才是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认同。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信仰、语言和服饰等多元各异,异质文化意味着差异,过多的差异易使国家缺乏凝聚力。少数民族认同过于强势,多民族国家就可能“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而国家认同强于族群认同,多民族国家便容易维持统一。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为了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必须把国家认同置于首位,不能让族群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注]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08-109页。
第二,结合刚性的政治手段和柔性的文化手段,强化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建立国家认同的内部同一性。国家认同包括个体对国家主流传统文化、信念的认同以及个体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认同。[注]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第9页。巴列维王朝之前,伊朗中央政府孱弱,地方部落离心离德,对国家的主流文化与政治权威缺乏认同。自礼萨·汗时期以来,伊朗不断树立和强化政治权威,对民族分离主义实行强制性打压,同时通过一系列文化整合政策,建构或宣扬传统文化,强化民众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从而强化了国家认同。
第三,确立主体民族优势地位,同时兼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保证弱势族群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和社会发展红利的分享权。在伊朗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受限、经济发展滞后以及语言文化权利遭到压制,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致使伊朗国家认同存在弱化的隐患。有学者认为,国家内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多少是影响国家统一的关键变量,要想使各民族实现团结互助,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各民族共同利益越多,国家就愈稳固,反之亦然。[注]孙凯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91页。因此,在实现国家总体发展的同时,要确保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社会发展红利的分享权。少数民族具有获得感,才会对国家拥有认同感。
最后,伊朗承认国内各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伊朗民族治理的核心在于弱化和淡化差异、不人为打造或构建差异,致力于消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各民族向“和而不同”的方向发展。伊朗政府通过推广波斯语、实行民族服饰改革、身份证明不设民族识别以及清除各民族通婚障碍等措施,旨在淡化各民族的差异,促进各民族的同质化。费孝通先生指出,世界各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即“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由此可见,国族形成和发展的趋向在于弱化和淡化国内各民族的差异,促进民族间的交融,而不是维持、固化或人为构建差异。
五、 结 语
自古以来,伊朗各民族交往频繁,在伊朗大地上轮流建立王朝,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文化多元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特征。尽管多次遭遇外来民族的冲击与征服,但伊朗的文明一脉相传,文化认同根深叶茂,国家认同相对强烈,在族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显得非常特殊。
经过近百年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当代伊朗的国族认同价值体系已深入人心,各民族对伊朗的国家认同较为强烈。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滞后以及语言文化受限,部分少数民族对伊朗政府的不满情绪亦有所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管控,少数民族开始表达对自身贫穷、落后、缺乏地方自治权以及政府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不满。各民族提出了众多共同要求,包括保护地方语言文化、平等的就业和职业晋升机会、共享地方管理权以及分享各省收入等。由此观之,当今伊朗的民族问题已发生深刻变化,其主要方面不再是少数民族谋求分裂和独立,而是各民族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发展和文化自由等权利,换言之,是权利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创造公平、自由、共同繁荣的社会环境是当前伊朗加强民族凝聚力、夯实国家认同基础的有效途径。至于伊朗国家认同的持久性,伊朗社会史专家阿塔巴克对伊朗未来是否会爆发族群冲突的观点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他指出:“伊朗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或许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确保个人和集体在公平获得经济发展机遇、扩大政治参与度以及提高文化地位等诸方面的权利。否则,一切皆有可能。”[注]Touraj Atabaki, “Ethnic Divers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Iran: Domestic Harmony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pp. 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