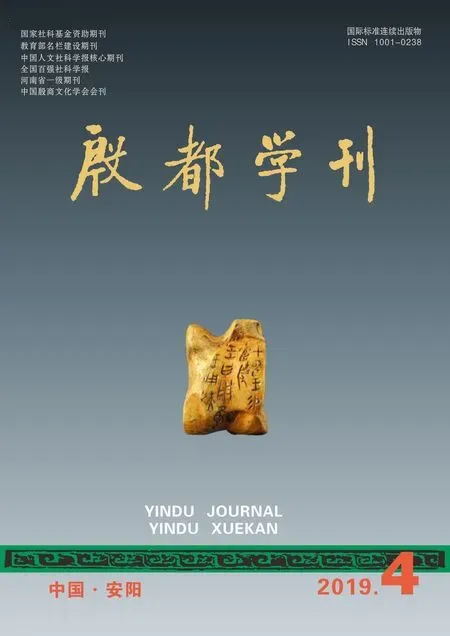《文昌杂录》所见入閤仪与北宋文德殿视朝仪研究
李 欣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目前学界对“閤门”、“ 閤门司”、“入閤仪”等问题的考察,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如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1],对閤门司作了详细的分类和解释;赵冬梅有两篇论文对閤门官员进行了专门研究,《试论宋代的閤门官员》[2](P107—121)主要从武选官担任閤门官等职来阐述宋代武选官的三途分立,另一篇《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3](P128—131),主要论述唐宋閤门司沟通君臣、朝会赞引等功能;周佳《沟通内外:北宋閤门的位置与功能考论》[4](P93—108),通过对比唐宋“閤门”、“ 閤门司”,论述北宋“閤门”位置的重要性,以及“閤门司”是宋代“防弊之政”的组成内容之一;束宝成《论宋代閤职》[5](P99—102),从宋代閤门司长官、“閤职”官员的设置、“閤职”武臣清选等几个方面探讨宋代閤职对维护君主统治的地位和意义;李芳瑶《论北宋时期的“入閤仪”》[6](P32—39),以北宋前期张洎、宋庠、欧阳修三人对“入閤仪”的论述为切入点,探讨北宋“入閤仪”的源流;任石《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7](P90—98),主要从唐后期至五代、北宋前期两个时间段分析北宋入閤仪的演变。虽然已有相关文章论及北宋入閤仪,但是更注重论述五代至北宋前期“閤职”、“閤门司”的演变与发展,一些地方仍存在着薄弱环节,对北宋“入閤仪”,尤其是“入閤仪”的程序与变化,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文昌杂录》是北宋庞元英任尚书省主客郎中时撰写的一部笔记。庞元英,字懋贤,北宋单州成武(今属山东菏泽市成武县)人,为宰相庞籍第四子,恩荫入仕。《文昌杂录》内容庞杂,其材料多来自作者亲身经历、古代史籍、他人转述。书中叙事简略,但详于章表、奏敕及书檄,论及典章制度、风土民俗、诗文典故、文人轶事等。其中尤以典章制度内容最为丰富,对元丰改制前后官制、礼制的变化记载颇为详致,可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相互补正。
一、北宋閤门与入閤仪
要研究入閤仪,首先应了解“阁”、“ 閤门”的定义以及北宋“閤门”的位置,从而进一步探讨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视朝仪。
(一)“阁”与“閤”、“閤门”
“阁”,据《王力古汉语字典》有“阁道;古代公众藏书室”等,但仅作中央官署时与“閤”通。“閤”,段玉裁对《说文》中的“閤”作注文:“按汉人所谓閤者,皆门旁户也。”[8](P587)又《尔雅义疏》:“是则閤有东西,随所在以为名,后世辅臣延登谓之入閤,或称‘閤下’,义本于此。作‘阁’非。”[9](P1556—1157)由此可知,“阁”、“閤”二字不可等同,閤门就是正门旁边的小门,即侧门。
《云麓漫钞》对北宋“閤”与“閤门”的概念曾有辨析:
参诸众说,则閤者,殿后之便室无疑。本朝殿后皆有主廊,廊后有小室三楹,……先坐此室,俟报班齐,然后御殿……室之左右小廊通处,即閤门。[10](P48)
由此可知,唐宋时期“閤”基本含义是后殿便室,“閤门”即是便室连接东、西正廊之门,成为“东西閤门”。
唐宋时期,閤门是连接外朝与内朝的“咽喉”通道。根据唐代皇城布局,“正殿与便殿之间均设有閤门”[11](P112),随着皇帝起居地点的变化,朝参的地点也发生了变化,皇帝朝会由前殿逐渐后移,前殿视朝之仪式亦经东、西閤门入便殿,即入閤,而入閤真正成为相对稳固的朝拜仪式,是在唐玄宗以后[12](P2022)。《文昌杂录》卷三亦载:“开元中,……唤仗入閤门自此始也。”[13](P152)玄宗认为朔望日亦是太庙荐食之日,为表思政之意,也应退正殿,令大臣至紫宸殿(即内殿)朝参,自此,“唤仗入閤”仪式开始。閤门关乎朝会等重大政治活动,具备礼仪、政务双重功能,因而閤门位置显得尤为重要。
(二)北宋“閤门”的位置、概念
对于唐代閤门位置与含义的界定,可以参考贺忠、金程宇《唐代入閤礼仪考索》、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等文章。相对于唐代,宋代閤门的位置与概念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本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殿。”[14](P331)可见文德殿在外朝,垂拱殿,紫宸殿、崇政殿等在内朝。庞元英《文昌杂录》对唐宋皇城之变化亦略有记载:
朝廷承五代之弊,名式未正;文德殿东西有上閤门而无上閤。按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谓正衙。紫宸殿直其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东偏;文德殿东、西但有上閤二门,未审以何殿为上閤。谓宜参详典故,正上閤之名,以复有唐盛事焉。[13](P182)
北宋皇城基本上呈正方形,皇城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东、西华门之间有一条横街,将皇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外朝,包括文德殿、大庆殿;北部为内朝,包括垂拱殿、紫宸殿、崇政殿。另外,垂拱殿坐落于文德殿的正北方向,紫宸殿坐落于大庆殿的正北方向,崇政殿又位于紫宸殿的东北方向。《文昌杂录》有“文德殿东、西有上閤门而无上閤”[13](P182),并且文德殿的东、西上閤门位于横街南侧,垂拱殿与文德殿之间有柱廊联通[15](P83)。
由于北宋君主权力进一步强化,君主更注重增强对日常政务的操控权,白钢在《中国皇帝》一书中也指出,在宋太祖之前,是“皇权相对独裁时期”,宋太祖之后,是“皇权绝对独裁时期”[16](P162),这种“独裁”反映在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在:首先,不仅采用日朝制度,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奏事的官员范围也随之扩大。其次,皇帝对政令文书的裁决权增强。再者君主掌握的信息渠道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形式上都更加多元化[17]。表现在听政空间上,那就是更加趋于内朝化,主要以垂拱殿为中心[4](P97)。关于北宋“閤门”涵义的界定,周佳在《沟通内外:北宋閤门的位置与功能考论》将其分为三层含义:第一,是“入閤礼”。宋初,将“入閤礼”作为文德殿月朔视朝的重大典礼,后因“入閤礼”名实不符,到神宗熙宁年间正式被废除。第二,指文德殿两侧的东、西上閤门。第三,指垂拱殿门[4](P98—100)。
笔者认为,北宋“閤门”应为垂拱殿门。《长编》:“群臣上尊号册于大庆殿,太尉奉册授閤门使转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进。”[18](P5073)上尊号礼时,“由垂拱殿以进”表明垂拱殿门是当时进入内朝的正式通道。《长编》《宋史》在《孔道辅传》中有“诣垂拱殿门”、“诣垂拱殿伏奏”。[18](P9884)此内容记载非常明确,所谓北宋的“伏閤上书”与“伏閤请对”的“閤门”就是垂拱殿门。随着閤门的确立,“唤仗入閤”作为一种朝会仪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皇帝的权威性,也因此备受皇帝与大臣们的重视。
(三)北宋入閤仪至文德殿视朝仪
李芳瑶在《论北宋时期的“入閣仪”》一文中提到,五代时期是“入閤”变为“入閤仪”的关键时期,五代之前,常朝仪仗并不是特别隆重的仪式,因此《唐六典》等文献只记载“入閤”而非“入閤仪”。唐末至五代时期,“入閤”被赋予特殊仪仗形式的代称,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仪式[6](P35),至此,文献中出现“入閤仪”。
北宋太宗、仁宗朝,大臣对入閤仪进行修定,引起了对“入閤”源流等问题的一系列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欧阳修、张洎、宋庠。根据《长编》等古籍记载,欧阳修认为唐代皇帝“常参”地点为宣政殿,“入閤”即入紫宸殿;张洎对于“入閤”的含义与欧阳修相似,但也指出唐代没有“常参”制度;宋庠对“入閤”源流又与张洎相仿,即“入閤”是唐代皇帝平日视朝的制度。庞元英在《文昌杂录》对“入閤”源流的相关问题也作了解释,认为唐代常参时皇上入便殿,唤仗入閤由此开始,之后不入前殿,入閤仪也随之废弃。“入閤”包含着繁杂的常朝礼仪,其涵义经过了一系列的转变,至熙宁三年(1070)五月终因众多弊病被废止,六月九日修《閤门仪制》,宋敏求上言:“本朝以来,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视朝。今既不用《入閤仪》,即文德遂阙视朝之礼。欲乞下两制及太常礼院,约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文德殿仪,以备正衙视朝之制。”[19](P2313)自此,文德殿视朝仪注得以修订。又《文昌杂录》:“今上熙宁五年,方讲朔日文德殿视朝立仗之仪。”[13](P145)熙宁六年(1073),神宗又制定了“朔御文德,望坐紫宸”之仪,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代替了入閤仪。
二、《文昌杂录》载文德殿月朔视朝仪
熙丰年间,神宗仿《唐六典》对多项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包括文德殿入朝仪。《文昌杂录》所载文德殿月朔视朝仪即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视朝仪式,现将视朝仪按次整理如下:

表3-2 熙宁五年“文德殿视朝仪”[13](P145—151)
以上是《文昌杂录》记录的文德殿月朔视朝仪过程:正衙仗卫、文武臣僚先入文德殿依次分班对立恭候皇帝;皇帝靴袍至垂拱殿,内侍、枢密使等迎立;皇帝自后閤出,升坐于文德殿,群臣依次拜谒行礼,致辞祝月,之后依次退出;皇帝降坐乘撵还垂拱殿,中书、枢密及请对官凑事;如遇德音等,后殿再坐,临时取旨。另外,《宋史》载有太宗淳化二年“入閤仪”[20](P2766),《宋会要》载有仁宗景祐三年“入閤仪”[19](P2309—2311),笔者将《文昌杂录》所载熙宁五年“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与太宗、仁宗时期“入閤仪”对比,发现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仪式性”逐渐转变为“实用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唤仗入閤”这一顺序发生了变化,太宗、仁宗时期,皇帝正式升坐于文德殿后,由閤门使依旨唤仗入文德殿。而熙宁时期,正好相反,在皇帝至文德殿之前,衙仗与群臣已经提前分班入殿等候。由此一来,省去了皇帝升坐后各衙仗、大臣的入閤时间,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其二,将太宗、仁宗“待制、候对官奏事”转变成“转对官”奏事,文德殿月朔视朝仪成为转对官惟一能够依附的朝参方式[7](P96),将之前的“走过场”形式转变为实际奏事。总之,通过对比,神宗熙宁五年时期的文德殿月朔视朝仪比太宗、仁宗时期“入閤仪”更加注重务实。
《宋会要》仪制一对入閤仪亦有相关记载,二者对这一过程整体描述相似,但仍有差异,根据文德殿→垂拱殿→文德殿→垂拱殿→后殿的顺序,对比《宋会要》仪制一载熙宁三年“文德殿视朝仪”[19](P2313—2316)与《文昌杂录》载熙宁五年“文德殿视朝立仗仪”,现列举各殿举行仪式过程中的显著差异:
(一)文德殿
视朝仪之前,文德殿殿庭东面的布置情况:《文昌杂录》“金吾仗碧襕一十一,……兵部仪仗排列职掌二人,……告止幡一”,《宋会要》记载与此相异,“金吾仗碧襕一十二,……兵部仪仗排列职掌两人,……告止幡八”。[13](P145)《文昌杂录》缺《宋会要》对殿庭西面的介绍,但《文昌杂录》对慕次朝堂的百官介绍的更为详细。
(二)垂拱殿
皇帝御垂拱殿后,内侍等迎谒:《文昌杂录》“四拜起居讫,次呈进目客省閣门使、副使,……次殿前诸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并依朔、望常例”,《宋会要》在记录这一环节时,无“閤门副使”,并且将“殿前诸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用“管军臣僚以下”代替。
(三)文德殿
1.皇帝进文德殿前,文德殿的准备工作;《宋会要》指出,作为前导人员的是枢密、宣徽使等,并且是前导至文德殿后閤,然后各归殿上侍立,与《文昌杂录》记载的枢密使已下至閤门使、殿前都指挥使以下,并前导、至文德殿门相异。
2.皇帝自后閣进入文德殿时:《文昌杂录》“通事舍人一员就弹奏御史立位稍东西喝拜大起居”,《宋会要》则指出“舍人于弹奏御史班前西向”。二者对于通事舍人与弹奏御史的相对位置,记载略有不同。
3.文德殿致辞祝月:《文昌杂录》记载的是“仲春”,而《宋会要》在祝词中说的是“孟春”。
4.皇帝降座:皇帝降座,乘撵还内之时,舍人放仗,《文昌杂录》“四色官鞾急趋至宣制石位南,称奉勑放仗”,而“奉勑放仗”未见于《宋会要》。
(四)垂拱殿
对于皇帝再至垂拱殿之程式,《文昌杂录》与《宋会要》记载同。
(五)后殿
《宋会要》指出自垂拱殿出,或有后殿再座,宰臣按程序临时取旨,之后有赐茶酒、之后按仪制分班出,而《文昌杂录》对分班出这一过程则不载。
小 结
《文昌杂录》对改制时期的礼制,尤其是北宋文德殿月朔视朝仪节也有论述。在将其与其他传统史籍的对比中发现,《文昌杂录》记录虽有疏漏,但因当事人撰写当时事,其史料价值仍然很高。
通过对比,《文昌杂录》与《宋会要》记载文德殿视朝仪程序各详各细,并有部分记载相异,因此,二者在细节上可相互补充,相异之处又可进一步考证。另外,《政和五礼新仪》记载了徽宗政和年间的“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任石《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对政和年间视朝仪程式也作了叙述[7](P96),此处不再做过多分析。对比《文昌杂录》所载熙丰年间“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与太宗、仁宗时期的“入閤仪”,再与政和年间的“文德殿月朔视朝仪”,不论是程式步骤,还是仪仗规模,整个仪式过程趋向简化,“仪式性”减弱,“实用性”增强。

北宋开封宫城主要部分平面示意图(1)原图参见《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