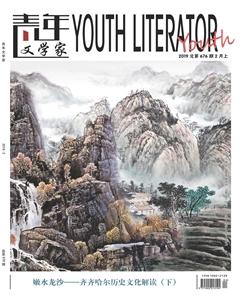品读卜奎
作为齐齐哈尔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齐哈尔历史文化与齐齐哈尔“自然、和谐、忠义、英勇”的城市精神、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鹤文化”一体,共同构成齐齐哈尔文化体系三要素。纵览改革开放40年的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研究,凑成四题,权当刍议。
称谓的泛用
齐齐哈尔历史文化探讨之热,莫过于近20年间。先是,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关于建城史的讨论。相继的,市委市政府多次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辽金界壕古迹踏查论证、启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并最终获得国务院批准、规划动议黑龙江将军府的复建、修缮了部分文保建筑、开展了江桥抗战等地方历史文化的学术交流,不一而足。由此引发的学者对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现象表述和界定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些表述和界定,大多冠以“齐齐哈尔”之名、“历史文化”之性,延展至齐齐哈尔社会各个层面和角落。
举例说来,从历史阶段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昂昂溪新石器文化”、“辽金文化”、“明清文化”等称谓;从地域土风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北疆文化”、“边疆文化”、“关东文化”等称谓;从自然特征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黑土文化”、“冰雪文化”等称谓;从民族构成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满族文化”、“达斡尔族文化”、“鄂温克文化”、“蒙古族文化”、“锡伯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称谓;从人口变迁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驻防八旗文化”、“流人文化”、“站人文化”、“水师营文化”、“官屯文化”、“移民文化”等称谓;从人文精神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以抵御外辱为主题的“抗俄文化”、“江桥抗战文化”,以创业为主题的“闯关东文化”、“装备工业文化”,以宗教为主题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称谓;从地方风物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玛瑙石文化”、“榆树文化”、“库木勒文化”等称谓;从文化遗产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萨满文化”、“木板书文化”等称谓;从民风民俗角度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衣着的“皮草文化”、饮食的“烧烤文化”、居住的“大草房文化”、出行的“勒勒车文化”等称谓;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表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出现了达斡尔“牧猎文化”、鄂温克“桦树皮文化”、蒙古族“马背文化”、回族“清真文化”,以及与少数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海东青文化”、“打貂文化”等称谓……。
如果不是专业从事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研究的人,大概不会涉足如此众多的历史文化领域。而如此众多的历史“文化”称谓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值得研究和探讨。以上罗列的这些“文化”称谓,也仅仅为笔者泛泛收集所得,尚有许多“文化”称谓因笔者眼界所限,没有列入其中。从发展趋势看,今后还将产生新的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称谓。
这难道不好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繁荣的表现吗?我以为,涉及领域如此之广的诸多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称谓的出现,是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研究现状在学术界的反映,并非坏事。然而,也无可否认,受“泛文化主义”思潮影响,有的“文化”称谓尽管冠以历史文化之名,但并不符合学术意义的历史文化界定;有的“文化”称谓虽然是历史文化,但涵盖面极广,并非齐齐哈尔所独具;有的“文化”称谓源流不清,尽管存在,却不符合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范畴;还有的“文化”称谓属于自然文化或属于精神领域范畴,与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关联不大,等等。反映在媒体、社会生活中,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潜移默化,其引领、辐射作用不可低估。基于此,亟需相关方面组织力量,厘清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称谓杂糅的状况,把具有齐齐哈尔特质的历史文化梳理、提炼并呈现出来,供学人参考、探讨和研究,供媒体传播、介绍和推广,供大众学习、使用和交流,这既是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现实文化发展的需求。
模糊的背影
多年以来,学界对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并没有规范性的表述,由此才出现了上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称谓的泛用。梳理这些文化称谓,核之以文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许多“文化”表述苍白无力,许多“文化”内容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除文字记载缺略外,也有考古发掘滞后、研究不够等原因。
对于齐齐哈尔的历史文化符号,大家存在着误解。许多人认为坐落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昂昂溪新石器文化是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殊不知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以五福遗址、藤家岗遗址为标志的昂昂溪文化,与半坡文化、周口店文化一样,是中国古代石器文化的一个类型,因发现于昂昂溪,因此被专家定名为昂昂溪新石器文化,同期同区域同性质的新石器文化均属于这种文化类型。因此,昂昂溪历史文化是世界的,不会因为坐落关系而被我们独享,在嫩江中上游,相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尚有多处。
对于齐齐哈尔的古代归属与源流,观点不尽一致,标准的表述一直悬而未决。大家公认,在没有定居居民活动、没有更多文化遗存的古代,齐齐哈尔地区是少数民族游牧弋猎的苑囿。尽管缺少准确的文字记载,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先贤和史志学家孜孜以求的考证下,齐齐哈尔古代归属和源流还是初露端倪。据《齐齐哈尔地名志》记载:齐齐哈尔“唐虞(夏商周)三代属肃慎,秦汉时为秽貊之地,后汉、三国属夫余国,晋属寇漫汗国,后魏属豆莫娄国,北齐、隋属黑水部,唐属黑水靺鞨(贞观中期属黑水府),辽属东京道长春州北边及东北部统军司伯斯鼻骨德部,金属蒲与路,元属斡赤斤,明属朵颜卫”。这一观点,明显采用了民国魏毓兰先生在《龙城旧闻》中的考证。与之不同的,《齐齐哈尔市志·综合卷》则表述为,齐齐哈尔“夏商周时期属索离国,秦汉时为夫余国属境,魏晋南北朝时期属鲜卑和豆莫篓,隋唐时期属室韦都督府管辖,辽代属上京路、东京路;金代属上京路、北京路;元代属辽阳行中书省所辖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明朝先归属大宁都指挥使司,后属奴儿干都司”。
翻检近年出版的其他史志书籍,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虽然出处和表述不尽一致,但大体相合。由于没有统一标准的认定,齐齐哈尔古代归属和源流处于各自各说的状态。研究民族史的人知道,東北少数民族源流为三大系,即,肃慎一挹娄一勿吉一棘鞨一女真一满族;秽貊一索离一夫余一豆末娄一高句丽、百济;东胡一乌桓一鲜卑一契丹、室韦一达斡尔族、蒙古族等。如果上述所说的齐齐哈尔古代归属和源流无误,那么无疑的,齐齐哈尔在明代以前曾经先后受到了三大族系的浸润。
辽代,齐齐哈尔是契丹人的边地。因缺少较为翔实的记述和考证,不论是历史面貌还是文化特征都非常模糊。据《析津志》、 《东北古代交通》等史志记载,从唐代以来,就有一条从齐齐哈尔附近出发,西南行三百五十里至淖尔河,西南行三百里至归流河,再南行一百五十里至老头山,而后绕道老头山东侧南行一百里,涉交流河,一百五十里涉霍林河,三百五十里涉辽河,又南行过努鲁尔虎山,四百五十里至今辽宁省朝阳市境,全程一千八百五十余里的古道。元代以吉苔(齐齐哈尔为中心),设置了向西、向北的两条驿路。
按照史书描述,向西的驿路是从设置在嫩江以东的驿站,过江至明安伦城(今梅里斯),西北行渡雅鲁河经金代界壕(在雅鲁河、济沁河交汇处),然后横过兴安岭到伊敏河流域,抵达地点是阿木哥大王府所在地(今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总计14个站点。清代所建从呼伦贝尔至齐齐哈尔的驿路,基本与此吻合。
向北的驿站,则是承接西祥州站(吉林农安),经泰州站(塔子城)、吉苔站(齐齐哈尔)、牙剌站(今富裕塔哈)、苦怜(今讷河县拉哈),抵达失宝赤万户府(失宝赤译为鹰官,今孙吴县霍尔莫津),清代所建吉林至黑龙江城的驿路基本与此路吻合。吉苔真的是齐齐哈尔吗?如果是,那么具体位置是哪里?是什么样子的驿站?史志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既然是驿站,也许连村落的规模都算不上吧。
金代,有一条东起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蜿蜒向西、向南延伸万里至包头市东黄河北岸的土石材质的“墙”,被学者们称为金界壕、金源边堡、金长城。清代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则称之为“乌尔科”。据专家考证,金界壕经过的今齐齐哈尔之地,约二百余公里。在这一地理范围内,有哈拉、洪河、罕伯岱、丰荣、沙家街等数座辽金时期古城遗址。这些以戍边为目的屯兵城堡,元代前期,在蒙古铁蹄蹂躏下,最终成为片片瓦砾。延至明代,齐齐哈尔作为松嫩平原与兴安岭过度地带,森林、草原、濕地遍布,定居居民很少,至明成为达斡尔、锡伯、卦勒察等少数民族游牧弋猎之地。清顺治年间,沿嫩江两岸绵延六百里,居住着从黑龙江流域迁来的达斡尔和鄂温克人。直到康熙中叶齐齐哈尔城筑建后,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人烟辐辏之地。
以上是齐齐哈尔归属和源流的大致勾勒。在如此模糊的历史背影中,如果说辽金文化是齐齐哈尔的特质历史文化,那么,与哈尔滨(阿城)的金源故里文化相比,我们显然感到中气不足。假如把辽金文化确定为齐齐哈尔特质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很难展示出更多的文化现象、文化遗存、文化符号。仅凭塔子城、蒲与路等几座文化遗址来表达,是难以企及的。
多重的特质
当年,从我市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计划启动伊始,相关工作一直受到市内许多学者,特别是部分地方史专家的关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申报方案如何表述我市的历史文化脉络;第二、申报方案如何呈现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第三、文物建筑保护状况是否能够达到验收标准,等等。很明显,与申报工作相关的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内容急需厚重的研究成果展示;过去一些不曾深入思考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脉络纵横,哪些是“主动脉”和“静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具特质的历史文化?如果这些独具特质的历史文化被我们所认知,那么,这些历史文化的脉络我们是否已经把握?底蕴和精髓是否已经吸收?研究和展示是否已经开始组织实施?学界和大众是否接受和认同?
把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端点放在哪里?历史文化的研究力量投放在哪些领域?我以为,既然是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城而论,当实事求是地立足于清代,以康熙三十年(1691)齐齐哈尔建城为基点,适当延伸。特质历史文化的主攻方向,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这个文化,是极具齐齐哈尔特质的历史文化,涉及古今满、蒙古、达斡尔、鄂温克、回、锡伯、巴尔虎、卦勒察、厄鲁特、柯尔克孜等多个少数民族,研究领域跨越了民族史、地方史和文化史,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大、链条长,受到的关注度较高,以齐齐哈尔各少数民族学会为单位,可以组织或参与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活动,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
清代驻防八旗文化。这个文化,仍然与民族文化有关。从康熙三十年(1691)伊始,齐齐哈尔成为满、达斡尔、鄂温克、锡伯、巴尔虎、汉军等八旗披甲驻防城池,驿站、水师营、官屯隶属八旗。在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副都统统辖下,齐齐哈尔城与黑龙江城(今爱辉镇)、墨尔根城(今嫩江县)、呼伦贝尔城等一体,成为捍卫大清北部边疆安全的屏障。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历时200余年完结,形成了新满洲文化。
流人文化。齐齐哈尔流人的组成,除因犯罪而发遣至此的官员、百姓外,也有水师营营丁、驿站站丁、官屯屯丁。不仅有汉族,也有满族、蒙古族、回族,甚至有宗室、觉罗、外国人。从总体上看,流人文化是以汉族人为主体植根齐齐哈尔这片土地,结合地方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汉文化。流人现象消失于清末,但文化影响深远。清代以降,齐齐哈尔历经民国变乱、日伪统治,至解放后形成了移民文化、老工业基地文化至今。
宗教历史文化。齐齐哈尔宗教文化原以萨满教为主。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传入后,各教互施影响,宗派林立,经久不衰。至民国年间,以教派为依托,还形成了一特殊慈善组织一一五教道德院。这些宗教活动,虽然在建国后一度中断,但在新时期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指引下,大多恢复并走上了发展轨道。极为难得的是,许多宗教场所古迹留存下来,文化符号清晰,值得研究。
笔者不揣冒昧,将个人所见和研究心得呈现给大家,狭隘与浅薄在所难免。
收藏的背后
在我所收藏、参考、引用的图书之中,有关达斡尔族方面的占有一定比例。其中有自己购买的,也有许多专家赠予,这些书籍对于笔者研究达斡尔族历史文化颇有裨益。2011年8月11日,在省、市达族学会的倡导下,全国20余家达斡尔族学会与省鄂温克族学会、柯尔克孜族学会百位民族史、文化史、地方史专家、学者齐聚鹤城,纪念清代达斡尔族筑建齐齐哈尔城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共同见证达斡尔族同胞为先贤孟额德、玛布岱碑揭幕。我常想,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少数民族学会,能够坚持30年有计划、不间断地组织民族历史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并且取得累累硕果,这里面,既有民族凝聚的力量,也有文化渗透、传承的因子。
我藏书的另一个系列是地方文史资料,清点一下,总计六大部分,数量不少于千册。第一部分是齐齐哈尔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志书、志稿、史料文集;第二部分是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刊物和出版的各专门史料;第三部分是市档案馆编印的档案资料;第四部分是市委党史委编印的党史资料;第五部分是齐齐哈尔市社科院编著的齐齐哈尔历史丛书。其余還有一部分是部分县(市)区编印的文史资料、志书等。这些书刊,很少一部分为近年出版、编印,绝大部分是上个世纪八80代至90年代的出品。每每查阅资料,翻看着这些由卜林、谭彦翘、陈志贵、孟昭星、杨优臣、曹志勃、刘佩霖、王延华、刘玉和、胡绍增、邵哲文、兰殿君、林伯平、张港、张振华、徐晓慧、辛健、李继武等诸位先生著述或编撰的书籍,内心往往涌出崇敬之感。而今,有的地方历史文化学者已经故去,有的年事已高,但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未减,需要代代相传。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那个年代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多的文史书籍精品,除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解放的环境因素外,齐齐哈尔市整体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规划、学术机构的研究空气、社科课题的支持力度均是空前的。当时曾有市政协编印的《齐齐哈尔文史资料》、市志办编印的《齐齐哈尔史志》、市档案馆编印的《齐齐哈尔档案》、市党史委编印的《齐齐哈尔党史资料研究》、市社科联编印的《齐齐哈尔社会科学》等多种内部期刊支撑着全市的历史文化研究!然而,转型期的政策性调整产生了断裂,市内各专业文史刊物无一幸存。
展望未来,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在建设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氛围中,真诚希望相关方面能够把齐齐哈尔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重视起来,给予全力的支持,组织力量编著更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精品,使齐齐哈尔历史文化名城之称能够符合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名。
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活跃气氛的启发和影响,2009年,为发挥高校在传承、发展、引领区域文化方面的作用,齐齐哈尔大学提出了建设“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产学研基地”的战略构想并建立了“嫩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与市政府签订了文化传承与发展框架协议,成立了校地合作委员会,陆续开展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流人文化、鹤文化等专项研究工作。2010年6月,该中心被黑龙江省教育厅批准为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些地方历史文化课题研究正在逐渐展开,成果令人期待。
齐齐哈尔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厚重的,市内部分组织、专业机构及有识之士对我市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的。如何正确导引学术力量围绕我市科学发展的大目标,投身和服务于我市历史文化研究的新任务、新课题,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