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创建初期的五位指挥(下)
宫宏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即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但中外学界所聚焦的大多是梅百器(Mario Paci)1919年接手后的工部局公共乐队,对梅氏的几位前任及其事工却大都语焉不详。本文将视野投向工部局公共乐队草创时期的五位指挥,意在考察清末民初西洋专业乐人在沪的经历,重构晚清上海西洋音乐图景。
三、菲利克斯·斯特恩伯格(Felix Sternberg)——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任期最短的指挥
由于维拉意料之外的辞职,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指挥,所以决定临时聘用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德国钢琴家菲利克斯·斯特恩伯格(Felix Sternberg)担当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合约最初为六个月。由于斯特恩伯格的工作令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非常满意,在1899年7月致工部局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哈同(S.A.Hardoon)等管理委员会委员建议“订立一个由斯特恩伯格先生担任乐队指挥的长期聘约”,并且高兴地提到“现有的乐队人员是所能雇请到的人当中素质最好的”。①但是,工部局当局觉得短期合约比较合适,并于同年9月为其续约六个月。②1900年初,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向工部局董事会提出建议,希望将斯特恩伯格担任指挥的协议续约一年。起初,斯特恩伯格对这样临时性的合同和薪资不太满意,不准备签这个短期协议,但在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在“不再提供额外津贴的情况下每月工资增加到175两白银”后,他决定继续担任指挥。不过,就在斯特恩伯格考虑是否接受合同的时候,工部局董事会已决定“明年聘请一位新的指挥以替代斯特恩伯格”。所以此一任命只持续了一年,到1900年12月31日,工部局决定不再与斯特恩伯格续约。尽管乐队委员会成员罗达对斯特恩伯格的才能评价甚高,不同意免除斯特恩伯格的职位,并警告“工部局在物色一位要求他能满意地完成许多任务的乐队指挥时会有巨大困难”③,但工部局董事会不为所动,执意从英国聘请专职指挥。④
斯特恩伯格虽然是1899年3月才被正式任命为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的,但他在这之前就活跃在上海租界的乐坛。斯特恩伯格出生何时、来自何方、他的生平及音乐背景以及何时到上海等细节现已无法查考,但《北华捷报》的消息表明,他在任工部局指挥之前在上海不仅举办过钢琴独奏音乐会,从1898年开始,他还多次参加上海乐人的各类音乐活动。如1898年12月在兰心大剧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作为专业钢琴家的他就娴熟地弹奏了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给上海的听众留下了极佳的印象。⑤在同月16日举办的斯特恩伯格的个人音乐会上(见图7),他为上海的外侨听众献上了亨德尔的《广板》,莫扎特的《主题与变奏》、《A大调第11号钢琴奏鸣曲》中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斯卡拉蒂的《田园》《即兴曲》,施特劳斯/陶西格(Carl Tausig,1841—1871)的《华尔兹随想曲》,舒伯特的《鳟鱼》,莫什科夫斯基(Moritz Moszkowski,1854—1925)的《西班牙随想曲》《马祖卡舞曲》,李斯特的《匈牙利幻想曲》,肖邦的《前奏曲》《即兴曲》《波罗乃兹舞曲》(也称《英雄》)等钢琴独奏曲。在当晚的音乐会上,他还演奏了他自己作曲的《加沃特》舞曲。在1899年1月6日举办的第二次个人音乐会上,斯特恩伯格又演奏了贝多芬的《D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降B大调即兴曲》《军队进行曲》、鲁宾斯坦的《G小调船歌》、李斯特的《降D大调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等。在同年3月和5月举办的音乐会上,斯特恩伯格演奏的节目包括尼科莱(Otto Nicolai,1810—1849)、肖邦、戈达德(Benjamin Godard,1849—1895)、李斯特、门德尔松、莫什科夫斯基、布鲁赫(Max Bruch,1838—1920)的钢琴独奏和重奏作品。⑥

图7 《北华捷报》上刊登的斯特恩伯格钢琴独奏音乐会节目单(1898年12月10日)
与他的几位前任一样,斯特恩伯格除自己举办音乐会外,也积极参与上海外侨的业余音乐活动,特别是寓沪德侨的音乐会活动。1899年5月,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寓沪德侨成立了由男女各20人组成的“德国合唱社”(The Deutscher Gesang Veran,or the German Choral Society),并在同年5月25日在共济会堂举行了首场音乐会。该会的目的是排演和介绍德奥古典音乐作品。在25日的演出中,他们成功地上演了克莱科么尔(Edmund Kretschmer,1830—1908)的歌剧选曲、门德尔松的无伴奏合唱《再见了,森林》(Abschied vom Walde)、舒曼的《吉卜赛人的生活》(Zigeuner leben)等作品。斯特恩伯格本人则演奏了肖邦的《升F大调即兴曲》。⑦
斯特恩伯格在担任工部局公共乐队临时指挥期间也恢复并指导了“上海爱乐协会”的大型演出活动。在他的安排下,该会从1899年12月10日开始,举办了一系列的交响音乐会。演出的曲目除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交响乐作品(如《朱庇特交响曲》)外,还包括了贝多芬《费德里奥》序曲、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选曲《艾尔莎行进至大教堂》、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1829—1894)改自其1862年才创作的歌剧《法拉摩斯》(Feramors)的《婚礼进行曲》、比才《卡门》选曲《波西米亚之歌》。在12月19日晚的交响音乐会上,他还指挥了丹麦作曲家盖德(Niels W.Gade,1817—1890)的《B大调交响曲》、德国作曲家布鲁赫(Max Bruch,1838—1920)歌剧《罗蕾莱》(De Loreley)引子、比利时/丹麦作曲家拉森(Eduard Lassen,1830—1904)的《节日序曲》等,他自己则演奏了肖邦著名的《升F大调夜曲》(Op.15,No.2)和李斯特根据舒伯特《随想圆舞曲》改编的、技巧要求很高的《维也纳之夜》(Soirées de Vienne,9Valses caprices d’après Schubert,S.427)。在1900年2月的音乐会上,他指挥了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弗洛托(Friedrich von Flotow,1812—1883)喜歌剧《因陀罗》(Indra)序曲、瓦格纳《罗恩格林》序曲、奥伯瑟(Charles Oberthür,1819—1895)《圣洁 无比》(O.Sanctissima)等。虽然“上海爱乐协会”的管弦乐队的编制小,不齐备,演奏交响乐作品气势不够宏大,但他们的演奏还是得到了《北华捷报》乐评人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是他们演奏的贝多芬《第一交响乐》第一、第三、第四乐章,深受乐评者赞誉,称其演奏得“清洁、精准”。只是第二乐章(Andante Cantabile如歌的行板)演奏得不尽如人意,显露出乐队的不足(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声部被第一小提琴罩住了,本应缓慢的旋律演奏得不流畅)。斯特恩伯格本人演奏的舒伯特晚期创作的《降A大调即兴曲》第四首、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也受到了好评。在1900年12月举办的“斯特恩伯格教授第二次交响音乐会”上,斯特恩伯格将海顿的《B大调交响曲》、莫扎特的《唐璜》序曲、唐尼采蒂歌剧选曲、迈耶贝尔管弦乐选曲搬上了上海租界的音乐会舞台。⑧
遗憾的是,斯特恩伯格虽然在上海乐坛极为活跃,工部局管理委员会也承认他工作认真,办事有效率,特别是对工部局公共乐队整体演奏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⑨,但最终还是决定不聘他为常任指挥。1901年4月2日晚,倍感失望的斯特恩伯格在上海共济会堂举办了他的告别音乐会。是晚,他弹奏了舒曼的《交响练习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十二号》和他自己的作品《安慰》。一月后,乘船黯然离开上海。⑩
四、梅尔吉奥尔·瓦兰扎(Melchior A.Valenza)——最令工部局当局失望的指挥
斯特恩伯格1900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之后担任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的是工部局特地从伦敦聘请来的意大利人梅尔吉奥尔·瓦兰扎(Melchior A.Valenza)。但对于爱好音乐的上海西侨来说,瓦兰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早在1885年底,他就曾作为英国福神歌剧团(Mascotte Opera Company)的钢琴伴奏来上海演出过,并得到过《北华捷报》乐评人的热情推荐。⑪;与维拉18年的长任期相反,瓦兰扎1901年3月7日就职,不到五年即被解雇。他虽是工部局董事会从伦敦特聘而来,但工部局对他的工作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早在任职之初(1902年8月),他就因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没有带队参加万国商团游行等)而被工部局董事会“正式谴责”过。⑫1906年其在欧洲休假期间,工部局当局决定不再给他续约。显然他的工作一直不被工部局认可。瓦兰扎在上海六年的表现,虽然不太令官方满意,但上海的西侨对他本人及其家人还是十分感激的。因为他一家的到来,毕竟极大地丰富了寓沪外侨的音乐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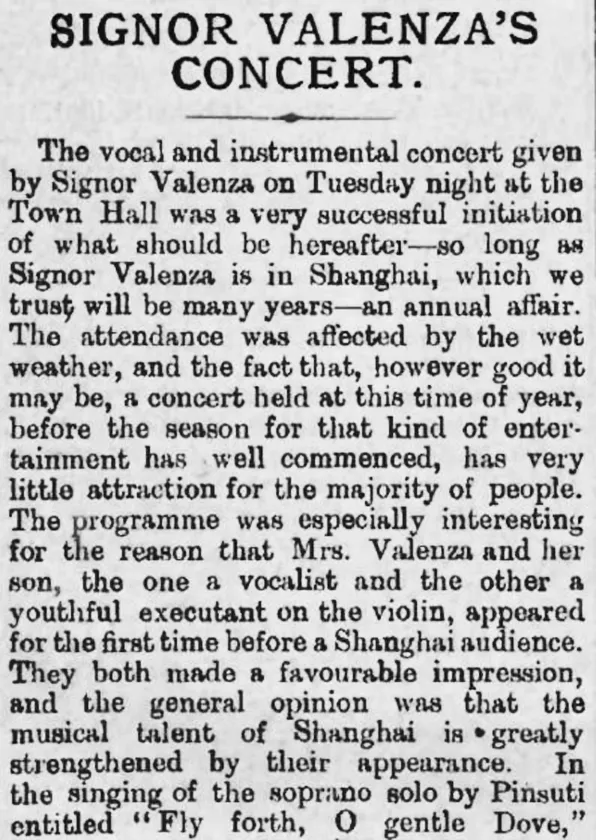
图8 《北华捷报》上刊登的关于瓦兰扎音乐会的报道(局部,1901年10月23日)
瓦兰扎之所以被任命为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很可能是因为他有国际资历。与他的两个前任雷慕萨和维拉一样,瓦兰扎来上海之前就曾有过辉煌的演艺经历。《北华捷报》报道说他曾担任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第三子阿瑟亲王(Prince Arthur)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1850—1942)在印度时(1886—1890)的钢琴师。他在英国本土也工作过,曾担任过卡尔·罗莎(Carl Rosa Opera Company)和阿瑟·洛斯彼歌剧团(Arthur Rousby Opera Company)的总监。⑬除了指挥以外,他还是个“有能力的钢琴和声乐教师,是美声唱法专家”。⑭与维拉的太太一样,瓦兰扎的苏格兰人太太也是小有名气的歌唱家,来沪前也曾有过不凡的履历,如曾在著名的阿瑟·洛斯彼歌剧团担任首席女高音。瓦兰扎的儿子也是音乐家,是在意大利罗马有名的音乐学院圣塔则济利亚学院(Santa Cecilia Academy)训练出来的小提琴家。他们一家人在上海的最初的演出就得到《北华捷报》乐评人的好评。⑮
瓦兰扎到上海后,除了和他的数位前任一样,指挥工部局公共乐队参加上海租界各式各样的公务演出外,他和他的家人还举办自己的音乐会,尤其是声乐演唱会。⑯早在1901年9月,他就提议举办大型的声乐和器乐音乐会,向上海听众介绍其歌唱家的妻子和小提琴手的儿子。在1901年10月在工部局市政厅举办的音乐会上,瓦兰扎太太演唱了意大利作曲家平苏悌(Cico Pinsuti,1829—1888)、托斯蒂(Paolo Tosti,1846—1914)和英国指挥家、作曲家甘兹(Wilhelm Ganz,1833—1914)的独唱歌曲,瓦兰扎的儿子演奏了舒伯特的《小夜曲》、拉夫 (Joseph Joachim Raff,1822—1882)的《抒情短曲》,瓦兰扎自己则弹奏了肖邦的《大波罗乃兹》(Grand Polonaise,Op.22)。⑰
与其几位前任不同的是,瓦兰扎对歌剧尤为热衷,1902年他就曾有过在上海租界开办歌剧培训班的想法。他还向工部局董事会“申请利用戏院,以供一家来自澳大利亚的职业乐队演出,并有意为之宣传”。但由于工部局的否定,此两项计划都未能实施。⑱与他的前任一样,瓦兰扎也积极参加上海英人爱美剧社的演出活动,特别是合唱队的培训。该剧社1901年成功重排吉尔伯特和萨立文的轻喜歌剧《爱奥兰茜》时,其合唱队就是瓦兰扎培训的。⑲
瓦兰扎还是个“美声唱法专家”。他对声乐艺术的热衷表现在他对上海合唱事业的大力支持。他到上海不久就和在上海的几个音乐爱好者一起恢复了已偃旗息鼓的“上海合唱团”(The Shanghai Choral Society)的活动,并担任了组委会委员。1905年,瓦兰扎还重新组建了自斯特恩伯格离去后就偃旗息鼓的上海爱乐协会管弦乐团,接着又在1905年冬成立了“上海歌剧协会”,并于11月在工部局市政厅大礼堂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此次演出中,除了工部局管乐队演奏的韦伯《奥伯龙》序曲、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选曲外,瓦兰扎的太太和其他的歌手在工部局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唱了罗伯特·普朗凯特(Robert Planquette,1848—1903)《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也译“李伯大梦”)、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1863—1945)《乡村骑士》、威尔第《假面舞会》、古诺《浮士德》、托马(Ambroise Thomas,1811—1896)《迷娘》等歌剧中的著名选曲(见以下图示)。⑳第二年,瓦兰扎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将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全剧推出,但由于瓦兰扎回欧洲休假等各种原因,最后的演出仍是以歌剧独唱音乐会的形式,选取了剧中的几段音乐在兰心大剧院演出。㉑瓦兰扎也曾试图将瓦格纳的《唐豪塞》搬上兰心剧院的舞台,为了演唱好瓦格纳《唐豪塞》中的合唱曲,他甚至还特别组织训练了一个由14位女士与17位男士组成的合唱团。在1906年1月21日晚的音乐会上,工部局管乐队在瓦兰扎的指挥下,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瓦兰扎的女儿不仅自己演唱了《瑞普·凡·温克》选曲,还为当晚的一个男高音歌手用竖琴伴奏。瓦兰扎太太也演唱了《乡村骑士》中的选曲。㉒

图9 《北华捷报》上刊登的关于瓦兰扎一家参与“上海歌剧协会”演出活动的报道(局部)
瓦兰扎任职期间的工部局公共乐队基本延续了前任雷慕萨、维拉、斯特恩伯格时代的经营方式。即夏天举办露天音乐会,冬季则以室内音乐会为主,仍在市政厅举行。但不同的是,瓦兰扎任职期间工部局公共乐队演出的场合和场次有所增加。自1904年增加了救火队阅兵奏乐外,㉓从1905年起,工部局公共乐队除了在公共花园、市政厅、跑马场、赛艇会、板球场、花卉展和乡村俱乐部演奏外,每星期还需再增加一次晚间音乐会。㉔此外,这一时期的工部局公共乐队依然欠缺经费。为了保持收支平衡,瓦兰扎开始接受更多的私人甚至也包括富有华人的聘请,为各种场合配乐。尽管如此,在演出的曲目上,瓦兰扎领导的工部局公共乐队仍试图改变维拉时代太过注重舞曲和进行曲的状况,尝试引进一些新的、具有一定水平的曲目,特别是意大利歌剧选曲,旨在提高上海听众的音乐欣赏水平。对此,《北华捷报》的乐评人早在瓦兰扎就任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大加赞赏。㉕
为了方便听众理解音乐会所奏的乐曲,瓦兰扎还引进了音乐会节目单形式,每次演出都为听众印制一份节目单。㉖
瓦兰扎在任期内还增加了工部局公共乐队的编制。为了解决乐手招聘难的问题,他在马尼拉设立了一家中介公司。通过这个公司,他于1903年“成功地”招聘到了九名“令人满意的马尼拉乐手”,使工部局公共乐队的编制达到工部局董事会同意的编制35人。在瓦兰扎的指挥下,工部局公共乐队的演出次数也大大增多,特别是非职责范围内的营利性演出从1902年度的272场猛增到339场,公益性的演出也从182场增加到188场。1903年,他还向工部局董事会建议将乐队的编制增至40人,这样,工部局公共乐队就可以从现在的一分为二变成一分为三,创收的可能性和机会也会更多。㉗当然,瓦兰扎这样卖力地增加演出场次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早在1901年10月他就向工部局董事会提出分红,希望“领取工部局从私人使用乐队的部分收入的四分之一”。㉘
瓦兰扎也曾为提高工部局公共乐队队员的演奏水平作过努力。为了解决乐队马尼拉乐手总体来说作风散漫、演奏水平较低的问题,瓦兰扎曾力图从意大利高薪招聘乐师,他认为这种做法亦可以解决乐队队员在合同期满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可是工部局当局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他们从财政上考虑,决定还是应尽量从马尼拉聘请便宜的乐手。
瓦兰扎还有带工部局公共乐队出国演出的想法,但他提交的去欧洲访问的申请也同样被工部局管委会驳回。显然工部局当局对提高上海外侨的音乐水平和乐队出国巡演没有任何兴趣,“董事们认为,乐队指挥的首要职责是对公园音乐会的监督管理。”
1904年11月,屡屡受挫的瓦兰扎又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工部局“董事会准许他支付少许费用在市政厅举行通俗音乐会”。结果,董事会不仅“认为租用市政厅的规定价目不得变更”外,还怀疑他可能“在经济上捞好处”,再次否决了他的提议。㉙
1906年,工部局董事会同意了瓦兰扎自5月1日始休假半年的申请,休假期间由1882年就进入到工部局公共乐队服务的助理指挥卡斯特罗(C.de Castro)代替他履行指挥职责。但在他休假之前一个月,工部局董事会设立了一个由“对音乐感兴趣绅士”组成的四人“乐队特别委员会”,并赋予他们决断权。该特别委员会对瓦兰扎任职以来市府乐队的工作非常不满。在1906年5月14日提交给工部局董事会的报告中,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市府管乐队过去几年来的表现,无论在曲目的选择上还是在演奏水平上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就连基本的音准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瓦兰扎,特别表明“本委员会并不认为这种不令人满意的状况完全是乐手们的错”,指挥应负主要责任。他们提出的四条具体改进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尽快招聘新的指挥”。㉚听从“乐队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工部局董事会决定瓦兰扎合约期满后不再与他续约,并在合约还未满时就已开始从德国物色新的乐队指挥人选。9月,休假中的瓦兰扎被迫递交了辞呈。㉛瓦兰扎虽然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但上海的西侨并没有忘记他。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有老上海外侨在文中不时提到他。㉜
五、鲁道夫·柏克(Rudolf Buck)——将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转为交响乐团的德国指挥
1866年5月18日出生在德国伯格斯坦福特(Burgsteinfurt)的鲁道夫·柏克(Rudolf Buck)是瓦兰扎的继任者。柏氏他是工部局特意委托前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耐佩博士(Dr.W.Knappe)从柏林聘请到的。㉝与他的前任一样,柏克不但受过非常正规的专业音乐教育,也受过名师指点,曾先后在科隆和柏林随德国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弗兰茨·福纳尔(Franz Wüllner,1832—1902)和罗伯特·拉德克(Robert Radecke,1830—1911)学习作曲。他也曾担任《柏林新闻报》乐评人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客座指挥,㉞在来上海之前就已有过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历。㉟
从1906年12月24日率六名德国乐手抵达上海,到1918年6月23日以获准休长假为名被解约(但工资一直付到他12月23日合约期满)后离华㊱,柏克统领工部局公共乐队几近12年。是他为后来梅百器时代(1919—1942)工部局管弦乐队的辉煌期奠定了基础。柏克任内最主要的功绩具体表现在:1.促成了工部局公共乐队从管乐队到了管弦乐队的最初的转变;2.引进了多样化的音乐会演出机制;3.演出曲目从轻音乐到古典曲目的拓展。㊲
与以往不同的是,1906年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对拟聘任的指挥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该指挥有责任将乐队的表演提升到与同等规模的好的欧洲管弦乐队相类似的水平。为此,工部局当局不惜重金从柏林聘请既会弹钢琴又会编曲并能用英语沟通的指挥,以及既可担当独奏又可训练马尼拉乐手的欧洲器乐手,还专门拨款购置一批与欧美音高相同的新乐器。㊳柏克1907年1月1日正式就职时,工部局公共乐队有马尼拉乐手32人,时任临时指挥的是葡萄牙人德·卡斯特罗(de Castro)。柏克上任后,按照工部局的要求“首先就需要演出的曲目,遵循由简至繁的原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发现乐队中的“这些菲律宾人虽然愿意学,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某些能力,结果也说得上令人满意。但他们对欧洲式的演奏方式完全陌生”。再加上乐手演奏水平的高低不平,差距很大,有些乐手在弦乐队中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场。为此,柏克同意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1906年将乐队分成管弦乐与管乐两队及裁退八名最差马尼拉乐手的提议,以便在提高管弦乐队演奏水平的同时,能完成乐队在不同场合行使不同职能的任务。㊴柏克对工部局公共乐队的乐器也不满意,刚上任不久就向董事会“建议采办一些德国造的新乐器”。幸运的是,工部局对柏克有求必应,“此建议已引起特别委员会注意,并得到批准,费用合计约为2000银两。”㊵
柏克提高上海音乐会水准的另一实际措施是逐渐引进欧洲专业乐师。1906年工部局公共乐队委员会决定在改组后的乐队中除指挥外,还需引进有能力担当各声部首席并可以独奏的欧洲乐师八名。他们分别是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短号、单簧管、大管(巴松)、长笛和圆号。新聘的弦乐手还必须具备(或愿意学习掌握)演奏一种管乐器的能力,以便夏季在户外演奏。㊶但在1906年底实际上只招聘到六名,另外两名1907年夏季才到上海。㊷柏克一上任就将这六名欧洲乐师编入乐队,并于1907年1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排练”。㊸1909年秋,又有三名德国乐师加入工部局公共乐队。㊹
柏克在从德国招人的同时也注意网罗在中国境内的西洋专业乐人。得知青岛乐队的一位竖琴手的合同即将到期,并有意“按照西人乐师的聘用条件参加工部局乐队”后,柏克于11月上书工部局董事会建议招聘这位“还善于演奏提琴和钢琴”的乐人。㊺1910年10月,小提琴手汉斯·米利斯(Hans Milles,1883—1957)加盟。到1913年,工部局管弦乐团中的欧洲乐师的总数已达到14名。随着欧洲乐师的不断增多,乐队开始定期演奏古典管弦乐作品,以1909年的音乐季为例,“最高水平的新作品几乎以每星期都上演一部的速度呈现”㊻。

图10 柏克(中站立者)与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㊼
在柏克的指导下,工部局公共乐队除了夏季在公共花园举办室外音乐会外,还引进了几种固定的室内音乐会形式:冬季舞蹈音乐会(每星期五)、星期天管弦乐音乐会、逍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工部局公共乐队乐手独奏音乐会、作曲家专题音乐会、预约(定期)音乐会(Subscription Concerts)。

图11 1909年1月《北华捷报》上刊登的柏克指挥工部局公共乐队的节目预告
与以往只在夏季黄浦花园举行的户外音乐会不同,柏克引进的冬季舞蹈音乐会,每周五下午五点半在工部局市政厅会堂内举行,所演奏的节目仍以华尔兹、独步舞、二步舞和探戈为主。㊽为满足西侨渴望严肃音乐的要求,他从1907年开始还引进了星期日管弦乐音乐会,每周日下午四点半在工部局市政厅会堂内举行。㊾他的这一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冬季的周日音乐会吸引的听众每场平均达900人之多”。㊿
柏克在上任初期还试着引进逍遥音乐会形式。在1909年的指挥年度报告中,他回忆道:
我们第一次逍遥音乐会1907年的第一个星期三在市政厅举行。座椅起初被放置在靠墙的地方,这样市政厅的中心可以有自由走动的空间,这种座位安排在接下来的几周一直维持不变。后来听众多了,就又在大厅中间背靠背地加了两排座椅。这样的安排对听众来说自然非常不舒服,因为他们无法面对音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又将椅子交叉着摆放在大厅里,可之后不久听众就多到了加多少个座位都不够的程度,逍遥音乐会也自然不再是逍遥音乐会。从这一刻起音乐会的整个特色就变了,不再有噪音,也不再有躁动不安的孩童,更不再有怀抱哭泣婴儿的阿妈。[51]
为了提高寓沪西人的音乐欣赏水准,柏克从1908年1月开始印制有时代背景说明和音乐简介的音乐会节目单。[52]从1909年起,他还开始举办具有教育意义的欧洲作曲家及历史时期的专题音乐会。此类音乐会仅1909年就包括贝多芬、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海顿、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瓦格纳。[53]1912年,他又引进了预约音乐会形式,这样,不仅工部局公共乐队的欧洲乐手们可以展现他们在别的音乐会形式中无法展现的独奏技艺,西侨业余独唱(奏)爱好者也可以得到登台表演的机会。[54]
从就任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的第一年起,柏克就有意识地将欧洲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品搬上上海的音乐会舞台。用他自己在1908年的“指挥报告”中的话说:
那些可冠以“古典”风格的作品,不少于115首已在周日音乐会上演奏。这些主要作品包括:贝多芬的三部交响曲和五首前奏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韦伯和莫扎特的各四首作品;瓦格纳的三首前奏曲和一些《纽伦堡的名歌手》选曲;柴可夫斯基的两首重要的作品以及门德尔松、李斯特、格里格、柏辽兹、圣-桑、比才的几首曲目。[55]
在1910年和1911年的“指挥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工部局公共乐队如果仅提供轻娱乐性的作品将不会满足听众的要求,因为随着工部局公共乐队近年的不断改进,上海听众希望听到西方文化精华之作的愿望已被燃起,他们也渴望体验那些生活在母国所享有的“真正的艺术”。[56]
柏克所指的“真正的艺术”是从古典到浪漫时期的交响乐作品,特别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以1911/12年冬季音乐季为例,全季共演出的23场星期天音乐会曲目中,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各占17%,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占26%。[57]
柏克为工部局公共乐队所做的贡献虽然重大,工部局董事会对他的工作总体来说也十分满意,[58]但他最终也和前任瓦兰扎一样,没逃过被解聘的厄运。不过他的解聘与他的工作能力无关,他实际上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身为德国人的柏克自然无法在英人主政的上海工部局任职。他手下的德、奥籍乐手有的被征入伍调往青岛,有的因私自在家制作炸弹而被解雇。[59]1918年5月,柏克在合约还剩七个月时被迫请辞,但委员会仍将按其协议付薪至1918年12月23日。之后就不再与其续约。[60]1919年柏克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上海回国,1952年5月12日,在德国图宾根去世。[61]
结 语
以上,作者以上海开埠后不久即创刊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1864年发行的《北华捷报》日刊版《字林西报》和上海工部局历年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及其他相关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工部局公共乐队“草创时代”和“扩充为管弦乐团时代”的五位指挥的生平及在上海的事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追溯。可以看出,在梅百器1919年执掌工部局公共乐队之前,这五位指挥通过各自的努力已为乐队梅百器辉煌的时代(1919—1942)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柏克执棒时期,工部局公共乐队不仅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以及乐人组成上已基本完成了从“市府管乐队”(Town Band)到“管弦乐团”(orchestra)的过渡,在演奏曲目上也实现了从早期单纯的演奏各类舞曲、进行曲到后期排演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甚至现代音乐作品的转变。诚然,在梅百器之后长达23年的苦心经营下,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最终发展成了一个“50人,以欧洲专家为主,后期又加入了少数华人为编制完整的交响乐团”,在音乐会的形式方面,梅氏“推出特别音乐会、室内乐系列、儿童音乐会、学校音乐会和电台广播等”。但他“定期举办夏季公园音乐会和冬季室内(星期日)音乐会”以及专题音乐会的做法则是延续了前任所开创的先例。[62]前辈筚路蓝缕之功似乎不应随时光的流逝而被后人遗忘。

图12 雷慕萨肖像(绘于1848)[63]
注释:
①上海档案局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十四册),第496页。
②North China Herald(March 22,1899;April 3,1899).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899,p.122.North China Herald(September 4,1899).
③同①,第520-521、524、571页。
④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0,p.140.
⑤North China Herald(December 5,1898).
⑥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28,1898);(December 5,1898);(December 12,1898);(January 9,1899)(March 13,1899);(May 8,1899).
⑦North China Herald(May 22,1899;May 29,1899).
⑧North China Herald(October 30,1899);(December 27,1899);(February 7,1900);(December 26,1900).
⑨同④。
⑩North China Herald(April 10,1901);(May 22,1901).
⑪;“The‘Mascotte’at the Lyceum,”North China Herald(December 2,1885).
⑫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1(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02),p.162.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十五册),第560页。
⑬North China Herald(March 3,1901).
⑭North China Herald(July 3,1901).
⑮North China Herald(September 11,1901;October 2,1901;October 23,1901).
⑯“Signor Valenza’s Concert”,North China Herald(October 23,1901;November 20,1901);“Signor Valenza’s Concert at the Lyceum”,North China Herald(July 3,1903).
⑰North China Herald(September 11,1901);(October 23,1901).
⑱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十五册),第556-557页。
⑲North China Herald(December 24,1902).
⑳North China Herald(February 24,1905);(November 10,1905).
㉑North China Herald(March 16,1906).
㉒“The Shanghai Operatic Society,”North China Herald(March 30,1906).
㉓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第64页。
㉔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606页。
㉕North China Herald(July 3,1901).
㉖C.E.Darwent,Shanghai: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11),p.162.
㉗ M.A.Valenza,“Bandmaster’s Report”,in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3,pp.130-131.
㉘同①,第627页。
㉙同⑱,第595、662、685-686页。
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6,p.200.
㉛同㉚,p.205,422.North China Herald(June 15,1906).
㉜“Past of Municipal Band Recalled”,North China Herald(April 18,1934);“Memories of Old Shanghai”,North China Herald(May 1,1935).
㉝同㉚,p.204.克耐佩(W.Knappe)1899—1905年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㉞ Hugo Riemann,Musik Lexikon(Mainz:B.Schott’s Söhne,1959),p.245.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载《韩国鐄音乐文集》(四),乐韵出版社,1999,第143-144页。但韩文中的“1906年应邀到上海任公共租界教堂唱诗班乐长”及“柏克就任工部局公共乐队的时间是1906年11月24日”之说与事实不符。1906年《工部局年报》(第204页)和柏克本人的“乐队报告”(收入1907年《工部局年报》第108页)都明确地说他是1906年12月24日与六名欧洲乐人一同到沪。
㉟同 ㉓,第81页。
㊱同㉚,p.422.The Municipal Gazette(June 27,1918),p.208.The Minute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1917—1919)(Shanghai: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1),Vol.20,p.278.
㊲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第143-147页。
㊳同㉚,pp.203-204;33.
㊴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7,p.109.
㊵ 同 ㉔,第677页。
㊶ 同 ㉚,第201页。
㊷同㊴,第108-109页。这六名欧洲乐手为:G.Preussler(圆号),R.Lidemann,B.Strange(大提琴),J.Pröfener(长笛),W.Biswang(短号),and H.Klauss.Annual Report1906,p.430.
㊸Der Ostasiatische Lloyd(Januar 11,1907),转引自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第84-85页;榎本泰子著,赵怡译:《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55页。
㊹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6,1909).这 三名欧洲乐手分别为:M.Gareis(中提琴),A.Geyer(小提琴),A.de Kryger(大管)。柏克1918年6月被解雇后,A.de Kryger(德·克里格尔)还兼任过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一职。见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二十册),第700-721页。
㊺上海市档案馆编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十七册),第635页。
㊻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6,1909).
㊼照片来源:University of Bristol-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reference number:EH01-072.
㊽Pang,Pui-ling, “Reflecting musically: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s a semi-colonial construct”(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5),pp.112-113.
㊾同㉔,第682页。North China Herald(November 6,1909).
㊿榎本泰子著,赵怡译:《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第51页。
[51]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9,p.284.
[52]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08,p.102.
[53]同[51],p.283.
[54]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12,p.136B.Pang,Pui-ling,“Reflecting Musically: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s a Semi-colonial Construct”(Ph D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5),p.119.
[55]North China Herald(January 9,1926).
[56]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Annual Report1910,p.284.Annual Report1911,p.226.Pang,“Reflecting musically: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s a semi-colonial construct”,pp.113-114.
[57]Pang,“Reflecting musically: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s a semi-colonial construct”,pp.114-115.据王艳莉最近不完全统计:“柏克执棒工部局乐队首演的作品约有82部,主要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英国、俄国等欧洲国家的经典交响乐及室内乐作品,其中又以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居多,约有28部,占总数的34%,其余由意大利、法国、俄国等交响音乐大国分占。这些作品中,交响音乐作品有69部,占总数的84%,其中歌剧选段和管弦乐作品各占一半,而柏克更为偏爱瓦格纳的歌剧作品和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见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第42页。
[58]王艳莉在《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书中注意到工部局曾因柏克私自教授音乐的行为在1908年谴责过他。
[59]R.B.Hurry,“A Far-Eastern Gateway”,Music and Letters(October 1922),p.372.
[60]North China Herald(June 27,1918).
[61] Walther Killy and Rudolf Vierhaus eds.,Deutsche Biographische Enzyklopädie,Band 2.(K.G.Saur,München 2005).
[62] 同 ㊲,第189页。
[63]图片来源:上海交响乐团档案馆。

